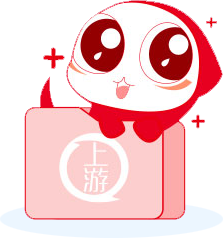

上游专访重庆籍著名作曲家郭文景

郭文景
“我记忆深处常常飘出金钱板的声音。这种继承元明词话传统的诗赞体曲种,用沙哑的嗓音唱书,连比带划,故事讲得活灵活现。如今在四川已极难听见了。那种说唱的嗓音,是用烟叶熏过的,酽茶泡过的,还掺入了蒲团扇的沙沙声和麻将牌的哗啦声,老到练达,情趣非常。随着一种生活方式的消失,这声音也差不多消失了。现在,不知由茶叶的袅袅馨香和碗盖相碰的叮当声化成的四川清音的清脆花腔,还在否?那是一种俏丽、泼辣的声音,从中颇见一方女子的风韵。”
——郭文景忆老重庆
重庆的深冬,少有晴朗的时候。日历翻到二月第二天,春的脚步近了,天空却还阴沉。寒风拂面,路人裹紧大衣,行色匆匆。区县农人带来土货大集把步行街填得满满当当,热闹的解放碑已是一派过年气象。
前一晚,中央芭蕾舞团新作芭蕾舞剧《敦煌》在重庆大剧院首演,作曲郭文景随团回到家乡。忙到凌晨才睡,一大早又起床,从下榻的青年路酒店赶往歌乐山探望母亲。
之后他还想去转转小时候生活过的道门口,“东看西看硬是找不到路,连解放碑怎么走都要先问酒店服务员”,郭文景摇摇头,对重庆晨报记者笑道,“你说好不好笑,我这个市中区长大的老重庆,也成了外乡人。”
62岁的郭文景迁居北京已经28年,更早他还曾在中央音乐学院求学5年。京城度过的前半生将他塑造成了享誉世界的作曲家,但他更感念的还是从小浸淫的巴渝文化:江边的吊脚楼、码头的号子声、闷热的青石小巷、透亮的川剧高腔……
他说,那些隐于基因里的记忆内化为灵感,冥冥注定一样,跃然纸上构筑成他最初的华章……

日前,郭文景在纽约林肯中心举办两场音乐会,他在著名的爱丽斯·塔利厅留影。两场音乐会分别演奏了《野草》和《中国锣的宣叙》。
老重庆是内化于心的记忆
《敦煌》是郭文景与中央芭蕾舞团合作的第二部芭蕾舞剧。五年前,双方曾在另一部原创舞剧《牡丹亭》中首次合作。
依然是东方故事与西方芭蕾的结合,舞台上,他天马行空的想象力再度创造出一个神奇瑰丽的音乐世界——
排箫阵阵引领大漠敦煌的主题跃然眼前,仿佛穿越古今的历史纵深感扑面,序幕结束突然闯入圆舞曲的巴黎主题,繁华景象又与寂静荒凉形成鲜明对比,观众的心总被紧紧抓住,升腾起一种不言而喻的庄严肃穆。
重庆成为《敦煌》2018年巡演首站,中芭方面邀请郭文景随团宣传,尽管事务繁忙,他还是一口答应,“三年没回来看看了,真的很想念家乡,怎么也得走一趟。”
这时间显然是挤出来的。在与记者聊天的两小时里,郭文景接了几通电话。每次接听前他都很客气的表示歉意,“没办法,学校事情太多,各种工作要安排协调……对了,我们刚才聊到哪儿了?”普通话中还略带椒盐味,学者范儿里依稀可辨重庆的江湖气。
采访安排在郭文景住的酒店咖啡厅。这家老牌星级酒店距解放碑很近,却恰好处在老市区改造边缘,一条小街分隔出两个世界:整洁明亮的酒店大厦立在这边,对面一排旧式民宅灰暗低矮。俨然八十年代电影里的山城街景,正是郭文景记忆里的老重庆。
“我在新桥医院出生,当时还叫西南军区陆军后方总医院,父母都是军人,后来转业到了市中区的道门口第一人民医院,我也就跟着进了城。”
似乎是习惯性的皱皱眉头,他随即陷入对童年的回忆,“五六十年代重庆已经是大城市,但没什么高楼,市中区也一样,解放碑好像算最高了,街道窄小,房子低矮,对,就跟酒店旁边那排房子差不多,现在也快拆了吧?”

1970年代的郭文景(前排左一)和重庆市歌舞剧团乐队少年合影。
小学就近入读, 郭文景的母校是解放东路一小,“学校靠近长江嘛,我们经常去江边玩,大人肯定是不许的,但小男孩嘛难免调皮捣蛋,最爱光屁股下河游泳,干各种不要命的事情。”
重庆城里的孩子小时候应该都被家长警告过,“大河是没扛盖盖的”,郭文景记得小学有个同学叫聂朝金,曾在长江里救了他一命。
“我们喜欢在水流湍急的码头游泳,有一次我差点卷进水里出不来,幸亏班上有个叫聂朝金的同学水性极好,他从我身后用胳膊卡住我脖子,让我以仰面朝天的姿势被拖到岸边。”
他啜了口咖啡,表情略带劫后余生的窃喜,“现在想想,他的水性真是堪比阮氏三雄啊,不然么我也活不到今天。”
高低曲折的梯坎巷子连接起老重庆的上半城与下半城,迷宫般的地形也是孩子们的天堂。郭文景喜欢穿街转巷到处晃,“茶馆里有雅俗共赏的说唱,院子里死了人要搭个棚子敲锣打鼓唱川剧,街坊邻居的婆娘崽儿有时候会吵架打架,还有滚铁环、旋陀螺、放鞭炮,我记忆里的老重庆就是这样的市井生活,弥漫人间烟火,现在还很感动。”
然而这一切之于郭文景的意义,要到很久以后他才有所感悟。
“生活在这里的时候,觉得一切么都理所当然,直到78年去北京上大学,置身于更大的世界,并且以作曲家的立场思考生活与艺术时,我才第一次意识到,老重庆记忆成了我的资源和财富,山水、乡音、号子、建筑、个性、戏曲等,构成了我的文化立足点和灵感源泉,也正因为这样,我最初的作品都跟重庆这片大地很有渊源。”
命运之手牵引我别无选择
1983年《川崖悬葬》美国公演,郭文景这个陌生的名字一出现便令西方音乐界惊叹。接着是交响乐《蜀道难》、钢琴前奏曲《峡》、弦乐四重奏《川江叙事》、大提琴狂想曲《巴》、小提琴独奏组曲《川剧音调》、竹笛协奏曲《愁空山》……八十年代后期开始,他创作的一批与巴渝风物有关的音乐作品陆续问世,不断刷新着东西方音乐界对他的认知。
巴渝题材作品让外界看到他音乐风格的“阴沉、狂暴、神秘”,然而他的艺术视角当然不只限于巴渝大地。在歌剧《狂人日记》、《夜宴》、《骆驼祥子》、《李白》,川剧《思凡》、大型作品《英雄交响曲》、《远游》等更为开阔的创作中,人们又感动于他厚重的人文性与知识分子关怀。

1月出版的《纽约时报》副刊整版报道郭文景等中国本土作曲家。
爱丁堡音乐节、巴黎秋季艺术节、荷兰艺术节、纽约林肯中心艺术节,还有伦敦阿尔梅达歌剧院、法兰克福歌剧院、鲁昂歌剧院等,都曾安排郭文景个人作品专场音乐会或上演他的歌剧。这也不难理解,为何《纽约时报》称他为“惟一未曾在海外长期居住,却建立了国际声望的中国作曲家”。
“有没有想过,一开始是什么成就了你?天分和勤奋,你更看好哪个?”这问题让郭文景咧嘴一笑,笑起来眉眼弯弯竟有些可爱,他认真的盯着记者眼睛,缓缓说道,“从事艺术还是更需要灵感和天分,我觉得勤奋帮不了你。”
他认同命运对于人的选择性。正如求学中音时同学刘索拉那篇轰动文坛开风气之先的小说题目——《你别无选择》,“很多时候,生活道路不是个人选择的,而是无形的手推着,所谓灵感和天分也是如此,一切命中注定。”喝口咖啡,他又补充道,“这并非提倡什么唯心主义,只是现在老了的一些感慨,恩,回想起来,是这样的。”
聊起家事,也是巧了,郭文景与已故老艺术家阎肃算忘年交,不但同为音乐行业的重庆老乡,连祖籍地也同样是河北:1937年为避战火,阎肃随家人来渝定居,自此视重庆为第二故乡;郭文景的父亲也是1937年七七事变后逃离河北参加八路军,后来参与了重庆的解放工作并就此扎根。
“我祖上没有人跟音乐沾边,甚至任何一门艺术都不懂的,父亲来自河北乡下,据他讲当年日子很惨,爷爷都是饿死的,解放后父母在军医院工作,可以说在12岁以前,家里从没有人想让我搞艺术,我的生活环境与艺术完全无关。”
“12岁第一次摸小提琴,8块钱的那种;14岁第一次见到钢琴,吓一跳,那么大。”郭文景边说边比划,“那为什么突然学琴呢?当然不是我一个调皮娃儿平白无故喜欢上艺术,而是在1968年那个特殊的时代,普通年轻人只有两条好点的出路,要么当兵,要么参加文工团演样板戏,所以我爸给我哥买了把琴,我也跟着自学。”

郭文景作品
命运之轮开始转动,它第一次向郭文景展现了神奇,“哥哥和妹妹都下乡了,父母本以为我也不可抗拒,就有这么巧,我爸认识的一个人带来了点新消息。”
那时全国城乡正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重庆这边文艺界和医疗界两个系统一起下乡。“我爸是其中一支下乡队伍的队长,队里有卫生局医院的人,也有文艺院团的人。”
郭文景回忆,知青下乡让家里孩子走了俩,他的命运让父母忧心,“这时有个文艺系统的熟人告诉我爸,最近市文化局在招样板戏班学员啦,老二不是会拉小提琴吗,去试试吧,我就这样上了道。”
“所以你看,这是命运。”郭文景正正身子,一脸笃定,浮现出阅尽千帆的神情,“我生长在完全和艺术无关的环境,但命运总是很神秘的出现一些人和事把我朝这路上推,先是我哥想要一把小提琴,我就摸到了琴,并且因为这把琴我就在家坐得住了,也不老想往外跑了;有了琴得定弦呀,怎么弄家里没人知道,我家老保姆呢有个当长途司机的侄子,他刚好来了,还懂定弦!好,又解决了;接下来该识谱了,谁能想到我们楼下一个邻居不但会五线谱,家里还藏着乐谱书!”
楼下这位邻居,说起来又是传奇。她在郭文景父母医院当外科主任,一个很不幸的女人。
“过去是有钱人家小姐,医科大学毕业,听说丈夫曾在国民党当官,解放后剩她自己一个人带一帮孩子,还有个瘸腿老母亲。”他半眯起眼,接着道,“本来我跟她并不熟,但有一天她正好看到我拉琴,完了她把家里藏得很深的一本五线谱翻出来,告诉我说,下面加一横上面一点是哆,黑的头一个杠是一拍,白的头一个杠是两拍,黑的头一个杠加个尾巴是半拍……呵呵,这也是她唯一一次让我看到她的过去,当时的场景记忆犹新,现在好像很多人说学个五线谱难死了,我却就这样学会了。”
像说故事一样,这些早期经历他也曾给一些音乐家朋友讲过,“说给他们听,谁都不信。这不是注定是什么。”他又笑了。
赞美苍茫大地深处的力量
郭文景的音乐就像他这人一样充满力量。去年,61岁的他在国家大剧院出版了一张集合多年创作的唱片《天地的回声》,对上世纪80年代至今的创作予以小结。作品数量众多,虽然题材各异,却都偏向直面人性、剖析精神世界主题。有人说,这是来自巴渝大地的加持,有股“迷阵般的气势”。
从演奏转向创作的路上,郭文景又有不少奇遇。先在重庆市文化局样板戏学习班呆了两年,14岁考入重庆市歌舞剧团做小提琴手, “依然给样板戏伴奏,像前段时间冯小刚电影里的《沂蒙颂》、草原女民兵等,看得很有感触,这些我都亲自演奏过的。”
他形容那时的生活像掉进了福窝,“有些人回忆起那个年代,会提到迷茫和惶恐,不知道人生道路该往哪走,这个问题在我看来并不存在,歌舞剧团的工作已经是当时青年能想象的最好工作之一,进团就是掉到福窝里。”
他打量了下记者,笑道,“你们这辈可能没感觉,问问你们父母就知道了,七十年代啊,不但吃饭不要钱,还有工资拿,全市人民一个月就二两肉,我们天天有,工资将近二十块钱,我用不完就去解放碑逛新华书店,买了一堆毛泽东马列著作,别的时间就练琴,简单充实,其乐无穷,我的青春从来没有枯燥过。”
似乎还不够,为了强调那种幸福感,他忽然想到一个反面例子,“王安忆写的《文工团》知道吗?哦,你还看过,那篇小说写得特别好,只是她所在的团呢比较惨,我所在的是很好的团,是她书里提到的那种令人羡慕的文艺院团。”

郭文景与太太唐俊乔(著名竹笛演奏家)。
18岁时,终于有了新的期盼,郭文景偶然听到肖斯塔科维奇的《第十一交响曲》,有种“被电击中的感觉”,他决定自学作曲,“既然小提琴能自学,为什么作曲不行?”
古典音乐令他持续着迷,后来又在团里一位老同志家听到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不可思议的旋律,不像中国传统音乐线一样的起起伏伏,蜿蜒伸展,贝多芬的曲子是‘滴滴滴当!棒棒棒!’,高高低低的力量,动机和细胞不断重复变化发展,进而构成宏大建筑。”他模拟着《命运》的旋律,右手在空气里划着节拍,激动得一拍大腿,“第一次听啊!太震撼了!”
渴望学作曲,于是有了拜访朱践耳先生的经历。一次随团进京参加全国文艺调演后,郭文景与团里一位定音鼓手径直去了上海,那位鼓手是朱先生外甥。
去年离世的朱践耳先生也是中国当代乐坛传奇。现在很难说清他当年是否具有识珠之才,但对素昧平生不请自来的郭文景来说,他的确是位重要的引路人。
“就像现在年轻人追星,不会考虑是否打搅人家,没想到朱先生人真好啊,根本不认识我还管吃管住管上课。呆了两周吧,现在还记得他在钢琴前给我们上课的情形,还有他家的饭桌,上海人家餐具很精致秀气,跟我们单位大茶缸子吃饭完全两样。”
临走时,朱践耳亲自托关系,帮郭文景他们搞到上海回重庆的船票。
“我很在李白的诗里读到过三峡,然而这才是我第一次坐船过长江,诗歌意象和真实风光结合了,我第一次对川江、对三峡有了直观体验。激流、峭壁、悬棺,后来都写进了我的毕业作品《川崖悬葬》,有人听起来说阴森阴沉,我不这样看,我觉得这些神秘所在充满了从大地迸发出来的野性力量,这是远古僰人文化记忆的留存,这力量令我陶醉,后来我也反复赞美它歌颂它,大概这也是巴渝山水对我的影响。”
“因为朱先生,才有了这趟神奇的旅程,后来想想,这不正是杜甫写过的,‘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 喝掉杯里最后一口咖啡,郭文景慢悠悠做个了伸展,声音忽然低缓了许多,“所以说有天分,还得有命定之人,包括后来考学、就业,我的艺术道路也并非全无艰难。那时我才十几岁,从长江入海口逆流而上,七天航行到朝天门,简直就是我后来艺术生涯的象征和暗示,这种话说多了矫情,但事后想来似乎的确赋予了这样的含义,所以哪怕觉得隐喻有些神奇,于我而言也成了某种真实。”
人物名片:
郭文景,当代著名作曲家,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1956年生于重庆沙坪坝,1978年考入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与同学谭盾、翟小松、叶小纲并称中音“四大才子”,1990年开始在母校执教。
1983年,他的大学毕业作品交响乐《川崖悬葬》在美国公演引发轰动。他的代表作还包括《蜀道难》、《巴》、《愁空山》、《川江叙事》,以及歌剧《狂人日记》、《夜宴》、《李白》,芭蕾舞剧《牡丹亭》等。他的作品在全球范围内广泛上演,《纽约时报》称他是“唯一未曾在海外长期居住,却建立了国际声望的中国作曲家”。
重庆晨报记者 赵欣 高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