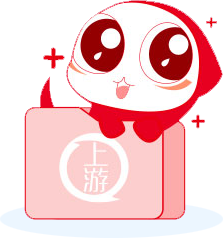

上游深阅读丨著名作家张恨水之女回渝重温父亲往事:七十多年前,父亲回家的路太不容易了!

20日上午,著名作家张恨水的长女张明明时隔73年回到重庆,在通远门城墙附近找寻父亲当年工作过的《新民报》报社。
张明明站到储奇门长江边举起手机拍照前,特意跟记者确定了一下江对岸海棠溪的位置。这一刻,她完全不像一位已经78岁高龄的老人,而更像那个守在屋檐下等爸爸回家、喜欢围着爸爸要零食吃的女儿。
七十多年来一直萦绕在她脑海里、有些不明就里的“父亲回家那条路”也在此时开始渐渐清晰了起来——70多年前,父亲扛着得来不易的平价米就是走过了那些高高低低的梯坎,一路穿行到这里坐上过江轮渡到达长江对岸的海棠溪,再换乘长途车回到远在南温泉桃子沟的家的……
张明明的父亲是张恨水。早在张明明出生之前,他的名字就已经随着《金粉世家》、《啼笑因缘》的文字享誉全国。
73年前,还不到5岁的张明明每次守在南温泉桃子沟那栋茅屋屋檐下眼巴巴望着爸爸回来时,总是在想“已经走到对面坡上扛着米袋子的父亲背后是怎样一条路”。直到前天(19日),已经年近八旬的她回到这里,亲自走访、探寻了一番……
重庆行初衷
“我想看看父亲当年的辛苦”
张恨水和重庆的渊源最早可以追溯到1937年底。当时,在抗日烽烟下,他前来重庆成为了《新民报》的主笔和分管副刊的主编。最初,他和夫人租住在新金山饭店。后来因为日军持续不断的轰炸,他们一家被迫搬到了南温泉的桃子沟。1940年,长女张明明就出生在这里。
1945年抗战胜利后,张明明和妹妹先跟着妈妈回了父亲的老家安徽。在那里住了10个月,之后就去了北平。“后来我们在北京读书,再后来出国,就一直没有机会回来重庆。”
所以,想回自己的出生地看看,也就成了张明明此次重庆之行最原始的初衷。

20日上午,张明明和陪同她在重庆探访父亲生活工作足迹的随行人员合影(从左至右:本土资深文保志愿者赵爽、李炼,张明明和安徽池州学院通俗文学与张恨水研究中心的谢家顺教授)
“同时,抗战时期有志气、有骨气的文化人,我父亲算是一个代表。重庆也是他生活、工作过的地方,所以我决定再去好好看一下。”张明明说,加上近年自己常回父亲的老家安徽:安葬了他的骨灰,帮助潜山县在他的故居成立了张恨水博物馆,进一步触动了自己回重庆看看的想法。
回到出生地
屋前有小桥的茅草顶平房
本次回重庆张明明并没有家人陪同,随行人员也只有一位:来自安徽池州学院通俗文学与张恨水研究中心的谢家顺教授。本次行程中,19日,张明明先回到了自己的出生地了却了自己回渝的第一大心愿。
张明明口中的桃子沟实际上位于南泉建文峰和仙女峰之间,是一条狭长山沟,坡陡路窄。被张恨水后来戏称为“待漏斋”的住所其实是一字排开的一座平房。“我记得一共是10间屋,我们家住了其中三间,剩下部分是两位教授的家。”张明明说,房子的屋顶盖着茅草,四壁则是用竹片糊泥而成。

本报记者、本土资深文保志愿者李炼跟张明明介绍通远门城墙当年的走向、地势。
“屋门前有一条走廊。我记得爸爸经常在走廊上踱步。”张明明印象中,离得不远就是一条平时干涸的小溪沟。说到这里时,她用手比划了一下,大约5、6米宽。“上面架着一座小木桥。父亲想稿子时就在上面来回走。”张明明说,过了那座小桥再上几步梯坎就是一条通往外面的小路。”
19日,再回到桃子沟时,场景自然是完全变了模样。不过,张明明还是根据自己的记忆,结合现在能找到的报道和大家研究之后的数据、照片等确认了自己的出生地。
父亲的回家路
70多年后终于看清这条不容易的路
对张明明来说,出生地桃子沟算是一个起点,但在她本次回渝探寻中却又是一个“父亲的终点”。在跟记者仔细回忆起父亲之前,她先讲述了这样一个自己记了70多年的场景——
“知道我父亲要回来的那天,我就会在门口那个茅檐下等着,看着对面山头上出现一个人,穿着长衫,肩膀上扛着东西。我就知道是父亲来了,然后我就跑上石头台阶在路上等他。”张明明说这个情景自己总是忘不掉。“那时我不知道父亲走到南温泉山头上时他背后的那条路是什么样的。”

1945年美国《生活》杂志记者曾拍摄的通远门城墙,可以看到《新民报》报社办公小楼就在紧贴城墙根的位置。
张明明随后的行程也正是为了解答自己的这个疑惑。“从《新民报》报社到桃子沟这段距离我父亲来回走了无数次,相当辛苦。我也想体会一下他的这种辛苦。”
19日,张明明先去找到了海棠溪的渡口,但这还不够。20日一大早,在本土资深文保志愿者李炼和赵爽的带领、陪同下,张明明先去了通远门城墙。
对照着1945年美国《生活》杂志记者拍摄的一张重庆市井照片,大家首先推断出了张恨水当年工作的《新民报》位于紧贴着通远门城墙根的位置。
而在一街之隔的华一坡,虽说当年遍布坡上坡下的“抗战房”早已被规整成了方便上下的公路。但当年张恨水供职的《新民报》创始人陈铭德就是住在这里。他也经常请包括张恨水在内的报社员工到住所小聚。


张明明在华一坡,当年父亲供职的《新民报》创始人陈铭德就住在这一带,他也曾多次邀请张恨水等员工到家里小聚。
随后,张明明乘车穿过通远门城墙,经和平路、较场口、凯旋路下到储奇门码头。当听说父亲当年扛着报社分发的福利平价米就是走过这条路到江边坐轮渡时,她特意问起了这一路步行走下来需要多少时间。
“因为重庆是山城,所以这一线下来一般没有黄包车可以坐。”听到记者这么说时,张明明还专门用自己童年印象中的重庆话问了一句“滑竿也没有吗?”当她真的站到江边,隔江远眺海棠溪码头时,就出现了本文开头的那一幕。“父亲过江之后还要再坐车,时间不不凑巧错过了班车,就只能走路回家。这一路真的不容易!”
感慨
那一代文化人的付出都不容易
虽说张明明今年已经78岁了,但在整个行程中,她几乎没有出现过任何的腿脚不便。非常想探寻父亲当年足迹的愿望,让她爬坡上坎时也始终精神抖擞。
当年父亲一路的不易,此前张明明只在他的文字中读出来过。“比如他写的《黑暗中的光明》就是写的他过年的时候赶回家跟我们团圆:下午3点从报社下班,4点过江后到达海棠溪码头,又错过了班车,最后只得走路回南温泉桃子沟。这种对家很浓的心愿、感情不是一两句话就能体会的,想体会得深一点就只有走一趟。”
张明明说,自己这一趟走下来都觉得那是一条多么长的路。“更何况,那是80多年前,他穿一双布鞋走这么远,有时晚上灯笼没了还要摸黑走路,这是一种什么心情。”

张明明在人和门遗址旁。
张明明说,父亲作为报人,当时认为自己的第一使命就是要对得起百姓、国家和民族。“在国难时,报人的责任或者说相对便利的条件是你可以呼吁全国人民团结起来,放弃掉自己的小我利益,团结在抗日力量下,抛弃各自的私念对抗日本人的侵略。”
“我觉得亲自走一趟父亲那一辈人走过的路,熟悉一下父亲所代表的那一代文化人经历过的辛苦,可能比光是通过想象去理解老一辈人的那种情怀,是更有帮助的。所以我就来了!”张明明感慨道。
童年趣事
女孩不会的爬树我是在重庆学会的
1940年春天,张明明出生在南温泉桃子沟。她出生时的情景后来成了妈妈和哥哥调侃她最喜欢提及的内容:“我出生前父亲就特别想有个女儿。那天妈妈在屋里生产,爸爸就在外面走廊来回踱步。等到生了,护士出来告诉他:恭喜张先生,喜得一位千金。他就在走廊上对着天把这句话重复了好几遍。”
在1945年底离开重庆前,张明明印象中还在南温泉附近上了幼儿园。这是她倒推回去的结果。“我只是有印象,我有一个很小的皮书包。有一天早晨起来被老鼠咬坏了,结果那天我就因为不高兴没去上幼儿园。”
在重庆的那段岁月里,一起生活的还有张明明的2个哥哥和1个妹妹。“哥哥们喜欢打着光脚板满山跑,我也跟着。我性格里很多男性化的东西,大概就是从那时受哥哥影响很深导致的。很多女孩不会的像爬树,也是那个时候跟着哥哥学会的。”

在通远门城墙下,张明明仔细查看地图确认位置。
关于川渝地区爱说的“打光脚板”,在张恨水家里也有好玩的故事。
张明明记得有一天,爸妈在家聊天说到四川人都光脚板,就想试一试。“我们家里的地是凸凹不平的,所以他们走在上面跌跌撞撞,还要互相搀扶,我们孩子就在旁边笑。”后来,每每想起这一幕张明明就觉得格外有当时的生活情趣。后来,他还以这个主题画了一幅画《待漏斋日夜》。
当年还有两种小吃,让张明明一直记到今天。一就是炒米糖开水。“我记得当时还是我们到码头去接一个客人,本来我住的山里是没有的。还有就是一种像元宝的米糕或是发糕。卖的人一般是头顶一个簸箩,我们看到就会把他叫住买两块。”
待漏斋风雨
这一幕的温情让她至今铭记
张明明出生的茅屋最初是被张恨水称作“北望斋”的。他希望借此表达盼望早日驱逐日寇,收复国土、凯旋北上的愿望。不过,后来因为茅草屋顶时常漏雨,就被张恨水戏称为了“待漏斋”。“漏雨实在太频繁,父亲也有了经验。等到乌云一上来,父亲就会让我们几个孩子把盆盆罐罐提前放到要漏雨的地方接水。听着叮叮咚咚的声音,我们几个孩子也觉得很有意思。”
虽然屋里漏水,窗户也是残破的,但一个雨天发生的一幕却让张明明记到了今天。
“那天写稿子时,雨点滴在了父亲的稿子上,他想办法避开。”张明明印象中,此时刚好哥哥拿着伞走进来,他就把伞接过来一只手撑伞一只手写稿子。“还是邻居看到了,张先生你这丫样不行啊。你写文章需要有灵感,这只手应该是拿香烟的。”
很快,邻居从自己家找来了一块从竹床上拆下来的竹筒,让张恨水绑桌腿上了,再把雨伞放进去。“这样爸爸的手就解放了。我们几个孩子都觉得很好奇好玩,就都围在爸爸身边,外面是风风雨雨……这个场景对我一生的影响很重要。”
张明明很感慨,这种温馨恰好说明了夫妻的恩爱不在于钱多钱少,父母对孩子的爱也不在于你买了什么名牌书包、送他读了什么高级学校。“这一幕的这种温情我终身记得,这就是一个慈爱孝心的种子,让你不会忘记父母对你的恩情。”
躲避大轰炸
“瘦小的妈妈把我护在身下”
重庆的抗战岁月里,躲轰炸是一个无法避开的话题。张恨水一家自然也经历过。在张明明记忆里,躲防空洞总是爸爸抱着自己去。“把我们几个孩子和妈妈送到山洞里之后,他就会另找一个更安静的山洞里一个人躲着看书。”
躲的回数多了,自然有了经验。“如果有月亮我们就要去躲防空洞,而云层很厚看不到月亮,没有飞机来就是很舒服、安静的晚上,只能听见山里的虫子叫。
但次数多了也会有意外。“有一次,我们躲的山洞有两个出口。一颗炸弹在其中一个口子爆炸了,烟尘就扑了进来。大家就往另一个出口跑。妈妈长得瘦瘦小小的,就被冲倒了一下扑在我身上把我护住。很多人从妈妈的背上踩了过去,后来看背上青一块紫一块的。”这种感动张明明记到现在。
苦中作乐的时光
父亲拉京胡,母亲跟着唱戏
张恨水一家在重庆的8年虽然物质上只能用清苦来形容,但张明明印象中父母总能找到各种乐趣来装点生活。
“我父亲很爱京戏,自己也会拉京胡。经常他拉琴,母亲就在房间里也会跟着哼哼。父亲就开玩笑说:我没请你啊,你怎么来唱了?妈妈就说,这山村的生活实在太无趣了,你的胡琴虽然拉得不好,但聊胜于无。我就唱两句。”
妈妈有时也会逗趣地说,父亲的京胡其实拉得不好。“他耳朵听音有问题,所以拉出来是‘左的’,唱的话要站到爸爸的左边去唱。”
众所周知,张恨水曾自诩有三好:收书,听戏,养花。到了重庆之后,他也写过“当初入渝时,花值贱而品繁,犹饶此趣。寓楼三间,有花瓶七八具,亦足婆娑期间,藉遣客愁。”张明明可以证明的是,父亲的小书桌上一直有一个紫色的小花瓶。“花买不起了,就去山上采野花,豌豆花等等,什么都有。他还会配色。”后来,这个花瓶被张明明打碎了,也被张恨水写进了一篇文章中。

在储奇门码头长江边,拍照前张明明专门确定了江对岸海棠溪码头的位置。当年她的父亲张恨水就是从这里乘轮渡过江到海棠溪码头回家。
这个家庭的温馨还不止于此。
因为报社工作所需,张恨水常常很晚回家。张明明印象中,妈妈总会为爸爸留一盏煤油灯,自己坐在下面缝缝补补看看书等爸爸。“三更半夜走那么远的路回到南温泉爬上山小屋子里有一盏灯是亮的,妻子在等你。这个场面后来在爸爸的很多诗里都出现过。”
在张明明看来,父亲的《巴山夜雨》就是当年自己家最好的写照。“因为完全就是按我们家和邻里这种很平凡的油盐酱醋生活来写的。”这也是张明明认为《巴山夜雨》是父亲最好的一部作品的原因。“就是没有什么喧哗、华丽辞藻的素描,也没有什么副总理这样的家庭背景(指《金粉世家》)。就是大家为了一点吃的东西怎么绞尽脑汁,有的人投机倒把,有的教授也不再好好教书了。写了很多人性在变革的时期的考验。”
对话张明明:我们看到的总是父亲的后背
重庆晨报:你印象中父亲那些年的作息是怎样的?
张明明:我总是看见他的后背。不是在写稿就是在看书。他刚到重庆时去报社比较多,后来就在家写作偏多。
八年中,他写了800万字的抗战文学,还不算他给读者的回信,平均下来每天要写3000字。据我了解,这在我们中国是绝无仅有的。
重庆晨报:你们几个孩子去过父亲工作的地方么?
张明明:没有。我印象中我们唯一一次进城就是父亲做五十岁生日的时候,文艺界要给他做寿。他原本说自己没有这个资格推了。后来还是几个好事的朋友把我们和妈妈接到了重庆城里。我记得当时吃的是西餐,妈妈还教我们怎么用刀叉。可以说我们对重庆城区的印象几乎是零。
重庆晨报:父亲对你们的教育是怎样的?
张明明:流自己的汗,吃自己的饭。不贪污、不拿不属于自己的东西,不贪小便宜,勤勤恳恳做事。
他还说自己是一个“封建的儿子,民主的老子”。因为他对我奶奶是下跪的。但对我们几个孩子又很民主。我们几个孩子中并没有作家。他说你们学什么我不管,但都要学一门技术,要能养活自己,像我就是学的设计。他总说当作家是不能强求的,要有很多的经历,没有经历写不出来的,他更不赞成瞎编乱写。

张明明为曾家岩书院收藏的张恨水作品题词。
重庆晨报:父亲的故事你有讲话给你的子女、孙辈听么?
张明明:这些经历我经常讲给他们听。我们家客厅里有一墙壁的书架都是父亲的书,够了。我觉得不必说太多。用他的作品来告诉子女吧。
重庆晨报:这次回了自己出生生活过的地方,对这里有什么愿景么?
张明明:我希望南泉桃子沟能建成一个抗战文学的基地。当年那些正年轻、正是才华横溢的年轻人到了那里,没有放弃写作,没有怨天尤人地在写,这是中华民族的精华,是很了不起的一点。我们忽略了这么多年抗战文学发掘和宣扬,这是很遗憾的。
那八年重庆支援了全国的抗战,滋养那么多作家。这应该得到一定的肯定。我觉得可以做一些当年他们住过的茅草屋的模型,让大家看看我们的作家文艺家就是这样生活、创作的。文化要传薪,应该让大家知道重庆曾经在抗战时候起的作用是了不起的。
链接
张恨水笔下曾有这些重庆
张恨水笔下除了有“金粉世家”,他生活了八年的重庆自然也被他写进了书里。在四川文艺出版社2007年出版的《张恨水写重庆》一书中《不堪风雨吊楼》、《出门无处不爬坡》、《望龙门缆车》以及系列散文《山窗小品》都是专门写的自己对重庆山水的感知。
1938年1月10日,张恨水从水路到达重庆,第一站就是两江汇合处的朝天门。他就曾在《重庆旅感录》中写道:“重庆地势如半岛,山脉一行,界于扬子嘉陵两江之间。扬子之南,沿山居人,街市村落,若断若续,统称之曰南岸。嘉陵之北,一城高踞山巅,与重庆对峙,则为江北县。旅客乘舟西来,至两江合流处,但见四面山光,三方市影,烟雾迷离,乃不知何处为重庆。”
而让张明明记到现在的“炒米糖开水”则出现在他的《夜半呼声炒米糖》中。《不堪风雨吊楼》写的就是如今洪崖洞最原始的吊脚楼风光。

《张恨水说重庆》。
《苔前偶忆》、《月下谈秋》、《路旁卖茶人》等都是写的他们一家在南泉桃子沟的的山居生活。单是描写桃子沟的山野之花都有独立成篇的多篇文章。
1945年底离开重庆时,张恨水又写了一篇《告别重庆》发表在12月3日的《新民报》上。“不知不觉,在重庆时过了八年的暴风雨,现在要走了,我实在有点依依不舍。以往八年,每在爬坡喘气,走泥浆路战战兢兢之余,就常和朋友说,离开了重庆,再也不想来了。到了于今,我不知何故,我不忍说这话。人和人是能相处出感情来的,人和地,又何尝不是?嘉陵江的绿水,南温泉的草屋,甚至大田湾的泥坑,在我的生命史上,将留下不可磨灭的一页。”
张明明简介
张明明,张恨水长女,1940年出生于重庆南温泉桃子沟。现居美国华盛顿。
1964年毕业于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室内设计系。1976年移居香港。1979年移民美国,曾就读于美国华盛顿室内设计学院,著有《回忆我的父亲张恨水》、论文:《油画<待漏斋之夜>创作情愫——兼怀父亲张恨水》等。
上游新闻·重庆晨报记者 裘晋奕 摄影 胡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