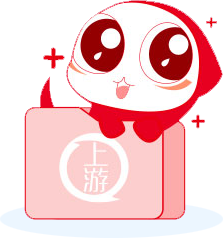

凌宗魁:嬉笑怒骂60年,舞台没终点!

早年表演剧照和舞台经典形象。

不演出时,凌宗魁与夫人隐居荣昌凌家铺子。

凌宗魁主演反腐剧《台上台下》。 上游新闻记者 高科 摄
“老头子,看啥子,我们要锁门了哟。”
“婆婆,晚上我要演戏,想提前看一下场地。”
“恁个大岁数还演戏啊?看你走路都打偏偏儿,演戏怕是不好看哟。”
“嘿嘿嘿,那你老人家晚上来看一哈嘛。”
12月13日下午,76岁的凌宗魁坐在四川大竹县文化馆简陋的剧场里,向重庆晨报记者说起早上提前看场子时的趣事。模拟起当时对话双方的神态语气,惟妙惟肖。
受当地政府之邀,他携反腐大戏《台上台下》巡演到了这座川北小城。剧场的清洁工婆婆做梦也想不到,她遇见的这个走路杵拐的“糟老头子”,正是当晚大戏的主角。她更想不到,这位老演员看似孱弱,体内却藏着多么惊人的舞台能量,可以在三年近50场的各省市巡演里,持续带给观众感动,多少个现场,人们湿了眼眶……
在这部自编自导自演的作品里,凌宗魁扮演一位失足下马的官员,却最终难敌各方袭来的糖衣炮弹,堕为阶下囚。
舞台上的凌宗魁仿佛变了一个人,模样年轻了20多岁还得归功于高超的化妆技术,但扔掉拐杖行动自如的表演,则让人不得不对老艺术家深厚的功底和坚强的毅力深感佩服。
从2015年首场巡演起,本报记者曾多次观看这部戏。尤其震撼的最后一幕里,凌宗魁手戴镣铐身着囚衣坐上审判席,忽然扑通一下跪在老母面前,肩膀不住颤抖,嘴唇哆嗦,涕泗横流,覆水难收,忏悔无门……高强度的表演让人物刻画入木三分,虽感人至深,却也叫人心疼。
“巡演三年,您跪了都快五十场了,七十多岁的人了,本来腿脚就不方便,身体也不好,还有那么多哭戏,这又是何必嘛。”身为晚辈的记者,打心眼里为老爷子的健康担心。此时已经演出结束,天寒夜深,大巴车上他拉我坐在身旁,踏上回渝的旅程。
“诶,你说不这样演,又该怎样演?”凌宗魁深吸口气,镜片后的双眼炯炯有神,写满真诚,“这个戏可能是我最后一个作品了啊,也代表了我对我们国家的热爱和牵挂,用文艺的形式鞭挞社会丑恶,是我一辈子都在做的事,舞台上必须演得让观众信服,才能起到文艺春风化雨的作用。”
“感动观众就不顾自己呀?前几天您还说膝盖必须动手术了,万一跪下去起不来怎么办?”
“呵呵,到点儿了嘛,能死在舞台上也不错嘛。”他笑着摇摇头,轻轻握住我的手,“演戏演了60年,一辈子图个啥子嘛,就是喜欢这个东西啊,演戏养活了我,我也通过演戏为社会做点事,这辈子,不亏了。”
1959年,任白戈的奖状
凌宗魁幼年家贫,记忆里第一次接触演戏是1950年。
7月的一天,一个帆布搭建的戏棚子出现在江津白沙镇江边。“之前从没看过演戏,我被棚子里的锣鼓声吸引,却又没钱买票,只好围着棚子转来转去,终于发现有个接头处开了缝,就把眼睛凑过去看,看又看不清,于是想拿手指拇去撕大点,结果遭卖票的大汉撵得鸡飞狗跳,逃跑时脚还被江边的石头划伤了。”
戏没看成,但敲锣打鼓、又哭又笑的舞台留给他许多遐想。1953年随父亲工作调动,他转学到了九龙坡铁路子弟小学。“‘村娃儿’进城,一口江津话常常逗得同学哄堂大笑,比如‘辣’,江津人读成‘嘞’,‘热辣辣’就成了‘热嘞嘞’,虽然穿着说话都土里土气,但长得周正,声音洪亮,当了大队队会司仪,每次我高喊‘奏乐、出旗、奏国歌’都很得意,终于站上大舞台了嘛!”
上了初中,生性活泼的凌宗魁开始如鱼得水,自学了吹笛子、拉二胡、打扬琴,还被九龙坡铁路俱乐部乐队每周请去演奏。50年代末台海关系紧张时,愤怒的他写下了第一个活报剧《打到杜勒斯》,这个剧不但在学校公演,还多次走上街头演出,受到欢迎。
哪晓得母亲却极力反对,“她几记闷棍打来,骂我说‘喊你龟儿子好好读书,偏要去学二流子’,结果我也没遭打怕,骨头硬哈哈。”
1959年,不到16岁的少年凌宗魁迎来了人生第一次高光时刻。“学校推荐我参加‘重庆市群众文化积极分子代表大会’。我接过盖着时任市委书记任白戈大印的奖状时,心里的激动不摆了!”从此,他将1959年视为艺术人生真正的起点。
1977年,两斤三花茶
初中毕业,是继续升学还是为当演员而努力,成了1960年夏天凌宗魁面临的难题。
“其实毕业前我去考过一次剧团,结果落选了。”他回忆,当时学校推荐他与另两位文娱活跃分子报考新成立的峨眉电影制片厂演员剧团,“考试地点在市歌舞剧团,我还记得考官出的题目:一个寒冷冬天,一个四面透风的房间,我就在这屋里,如何表现?”
凌宗魁没有多想,立即进入角色,“我抱着肩膀逐渐颤抖,嘴里发出唏嘘声,继而靠着墙角慢慢梭了下去,蜷成一坨……我那时也是表现欲望太强,忽然跳将起来抱着一个五人座木靠椅转圈,这个陡转表演反而加深了考官好感,他们哈哈大笑,让我顺利过关。”
不过因为近视,凌宗魁最终未被峨影厂录取,毕业进了成都铁路文工团。后来多方辗转,受四川评书泰斗程梓贤邀请,回到沙坪坝曲艺队。“1963年3月到1988年12月,我在沙坪坝曲艺队待了26年,度过了最美好的年代。”第一次发表作品、第一次作曲、第一次上电台录音、第一次学演相声、第一次创演评书、第一次演方言话剧引发轰动……艺术生涯的太多第一次,都发生在这一时期。最重要,还第一次听说了谐剧创始人王永梭的名字,并最终得以拜入门下。
“有一晚,有个朋友问我认不认得王永梭,我茫然地摇脑壳,他一拍大腿,‘嚯哟,王永梭,奇人哟!他演的谐剧《卖膏药》笑死个人,他一个人在舞台上扯把子扯得圆惨了,逗得观众眼睛水都笑出来!’我记下这个名字,很想跟他认识。”
1977年初夏,有一天翻阅四川日报时,凌宗魁忽然发现广告栏刊登了王永梭将于7月11日在成都人民公园演出的消息,“我一咬牙,丢下产后才七天的妻女,连夜坐火车跑去成都。”
那时凌宗魁工资低,手头拮据,“演出前求见先生,我只能递上两斤成都人当时都喜欢的三花茶,便宜撒,王老师见我谈吐可以,身材相貌也长得不错,答应了拜师学艺的请求。”
第一次看师傅演出的经历,在四十年后想起来都还无比清晰,“当晚我老师演了两个戏,《买三花》和《卖膏药》,一买一卖两段谐剧,我大开眼界,觉得这是世界上最奇妙的戏剧,表演惟妙惟肖,语言机智风趣,包袱一甩即炸,我真的五体投地!”从此,凌宗魁开始成渝两地奔波,一心一意追随王永梭先生学习谐剧。
2000年,牡丹奖与一千元
谐剧对演员要求高,凌宗魁也是拼了命在学,“一是出于真心喜欢,一是也想借此改变生活,说起来有些俗气,那时我家庭拖累重,必须要靠演出挣钱养家,这样的动机是不是有点不纯?但这是我真心话啊。”
跟王永梭学习的第一个段子正是《卖膏药》,因为观摩过,学习起来容易上手。“但最难的地方是结尾处要展现一套拳术,必须货真价实,才能说明卖膏药的弟兄不是江湖骗子,而是凭真本事卖的良心药。”
他四处托人,终于拜入沙区供电公司职工、武林高手张慧积老师门下学习拳术,“真的是闻鸡起舞,每天天不亮就赶到张老师那边的练功场,熬过了筋骨疼痛期,倒也打得有模有样了。”
很快,凌宗魁带着《卖膏药》参加了文革后重庆市专业院团第一次的青少年演员汇演,“也是苍天怜见,汇演的年龄放宽到34岁,刚好是我的坎儿!”如今回想,他还觉得是上天赏这口饭吃,节目拿了三等奖,他第一次用谐剧证明了自己。
从这个市级三等奖起步,凌宗魁陆续创作演出了《退货》《听诊器》《开会》《王保长》、《如此旅客》、《父子春秋》、《会议在进行》、《王老三卖桃》、《懂得起》等作品,将一百多项国家级、省部级文艺大奖收入囊中。整个八九十年代,凌宗魁红遍全川,成了重庆最炙手可热的本土演员之一。
顺理成章的,等到中国曲艺最高奖牡丹奖从2000年开始评选时,名震西南曲艺界的凌宗魁摘得首届牡丹奖表演奖,带着他心爱的谐剧站到了国家最高领奖台。有意思的是,当年这个全国曲艺最高奖只为凌宗魁带来了一千元奖金,想起来他还觉得好笑,“奖金很少,刚开始嘛也有些不理解,后头觉得,我把老师王永梭的谐剧发扬光大了,连北京的专家都一致认可了,这样想就觉得很舒服了。”
18年过去,如今的凌宗魁也堪称曲艺界一方泰斗,门下弟子杰出者众多,儿子凌淋、弟子吴文、鲁广峰等都陆续摘得牡丹奖、群星奖或获得提名,弟子们遍布全国,有九位任职重庆、宁夏、贵州曲协主席、副主席或秘书长,曲艺“凌家军”声名赫赫。
但老爷子仍然不愿退休,2015年起,他十年磨一剑将谐剧《台上台下》改编为话剧大戏,并自筹资金,开启百场巡演,场场皆亲自登台,催人落泪。为他心疼的不只有记者,还有他的家人和徒弟。重庆市曲协主席鲁广峰拜师十五年,与老师情同父子,他说,“《台上台下》老师每一场声泪俱下,他老泪纵横,我们也真的心疼。”不过徒弟也理解他,“老师一辈子眼里容不得沙子,他的作品都像标枪一样,辛辣讽刺,发人深思,他作为艺术家的社会责任感,也是我们后辈学习的标杆!”
老爷子自己则说,这一生惨淡经营,曲折坎坷,是舞台给了他梦想,所以才要永远心怀梦想,走向前方!本报记者 赵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