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面新闻消息,在写完第13部长篇小说《匿名》之后,王安忆终于松了一口气。因为“硬骨头”都啃过了,“形而上的边界”也触碰过了,写什么都不怕了。“每当我写到难过的时候,就想起陈思和(前复旦大学中文系主任)跟我说的托马斯·曼,告诉自己不要管写得好看不好看。但还是难免自我怀疑,写得不好看,是没找到更好的故事、更合适的载体。”王安忆说。此时正是上海的盛夏,她坐在番禺路一家酒店的咖啡厅里,脚下摆了一个袋子,准备采访结束后,去超市买一点菜回家。
2016年,她应美国纽约大学(NYU)比较文学系和东亚研究系教授张旭东之邀,前往纽约大学访学,在半年时间里,她住在一个休假教授的空闲房子里,距离校园只有一条马路,安静而且方便,在这里,她写下了两篇中篇小说:《乡关处处》讲述了一位绍兴阿姨在上海做钟点工的故事,《红豆生南国》是关于一个香港男人的半生经历。
今年6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王安忆的小说集《红豆生南国》,收录了这两篇访学期间写成的小说,还有一篇是在她美国西部收集“材料”回到上海后写成的《向西,向西,向南》。对她而言,写作这三篇故事的确费力,但更多感受到的是“写的趣味”。 她觉得自己的写作历程就在“艰难”和“有趣”之间不断流动,当年写完《纪实与虚构》,她回归了“市民生活”,后来写出了《长恨歌》,然后便是《启蒙时代》。
王安忆今年不打算创作长篇小说了,“准备写点儿闲散文章”。出版社一直以来青睐长篇小说,现在写长篇的人也越来越多,“但是长篇是很难写的,不是写得长就是长篇,我要找到一个长篇题材很难,”王安忆说。

王安忆
界面文化:你的《乡关处处》是关于绍兴保姆月娥来上海打工的故事,之前你也写过关于民工的《遍地枭雄》,你曾经说自己非常重视边缘人群的“小逻辑”。你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去写保姆和民工的故事,关注他们的“小逻辑”的?
王安忆:其实更能与《乡关处处》做比较的是《富萍》,但这两个人(富萍和月娥)完全是两个不同时代的保姆了。《富萍》是美学作品,这个阿姨和东家一起生活、水乳交融,而《乡关处处》是社会学作品,其中钟点工的生活是很独立的,她在城市留不下来,她的归宿就是回家乡养老。上次在一个城乡关系的会议里,我也说了自己的观点,很多人反对,陈思和和李锐都认为那些人能在上海生存。这其实是不可能的,他们的想法就是赚好钱,回家乡盖房子,这是基本出路,除非灰姑娘碰到王子。《乡关处处》表面上说到处都是故乡,实际上就是没有故乡。
至于为什么要写他们,我个人认为,主流以外的人才具有美学价值。主流内的人对于社会是主体力量,但是美学太一致了,所以在美学上,我不会把主流人群作为艺术对象,他们太同质了、太格式化了。而边缘人群不受体制化的影响,更有个性。
界面文化: 近来也有保姆自己写自己的非虚构范例,外界冠名以“底层书写”或“苦难叙事”,你如何看待这种自己写自己的行为?你觉得你笔下的保姆月娥和他们自己的书写有什么区别?
王安忆:我不能去评价他们。小说和非虚构当然是不同的。他们的书写是非虚构,写自己的生活,这很有说服力,因为那是真实体验,你没有办法去推翻它。小说和纪实不同,你不能讨论小说里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只能讨论写得好与不好。
界面文化:所以跟非虚构比,你认为小说的“虚构”的形式应该保留吗?
王安忆:当然应该保留,不保留形式叫什么艺术呢?这两天我看了一个电影叫《冈仁波齐》,后排坐了一个心理学院的老师,我俩看完以后不约而同地问:‘这老头是真死了,还是演出来的?’这个片子本身是一个纪录片,要说服大家里头的情节都是真实的。后来我就在网上找了一下,发现老头的死是摆拍的,老头是个群众演员,所以他们要说服老头去承担这一死亡角色。要知道,让一个有宗教天命观的人这样做很不容易。这就不是记录了,是创作。
界面文化: 在这本书的最后一篇故事《向西、向西、向南》里,你流露出对于女性情谊的倾向,在此之前你曾经书写过很多有关姐妹情谊的作品,比如《弟兄们》《姊妹们》和《姊妹行》,为什么女性情谊会引起你的特别关切?
王安忆:我在《中篇小说选刊》创作谈里提到过,我对姐妹情是有倾向的,姐妹情这个说的不是同性恋。我注意到男性好像“闺蜜”很少,基本每个女孩都有闺蜜,这是普遍的事实。在餐馆里,据我观察,两个女孩子坐在一起而且很亲密的,超过坐在一起的两个男性和一男一女的数量,为什么?这可能和女性的命运有关。
界面文化:“女性的命运”是指什么?
王安忆:女性的命运相当有共同点,而男性多是社会人格。男性之间的交流,不像女性之间的沟通那么私密深入,男人可以在一起喝酒,但不谈隐私。我常说女性是感情容量很大的动物,这很“危险”,可能会被看做同性恋,但把姐妹情当做同性恋的话,又落入情欲的窠臼里了。
界面文化:《红豆生南国》这篇讲述的是一位香港男人的故事,你也曾写过以南洋为背景、讲述父亲家族史的《伤心太平洋》,这次的《红豆生南国》与之相比,有什么不同?
王安忆:《伤心太平洋》不是写实式的,而是抒情式的。我之所以写成抒情式的,是因为可以写作的物质性资料很少,又因为是家里人,想象会受局限,只能多做抒发。而《红豆生南国》这个比较有想象空间,正因为中间有距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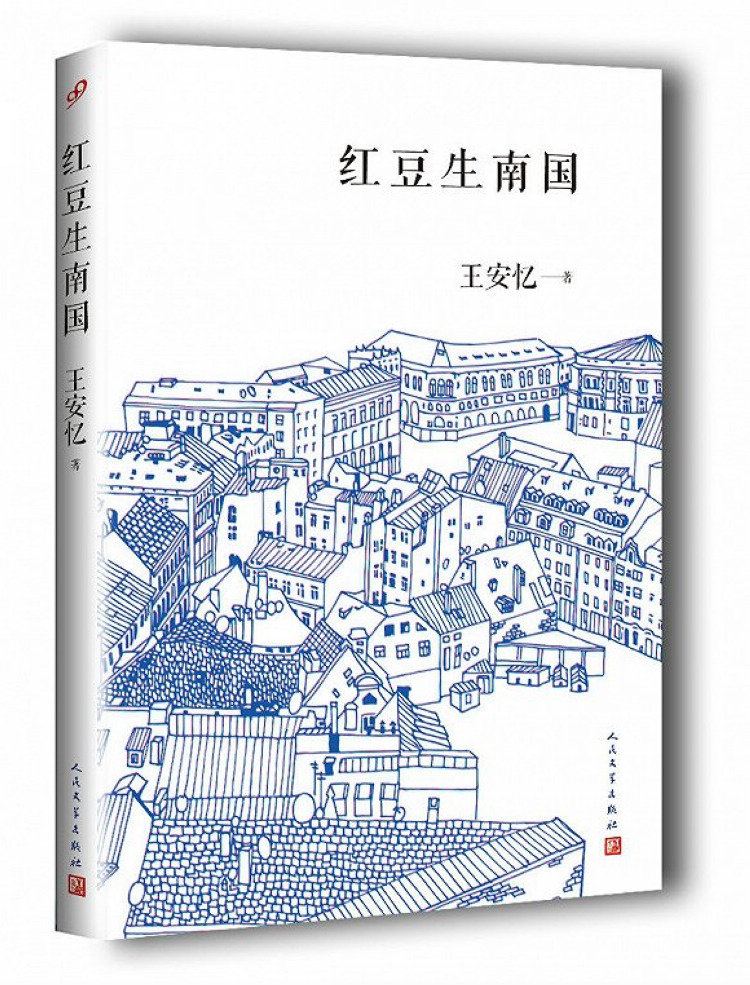
《红豆生南国》
王安忆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7年6月
界面文化:书写香港或是南洋的华人生活实质上也属于“华语圈写作”,这类作品与大陆本土华语文学之间构成了一种奇特的关系。你曾在有一次和黄锦树、骆以军的对谈里,说马华文学可能会为中文创作提供新的可能,这是什么意思?
王安忆:汉语在马来西亚是被边缘化的文字,办公语言不是汉语,社交语言也不是汉语,汉语没有功能性,而太有功能性的语言会被污染。我一直记得我第一次听顾城的诗歌朗诵,顾城说“汉语就像流通过度的钞票”,诗人对于语言是最敏感的,所以他想摆脱旧币、开创新币。这很难,因为说话是要让人沟通的。而马来西亚的汉语天生就是孤立的语言,这门语言除了华文写作之外,没有任何用途,作者感到寂寞,所以很多马来西亚作家都来到了中国,就像回到母语的胞胎里一样。马华文学孤立发展是很难的,但我觉得他们反而继承了“五四”的白话传统,他们的作品是很“五四的”,另外还加入了很强烈的译文体。
界面文化:那么美国华人写作也是一种孤立的写作语言吗?你如何评价他们的写作呢?
王安忆:美国的华人写作,我也不大好意思去评价它……承担写作的人水准比较低。在美国,生存很重要,做生意很重要,谁要写作了?哈金用英文写作,唯一的中文作品是他自己刚翻好的《Going Down》,写法拉盛的,我在美国公共图书馆借来读过。 美国跟我们不一样,美国人不喜欢看译文。我们一天到晚“走出去”,他们就喜欢看英文的(文学作品)。裘小龙用英语写作,但他的写作非常一般。在美国,凡是有名的作者都是用英文写作。但是我们中文读者也很多啊,如果没有“走出去”的压力的话……
界面文化:像你这样的作家“走出去”的压力大吗?
王安忆:我是不要走出去的。他们那么喜欢“走出去”是为什么呢?还是承认西方的标准更有价值。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战略投入了很多钱,有时反而把事情搞坏了。原来那些国外出版社规模小、钱很少,我们“走出去”,钱和人大量涌入,他们也喜欢钱,就放弃了自己的(文学)选择。
我原来《长恨歌》的译者是Michael Berry,我们叫他小白,是王德威的学生。如果是葛浩文译会不一样,但我最后还是尊重王德威的推荐。小白当时的翻译属于无名者的翻译,他找不到商业出版社,人家一看是没有名气的翻译者,就提出很多奇怪的要求,比如让你删掉一些内容,所以最后只能在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与《海上花列传》在同一个书系里——大学出版社是不可能走向市场的。后来还算不错,这本书得了翻译奖。出版社第一次给我寄书寄错了,我收到了一箱子《海上花列传》,我说要不要退给他们,他们说算了送给我了。
界面文化:你在复旦大学的创意写作项目(MFA)教导学生们写作,至今已经有10年了。你在课堂上是怎么教写作的?在课堂上教授写作对自己的写作有反哺吗?
王安忆:我教写作的时候,要首先把自己写作中遇到的问题都整理归纳出来,再跟同学交流。小说不像下围棋那样有段位,作者们从头到尾碰到的问题都是一样的,就是写什么和怎么写。学生们交作业,我从作业中发现他们的问题跟我的是一样的,只不过有的初级点儿,有的高级点儿。写作也是有技术的,但写作技巧通常和个人经验、社会情感、周围环境都有关系,很难像音乐技巧一样能够孤立出来。在教课的时候,我会努力把我的话组织成对方懂的语言。我们的生源现在越来越好,都是重点大学的学生,最后毕业作品也很好。但他们不一定会(把写作)作为未来的职业,很多学生最后都不会以写作为生。
界面文化:你认为现在以写作为生是可行的吗?或者对于学生以写作为职业有一些劝告?
王安忆:我不能劝告。现在很多人是靠写作为生的,比如网络上那些小说作者。但是中国现在还没产生类型小说的概念,比方说有些作者是好的类型小说家,但你不能这么说他们,这么说就好像贬低他们一样。
界面文化:前段时间有一篇对著名文学批评家哈罗德·布鲁姆的访谈,他说现在人们看类型小说,比如斯蒂芬·金、哈利·波特看太多了,脑子都看坏了,你怎么看待这种说法?
王安忆:总的来说,看类型小说比看电视要好。我家有线电视坏了,到现在都没修。看电视剧更加坏,它看着看着就产生一个惯性,每天都要见面,换不掉它。最近流行的电视剧是亦舒小说改编的?亦舒是个老作家了,怎么突然把她挖出来了?我不要看这些,看这些就想起沪剧里的“西装旗袍剧”、小三的故事,随时都可以想出来,何必要亦舒呢?
对我来说,看书是最有趣的事了,没有其他事可以代替;我看书是消遣,一天能看十万字。类型小说写得好看,但看多了就有模式,评判类型小说优劣与否就在这里。特别出色的类型小说不会体现很高的价值观,但很会编故事,阿加莎的好处是悬念你都知道了,还是想看,因为它还写了人物性格。不像本格派推理,本格派特别像工程师,我也不太喜欢硬汉派。东野圭吾出书我会买的,但我觉得他早期几部比较经典,最近有点儿式微的感觉。松本清张是社会推理,大概是我看过太多电影,看小说就没有耐心。宫部美雪也是社会类型的。我最近在看斯蒂芬·金的《暗夜无星》,这里面有常态的生活,当他写到西部田野,就是空中楼阁了。北欧现在也有一些值得关注的作品,我听八卦说《龙纹身的女孩》出来第四部了。
跟你们在学院里接受教育不一样,我们是插队落户,在社会上这么生长起来的,我们所有的文学素养都来自读书。不光是作家,就是那些种地干活的,也看过很多书,过着文学生活。 人(看书)还是要有些乐趣的。我自己掏钱买的书大部分都是推理小说,不好意思。我前天晚上跟我先生说,我去书店买书的时候,特别感谢我的读者,因为买书要犹豫的、要挑选的。除了推理小说以外,我买的还有一些是用得着的书,比方说我要写书评的书。我也喜欢社科类的,现在很奇怪,很多人类学倒用小说笔法写东西。朱天心在90年代还写叙事性的小说,后来放弃了,大概有点儿受现代主义影响,好像做音乐的写好听的歌,就很不好意思,非要写点难听的。
为什么小说会变得那么难看?这和知识分子的介入有关。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介入小说,我们的小说承担启蒙责任,这是知识分子把俗文化借过来了。当思想的任务重了,叙事就被忽略了。最好的情况是两者兼有。好的小说家有思想也会有故事,像是爱尔兰的托宾,思想是用故事来表达的;差一点的小说家急于把思想归类,但思想在生活中是无法被归类的。张怡微在台湾得过很多奖,这一点儿也不奇怪,因为台湾文学现在都是不讲故事的,她给台湾带来了一股清风。台湾作家对叙事问题也很纠结,朱天心有一次跟我对话,让我十分动容。她说,他们不是说不叙事,而是“刻舟求剑”。这和大陆的作者不一样,我们始终在叙事的传统里,现在的“80”、“90”后也有使用其他的手段讲故事。这也和不同地区的不同传统有关,长久以来,英国人狄更斯、奥斯丁的传统还在,美国人和日本人的小说就在走向现代化。
界面文化:小说告别叙事,是否因为很多人认为电影分担了叙事功能,而且做得比小说更现实主义、更充满细节?
王安忆:小说和电影的关系是个大问题,电影和小说是不同的,电影不能代替小说,小说也不能代替电影。电影太工业化了。我觉得对欧美小说造成伤害的,是他们的经纪人制度,你看《天才捕手》里是没有经纪人的,这才过去了多少年?现在经纪人制度基本架空了作者和出版之间的关系,这和整个社会的资本主义方式有关,就像房子要有中介,来保障各方面的利益不受损害——但经纪人制度对于写作不是好事。很庆幸我们没有这个制度,我们有大量的文学期刊,可以让所有无名作者有机会出场,哪怕一个短篇也可以署名发表。
界面文化:近来北岛主编的“给孩子”系列里有一本是你主编的《给孩子的故事》,在这本书里你挑选了很多通常不被认为是“儿童文学”的作品进去;今年儿童节,你在一个访谈里提到了与这本书的选排思路相关的内容,你认为儿童文学不应该那么“单纯”,儿童文学与正宗的文学之间没有界线。我们知道你早年曾在儿童杂志《儿童时代》工作过,你认为儿童文学应该是什么样的?
王安忆:当时我在美国,北岛问我能不能提供给孩子的故事的作品名单,我手头也没有东西,就给了他一份名单,回来他让我编《给孩子的故事》,我就开始编。我不会在“儿童文学”里头找故事,我是在真正的文学作品里找的——选进去的很多篇都不是故事,就是散文。记者把我这个话放在“六一”节,让很多儿童文学作家都对我有意见,好像我不看好儿童文学一样,其实我并不是不看好,现在儿童文学已经在分工了,有些是绘本,有些是别的,那么不看绘本就应该看跟大人一样的东西,不应该专门有一种给儿童看的文学。
(原标题:王安忆:女性是感情容量很大的动物)
【免责声明】上游新闻客户端未标有“来源:上游新闻-重庆晨报”或“上游新闻LOGO、水印的文字、图片、音频视频等稿件均为转载稿。如转载稿涉及版权等问题,请与上游新闻联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