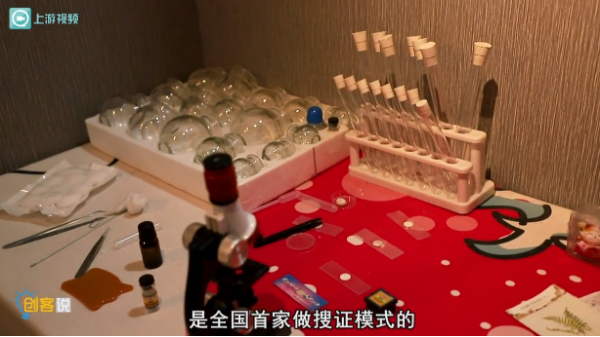澎湃新闻消息,看了复旦中文系的侯体健老师写王水照先生的办公室的文章,很是感慨。有他跟随先生治学的体悟,陪伴先生会见客人的观察,还有在先生的藏书间肆意遨游的点滴。复旦中文系的老师大抵有个习惯,喜欢邀学生去办公室,海阔天空,促膝长谈。听说这是当年朱东润先生带起的风潮。朱先生自牛津回沪上,一身英伦清谈的做派。老先生道骨仙风,教学不喜阶梯教室人头攒动,学生排得像是整齐划一的积木,估计看了心也烦。办公室里一方局促之地,师生几人围坐一团,暖光四溢,弹指一挥间,就把课给上了。陈思和老师也是,喜欢把学生箍在小范围的空间里上课。除了给本科生的公选课《中国现代文学史》在大教室里人满为患之外,研究生的课讨论,鲁郭茅巴老曹,一律摆上办公室的案头,全班在光华楼10层开圆桌会议。你一言来我一语,噼里啪啦谈将起来,末了他负责总结和点评。这个习惯仿佛是中文系老师的集体无意识,或多或少都在坚持着。

王安忆
因此,说办公室的故事,必须讲到上课,因为上课地点一般离老师办公室都不远,都在光华楼里。干脆有的就直接安排在办公室或隔壁屋,王安忆便是如此。
王老师给我们开两门课程,各一学期,一门是《艺术创作方法》,一门是《小说写作》、两门课都安排在晚饭后,临睡前,一夏一冬。那些个夏夜和冬晚,当我们拖着吃饱了的懒惰的身子,伴着校园里芬芳的桂花和满地的枯叶,从北区研究生宿舍奔走到光华楼27层,听王安忆讲什么样的故事是好故事,怎样讲好故事。纵观当代中国作家,王安忆的阅读量算很大,范围也广。她仿佛对书写出来、铅印在纸面的这些密密麻麻、用来叙述和说理的横竖撇捺,疯狂执迷。她的写作理论也反复强调,阅读经典是学习写作的必由之路。推己及人,阅读便成了她布置的一项基本功课。她在小说课上,也时常提点我们读得太少,她也总能把大家单薄的故事和人物与经典里的桥段相联系,希望同学能向契诃夫和巴尔扎克们汲取智慧,吸收营养。不过她并不开列书单,也从不让学生读她自己的作品,我揣测这样会有王婆卖瓜的嫌疑。但是,办公室的书柜却成为她留给我们的一笔巨大矿藏。
因为是班长,我在王老师和班级之间扮演了一个“中介”角色,需要经常出入她在光华楼27层的办公室,递送作业,拿取资料。更重要的,是收敛她交代同学们阅读的篇目。这就要说到她办公室藏书的结构,大致有三类:一是中文系老师们自己的著作,这里就包括她自己的小说和散文、王宏图老师的小说、龚静老师的散文和严锋老师的文化随笔。书的版本都很旧,品相也不精,好像被一代代学生摩挲过。我想在这些老师看来,读本专业老师的书,也是在大部分不得谋面的时间里,学生向老师求教的不二法门吧。
另外是一些当代作家的作品集,印象里有王蒙、梁晓声、冯宗璞、史铁生等等,还有一些复旦其他老师的著作。依稀记得,有郜元宝老师编著的复旦师生读鲁迅系列丛书、同济大学张文江教授讲庄子的书,和龙应台、马家辉等港台作家的赠书。他们都是王老师的朋友,有的与她过从甚密,影响过她的人生与创作,她自然希望我们也多读这些人的作品。
数量最大是整层的文学期刊,印象里《收获》和台湾的《印刻文学杂志》占了大多数,成堆垒着。这些期刊里的作品,她有时候会拿作上课的素材,说某某刊物上一篇小说好,就放在我办公室哪儿哪儿,你们一定要看。有些是名家新作,不过大多都是不知名的作者。那时候微信还没流行,没法建一个班级群分享阅读资源。一般当她这么交代了,课下我就去办公室翻箱倒柜,找到了再流散给同学们。还有一种情况是,她自己在家读到了某篇好东西,觉得应该分享给我们,就会在杂志里夹上一张荧光黄的便笺条,拿到办公室里,工整放在书桌上。一般我投递作业的时候看到偌大的桌上放着一本书,里面夹着簇新的便笺,便知道这是她要我们去读的了。不过试想哪怕是“群”雄崛起的今天,依王老师性格,估计还是会遵循那古早的纸笔交流。
她仿佛是个抵制智能手机和互联网社会的人,印象里她用的手机是十足的老人翻盖机,不过颜色很鲜艳,没记错应该是玫红色,不知道如今换了没有。就像她的衣裙基本是纯的大色块,不夹杂繁缛的花纹和图案。有个冬天晚上,她穿了件鹅黄色的高领毛衣,钻进黑暗幽深的光华楼来上课,毛衣黄得晃眼,换作别人,肯定土气,像是穿越过来的女大队书记,抄起家伙就能跑到田间地头给知青们计公分。但她穿上坐在课堂中间,莫名复古时尚。
作为“中介”,掌握着办公室的钥匙这一核心资源,有时我也不免占一点小便宜。王老师极少来办公室,也就上课那天。情况一般是这样:晚上有课,下午我就早早去11层的系办把晚上用的教室钥匙借到,然后开门布置一番。随后,我便踱步来到教室隔壁王老师的办公室,享用一番这张宁静的书桌。那时候,光华楼还是杨浦的第一高楼,五角场的官方标的物。坐拥27层绝佳风景,俯瞰复旦校园,有着登临天顶、一览三山五岳的爽快。不过那些个下午,我很少看书,大部分时间是玩手机和iPad,包括整理同学作业,还有背单词。至今,我苹果账号里的几个高分记录都是在王老师办公室里创下的,那是我游戏人生的巅峰。
有一次,我酣战正急,忽得有人敲门,我以为王老师约人来谈事。结果是一位要找办公室同在27楼的张新颖老师的韩国博士生,她要把写沈从文的论文初稿交给张老师。她操着不流利的汉语,结结巴巴问我张老师在不在这。我大手一挥,告诉他张老师在那里,这是王安忆的办公室。她眼里霎时冒出火焰,问了我一连串的问题,王安忆多久来上一次课啦,王安忆怎么讲小说啦,王安忆上课严厉还是温柔啊,王安忆啦啦啦啦啦……我像外交部新闻发言人一样,耐心给她解答。她开始听得出神入化,不过没一会儿,好像还是觉得论文重要,撒开腿就走向张老师办公室的方向了。
实话说,王老师待学生是严厉的,她的绝对写实逻辑,像是圭臬一般,风火雷电坚不可摧。一旦大家作业的叙事链条发生了脱节或断裂,她便正面相向,在课上发出尖锐的质疑和诘问。你写得这个人这么有钱,他的钱到底哪儿来的?这个人物总归有爸有妈有社会关系吧,你是怎么弄的?交通事故处理怎么可能这么草率,你去问问交警吧。你这么会给事物命名,命名完怎么什么都没体现呢?课堂上,有些同学被王安忆老师强大的逻辑和气场所震慑,对她都有些惧怕。可我相信,世间有一种爱,包裹着严厉的外衣,王老师是爱之深责之切,这也是她为人师者的职业道德。
话说回来,对那间办公室,我还是惦念有加。离开校园三年了也。从上海到北京,由南方入北地,由学生到职人,由文学而新闻,时间过得可真快。王老师曾说,我们毕业后很少有人从事专业文学创作。在南大文学院教书的毕飞宇老师前段日子也告诉我,他不会建议任何一个学生从事专业文学创作,毕竟文学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但在复旦读书给我们人生打下的底子,是像骨血和筋脉一般,融进肌体,重铸心灵。
余华有回来中文系讲课,说我们这帮学生很幸运,能跟中国最好的女作家学习,还说王安忆是他偶像。我当时听了心里想笑,觉得余华很幽默,要么就是情商高,到什么山头唱什么歌,现在想来,觉得他说得是铮铮之言。
回忆拉拉杂杂,可能有些细节都不准确,读者诸君莫怪,错误部分,文责由我自负。希望还有机会出入王老师办公室的同学,不要像写文章的学长一样,把时间都用来打游戏。认认真真读书,勤勤恳恳写字,踏踏实实做人,这才是王老师和所有老师的期许吧。
原标题:在王安忆办公室的日子
【免责声明】上游新闻客户端未标有“来源:上游新闻-重庆晨报”或“上游新闻LOGO、水印的文字、图片、音频视频等稿件均为转载稿。如转载稿涉及版权等问题,请与上游新闻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