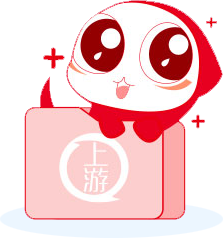

关于电脑的一点往事
2018年2月25日,一台用多年积攒的稿费购买的笔记本电脑来到我的书桌上。这个崭新的笔记本电脑,轻薄、清晰、迅速,带着足够激励人的便捷。
二十年前,这是不可想象的奢侈,今天,不过是一件寻常的工具而已。
我想起多年前的第一台电脑。刚刚工作一年多,攒下了两千多块钱,经亲戚联系,打算买一台二手电脑——新电脑太贵,属于当时的高端消费。尚在温饱线上的我,能有类似智力投资这样的消费观,自觉已经很超前了。
大冬天里,在重庆谢家湾的一个住宅区里七拐八弯了半天,上楼,推门,一大书架挤挤挨挨的书和光盘瞬间震慑了我。一个瘦瘦的中年人坐在桌前正捣弄着一台电脑。听到门响,他抬头望过来,微微笑着起身:“您好!请坐请坐……”是极其标准的普通话。他自我介绍姓阮,是北方人,过来做重庆女婿。我恭恭敬敬地叫他:“阮老师好!”可不应该尊敬么?我还连电脑都不会开,人家已经敢于把电脑大卸八块了。
因为囊中羞涩,我询问的语气是略带忐忑的,在害怕别人看不起之前,自己先有点看不起自己兜里那点小钱。可即使这点小钱,也是我节衣缩食好不容易才省下来的。
阮老师的态度却出乎意料地温和。仔细询问过我的需求后,给了建议,并组装配置了一台电脑,又留下电话给我:“如果有不明白的地方,或者遇到什么问题,都可以给我打电话。”
新手上路的各种乌龙自不必说,有时候仅仅是输入设置的一点小问题,也会慌慌张张去给阮老师打电话:还得跑一两百米去一个小商店才有电话,问三两句又回来摆弄电脑……一来二去,倒也慢慢弄懂了很多电脑知识,打字渐渐熟练了,小问题自己也能解决了。阮老师在电话里朗朗笑着,夸我会学习。
十多年过去,电脑已经换了几拨,阮老师还是我的朋友。他总是毫不吝惜地提供技术指导,有时还提供给我昂贵的软件,却从不肯收我一分钱。他不无羞惭地说,那个时候他刚从学校离职出来,一切的雄心、事业都刚刚起步,所以那台卖给我的二手电脑其实是赚了不少的——可是总价那么点,再赚又能赚多少呢?总归不过是知识分子从商的一点迂顽罢了。
除了电脑操作的师徒关系,令我和阮老师成为忘年交的其实是文字。作为一个略有愤青气质的知识分子,阮老师偶尔会为生活种种写点什么,孤芳自赏之余,就是跟有同好的朋友交流。我着实钦佩他思维的天马行空,他谦逊恭维我语言凝练——好朋友往往建立在互相鼓励的基础上,一来二去,淡如水的君子之交便持续了下来。
2005年夏,阮老师忽然淡淡告诉我,他去医院查出了肝癌,医生虽然语焉不详,但出身于医学名门的他一眼看出已经是晚期。怎么可能?震惊之后,我心存侥幸:万一是弄错了呢?
可是事实就是,他辗转重庆、北京,几经手术,几经抗争,几经希望与绝望的交相凌虐,一年多后,阮老师带着对世界的万般不舍悄然离去……
病中的他,完成了献给深爱的妻儿的小说《陪读妈妈》并终于付印;
拖着垂暮的病体,他但凡稍有力气,就谈笑风生,豪言要从北京骑行回重庆;
他将自己多年科研的发明专利陆续投产,并努力安顿好了身后各种经济实体;
名为“与癌共舞”的博客上,还留着阮老师强忍疼痛、血战癌症中留下的文章,激励了无数病友;而他走后,与他伉俪情深的妻子也在此写下了追忆的文字,字字锥心,读来令人酸楚……
在小镇一隅如常生活的我,偶尔遥遥关注,像看一个传奇,更像目睹一位迟暮的英雄——私心里默默以为,我不曾直面的这一切,或许不好的都会过去。终成诀别。
甚至并没有来得及好好告别。萍水相逢的他,君子之交的他,淡淡如水的他……一切追念仿佛都早已不合时宜。我甚至不敢承认自己的遗憾与愧悔。
只在每次打开一台电脑时,耳边传来那把清朗带笑的声音:“按开机键的时候不要太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