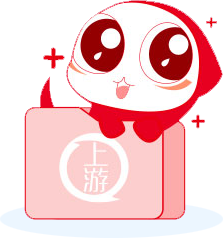

像花一样的老人:日本人如何养老之一
 善养传媒
善养传媒



日本是世界上人均寿命最长的国家,同时也伴随着老龄社会的各种严重问题。那么,日本人如何养老?记者罗洁琪在日本京都拜访了几家养老院,和一些相关的学者,试图寻找其中的答案。我们将陆续推出。今天的文章是关于一家专门照顾失智症老人和提供临终关怀的养老院,北白川的花之家。最后,花之家的创办人宫田女士问记者:中国也在步入老龄化社会,中国人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1
阳光耀眼,二楼的浅绿色百叶窗已经拉下,窗台和桌子都摆了鲜花,红色和绿色,点缀在十几位银发老人之间。恰好是上午的茶水时间,在二楼的公共活动间,每个人的面前都放了专属的茶具。有几位老人抬头看着来客,其余的或垂头闭目,或沉浸在自己的游戏里。
这是北白川的花之家,一所日本知名的私立养老机构,已有20年的历史,主要照料失智症老人,并且提供临终关怀。
两层楼,共住了36名老人,平均年龄在75岁以上。和日本其他的养老院一样,花之家的女性居多,只有4名男性。大部分人都不能自理,只有两名可以独立上厕所。每天清晨,介护士照顾他们先后起床,洗漱,进食,处理层出不穷的小状况。

北白川花之家的走廊花园,尽头是院长祖母曾供奉的观音菩萨像。

二楼的公共活动室。
我走到人群前面,自我介绍。 一位穿着紫色制服的介护士蹲下,拉着一位老人的手,低声解释。那位老人突然开口用中文说了一句,“你好”。她面容小巧,和其他老人一样,都是衣着干净,清清爽爽。她侧头看着我,抿着嘴唇,轻轻一笑,露出整齐的假牙。
另一位老人挺直腰板,精神矍铄,脸带微笑,一直看着我们。她姓本田,家乡并不在京都,年轻时是小学老师,结婚后就辞职做家庭主妇。她有一儿一女,儿子爱上了其他城市的一个女子,那是一个独生女。所以,结婚后,是她的儿子离开,搬到岳母家住了。她记不得这件事情已经发生了多少年,语气里仍然带着责备。她的女儿患病,视力不好,无法自理,她一直在家中照顾,直至其去世。她很悲伤,以泪度日,后来就进了这个养老院,她丈夫在外面工作。
我问她在养老院开心吗。她回答说,“与其说开心,不如说没有办法。”她又说,像她这样的老人,在其他地方很难生存。毕竟,日本老人的孤独死已经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
本田女士说,在北白川的花之家没有穷人,她也算是幸运的。在初入之时,花之家会收取105万日元,约6万人民币。每月再支付25万日元的费用,折合人民币约1.5万。还有一种方式,是签约20年,支付1千万日元,约人民币59万元,不论寿命多长,花之家都照顾到去世为止。据创始人、院长宫田女士(宮田さよ子)的介绍,大部分人会选择按月缴费,价钱都包括临终关怀。这在日本算不上是奢侈级别的养老,只是小而精的中高端。而且,收费的一半以上,都可以由政府推行的介护保险覆盖,个人只是承担部分。
我不敢直接问本田太多关于费用的事情,担心宫田院长误会。在一楼的楼梯口,宫田院长严肃地说,有介护士告诉她,我在采访时问起老人的家庭。她认为这样的提问很不好,毕竟有的老人终其一生没有结婚,或者没有生过孩子。她说,关于老人的背景,我可以问护工,不能直接提问,“花之家非常注重老人精神的愉快”。我连连道歉,并且应诺。
事实上,因为缺乏失智症的知识,在短时间内,我也找不到和老人交流的方法。我重新回到二楼,坐在一旁观察。
二楼公共活动间的秩序没变,就像我早上刚见到的那样。一位大约80岁的老人一直坐在沙发上的位置,面前摆了一张凹型桌子,身边堆了好几个毛绒公仔。
还有另一位老人,她只爱小狗,一只白色的毛绒小狗令她爱不释手。在喝茶的时候,她自己喝一口,再用勺子喂小狗。有些更加衰老的,就半躺在轮椅上,抱着一个大枕头,支撑着垂下来的头部。
最让我不解的是,有一位老人一直用手抚摸着她身边的同伴,摸着她的手,她的背,颈部。我忍不住问身边的介护士。她说,那是一对姐妹,曾经都是滋贺县的国立幼儿园老师。姐姐比妹妹大四岁,结婚没孩子;妹妹有个女儿。妹妹和女儿关系不好,长期冷战。两人的丈夫相继去世,姐妹俩搬到一起,相依为命。随着年龄增长,失智症变得严重,她们一起来到了京都的北白川花之家。妹妹的眼睛几乎失明了,姐姐习惯触碰妹妹的身体,护工说,可能这样可以缓解妹妹的不安。

左二是本田女士,右一是做了11年的介护士,脇坂菜採。

左边的老人一直在玩毛绒玩具。
2
宫田是机构的创始人,今年70岁。她胸前挂着饰物,透过眼镜的玻璃,可以看到浅浅的桃红色眼影。

宫田院长。
宫田生于1948年,在日本西部熊本县的天草市,一个自给自足的村庄,有连绵的森林,成片的稻田,自行车小贩,新鲜的海鱼。
“在羊角湾村庄,祖父大声喊,‘站着’,我赤脚站在碎石路上。旁边种植水稻的人立刻站起来看着我,‘哦,宫田站起来了’。这是我记忆里的第一个世界。在身后呵护我的人,是祖父。” 宫田的自传《我是高龄介护承包人:让生命之花盛开的介护》,是以对祖父的回忆作为开篇。
有时候,祖孙俩早晨吵架,放学回家,又有说有笑。宫田怀念那一段吵架的经历,感激祖父把她从“服从”的社会概念中解放出来。她学会了在任何人面前,坦率地表达自己的观点。
她一度贪玩,在放学路上和别人摘橙子和挖红薯,爷爷在村里用最大的嗓门喊她的名字。从那以后,天一黑,即使爷爷没有喊,她也会听到这个声音,心里不安,独自奔跑回家。祖父总是站在家门口等她,面带忧伤地说:“我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死去。”
她照顾着衰老的爷爷,从小就了解老年人的疾病痛苦,懂得他日常生活的需要。几年后,她离开了村庄,去外面读书,先后就读于看护师预备学校,日本福祉大学和近畿高等看护专业学校。22岁时,在一个山上的肺结核病疗养院,她第一次为祖父之外的老人做护理工作。有资格证书的护士都忙于注射和各类检查,没有时间和耐心,病人经常长时间陷于沉默。宫田注视着病人,用微笑表达关心。早上分发茶水,她会微笑问候病人:“早安,您感觉如何?昨晚睡得好吗?”刚开始,病人有点不自在,回应时会带着奇怪的微笑。宫田认为,她需要做的是微笑着继续等待。
每个上午,她要照顾5个卧床不起的病人淋浴,其中有孤寡老人,没有任何亲属。老人深切的孤独和无助,让她震惊。她渐渐地感觉到身上有一种温和的使命,要努力照顾命运不幸的人,帮助他们有尊严地“生活”。在医院,她常常思考生死。在她眼里,死亡是“回归珍珠之地”,一个人长时间生活的地方,也只是栖居之地。人活着,就是向死而生。
在职场之初,她劳累过度,有一半的身体感到僵硬,以至于不得不暂停工作。她异常痛苦,直至一位医生告诉她,“在照顾别人的时候,要把自己也当成人一样对待,要找到生活的感觉”。
这些经历帮助她形成了机构养老的理念。人总是喜欢亲情的,特别是在生病的时候,希望有亲人照顾。但是,她认为,对于负责照料的亲人来说,难道这不是一种精神上的折磨吗?一个人的生命会永远为别人牺牲吗?特别是对于失智症老人,她认为专业的料理机构比家庭和医院都更加有现实意义,更符合病人的利益。
与此同时,日本的家庭结构、年龄结构都发生了变化。从上世纪60年代起,日本从传统的几代同堂,变成以核心家庭为主,即一个家庭只有一对夫妇和他们的孩子。年轻人成家后,就搬离了父母的家庭,两代人不再共同生活。老人相依为命,或者丧偶独居,或者参加日托型的社区养老机构。
养老早已成为日本全社会重视的系统性问题,在日本各地,有各种投资模式建起的养老院,有社区养老机构,也有针对不同阶层需求的特殊养老院。
20年前,宫田在一个养老院工作,其中一位老人是儿科医生松田道雄的太太。宫田对松田夫人悉心照料,老人的食欲消减之后,某一天突然想吃冰淇淋,宫田就出去买,尽力尊重她的意志。后来,老人去世了,松田医生对宫田非常感激。他认为,人到了晚年,需要的不是治疗,而是看护,但是,要实现这个理想是很困难的。于是松田医生鼓励她创立养老院。1998年,宫田从银行贷款,在京都市的高野开设了花之家,专门针对失智症老人,并且提供临终关怀。在当时的日本,这是首创之举。若干年后,她在京都市的北白川又成立了第二个花之家。
她很自豪地说,在她的花之家,很多老人的孩子都是医生,因为医生更容易理解,她的花之家是对失智症老人最适合的地方。
3
5月9日,一位叫堀井的介护士在巡逻卧室时发现了一位老人没有表情,也没有了呼吸。她有7年的看护经验,可以毫不惊慌地处理这类事情。按照应急制度,她马上通知宫田院长,副院长,和机构签约的专业护士以及家属。机构的领导都住在附近,是5分钟的距离。护士过来确认死亡,通知家属安排后事。这位老人享年103岁。
遇到这种情况,花之家很少叫救护车送去医院急救。如果是骨折之类,会让护士诊断必要性。宫田女士认为,让老人住在医院的病房里接受各种检查和治疗,会导致精神孤独,生活质量太低。
花之家对老人的护理,散见于每天的日常。介护士定时给老人们测量血压、体重、记录进食的数量和慢性病用药的情况;对于重症患者,需要输液的,也是根据医生的处方,在花之家进行。对于这类病人,副院长会亲自监测输液的反应,定时记录。在这样的护理制度下,老人的每个变化都是受到监控的,甚至其死亡也可以通过观察征兆,进行预见。在花之家,老人的平均寿命是90多岁,如果是80多岁去世,就觉得有点太早了。
花之家有25位全职的介护士,还有 15位兼职。夜晚每层楼都有全职的介护士守夜,巡逻。一个月里,一位全职介护士有8个晚上是需要值夜班的,兼职介护士只是白天上班。根据宫田院长的定义,只有全职的工作人员可以承担责任,兼职介护士只是支持和配合。
堀井很年轻,20多岁的样子,原本是学美术的,妈妈是一名介护士。毕业后,她也考取了介护士的资格证书。她祖父是反对妇女出外就业的,但是她父亲并不反对。
脇坂今年31岁,毕业于护理学校,在北白川花之家已经工作了11年。她剪着短发,穿着深蓝色运动服,紫色的制服裹在里面。她刚值完夜班,从夜里10点到次晨7点。她的角色是管理人员,在厨房里帮忙做精细的料理,有时候也做护理,打扫卫生,指导护工,给老人们斟茶倒水。花之家的主业是提供护理,而护理的活是细小繁琐,几乎没有角色边界。
9号凌晨,她代同事值夜班,熬夜照料了那位103岁的老人。
脇坂初到花之家时,觉得压力大,精神紧张,因为取得老人的信任,需要很长的时间。曾经有一位新来的失智症老人,脾气暴躁,每天频繁要求上厕所,就算上了,也忘记了。有时候,一天要去8次。脇坂用耐心和专业的护理,赢得了信任。
她认为宫田院长是非常严格认真的人,对护理工作有极高的要求。她在工作中会因为同一件事被反复批评。她承认,肯定有心情起伏,可是她一直没有离开,不仅仅因为报酬可观,年薪约450万日元(约26.5万人民币),更重要的是对理念的共鸣。宫田院长把她坚守的理念贴在墙上——创业的精神:即使老了,得病了,也要让每个人的生命之花直到最后都免于践踏,努力让生命更璀璨。实践的精神:基于创业的精神,为了让利用者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都保持尊严、为了保证他们的生命完整而提供支持。

花之家的理念。
次日,汽车运送逝者离开,工作人员会在门口集体鞠躬目送。 脇坂说,内心难免有悲伤,同时也感慨,“您辛苦了”。
4
中岛女士生于1948年,今年70岁,是一位兼职介护士。和多数同龄人一样,结婚之后,她就辞掉文员的工作,做家庭主妇。生了孩子之后,参加了婆家的生意,学习做和服的刺绣。50岁以后,进入了人生的后半期,她对生活的热情在消减。这样的人生轨迹,恰好是日本典型的M型女性就业曲线。在年轻时工作,婚后当家庭主妇。等到孩子长大,人生进入“思秋期”,重新就业,随着衰老,逐渐回归家庭。M型曲线最突出的,恰好是生于1947-1949年的战后一代。
中岛是在55岁的时候,家族停止了和服刺绣的生意,她来到了北白川的花之家。她选择护理的行业,在某种程度上,源于内心的愧疚。她是独生女,母亲年老后,和她同居。可是她缺乏专业护理的知识,不善于照顾,后来,母亲去世了。她继续照顾丈夫的母亲,那是一位很聪明的女人,妥善地处理婆媳关系,让大家庭融洽。可是,等她自己的3个儿子长大,日本已经进入了“核心家庭化”,她不再和儿孙共同生活。

左一为70岁的中岛女士。
在我对她进行访谈时,已经是上午11:50,另一位兼职介护士开始带领老人们做口腔操。领操者和中岛年龄相仿,在花之家兼职13年。长期繁重的护理工作,让她看起来相当健壮,而且手脚麻利,反应迅速。她声音响亮,嘴型夸张地带领大家唱简单的歌曲,念字母,同时舒张双手,做各种动作。有的老人仍然在垂头闭目,有些人能跟着活动一下,领操者会尽量带动她们。中途,口腔操会暂停,因为护工需要照顾某些老人上厕所。
口腔操完毕,就是午饭时间。穿着白色制服的厨师推着一个不锈钢的架子从电梯走出来,里面是按照人名分配好的日式料理。同样的食材,厨师根据护士的要求,做成多种状态,适合不同的吞咽能力。当天的菜有肉块、肉末和肉泥,青菜叶子,青菜泥,甚至豆腐也切成块或者碎末;主食有米饭,稀饭,或者半透明的大米啫喱。介护士在分配主食时,都要把碗放在桌上的电子秤上,根据每个人既定的营养表,确定分量。
宫田院长非常注重食物,对厨师强调精美和味道,要保证老人喜欢吃,吃得下去。她说,如果只有营养,没有美味,那么进餐就不是享受。食物要给人带来精神上的愉悦。对于食物的供给,她很自豪,反复强调她在这方面的理念和个体化的管理。
在进食时,老人的自理能力都不相同,有些人是需要喂食的。介护士麻利地给老人围上手帕,在双肩处用小夹子固定。小夹子是用布缝过的,外层是柔软的棉布。在喂食方面,宫田院长也制定了书面的规则,每次的勺子不能太满,等吞咽完毕,才能喂进第二口。在我身边的一位老人,一直处于半躺状态。他喝东西的时候,是用特制的喂食泵,用手一按,就直接从喉咙里进去,不经过口腔。

饭菜已经按照人名分配好了。同样的食材,厨师根据护士的要求,做成多种状态,适合不同的吞咽能力。

2018年5月10日花之家的下午茶点。

老人的自理能力都不相同,有些人是需要喂食的。

花之家的会客厅,员工吃便当的地方。
照顾老人们吃饭之后,介护士们才拿着从家里带来的便当到一楼餐厅。吃完饭,翻阅一下杂志,这是她们可以缓口气的一个小时。
下午1:30,她们重新回到楼上,准备2点钟的“被动操”。这些体操都是宫田自己创立的,我跟着做了20分钟,发现动作虽然简单,可是对协调能力要求很高。在领操者响亮的节奏中,其他介护士配合着帮助老人们一起活动。那位从滋贺县过来的姐姐一直喊,“我不会,我不会,你们教的,我都听不明白。” 一位介护士走到她的身边,蹲下来,握着她的手,轻轻念着节奏摇摆。当老人可以自主活动一下时,领操者就让大家给她掌声,鼓励她。

下午介护士带领老人们一起做体操。
下午2点钟,中岛开始照顾老人们念佛经,每个人手里握着一张打印出来的《般若心经》,跟着带领人一起朗读。宫田说,在日本,很多人信佛,佛经能让人缓解情绪,心灵安宁。有时候,老人会和同伴闹情绪,哪怕读不懂,当成音乐去感受,也会有帮助。在花之家楼下的走廊花园,她也摆了祖母曾经供奉的观音菩萨像。她说,那会让老人们感到亲切,有家的感觉。
半个小时后,介护士从厨房搬来下午茶。当天是自制的橙子布丁和咖啡。老人们在自己的宿舍休息,陆续自己推着助行车出来,或者需要护工推轮椅。在休闲的时间,尊重各自的节奏。精细的护理制度,源于宫田在医院长达20年的护理经验,和近乎苛刻的管理。
中岛每个星期来3天,其余的时间仍然可以照顾家庭。照顾失智症老人很辛苦,责任重大,她说,工作有多充实,精神就有多紧张。这份兼职,她已经做了15年,每天的酬劳不如全职护工。打零工,时间灵活,报酬偏低,是日本主妇重新就业的主要状态。有些主妇在30多岁,孩子上学之后就重新就业,而她是55岁才加入,体力不能迎接更大的挑战。相比于以前的主妇生活,她更喜欢出来工作,是前半生没有的自由。
5
宫田院长严厉的个性体现在一切细节。早晨初会面时,她皱着眉头看了一下我身旁的年轻翻译,用手指了一下她肩上露出的黑色胸带,还有膝上短裙,直言不讳地说,这样的打扮会让高龄者感觉不敬。
5月10日,我从早上九点半就开始呆在花之家,到了夜晚7点,我实在太饿了。本来想去旁边的便利店买个面包就回去继续采访,可是一念之差,我决定去餐馆吃顿肉。吃肉误事,赶回花之家时,已经是晚上8点半。 值班的护工马上给宫田院长打电话,说我终于回来了。宫田院长在电话里生气地责备我没有赶上介护士哄病人睡觉的环节。她骂了有20分钟,说她安排了介护士在等我,我竟然去了那么久。我请求她再给我一个机会,找时间让我再去观察夜里的护理。她拒绝了。
5月11日早上,是我们约定的第二次见面时间,她要“反采访我”。她问我,中国也步入老龄化社会,中国人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我说,在中国,无论政府还是社会都尚未建立应对体系,甚至在意识上也还没反应过来,在不久的将来,就会变成非常棘手的困境。她很自豪地说,在她的机构里,老人可以得到非常专业的,人性化的照顾。不过,她也承认,就算在日本,很多人在理念上还不能接受机构养老,更加依赖医院或者情愿呆在家里。他们都认为,在医院,老人是最安全的。
在国内劳动力短缺的情况下,日本政府又没大幅度开放国外劳工的市场。缺乏渠道和法律的支持,她很难雇佣国外的介护士。她问中国的临终关怀做得好吗?我说,只能说在起步的阶段。她很认真地说,希望这篇报道能传达她的心意,欢迎中国的优秀人才去她的花之家接受培训,有住宿的地方。她愿意传授临终关怀和介护的知识和经验,但是只针对有志于当领袖的高素质人才。这些人才回到中国,可以带领临终关怀的行业。她反复地强调,她的时间不多,耗不起了,如果只是为了个人谋份职业,请不要来了。她希望有一天,有机会亲自去中国挑选合意的培训对象。她说,“无论是为了日本,还是中国,这样的交流是互利的”。
15年前,宫田的女儿西原女士在大学毕业后就去医院工作,积累了看护经验,女继母业,担任花之家的副代表,管理日常的工作。她觉得这份工作是对人生命的最后护理,责任非常重大,在和病人以及病人家属签约时,都要充分沟通,获得十分的信任。唯有信任,家属才能相信她们在危急关头采取的专业措施,即使发生意外,也不会责备。对于理念不一致,不信任,甚至犹豫的家属,她们都情愿拒绝接收。

宫田院长和女儿西原。
当我说,作为女儿,她正在坚守母亲的事业。听到“坚守”这个词,她和母亲对视而笑。她说,最初,她其实并不是那么喜欢,后来,慢慢地,就觉得这算是一份不错的工作。也幸好,她嫁给了一位“好男人”,理解她,支持她在生育之后仍然继续工作,并且对家务的质量不挑剔。
在采访的最后,我问宫田母女,那天送走103岁的老人是什么心情?她们说,是解脱,“那位老人在花之家住了17年,走的时候很平和,面容慈祥,很漂亮,像花一样。”
善养传媒——为中国一流养老服务
文 | 罗洁琪

善养传媒致力于老龄全产业链的品牌策划与整合营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