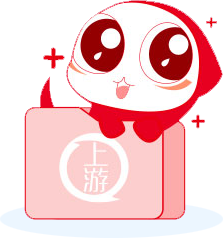

养老院“阿姨”的无奈与妥协
 善养传媒
善养传媒


2016年夏天,我来到江苏省南部的一家养老院开始博士论文的田野调查。当我换上护理员穿的连身白大褂从值班室出来,几位老人便纷纷询问:“这是不是新来的阿姨?”
我所在的这家民营养老院成立于2009年,共有三百多张床位。一到五楼是双人间,有点像上世纪90年代的招待所,两张床对着一台电视机。这里的老人大多可以依赖扶手或者拐杖自主行走。六到九楼住的都是重度失能和失智的老人,需要24小时的看护。一个房间里有五到六张床,床头有呼叫铃、供氧端,床与床之间用粉色的塑料帘布隔开,看起来更像医院的病房。通常,当一个老人大小便不能自理,他就得从楼下“升级”到楼上。
阿姨们分组日夜轮班,两个日班一个夜班后可以休息一天,上夜班的时候每两个小时得巡房一次,所以通常只能在值班室打个盹儿。因为照顾工作的特殊性,他们也没有节假日可言,如遇病假或事假则由班长安排调班。楼上做全护理的阿姨每个月拿2700块,比楼下多200块——他们把这笔钱称为“肮脏费”。
这两年,新入住的失能、失智老人越来越多,四、五楼也都逐渐改造成了护理型床位,但养老院仍然一床难求,想要住进来多少还得托熟人、找关系。根据全国老龄办、民政部、财政部2016年联合发布的第四次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抽样调查结果,中国失能、半失能老年人约为4063万人,占老年人口总数的18.3%。对这部分家庭来说,专业的长期照护是一种刚需。
清洁是工作的第一要务
养老院的负责人蒋院长告诉我:“我对环境比较看重。原则上,我要求做到没有味道。不像有的养老院,走进大厅就‘轰’一阵。”家属们评判一家养老院照顾质量的标准,首先也是看它“干不干净”,“有没有味道”。
阿姨们的工作节律围绕老人的一日三餐,除此之外,最主要的任务便是“清洁卫生”。一方面要维护空间的清洁,扫地、拖地、抹桌子、清理床铺,另一方面更要时刻保持老人身体的清洁。
如果一个房间有六个重瘫在床的老人,“没有味道”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比如,要协助无法自理的老人起床大小便,及时检查、更换尿布和集尿袋,每天帮老人洗澡或擦身子,长期卧床的老人则需定时翻身以免得褥疮溃烂。有的老人包着尿布不舒服,常常下意识地撕扯,大小便就会沾染整个床铺。这个时候阿姨得把老人推去卫生间冲洗干净,再请隔壁房间的阿姨一起帮忙换床单被褥,铺好两层隔尿垫,这一趟下来就得花费近半个小时。
失能和半失能的老人因为失禁的大小便,口腔和内脏问题所导致的气味,乃至衰老和濒临死亡的意象,成为需要被清洁和隔离的“污染源”,甚至连老人的家属也认为他们是“肮脏”的。
89岁的高好婆肠癌晚期,常常难以控制自己的大便,沾到裤子和便桶上。一个周末的上午,高好婆正坐在自己的桌子前吃点心,她的儿子、孙女带着三岁的重孙子一起前来探望。小朋友好奇地四处走动,时而翻翻老人桌上的东西。这时老人的孙女,这位年轻的母亲,再三叮嘱自己的儿子:“老太太含过的东西囡囡不要含”。坐了没多久,这位母亲在临走的时候又叮嘱:“囡囡洗手”。
另一次,一位老人的女儿请我吃她带来的茶叶蛋。当时我刚吃完午饭不久,便谢绝了她的好意。没想到老人的女儿立即向我解释“这个干净的呀”。她几乎下意识地认为我的拒绝是出于嫌弃,才会马上说明这并不是老人吃剩下来的、“受过污染”的食物。
老年人的“肮脏”既与实质性的生理变化有关,同时也是象征性的。在以创造财富为驱动,标榜健康与生机的现代社会,衰老的生命一旦丧失生产性的潜能,往往会遭到社会秩序的排斥和贬低。
近年来,多个城市发生规划中的养老机构被附近小区居民抵制的事件。养老院与垃圾焚烧站、变电站、化工项目一样,成为中产阶级“邻避运动”的对象。抵制者认为老人聚集会给小区带来不利影响,比如医疗污染、丧葬噪音或者某种抽象的“晦气”,甚至宣称老人院是“死人院”。即便政府反复协商对话也无法得到居民的谅解,多个项目因此搁浅。“危险”、“晦气”的老人似乎理应被排除在城市空间之外,生活在一个隔绝的、不被看见的边缘角落。
因此,养老院的阿姨所面对的不仅仅是实质性的肮脏,比如处理大小便,清洁身体,也是社会象征意义上的肮脏。
每天与受社会排斥的老人打交道,让他们蒙受污名,照顾工作所包含的专业技能和身心劳动也遭到忽视和贬低。
虽然社会对专业护理员的需求越来越大,但养老院却一直面临着招工难的问题。“就像你去做清洁工,大家还是有歧视的眼光在里面”,蒋院长说。
“他们的神经像时针在转”
养老院的阿姨和家属都感慨,现在的“老年痴呆”不知怎么越来越多。
我们通常所说的“老年痴呆”其实并不是衰老带来的正常退化,而是一种疾病现象,主要包括退化性失智症(最常见的即阿兹海默症)和血管型失智症两大类,有时脑部肿瘤、营养失调和新陈代谢异常也会引发失智的症状。
失智老人会产生认知、语言和行为障碍。比如九楼的朱爷爷好像生活在另一个时间和空间里,把照顾他的阿姨当成“隔壁邻居”,阿姨帮其他老人换尿布则是“拆机器”,走路的时候常常提起脚来跨过一道一道隐形的门槛。但朱爷爷却还记得年轻时援建新疆的点滴,告诉我“新疆的棉花好,没有洞。棉纱都有级数,级数越大越好,还有精纤普纤,精纤摸上去滑一点”。朱爷爷喜欢偷溜出房间,念着要“回家”或者“上北京”。阿姨没办法,出门拿药、热饭都牵着朱爷爷的手一起去,像牵着一个小朋友,晚上睡觉前则得把他的手和脚都用约束带系在床栏杆上,以防他半夜爬出跌倒。
阿姨们常常像哄小孩一样哄老人,“乖囡,睡觉”,“快点吃,跟那个老太太比赛”,有时则需要威吓,“不要哭了,再哭去喊护士打针了”。
不过这样的老人在阿姨看来还属于“乖”、“听话”的那一类,养老院中也有为数不少的“麻烦制造者”。
八楼的邓好婆今年 80岁,行动无法自主,有失智的症状,几乎每隔20分钟就会按床头的呼叫铃要求起床小便,有一天夜里甚至按了90多次。同房间的老人抱怨她“像发电报一样啪嗒啪嗒按”,“不是真的小便,是脑筋小便”。阿姨们常常劝导邓好婆“不急就不要按铃”,“阿姨心里有数,一两个钟头会叫你小便”。邓好婆每次都道歉“是我不好”,可是依然如故。
一天上午,邓好婆又连续不断按铃要求起床小便,不断哀求道:“好阿姨,求求你,你让我上(厕所)”。范阿姨有些生气了:“你又打铃!今天我不依你了,现在我要当坏人了。人家正常的是一天几次,你这样的就是假小便。我们是够好心了,好婆,你也不能这样的,你这种属于软折磨阿姨了。都像你一样,阿姨一天到晚兜圈圈,就一直弄这几场小便了。”
事实上,一个阿姨要同时照顾同房间的五六名老人,如果每次都顺应邓好婆的要求,势必难以负荷。把老人抱起床大小便其实是一项非常耗费时间和体力的工作。如果我们单独看到阿姨回应邓好婆的那一幕,或许很容易认为他们“冷血”、 “缺乏爱心”。但若深入这一环境,便会发现在养老院令人疲累、身心耗竭的照顾劳动中,阿姨们在很多情况下不得不发展出自己的一套情境界定,比如在他们认为正确的时间协助老人大小便,其他情况下则是老人“乱讲话”,因此“不能当真”。另一名护理员张阿姨对此曾有一句比喻,她说:“他们的神经像时针一样一直在转,有时候搭得准,有时候搭不准”。
相应的,护理员便掌握了界定他们“神经是否正常”的最终裁量权,只有这样才能避免沉重的负担,协调好对多位老人的照顾,更重要的是,能够在伦理上正当化自己的行为,不必为忽视或拒绝老人的某些要求感到负疚或失职。
但长期照顾失智、失能的老人确实极易引发怨怼甚至暴力,就像一个阿姨所说,“在这里工作,有时候再好的脾气也要不好,(老人)说不听的。”
虽然我在养老院中没有亲眼看到,但护理员虐待老人的新闻不在少数。 2015年湖南省双峰县养老院一护理员持械袭击多名老人,造成九死九伤,因故意杀人罪被判处死刑。2016年,山东省青岛市某养老院的护理员在看护一名瘫痪老人的过程中多次实施虐待、殴打,致使对方骨折,被判刑七个月。几个月后,网络曝光江西一名男子在病房中咒骂、殴打自己 80多岁患有“老年痴呆”的父亲。而近年来各地居家保姆虐待、打骂老人的新闻更是层出不穷。
我认为,不能仅仅把这些现象视为照顾情境中出现的“异常”或“失控”现象。事实上,无论是老人还是婴幼儿,当他们的一举一动,乃至大小便这样最私人化、最基本的生理过程都需要他人的协助时,这种“无微不至”的照顾同时也意味着全方位的“受制于人”。由于身体的脆弱性全部向他人敞开,所以照顾关系本身就潜藏着伤害的可能。
在谴责个别施虐者的冷漠与残酷之外,或许我们更应该思考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照顾环境才是可以培育关爱与同情的。“ 我们这种年纪的人”
在我进行田野调查的这家养老院中,共有护理员50多名,全部都是女性,年龄大多在40到60岁。有的在工厂流水线工作多年,因为身体难以负荷而改行。有的从国企下岗后从事过饭店服务、客房清扫、超市促销等工作。这些私营经济部门往往不交社保,工作时间过长也是普遍情况。但是阿姨们由于有限的受教育程度和职业技能,即便转换工作也难有社会上行的空间,只能长期被局限在性质相似的低端制造业、低端服务业的轨道上。
46岁的章阿姨曾在工厂车间生产纱管,一早五六点钟就要上班,夏天甚至提前到三四点。纱管本来只是一个硬纸板,要通过流水线“上浆”、 “喷绒”等工序才算成型。章阿姨负责喷绒,白色的绒粉“像面粉一样,比面粉粗一点,对呼吸不好的,也很肮脏的”。后来刚好听说养老院招人,“我想想随他吧,反正都是肮脏活,反正都一样的”。“像我们这种年纪正尴尬啊妹妹,念书没念多少,水平不行,好好的工作人家也不要你。随他吧,凑合到退休再说吧。”在章阿姨看来,绒粉与老人一样是肮脏的,对她而言两者其实是同一性质的“肮脏工作”,只是养老院的工作安排更为自主,不用受流水线作业严格的身体控制。
在养老院的阿姨中,更多的则是来自农村的老年女性,她们每月通常只有几百块钱的养老金,因此不得不继续从事劳动从而维持生活。
蒋院长告诉我,近年来应聘的阿姨九成来自农村,“为什么都是乡下的?这个是体制原因。倒过来说,正因为这个体制,才有这些阿姨来做。城里的都有劳保,最差厂里职工退休也有两三千块,她们就不一定高兴来做这个。但是乡下没有,她们必须要出来做。”
根据中国人民大学公布的2014年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资料,按职业身份来划分,各类老年人养老金的中位数从高到低依次是机关事业单位3000元、城镇职工2300元、城镇居民1070.9元,而农村社会养老保险金中位数仅为60元。同时,城市老年人生活来源依靠养老金的比例为71.93%,农村老年人的这一比例仅为17.22%。这些制度性背景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何在养老院中会出现60多岁的农村老年人照顾 80、90岁的城市老年人这一吊诡的情景。有些时候,前者同样体弱多病,同样需要照顾。但对他们来说,颐养天年的退休生活显得遥不可及。
我刚遇到68岁的邹阿姨时,误以为她也是住在这里接受照顾的老人。当时她的腰绑着很宽的束带,走路佝偻,并且不住地咳嗽。后来我才知道,她是毛好婆家另外雇佣的一对一的看护,每晚自备一张折叠小床,睡在毛好婆的床边。邹阿姨常常向我倾诉“命苦”的一生,“妹妹,我们命苦啊。像你们城里还好一点。我们那里乡下。你说有了气力怎么可能不去做。现在这样,我这种脚(撩起长裤给我看她双腿绑的护膝),痛到抽搐,我都还在做”。
邹阿姨告诉我,六年前刚开始照顾毛阿婆时,她常常受到家属的责骂和“考验”。“我呢是这样的,让他们骂去。到厂里做,老板娘也要骂的。做条裤子要受屁的,做个人么要受气的,随他去。他们有的时候叉着腰大骂,我不响的,骂了就骂了。话说回来,妹妹,我看在铜钿的面子上!我这么几岁了哪里去弄这么多铜钿!”
经过多年的照顾,毛好婆一家逐渐建立了对她的信任和依赖。2016年,邹阿姨声称要去亲家母女儿开的厂里工作,“那边每个月3600”。毛好婆的儿子当即决定把她的工资也加到 3600,但是“他们现在把钩头(600元)留住了,要她过世才给我。他们怕我走,要看到她老死,等她上了铁板,吃了素饭,然后付清。”2017年年初,当我回访养老院的时候,听说毛好婆已经于几个月前过世,邹阿姨只能返回乡下老家。但她仍然常常打电话给养老院里认识的阿姨,请她们帮忙介绍工作,希望能回来继续当保姆。
2017年末,《这不是笑话:阿姨改变了中国》一文曾在网络引起广泛讨论,专栏作家张明扬在文中写到:“阿姨,这是一种转型时期普通中国家庭所能享受的中国特色福利。”
事实上,中国当前的社会养老体系正是嵌入在既有的社会不平等结构中,依赖一群在社会转型中处于弱势地位的中老年女性提供相对可及的养老服务。
“阿姨”们为那些不再具有生产性、甚至可能成为“社会问题”的失智失能老人提供照顾,也使得大量家庭得以卸下沉重的养老负担,但他们本身却难以得到相应的生活保障和社会支持。这不仅有违公平正义,同时也是难以持续的。
随着中国未来人口结构的改变,老龄化程度愈深,护理员的缺口势必越来越大。未来的照顾资源将如何进行分配?这个社会将依靠谁来提供照顾?当现在的这群“阿姨”逐渐老去,等到他们面对自己失去自理能力的那一天,谁又来照顾他们?这些恐怕都是将来难以回避的问题。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本文根据作者的学术论文《“脆弱”的照顾:中国养老院中的身体、情感与伦理困境》改写,该文刊发于《台湾社会研究季刊》第110期。)责任编辑:董怿翎 澎湃新闻,未经授权不得转载。新闻报料:4009-20-4009
善养传媒——为中国一流养老服务

善养传媒致力于老龄全产业链的品牌策划与整合营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