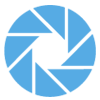文/苏磊
时间冲淡了记忆,少时在铁南的生活印迹,就像雨中渐行渐远的汽车,模糊在我的视野中。搬家离此已经将近二十年,我与铁南成了平行线,似乎这里的一切,将不再与我产生交集。一次偶然,零星的回忆碎片,又拼凑成了完整的板图,溯洄的时光,再次在脑海浮现。

几天前,到铁南的亲戚家中吃过晚饭,亲戚打算开车送我回去。我不肯,希望借此机会散散步,欣赏丹霞映衬下的美景。就这样,我闲庭信步,循着笔直的柏油路向西而行。已是黄昏时分,多情的夕阳带着对月亮的眷恋,占据着半个天空,迟迟不肯离去。周边一抹纱云,红透的可爱,似流彩的帔帛,飘动在天际。
迎着落日的余辉,我走到了桥边。在桥的东侧有一间低矮的平房,淡蓝色的外墙,在岁月的剥蚀下,已经斑驳褪色。破损的门窗在风中摇曳,显得孤独而无助。房墙两旁爬蔓的蒿草,诉说着昔日的沧桑。
时过境迁,此番重游旧地,我的心中五味杂陈,竟藏着许多的感慨。其实平房之于我的印象,也不过是浮光掠影一般,然而当我再次看到它,记忆的底片开始重新翻拍,那个人又出现在我回忆的照片里。

他是我人生当中的一个过客,却似一颗流星般,在我的脑中划过记忆的弧光。那是一个星明月朗的夏夜,爸爸急匆匆地从外面走了进来,他告诉我穿好衣服,和他出去吃饭。凭着以往的经验,我知道爸爸没有做饭,一定是有货物要准备装车运走了。
我一边系着鞋带,一边抬头问他要和谁吃饭?爸爸并没有回答我,只是催促我快一些。爸爸当过兵,军人雷厉风行的作风,深深地影响着他。所以无论做什么事,爸爸都是干脆利落,从不拖沓。时到今日,我也常常暗想,爸爸这么优秀的品质,我怎么没有学来呢?
吃饭的地方就是桥边那间平房,拥挤的房间摆着四张桌子。一条仅够一人穿行的过道,将桌子均匀的分成东西两部分。过道与外门、厨房,形成一条线,老板满面尘灰的在厨房里来往穿梭。他那忙碌的样子,简直像个陀螺。

我们在靠窗的位置坐好,爸爸给我点了我爱吃的烧茄子,接着他又点了土豆片、锅包肉、干炸花生米,又要了一缸散酒和二斤半饺子。当时看到爸爸点了这么多菜,我本以为会来几位叔叔,可是等了一会儿,只见到一个人掀起门帘,向我们走来。
爸爸看到了他,站起身来相迎,将他请到对面的座位。接着他告诉老板,人来齐了,可以炒菜了。听到爸爸的话,我的心中充满了好奇。我对自己和爸爸的饭量了然于胸,这么一大桌子的菜,那个人能吃得下吗?
带着怀疑的兴奋,我开始注意身边的这个人。他穿着一件深蓝的粗布短袖,就是搬运工人夏季常穿的,我的理解这身衣服也是这个职业的标志。他的头发短而齐长,且是一头银发,用蒲公英来比喻,应该很贴切。额头满是皱纹,这是岁月大师风刀镌刻的杰作。浑圆的脸上,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深嵌在凹陷的眼窝中,放射出坚毅的光芒。
看到我在注视他,他显得很窘,问了我一些家常话。我本对他饶有兴趣,对答起来,也算是知无不言了。很快我们之间畅快的交流,令他展颜欢悦,当菜上齐之后,他的喜悦更是溢于言表。
他一边喝酒,一边与爸爸畅聊着装货的事情,我无从插言,只好在一旁静听他们的高谈阔论。这位伯伯很贪酒,我只见他斟饮,却没见他夹菜。爸爸也劝他这样喝法,对身体不好,他说这是他喝酒的习惯。不把酒喝完,他是不会吃饭的。

在时间的见证下,他杯中的酒终于喝完。酒酣意阑的脸上,泛着红润之气。我想这个时候,他该兑现承诺,拿起筷子,将这满桌的菜一扫而光了吧。他没有辜负我的期待,手不停歇地将饺子送进嘴里,看到他风卷残云一样将菜一扫而光,我觉得他的嘴就像深邃的黑洞,吞噬着周围的一切。酒足饭饱之后,他冲我和爸爸打了声招呼,便消失在茫茫夜色之中。看到他走了,我对爸爸说:“刚才那位伯伯,饭量可真大。”
我的话传入爸爸的耳中,并没有让他觉得好笑。他二话没说,领着我到对面的货运站去了。在站台上边的铁道上,我看到一节货运车厢停靠在那里。几个搬运工人,借着灯泡的光亮,正忙着将站台上的麻包装运上车。那位伯伯也在其中,只见他将沉重的麻包扛在肩上,迈着坚实的步子走向车厢。他干活极认真细致,麻包卸下都是轻放在垛上,一摞一摞地叠加在车厢里,非常的平整。这样干活,对于一个花甲之年的老人,真的过于残酷。我心看了,十分的难受。见我在一旁观看,他笑着对我说:“孩子,这里脏,你退后一些。”
接着他又嘱咐其他的工人,也按他的样子,装卸麻包。他来回的奔忙着,发现有破损的麻包,他就用袋线将它缝好。汗水已经透湿他的衣衫,可是他仍然不知疲倦的扛运着麻包。
汗水浸透了他的后背,泪水却充盈我的双眼。这位伯伯用坚忍的信念撑起生活的艰辛,用一颗诚信之心,立足于社会。朴实、善良、坚毅,正是中国工人的写照。
图/图虫正版共享图库
文/科尔沁书虫融媒体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