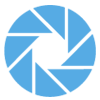近日,徐冬冬受邀成为星月SHOW第63期封面人物,并接受其专访,本期摄影王靖,采访&撰文黄馨月,以下是采访全过程:采访前,我问了身边很多人,“你知道徐冬冬吗?”得到的回答大意相同:“就是那个《余罪》里的大嫂吧?”《余罪》确确实实把她推到了观众面前,让众人记住了这么一位既稳重、强势又有些性感女人味儿的“大嫂”,本名徐冬冬。
当我见到这位网传中的“性感大嫂”,她正从车上下来,穿着黑色利索的运动服,套了一件黑色的休闲大衣,米白色的袜子和运动鞋随意舒服地踩着。眼前的这位素颜、面净的女生完全不是网络标签中的模样。
那天她感冒了,实在忍不住的时候才咳出一两声来,闲聊的话也不多,安安静静,沉沉稳稳地换衣、梳妆、拍摄。你知道她对你是亲切的、随和的,她不动声色地买了咖啡叫你来喝,她体贴所有一起工作的人员,但你又隐隐从她的不苟言笑中能觉察出一种冷冷的气场。

等所有的拍摄结束,我们上二楼采访,天已经开始黑了,人群散去,四下安静。她给自己补补了妆,提醒相机的位置可以高一点。
我们对谈的一个多小时里,能感觉到她收起了很多话没有讲,可能是觉得没必要。北漂的故事千千万,她能被众人知晓,已觉是幸福。少时追求“出名要趁早”,最后发现人生求的不过一份“爱与安定”。比起名利场上的鲜花和掌声,此时此刻,一碗热汤面里的“幸福感”,于她才是最重要的。
“性感”这个定位,我能吃一辈子
大学快毕业的时候,徐冬冬觉得自己做演员肯定不行,便转去当经纪人助理。“挑了一个离梦想最近的工作,就觉得看着这个梦想,看别人怎样实现梦想,也是一件很开心的事儿。”后来开始慢慢做群演,端茶倒水,充当剧组的搬运工,“那个时候就想让自己露脸,没准哪个戏就能给你一个机会,你预测不了的,好多东西。”

像浮萍一样,她在试戏、跑剧组间来回打转,没有方向,也看不到起色。有一个故事她讲过很多遍:有一次去试戏,导演让副导演赶他们走,具体的情景模糊在记忆里,但那种“我们低他们一等”“不尊重人”的感觉清晰地印刻在脑海里。她转身想跑下去,结果是从楼梯上直接摔下去的,“腿青了。”她轻描淡写地讲,她说:“这些其实都是很好的经历。”只是自那以后,她再也不想舔着脸不停地去跟别人推荐自己。
期间她还走过“中性风”,因为一个跑龙套的角色要求短发,经纪人直接呵斥她:“你剪不剪,你说一句话,你不剪,换人!”她剪了,剪完之后走在成都的大街上,兜里也没多少钱,“我觉得自己的头发自己都做不了主,自己也没有话语权,什么都说不了,只能照着去做。”那一刻她在孤独之外,又一次深刻领悟:“真正能依靠的只有自己。”
多的故事她就不再讲了,我在她一米开外的地方,看着她那双大眼睛,只能靠从市井听来的零零碎碎的有关演艺圈的不易故事,想象她当时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白眼,人性里改不掉的趋炎附势,她是有多深刻的领教,才那么激动地说:“我自己请的工作人员我绝对不会,我特别注意这一点,我特别注意这点,我自己请的工作人员,我以前收获到了难过,我绝对不会让这些难过,在我自己请的人身上发生。我觉得这是不对的,这个方式就是不对,不专业。”

后来她就参选足球宝贝,尝试拍了一些“性感照片”。我不知道如果没有人提醒她,她是否知道依靠自己的身材原来可以闯出一条路。还是说,她知晓,但不愿意。“周围很多人跟我说‘太low了’,我爸我妈一直都不开心。”但“性感路线”的确让她有了一点自己的定位,“起码有人开始找我去试镜了,而不是我要每天敲着门去试镜。”
拍摄时,有一套紧身的礼服短裙,间隙她偷偷把右肩上的一缕长布拉了一角掩在前面。她会不好意思,会尴尬,但更在意的是别人会不会尴尬,会不会很不开心。“所有人都以为我很随便,是很不好的人。”哪怕她什么都没做,影视创作里的性感形象,也让她在这个受儒家思想熏陶的民族里,难以找到身份认同。
她说服自己说:“只要我没有去骗人,没有去坑人,没有做任何伤天害理的事情,我不吸毒,不犯法,我觉得我可以试着改变一下,看看有没有机会”。“但是你一旦走上这样的路,再换风格的时候可能就特别困难”。

“对,但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个坑,先把自己的坑占住了再说。其实这一辈子你只要能在一个领域,或者一个平台,哪怕一件事情上有一次成就,这一辈子就算是成功的。有的人一个代表作品真的能用一辈子,或者是一个定位,你也能吃一辈子。我是觉得不用非要去做什么改变。”
“你觉得这个定位你能吃一辈子吗”?“能。你只要好好做,你用正面的能量让它更加完善,更加大众化,更加让大家能够理解就可以”。当然这个过程中她也有反反复复挣扎的时候,“一直感谢,一直开心,也一直难过,一直痛苦,都有。”她会不停地克服自己。现阶段就希望:“尽全力地能够在大众接受的范围内,做自己。”
我不行,我行

“你不行”这三个字对徐冬冬而言,就像是一句紧箍咒,但凡要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它就会被念起。“三岁看大,七岁看老。”这句老话,她以前不懂,现在深信不疑。三四岁时,母亲把她送到少年宫学舞蹈,经常被老师说“跳得不好”,每次排舞她都被放在边边角角的位置;七八岁时,母亲就把她带到北京读预科班,只希望她的人生能比别人都快一点,再快一点,“能早一点有成就”,“她觉得我22岁时就应该很成功了。”徐冬冬曾对媒体这样讲述母亲。
母亲对她的教育方式是“激将式”的,甚至有点“恨铁不成钢”。“她现在就什么都是我好,以前我什么都是不好。”但她不怨母亲了,那些家常便饭般“使劲跺脚、闹、喊叫”的激烈争执埋进了成长记忆里。
“我到现在都还有不自信的一面。”但她每一次会把周围人身上强大、自信的气场吸收一些到自己的世界里,在人生的经历中重新累积自己的自信值。母亲严厉的言传身教,也在潜移默化中深刻影响着徐冬冬的性格养成:要强,事业心,有一股韧劲。“一生她哪怕到八十岁,她也要干自己想做的事情。”
她没有完成母亲“趁早出名”的心愿,但现在“她觉得我知道自己要做什么,这一点就是一步成功,她就觉得够了”。“她现在老让我多休息休息,别那么累,反而我变得更加工作狂了。”

2016年,《余罪》播出,带给她从未有过的关注度,“余罪”和“大嫂”成了大家在介绍徐冬冬前的加注;与此同时,她的负面假新闻也扑面而来;对她演技的否定和肯定一样的多。后来,姥姥脑溢血做了手术,爸爸的心脏病犯了,一直在剧组照顾自己的大姨也突然间气胸,要做手术,所有的事情积压在一起,每天她要靠安眠药入睡。“那个时候我还不想没有工作,因为我家庭不是很富裕,需要我照顾。所以手里的工作也不能放,家人也不能马上回到他们身边。”
熬过了这段痛苦的日子,她的想法变了。“以前肯定会把事业排在最前面啊。”“上大学那会儿,家里给多少钱就买多少打折的名牌,一天恨不得换两套,那个时候就想搏关注嘛。”现在“十天换不了一套衣服”,生活优先级的排序也变成父母、爱情、事业。

“你太忙了,你太优秀,你太好了又能怎样?有一天你身体不好,连跟家人在一起吃完热汤面的时间都没有,有什么意义?”她现在谈及更多的两个词,一是“做自己”,二是“幸福感”。她说:“以前在积累能力的过程中做不了自己,但是要有那颗心,现在觉得还是幸福感最重要。要有自己的事业,同时要知道自己是谁,家人是谁,爱人是谁,生活本来该怎么样还是怎么样,不能脱离这些。”
她很向往郑爽的生活方式,“我感觉她就是在做自己,她参加发布会也不怎么化妆,脸上哪里有伤,贴上布她就出去了”。小时候总以为自己一定要“活得更精彩”,一定不能“像父母”一样,长大之后发现“还是有相像的地方”。
“你觉得相像好还是不好?”“好吧,有一种骨肉相连的感觉。”“我的感情里会看到他们的影子。我另一半的性格有些会像我爸爸,喜欢煮煮饭做做菜或者钓鱼那些,过简单的小日子那种。”

她说自己现在还有一个梦想——做一名喜剧演员。她慢慢发现自己在喜剧上“挺有天赋的”,参演《西虹市首富》让她在喜剧上有了一大提升,她的性感在影片中最后都走向了一种喜感。
上大学时学的话剧也是喜剧方向,但那时候爱玩、成绩不好,《西虹市首富》的导演之一是曾经同学校的大师哥,“他们疑虑我可能演不好,但又觉得我的型是适合的。”接演之初,让她试了好几遍戏。行动证明,她可以。
2019年4月12日,《最佳男友进化论》终于上映,在这部开拍于2016年的电影里,徐冬冬扮演了一位戴牙套、架眼镜,相貌平凡到甚至有些丑陋的女生。她说这个角色很贴合她,普普通通、平平凡凡,一路默默付出,最终从一个“丑女孩”蜕变成“女神”,她也在电影外的真实人生中,从千千万万名群演中的一员成为了今天独一无二的“徐冬冬”。

她说:“一定要好好地去做一些自己想要做的事情。”她不太在意别人觉得她火与不火,过得好与不好,偶尔负能量爆棚,就去运动,给自己一个安静的空间。“我会多想的事情,每个人都有,我这样算什么?而且坚持不下去的时候,我总觉得再坚持一下就会往前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