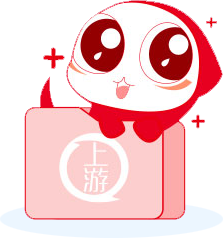

上海话演《繁花》,金宇澄不担心有障碍

《繁花》能感受到“时光”。 主办方供图

舞台剧《繁花》基于原作基础上做减法。 主办方供图
舞台剧《繁花》改编自金宇澄创作的同名长篇小说,主要讲述生活在上海的阿宝、沪生和小毛三人跨越三十余年的成长经历与离散重逢。作为第九届茅盾文学奖的获奖作品,导演王家卫曾对原著一见如故,形容“阅读《繁花》像是经历了一生一世”。
2018年1月,在上海美琪大戏院首演引发轰动后,《繁花》舞台剧终于要登北京舞台——6月21日至24日,北京天桥艺术中心上演。
为让观众快速了解这部大体量小说从而更好“入戏”,剧组邀请到《繁花》的忠实读者梁文道、俞飞鸿、史航、向京、吴琦,与原著作者金宇澄展开对话。同时,新京报记者在会谈后独家专访《繁花》舞台剧导演马俊丰与编剧温方伊,解锁了经典改编背后的创作细节。
小说 《繁花》
创作缘起于“时间的刺激”
史航:你观察到了什么样的世界,让你决定来写这样一个小说?
金宇澄:这个小说最主要给我的深度刺激就是时间。我在写这个小说之前的一个月,经过上海一条马路,遇到一个老女人在摆摊。我仔细一看就吓了一跳,她就是当时七十年代静安区最美的女人,就像《西西里的美丽传说》这种。但是过了四十年,她怎么会在这里卖小孩的褂子、鞋子?时间让一个我印象中这么好看的女人变成这样,非常残酷。这也勾起我很多对过去的回忆,尤其是六七十年代,非常有印象的碎片化的东西都浮现出来。
史航:我想起《繁花》中给我印象很深的地方。当时一个海员和他的同事们在远洋货轮上,忽然提起说现在床头都是谢芳的照片。《繁花》让我看到时光的魔法,让我们看到原来她在那个时候是这样地被人怀念和牵挂,像剥洋葱一样剥开,让我们看到欲望最初的形状。其实欲望本身一点不丢人。
金宇澄:实际就是时间的世俗化。《繁花》里有大量俗的故事,但是故事其实就是一个引子,让各种各样的声音来说话,各种层次的人说话,而且不做评判。我有意不写知识分子,因为我觉得其他人会更有意思。我们仔细描绘生活的世俗,用一种自然主义的方式罗列,其实是很有意思的。因为现在大家都有批判能力,可以用自己的角度来批判。
这是一个关于上海的寓言
俞飞鸿:有很多心理活动描写的小说会让我看不下去,但金老师很少去刻意描绘人物心理。小毛是这个小说里最主要的男主人公,你很少看到他写小毛怎么想,人物性格就在语言和行动中展示出来。同时,就像金老师所说,他不带个人态度,只是很如实地展示他成长环境中那些普通而真实的人的模样,不从大事件大情节开始,而是从这些人物来描绘出六十年代到现代、当代的众生相,这非常吸引我。完全从人物出发,这是小说好看的地方。
梁文道:这个小说让我印象最深的反而不是人物,而是整部书的调性。心理描写在小说历史上可能就是二十世纪之后才开始全面得胜的状态。在没有心理描写的时代,小说怎么样写呢?就是原来的寓言小说。我觉得《繁花》就是一个关于上海的寓言,这里有上海的调性和味道。我看整本书的时候,即便反复在看,头脑里面影像都很清晰,这个影像是一个在街道里面,有两排房子都会沿街伸出长长的屋檐,屋檐也许是铁皮或者幕布,屋檐下的光线介乎明暗之间,耗在那里面有点闷,但是你又搞不清楚那个光线是上午还是下午,是什么样的一种状态。这就是所谓的光阴或者时光。这种感觉又像我跟金老师提过的另一部电影,侯孝贤的《海上花》。
向京:《繁花》阅读体验非常惊艳,我没想到这个时代还有人这么写小说,这么去理解文学,我对他的写法挺感兴趣。德国汉学家顾彬有一个很严厉的对中国当代文学的批评,他说:中国人不省人,没有内心的描写。包括写一座城市,从来没有人真的很好地描写过一座城市。我觉得《繁花》确实没有什么心理描写,不是以这种方式去写作的,但我觉得《繁花》里面就是一个个的人,每个人都特别有意思,很真实。因为我也在上海生活过十年,我能听懂上海话。包括语言的调性,它会有一种质感。如果能听得懂上海话去看《繁花》,会特别有意思。我是通篇不由自主的用上海话在看《繁花》。我其实在上海的时候是非常不喜欢上海的。但是,《繁花》这个文本给了语言的感受,给了我可能在那儿十年都不能理解那个城市质感的感受。
舞台剧 《繁花》
改编:80后、90后团队让50后的我欣慰
俞飞鸿:对于《繁花》这本书,在我自己心目中,觉得改编太难,因为它的容量、跨度都这么大。电影、舞台剧都是有容量的,你不可能三天三夜的演。我好奇,不知道他们会从哪个角度,切取哪一块。
梁文道:我写剧本、做导演,做了很多年的实验剧场。改编这个东西到底难不难要从两方面来看,一方面是看戏剧导演、编剧,他想怎么诠释这个东西;第二,看我们金老师的量度有多大,《繁花》里面有太多的意象,如果我们把意象拿出来单独做,比如说饭桌,这要看原作者能不能容忍。
史航:沪生有一句台词:“人们不禁要问”。
金宇澄:我真的是没有态度。文学和戏剧还是不一样的,因为本身它给出的戏剧性不多,也就特别难改编。我记得王家卫导演跟我讲,你这个小说没有任何影视倾向。温方伊(注:舞台剧版编剧)在做的时候,我也是乐观其成的心情。尤其是我也有好奇,一个50后的老头子的东西,居然被80后、90后的团队改编,我也觉得这个小说特别有生命力。他们能够在这样一个老家伙的文字里面找到他们的动力。这可能是《繁花》作为戏剧的一种新的状态。所以说,我是挺支持的。而且我也觉得挺欣慰的,我就担心我的书就是我这代人在看,看完就完了。
语言:上海方言演出不是障碍,是加分项
吴琦:金老师,你的书也是从上海面向全中国的读者。现在的舞台剧两位都看过,当它来到北京的时候,你会有什么样的担心、什么样的期待呢?向老师的问题是,因为在北京我们很熟悉的是北京人艺的表演,你会不会看老北京戏剧?看完它们和这样一个充满上海味道的戏剧《繁花》时,你有什么样的感受?
金宇澄:到北京来做一个话剧,我一直非常纠结。我跟导演也讨论过,导演一开始就坚持说,要说上海话。我说非上海的读者怎么办?观众怎么办?担心观众会觉得不好。但现在的观众,实际上有非常强的读字幕的能力,这是我们上两代人都没有的,包括弹幕。实际上语言最能代表一个地方,我在写《繁花》的时候,用上海话的思维去写,困难至极,经常会跳到普通话语境。这种顽固的思维是非常的苦恼。但是,写到十万字以后,我慢慢的习惯了,什么话是写不出来的,要换哪一种方式。所以到最后变成了两大桌人一边吃饭,一边吵架。这些都是方言给予你的力量。我相信这是一个非常浓烈的地方特色。实际是给这部剧加分的。
向京:我赞同金老师,我觉得语言本身不是观看的一个障碍,至少不是一个最主要的障碍。因为这个故事发生的个人命运、集体命运,作为中国人都是可以理解的,况且它有那么强的故事感,你很容易卷入其中,是可看的。我觉得这种地域性的障碍还不如小说来的那么强烈。剧本身如果可看,到哪里语言都不会是障碍。
观众提问:《繁花》整部书里很少有上海话“侬”这个字,是特意规避,还是想减少一些符号化的东西?
金宇澄:“侬”这个字古文里面也有你侬我侬。“侬”这个字就是你。但是这个字不算常用,如果出现了这样一个字,一定意义上会败坏你的阅读感。所以,我考虑来考虑去。我要把它换掉,或者直呼其名,或者是转换人称。
新京报:如何通过舞台表现解决原著的文学性所带来的改编障碍?
马俊丰:在尊重原著的前提下,我们基本上只做减法,不做加法。
新京报:有读者会觉得舞台剧对于人物的塑造不够细化,失去了原著最动人的群像性和集体性,你怎么看?
温方伊:角色太多,对于观众来说也会造成一个非常大的障碍。在舞台上做群戏是很难的,尤其是每个角色都是有名有姓的时候,我只能说我尽了最大的努力。
新京报:如何在《繁花》众多的故事中选取、编排集中的故事情节?有没有在创作中想要留下但是却没有留下的角色?
温方伊:必须要有阿宝、沪生和小毛,因为这三个人是小说的灵魂。这三个人出来之后,其实我就别无选择了,只能拎他们的兄弟情作为主线。我觉得这并不是我主动去选择,更多的是一种必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