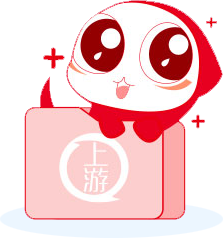

电视上看“球” 电影里看“城”
2005年初夏,一场重要的欧冠决赛即将在莫斯科卢日尼基体育场上演,对阵双方是西班牙的拉科鲁尼亚和土耳其的加拉塔萨雷。决战开始前的那个白天,一个英国女人被莫斯科的出租车司机坑骗,丢失了一切财物,她鸡同鸭讲着向附近居民楼一位热心老太太求助,并跟着去了警察局,在极其繁琐的官僚手续后,以旅行保险获得了全额赔付和紧急经济救助。老太太心满意足地打电话叫来儿子,正是打劫英国女人的出租司机。
以上情节,出自德国电影《欧洲的一天》。事实上,60余年历史的欧冠决赛上,从没出现过那两支二流球队,莫斯科卢日尼基球场倒是真举办过一次欧冠决赛,那是2008年,对阵双方是曼联和切尔西。这部有趣的电影,编造了一场不存在的欧冠决赛,在一天的时间框架中,分别以四个发生在莫斯科、伊斯坦布尔、柏林和圣地亚哥·德孔波斯特拉的不同倒霉故事,反映保险索赔的程序和在不同国家骗保的可能性,导演粗暴地划分出一道新铁幕,将讲规范的欧盟和乱七八糟的非欧盟分开,似在表达:买份保险进欧盟吧!
高考过后,四年一度的世界杯又到了。作为主场,那个让欧盟恐惧、提防和对抗的俄罗斯,会变得国际化和规范化吗?还是如同电影中那样,依然充满黑车司机和低效警察?这是德国导演在有意黑化俄罗斯吗?可当下那些片头都有着俄联邦文化部扶持的新电影,却大多丧到看不见一丝光明和一点希望呢。最近的例子,就是今年提名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的《无爱可诉》,一则莫斯科初冬绝望到底的寻子故事。
我们当然不能把电影当作旅行攻略和观赛指南,但也可以看看,11个全数位于这个巨大国度欧洲部分的比赛城市,在电影里都有过怎样的故事?这其中,高度集中了文化资源和重大历史印记的莫斯科和圣彼得堡,当然是最受电影人青睐的。而赛事举办城市中最没名气的萨兰斯克,实在抱歉,观影有限的作者找不出任何一部相关电影。
顿河畔罗斯托夫:《幽晦人格》
女导演安吉莉娜·尼康诺娃的处女作,就把背景设定在自己的家乡,一座破败的中型城市。危机四伏的林地、冷漠无助的城郊街道、破败逼仄的单元楼房、酝酿冲突的新型公寓,置身其间的主角,是破罐破摔的女人与无法无天的恶警,两人甚至发展出一段匪夷所思的虐恋关系。
城中没有一个好人,警车满街搜刮可供满足性欲的落单姑娘,餐厅服务员冷漠对待着顾客除消费以外的任何请求,受害女人在生日宴会上数落包括无能丈夫在内的一切亲友,制造出撕开一切虚情假意谎言的小高潮。女人在破烂街区意外碰上其中一名醉醺醺的恶警,正当摔碎酒瓶伺机于电梯间展开报复时,导演却不让观众痛快地引出彻底的反高潮。如同《她》中的伊莎贝拉·于佩尔,顿河畔罗斯托夫的这个年轻妻子,也把自己收拾干净,一遍遍交予罪犯(警察)。
加里宁格勒:《三天》
加里宁格勒是俄罗斯的一块飞地,与巨大的国土之间,被白俄罗斯和立陶宛隔断。而苏联解体过程中,立陶宛是第一个宣布独立的国家(1990年3月11日)。小国立陶宛著名导演沙鲁纳斯·巴塔斯的这部几近无对白的晦涩电影,就拍摄于独立初期。镜头下,两个立陶宛年轻男人来到凋敝的加里宁格勒河港,邂逅了两个俄罗斯女孩。寒风凛冽的初冬,从泥泞的港区堤坝到有着值班室的破旧单元楼,他们不言一语地寻找着可以睡觉的地方。
全片冷峻的气质,无疑让人想到北方不远那位芬兰导演阿基·考里斯马基,在他早期电影《坐稳车,泰欣娜》里也塑造了两个沉默的芬兰男人和陪伴他们的无聊外国女人。《三天》有着上世纪90年代同质化的昏黄胶片色泽,角色们近乎无意义的行为时间,为解体初期的建筑空间赋予可供读解的政治趣味。而镜中单人床上相依的萍水恋人,以及镜外单声道喇叭传来的舞会乐曲,又为分崩离析时代带来一丝温暖。
萨马拉:《驯火记》
热火朝天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苏维埃的电影人确实也带着满腔热忱,拍出一些深具艺术美学价值的正能量主旋律作品。《驯火记》的“火”,指的是火箭,电影开头是一次被叫停了的失败发射,总设计师安德烈脾气急躁地抱怨道:“卫星和人类都是我们最早送上太空的,现在却停滞不前,在和美国的竞争中落后了,实验台上做多少次都不如真正发射一次。”接着,灰心丧气的安德烈放假回到克里米亚老家,回想起自己儿时的飞天梦想。由《雁南飞》开创的情绪摄影,完美地用在闪回段落,少年带着自制飞行器,飞下山崖,俯拍镜头下的少女漫山遍野地狂奔,追逐着飞翔少年。
《驯火记》两个半小时的顺序时间线,都是安德烈实践大国航天梦的传记体故事。二战之前,他在克里米亚燃起玩具火箭;二战中,被紧急调往战备后方萨马拉的军工厂,主持完善喀秋莎火箭炮,却执著于上前线观察实战效果;战后,在科技与道德的思辨中,毫无意外地放弃家庭和爱情,选择与太空梦相依相伴,不停往来于哈萨克斯坦拜科努尔航天中心和莫斯科政治局之间。电影巧妙地摈弃了观众对社会主义建设劳模的想象,转而漂亮地塑造了一个科学狂人的立体形象。主角安德烈的原型,是苏联火箭总工程师谢尔盖·科罗廖夫。
下诺夫哥罗德:《沉默的灵魂》
战斗民族、酒精民族之外,或许还能给俄国人戴上另一顶高帽——忧伤民族。这其中,又以伏尔加河上游原住民芬兰-乌戈尔语族中的Merya人为甚。电影《沉默的灵魂》,通过带着一对百灵鸟的沉默公路旅行,以诗人Aist的视角,加之间错的回忆场面,算是完成了一次Merya人奇风异俗的展示。
“忧伤如同妈妈那样紧拥着我”,如此频繁出现的画外音,不断将族群和角色的忧伤日常化、正常化、浪漫化。上路的两人,是40岁的造纸厂摄影师Aist和更老些的好友企业主Miron。载着Miron的亡妻Tanya,他们从科斯特罗马州的Neya市行驶去下诺夫哥罗德州的Gorbatov,那里有一片湖水,是Miron和Tanya的蜜月度假地,也是Merya人相信的生命归宿。木柴燃起,身体成灰,归于河湖。一路上,坚强的Miron回忆着爱妻和自己情爱往事,他们的身体是那么契合,他曾用伏特加为Tanya洗身,如今却用伏特加引燃告别火焰。
再深的眷恋,也不妨碍河葬后的返程路上,跟同种族的两个好姑娘露水一夜,对于Merya人,“鲜活的肉体就如同奔流不息的河水”。即将回到家乡时,Miron平静道出知道好友与自己亡妻有过一段激情,冲进林地痛哭一番后,却相安无事,河水永淌。然而,这些俄罗斯人的先祖,是最需要被忧伤缠绕的民族,一场随即到来的意外车祸,还继续被画外音诗化着:“百灵鸟亲吻我们的眼睛,我们朝着母亲伏尔加河飞去,Miron去找Tanya了,我则看到了爸爸遗弃于冰河中的打印机,河水洗刷一切,包括我们Meyra人的痕迹,唯有爱无止境。”
叶卡捷琳堡:《暗杀沙皇》
这座位处欧亚分界线上的俄罗斯第四大城市,是罗曼诺夫王朝最伟大君主彼得大帝以自己妻子叶卡捷琳娜一世命名的。也是在这座城市,伊帕提夫之屋的地下室里,以最血腥的方式,终结了这个延续了300多年的封建王朝。
关于这段血腥历史,BBC拍摄过一些史料充分、讲解深入浅出的纪录片,纵深旷阔如《罗曼诺夫王朝》,具体到四个公主名媛的悲惨结局也有两集的《末代沙皇的公主们》。电影之父卢米埃尔兄弟,在1896年为尼古拉二世的加冕礼拍摄过纪录片,虽然并没留下处死沙皇一家的残酷影像,但却有后世电影人反复以不同的戏说方式,展现过这段历史。最值得欣赏的,是名导卡连·沙赫纳扎罗夫的《暗杀沙皇》,电影故事置于苏联解体伊始,一个精神病人宣称自己是刽子手,接下来,就在病患的臆想症和医生的自我催眠中,重构出一场独特的“重大革命历史题材”作品。
伏尔加格勒:《兵临城下》
说到这座城市以前的名字,斯大林格勒,人们都知道发生过人类近现代史上规模最大、最惨烈的拉锯战。从以前的苏联战争大片到当代俄罗斯的3D重拍,包括德国人视角的,美国人旁观的,关于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的战争片着实不少。但借助着明星和名导,最被人记住的应该是2001年让·雅克·阿诺执导的《兵临城下》,此片也曾以《决战中的较量》为名,在国内上映过。
高手间的狙击,本就是战争中最隐蔽、最生死未卜的部分,传递到成功的电影语言中,每每都能成为最让观众大气不敢喘的紧张桥段。法国导演如同一个操控拳击赛的经纪人,在给予正反两位选手充足表现舞台之外,熟练操纵着观众视野和心理,一会儿是红军神枪手瓦西里瞄准镜下的德军阵地,一会儿是纳粹狙击教头康尼瞄准镜下的瓦西里命运。让人紧张的客观镜头和给人命运主宰者身份的主观镜头,畅快淋漓地转换着。于是全片剧情,也像是观看一场苏德足球大战,苏联队先遣主力前锋瓦西里,连下对方几城,德国队见势不妙,立即调兵遣将,换上大将康尼,并几乎逆转局势,直至加时赛,被金球制胜。不过,这部电影并非在今天的伏尔加格勒取景,而是由德国波茨坦巴伯尔斯堡制片厂搭景“扮演”。
索契:《伊卡洛斯》
普京全力打造的冬奥城市,在还只是滨海度假胜地时,曾在一部荒诞烂片《道》(2009)中小露过一脸。不过那部简直是贴着中俄友谊标签的电影,是各种外景和元素的大乱炖,人人穿旗袍戴斗笠的江南水乡,出落了一位身手了得的少林俗家子弟,多年过后,却长成了一个混黑帮的俄罗斯小伙。
最近几年,真正涉及索契的,还是那些关于俄罗斯体坛禁药丑闻的纪录片,这其中最有影响力的,是提名了今年奥斯卡最佳纪录片的《伊卡洛斯》。导演布莱恩在自己吃禁药准备参加业余公路自行车赛过程中,与莫斯科奥运实验室主任格利高里·罗琴科夫成为网友。这位在索契冬奥会主持药检工作的官员,本职工作理应是抓到作弊运动员,却在布莱恩的纪录片里,大方和无私地替他制定用药计划。国际奥委会反禁药组织WADA开始彻查索契冬奥会俄罗斯系统性舞弊问题,替俄国体育部长背锅的罗琴科夫,成了镜像版的体育界斯诺登,飞离莫斯科,避难洛杉矶。纪录片的主角从导演自己彻底转为身处危难中的罗琴科夫,竞技体育的丑陋面目也在不经意中被一点点揭开。
喀山:《喀山孤女》
电影《喀山孤女》又名《娜斯佳和她的父亲们》,一则发生在大雪夜的温馨小品。新年前的最后一堂课上,小男孩问女教师娜斯佳:“你有没有去过喀山?为什么别人叫你喀山孤女呢?”事实上,妈妈早逝的娜斯佳,已通过登载信件的方式,想要寻找到生父。新年钟声敲响前,本想和未婚夫过两人时光的娜斯佳,却接连迎来三位抱着大狗熊的老头子,无一例外,他们都自称是娜斯佳生父,见报而来。
俄罗斯著名摇滚乐队Lube,有首与电影同名歌曲《Sirota kazanskaya (Сирота казанская)》,高亢地唱道:“为我祈祷吧,先生,或者是你的父亲。喀山女儿,打起精神,好好活着。”极夜中的电影布景极其简单。外景,是压雪拖拉机驶过的雪原和一个孤零零卖毛绒玩具的商店;内景,是娜斯佳的小木屋,像是一个戏剧舞台。起初冰冷空旷的单人世界,渐渐成了一场三老头争宠、未婚夫纳闷旁观的热闹晚宴。可以从教室一屁股滑雪到街道的小镇,木屋中的玩具狗熊和漂亮蛋糕,旁边林地里随手可砍伐来装点空间的圣诞树,粗颗粒彩色电视里敌台传来的美国国歌……这既是我们美好想象中的俄国年夜,也是他们自己上世纪90年代苦中带乐的欢笑记忆。
圣彼得堡:《意大利人在俄罗斯的奇遇》
毫无疑问,这座旧俄帝都是俄罗斯最高颜值的城市,围绕它的文学和电影作品数不胜数。有插上穿越翅膀、拉扯卫国战争勇气以振奋当代青年人的《我们来自未来》(2008),也有表现苏联末世恶警嚣张到无法无天的《棺材200》(2007)。不过其中最具旅游宣传价值的,当属喜剧大师1974年那部《意大利人在俄罗斯的奇遇》。
罗马病榻上,奄奄一息的老太太嘱咐给孙女的财宝的埋藏秘密,被各个大小角色全听到了。于是,他们蜂拥飞向当年还叫列宁格勒的圣彼得堡,展开一场充满荒诞、巧合、倒霉的寻宝之旅。直至今天,此片的编剧思路依然让人叫绝,飞机上丢了护照而在两国间反复往返不得落地的医生,满城挖坑寻宝却引来狮子追踪的瘸子,配角们持续不断制造的一个个小高潮,共同将主角们的滑稽戏推到了大高潮。而当年色彩饱和度不算很高的摄影画面,又把运河、石桥、雕像和教堂交错的古老城市,以一种旅游明信片的色泽呈现于全球观众面前。现在回看,当然更多了一份昏黄的怀旧色彩。
莫斯科:《我漫步在莫斯科》
和东京、纽约、巴黎、伦敦一样,此等级别的大都市,从来不缺电影将片名直接贴上来:如《莫斯科不相信眼泪》《莫斯科保卫战》《莫斯科陷落》《莫斯科,我爱你》……无论是战争大片,还是城市爱情,不同时期的电影作品或多或少都记载下了时代风貌的某个截面,让后世可以在光影中,见识一座伟大城市的毁灭与重生。
《我漫步在莫斯科》,有着上世纪60年代东欧青年电影无忧无虑又隐约忧伤的气质。十八九岁的尼基塔·米哈尔科夫,在成为导演之前,先在此片中“鲜肉”了一把,扮演了夜班工人高利亚,在清晨下班的地铁里,认识了一日游的维修工瓦洛佳,带着这个外地人,和即将在服役前结婚的好友萨沙,在一天之中,忙碌地做了好多事。那个年代的交通真顺畅,可以让青年们在一个昼夜间结婚离婚又复婚,让萍水相逢的主宾艳遇、约会还抓贼,让外地来的朋友到出版社赠书、批评并约稿。至于米哈尔科夫扮演的高利亚自己,则在转车吃饭上夜班路上,挥别了一日友情的新朋友,对地铁检票员轻快哼唱起“走在莫斯科大街上”,如同《雨中曲》的苏联公民版,忙碌而快乐。
(原标题:电视上看“球” 电影里看“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