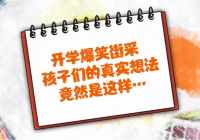在《沈从文全集》的第八卷收录了《边城》。《边城》后面有篇附录,就是沈从文对《边城》电影文学剧本的修改。

这个很有意思,首先我想跟年轻的你解释一下什么叫“电影文学剧本”,这个东西现在有点看不到了,但是在80年代的时候是非常流行的。
剧作者是把剧本当成文学来写,写完以后会率先发表在刊物上——以前我们看综合性的文学刊物,经常会看到有“剧本”这一栏——不像现在这样,第一剧本也不能随便外传,第二剧本更多的是台词的合集,用台词来推进情节,跟80年代已经完全不一样,像对人物的描写,对景物的描写,创作者真是把自己的剧本当做文学作品在创作。

《边城》是由姚云和李隽培改编的,写完以后,交给了沈从文,沈从文看完,写了很多的改评意见。虽然不管出于客气也好,出于感激也好,沈从文肯定会对这个剧本大体上肯定,但是你看改评内容,就会知道沈从文在里面动了很多的刀子。
沈从文在西南联大给汪曾祺他们上课的时候,反复强调“要贴着人物写”,恰恰在他对这个剧本的修改里面——现在因为我们看不到沈先生当年是怎么改汪曾祺他们的作文了,但是从这个剧本里面我们可以看得出来,沈从文那种细致,还有他的坚持。
就从这个修改来说,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沈从文不是一名文青,他绝非一名文青。
但是电影剧本的作者明显是一个文青。所以沈从文对文青作品的修改,其实是很值得学习的。大家可以自己找来看,但是我点几处,比如说,沈从文在里面会特别强调“虎耳草”。大家知道虎耳草是《边城》里一个特别的意象。
按说在剧本完成之前,编剧就已经去过湘西考察过拍摄环境了。但是很有意思的是,他们在剧本里面经常写“虎耳草在风中摇曳”这样的句子。然后沈从文就反复强调说,虎耳草是贴在岩壁上生长的,它不可能摇曳,“不管什么大风都不会动的”。
编剧也会编造很多的所谓桥段。比如给黄狗加了好多的戏,比如让黄狗衔着老船夫的酒葫芦奔回来了,沈从文说,不对,“使用狗要有个限度,超过了需要,反显造作”。
黄狗还有什么戏份?就是他跟着翠翠出去的时候,这个剧本就让它一会儿对着人叫,一会又跑来跑去,然后沈从文就说乡下狗是很怕生的,一旦离开了自己的家,他就不会离开主人,一定在主人跟前,所以你不要把狗的这个戏给它太多了。
包括后来有一段,说黄狗为了安慰翠翠,去舔她的脸,然后沈从文就说,这是洋狗才干的事情,中国的土狗绝对干不出这样的事情来,主人也绝对不允许它这么做。
像这样的片段什么的都特别多,还包括这一段,说翠翠第一次遇上了二老,“翠翠害羞地低下了头,散漫的光线下,翠翠跟那男子四目相遇”,沈从文就批评说“黄昏中哪会有什么四目相遇而害羞低头”,把这句改成“翠翠笑笑地顾自走了”——沈从文特别强调翠翠是一个还没有成年的小姑娘,这种少女的情怀,它实际上是朦朦胧胧的,“对恋爱只是感觉到,所以处理上盼处处注意到”。
但显然,编剧做不到“贴着人物写”,包括写翠翠爷爷给她盖被子,说把被子盖在了“丰满、修长的身体上”。沈从文就批注说“这人还未成年”。包括剧本写一个十一二岁的小姑娘,说她“白脸、长身”,沈从文说,十一二岁,即使城里人也还没有抽条,何况乡下。

类似这样的批评特别多。包括剧本特别喜欢写下雨,但是又非常的不准确。比如写说:“雨越下越大,青石板的街面上溅起持续升的白雾,在风中舒卷。”
沈从文批注:“杭州雨季是这种情形,湘西山城下雨可不这样。”还有剧本写湘西人,说老船夫和杨马兵“盘腿而坐”,沈从文就说我们那里的人从来不盘腿而坐。还有像什么“得了吧”这种北方语词,沈从文也非常不喜欢,必须给它改过来。
还有,有的时候编剧会把戏份加得很重,比如说在翠翠去看看龙船的时候,二老不断的盯着河边的窗户,镜头从一个窗户摇到另一个窗户,都没有翠翠。沈从文就觉得这样写,太俗气了,而且绝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还有剧本说苗家姑娘在在河街上走,沈从文说“这不是苗区,苗人并不会多,顶多是用三三五五”这样的话,像这样的改动,太多了。

问题出在哪里?我觉得,就在于编剧是个文青。所谓文艺青年,跟作家的一个区分点,就在于分寸的控制。文艺青年往往把文艺或者说文艺腔、文艺感,作为自己追求的最高目标。
因此他们写东西是务求华丽或者绮丽,希望用词越偏越好,越多越好,总琢磨着怎样把事情写得比较夸张,用一个词儿说叫做“刻奇”(kitsch)。
文艺青年在叙事的时候,是特别刻奇的,比如说写景物,他会写“淋得湿透的喜鹊,凄厉地叫了几声”——你怎么知道他凄厉?沈从文就注明说:“不可能,也不必要”。景物的描写,不能够完全跟人物的心境结合,何况你把人物的心境也写得很夸张。
其实人的心态是会自我调节到一个相对平静的心态,那种大哭大笑大悲的时候,没有那么多。这让我想起最近杭州女孩章子欣遇害,这个案件里面,很多人不是指责他的父母或者爷爷奶奶冷血吗?其实人的生活,不可能是那么drama的状态的。人总归要回到平静的生活,不管发生什么事情,人总要过下去。

恰恰是在这种充满了文青气息的文字里面,会经常出现什么都把自己投射进去的状况。像《边城》剧本里不断的使用喜鹊、草、风雨这些东西来映射人物的心境。
但实际上,《边城》之所以没有变成一个烂俗的虐心言情小说,就在于它保留了强大的克制力。他写翠翠的心思,特别的朦胧而优美——优美这个东西必须留白。如果是往前走过一分,可能就失去了它所有的意义。

汪曾祺在多年后重读《边城》,写下了自己的成名作《受戒》。大家比较一下,这两师徒其实都在这方面,有着非常好的控制力。
就像沈从文批评剧本时会写“这么描写,不合小说的素朴风格,似应简化”,后来汪曾祺也说过一句话,说“小说就是删繁就简的艺术”,这是今天的一个结论。
原标题:杨早 | 沈从文是怎么改剧本的
【免责声明】上游新闻客户端未标有“来源:上游新闻-重庆晨报”或“上游新闻LOGO、水印的文字、图片、音频视频等稿件均为转载稿。如转载稿涉及版权等问题,请与上游新闻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