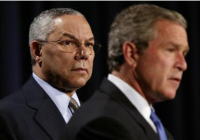北京头条客户端消息,“老师,我想研究拉屎,可以吗?”一个叛逆的学生问。
“可以,但你要有研究的方向,而不是仅仅开个玩笑。”老师一本正经地回复。
这是在一个名为“先锋”的新型教育学习社区里师生的对话,在这里,没有固定的课表,学生可以去选择他们感兴趣的事情,哪怕是连打游戏都可以算作学分,不愿意听的课也可以半途中止。
在这里上学的孩子,有的成绩优异来自重点高中或者重点大学,有的成绩低迷贪图玩乐,但他们大多都有一个共同点:曾经厌学、逃学,因为学习而消沉、抑郁。
于是他们走进了这些被称为“学习社区”的课堂里,如今这样的新型教育学习社区已有很多,他们觉得这里没有那么多枯燥的理论和成绩排名,也没有无法逃开的必修课。当然也意味着,文凭成为了他们返回“体制内”就业通道的一道阻碍。重回高考、出国留学、独自创业或留校任教,成为了他们最后的出路。无论结果如何,这些“特殊”的学生都在尝试,找到最适合自己的那一种。
重点大学退学生的新学业
穷游回来后,“鱼丸”离开了大学,走进了“先锋学习社区”,以半工半读的方式做起了志愿者。她觉得,这才是她找到自我的学习方式。
鱼丸出生在贵州的山间小城六盘水,她现在还很怀念小时候去大山里“撒野”的自由。但上了初中以后身为公务员的父母变得严厉和焦虑,他们租了一个离学校很近的房子,每天督导鱼丸学习,临近高考,鱼丸看课外书或玩手机都会被批评甚至挨打。
在父母的规划里,鱼丸的出路就是考一个好大学,回家乡找一份稳定的工作,然后组建家庭生儿育女。在这样严厉的督导下,鱼丸以616分的成绩考上了广州的一所重点大学,她选择了教育专业,想要当英语老师,毕业后回六盘水教书。
但在学校,她发现大学生活跟老师和父母描绘的不一样,身边的大部分同学都是在混日子,大家比的就是拿教师资格证、毕业证或者刷绩点。这让鱼丸开始对学习失去了热情,这个从小到大的“好学生”开始厌学和逃课。
她开始对抗自己的“叛逆”,告诉自己曾经高中的学习和高考是多么的不容易,必须要坚持下来才对得起自己付出的辛苦。到了大一下学期,她的身体开始为这种对抗付出代价,她开始抑郁,暴饮暴食到呕吐,她觉得自己变得太糟糕。
挣扎了三个月,鱼丸把自己的情况告诉了父母,母亲带她去看了心理咨询师,经过心理干预后,她的情况有所好转。但临近开学,焦虑感又一次涌来。鱼丸决定休学,但这个决定其实是把焦虑传给了父母,他们之间产生了激烈的对抗,不过,父母还是被她说服了。
“我感谢他们,他们很有勇气。”鱼丸回忆说,18岁的她背起行囊独自去西藏穷游,她从成都出发,或搭车,或徒步,或骑行,去了拉萨,后来又去了尼泊尔、非洲和东南亚。路上的盘缠都靠当义工或者写公众号文章的打赏来支撑。
在路上时,本打算旅行结束后回到学校复学的她看到了一篇微博,知道了“先锋学习社区”,她找“先锋”的校长聊过后,决定入学。
通过视频,鱼丸把自己的决定告诉了父母,父母露出了难以置信的表情,他们激动得骂鱼丸是得寸进尺,生生把她骂哭。于是鱼丸决定通过写信这种更平静的方式与父母沟通,从教育资源、经济成本和自己的本心三个方面分析退学后去“先锋”学习的优劣。这些让她得到了妈妈的支持,随后她又和爸爸展开辩论,最后也得到了父亲的默许。
“我深知,你们不答应我,是因为爱我,但谢谢你们答应我,因为你们明白了如何更好的爱我。”鱼丸这样跟爸爸妈妈说。
鱼丸在“先锋”一边学习一边做志愿者,一方面她在“先锋”上课,另一方面她日常写文章维护“先锋”的公众号,还帮助组织各种活动。她跟着老师去了草原阿坝参加了校长儿子的婚礼,跟着校长去了深圳参加中国创新教育大会,组织同学去了江门参加了校园团建。还在校长的推荐下,全程策划组织了学生们去美国的游学。
这次组织策划游学,让鱼丸意识到自己能力的不足,带领20多名学生去美国要做的事情,比自己穷游复杂得多,那两个月她几乎没睡过好觉,她要去跑签证,搞预算,做行程,在行程中,还要记录账单,安排行程,可就这样还要面对学生的评价和吐槽。尽管中间经历了波折和失误,回到祖国的那一刻,鱼丸却觉得这几个月开启了自己新的人生。
在“先锋”的学习,除了在课堂上举手争抢讨论的时候,她感受不到太多竞争,相反老师们更强调合作,愿意让几个同学一起分工去完成自己的项目。
鱼丸的计划未来做一名教育工作者,在这之前她想先学习管理。于是她去了另一个创新学院“致极学院”,这里发起了一个“1+3国际本科项目”,第一年在上海读书,后三年去美国6所大学中的一所完成学业,第一年在中国的课程里,有三门是美国没有的课程,分别是中国哲学、中国历史和中国经济。
这是一个以培养企业家为目标的教学项目,学生中多是企业家的孩子,也有一些普通家庭的孩子。鱼丸去参加了面试,拿到了录取通知书和全额奖学金。
这个项目刚刚开始一年,未来她会不会成为企业家,鱼丸自己也说不清。单就“学习社区”这样的创新教育来说,过去的毕业生中,大部分其实并不是什么“成功人士”,他们也仅仅是在社会上立足——用自己擅长的东西和喜欢的方式去解决其他人的需求换取报酬。至于每个人要用多久才能找到自己真正擅长的东西和喜欢的方式,以及如何去学到解决他人需求的技能,这还是要看学生自己。
戒网瘾学校出来的孩子
开学了,李宇棣还没有想好自己要学哪些课程,因为父母还是希望他回到普通高中上学,他们觉得“先锋”的这些课程看起来很“虚”,不与考试接轨,而在电竞学院学习电竞,每天都只是打游戏,没有前途。
没有办法,李宇棣一直拖延了开学报到的时间,直到9月15日他跟父母强硬表态后,才开始了在“先锋”的学习。
如果不是到先锋学习社区上学,李宇棣或许会游荡在网吧的电脑前,抑或是在戒网瘾学校里被殴打得遍体鳞伤。
在上初二之前,李宇棣都是班上的好学生,进入青春期以后,他的成绩有所下滑。班主任因为是李宇棣母亲的同学,对李宇棣异常关照,时常会直接跟他妈妈沟通,还会把他家里的事情拿到课堂上去说。这让李宇棣很反感,终于,觉得很没面子的他在和班主任老师大吵一架后,逃离了课堂。
李宇棣决定再也不去学校上课了,在家无所事事的他,除了打游戏就是外出闲逛。
父母忍无可忍,把他送到了河南的一家戒网瘾学校,在那里他的腿被教官生生打断了。直到三个月后,父母来探视发现异样,才知道他遭遇了毒打。
除了挨打,在戒网瘾学校的三个月时间并没有让李宇棣感到有什么收获,在那里有一些心理辅导,还有军事化的体能训练,但全都是灌输式的,而李宇棣觉得,那些教官和老师们讲的一些大道理“很幼稚,几岁的小孩子都懂”。
从戒网瘾学校出来后,李宇棣跟里面的同学偶尔还有联系,他们有的回到学校读书,但成绩并不理想;有的得了严重的抑郁症;还有的干脆离家出走至今未归。
而李宇棣,则被父母送到了“先锋学习社区”,在这里一切都是“自由”的,自由到他可以名正言顺去打游戏,去选择想要学习的科目,安排自己的课程表。
李宇棣有一些电竞技能基础,他被列入到电竞学院的第一梯队中,每天上午9点到12点,下午2点到5点都是电竞训练时间,除了电竞训练和体育课之外,其他的学科都不是必须要学的,李宇棣只需要按照自己的兴趣选择想学的科目。
文学鉴赏、经济学、历史学、语言学、电影鉴赏、新闻事实讨论、社会调研、自然科学、美学、城市探索等课程都是李宇棣可以选择的,学生选择课程后完成连续两个学期,每学期修满576个有效学时,就可以拿到申请进入国外学校所需的被美国大学认可的高中成绩单。如果选择的课程不对学生的胃口,学生可以随时终止学习,只不过花费的学时便重新归零。
除此之外,“先锋”的学生还有一种毕业方式,就是学生想清楚自己想做什么,并且有能力为自己的选择和行为负责时,就可以离开,成为毕业生。
现在,李宇棣每天大约用10个小时来进行电竞训练,这让他过得很充实,他觉得这是实现自己梦想的一种方式。
学了一个多月后,李宇棣能够感受到自己身上的变化。以前他遇到问题不知道怎么解决,只能等着问题随着时间的流逝而过去,但现在他可以主动思考解决方法。在与人沟通方面,他开始尝试去考虑别人的感受,去从别人的立场和角度去看问题,而不是像过去那样直来直往,只关注自己。
先锋学习社区的电竞学院创建只有一年多,上届学生还没毕业,其中有一些学生已经决定去国外留学,有两个学生开始在“先锋”担任助教,还有的退出电竞圈子去做语言方面的工作。
这些现实都向李宇棣显示出,目前的开心和快乐可能是暂时的,未来毕业后如何走向社会才是他一直都挂念的问题。
对于自己的担忧,李宇棣和“先锋”的老师也沟通过。老师说:“你要遵从自己的内心,要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然后就朝着这个目标去努力。”
李宇棣觉得这跟普通学校的老师不一样,跟戒网瘾学校的教官更不一样。李宇棣曾经想,是不是能把戒网瘾学校的同学介绍过来,这或许可以“拯救”他们。但他又想,那些同学的家长恐怕是不会同意的,“因为他们更希望孩子能够回到学校好好读书考出好成绩。”
现在,李宇棣有自己的打算,他想先树立自己走电竞这条路的决心,然后利用空闲时间把文化课补上去,再以社会考生身份参加高考。但现实问题就摆在眼前——“学习社区”的课程与高考内容不沾边,尽管“先锋”的老师提出会推荐老师给他补习,但仅靠补习去参加高考,恐怕很难有好的成绩。
李宇棣的另一条出路,也是“先锋”学生们普遍选择的一条。他打算学一门技能型的科目,比如音乐或者烹饪,然后试着靠这个立足,但这似乎与他现在感兴趣的电竞相距甚远,显然,他还在寻找适合自己的路。
没有文凭的独立音乐人
寻找自我,成了新型学习社区里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学生只有发现自己的兴趣和优点,才能够沿着目标走下去。
潘正是在“先锋”找到了自己的真爱,从此走上了音乐的道路。他是“先锋”曾经的学生,在“先锋”学习的最后一年,他几乎什么课都没上,拿出了所有时间去制作自己的第一张音乐专辑。到毕业时,他本来已经拿到了美国太平洋路德大学的录取通知书,但他放弃了,留在了国内组建自己的摇滚乐队。现在他是一名音乐制作人,给一些影视剧、电子游戏做配乐,同时经营自己的乐队。
在去“先锋”学习之前,潘正就读的是成都的一所重点中学,他在学校里是一名普通学生,成绩中等,用他自己的话说,除了音乐老师和美术老师之外,没有老师喜欢他,在学校里基本没什么存在感。
到了青春期,叛逆的潘正很反感学校里的一切,他觉得压抑,希望从学校逃离。他听人说“学习社区”跟普通学校不一样,可以边玩边学,于是他不顾亲人的反对,来到了这里。
刚来时,潘正有点“懵”,他说自己当时完全不知道这个学校是在干什么。这里根本不能被称作是学校,学生们完全是“放养”状态,以至于自己经常能够溜出去打游戏或者喝酒。学校里设置的课程在他看来也很奇怪,比如旅行课,每个周末都会去一个地方游玩,可能是古镇,也有可能是博物馆,有的时候还会在外面住上半个月。“旅行课想去哪里都是自己来选,选好目的地后就可以结伴,只要凑够一定人数,就有老师带着大家一起去。”
更疯狂的还有社会实践课,潘正记得,有一个在“先锋”学习的女生,想要去调查戒网瘾学校黑幕,于是就设计了这样一个项目,她进入戒网瘾学校暗访,然后将里面的所见所闻都写出来,做了一篇调查报道。这个女生的行为让学生们都觉得非常勇敢和敬佩。
在“先锋”学习的这段时间,潘正也找到了自己的方向。起初,他喜欢画画,曾以为自己会成为一名画家,但父母觉得画画没前途,想让他学设计,这样至少以后能更有就业市场,但他发现,父母的期望越高,他就越难静下心来去画。后来他迷恋上了打游戏,喜欢一边打游戏一边听歌。听着听着,他迷上了摇滚乐,梦想着自己能够有一支乐队,做出自己喜欢的音乐。恰好那时候他已经在“先锋”学习,这给他提供了施展想法的空间。此前只学过声乐的他开始想办法自学音乐知识和技能,这种学习到了一种痴迷的程度,他自己也说:“发现音乐才是真爱”。
在“先锋”的最后一年,潘正已经17岁了,他开始感觉到了压力,于是他打算制作一张音乐专辑。
正好“先锋”的一个音乐老师要带着同学们一起录专辑,但潘正很不喜欢跟着老师的要求来做,他干脆退了音乐课,自己做了起来。
如今,潘正蓄起了摇滚乐手的长发,拿着他的第一张专辑,在音乐圈里摸爬滚打,凭借自己对音乐的热爱和能力在社会上立足,做自己认为有意义的事情。
找到自我后的竞争同样残酷
“先锋”这种新型学习社区的学生,看似是没有压力的,但其实到了17、8岁的时候,他们也要考虑自己的未来。
因为在这里的学习别说参加高考,甚至都无法换来一张社会认可的高中毕业证。这里的学生要么选择出国留学,要么选择自己创业,要么就是用一技之长进入社会做自由职业者。
在中国目前有不少类似“先锋”这样的教育学习社区,仅受访者提到的就有“贵阳幸福学堂”、“成都好奇学习社区”、“致极学院”等等,对于新型教育来说,学历文凭是必须要面临的问题。出国留学、参加高考都还是为了拿到一纸文凭,而自主创业和留校任教则是另外两种不需要文凭的立足社会的方式。
在潘正看来,做音乐是他的兴趣也是出路,在这一行里拼的是作品,如果不是进入到体制内的乐团中,学历并不是那么重要。
他发现仅就音乐圈来说,自己虽然没有学历,但在学习社区的学习让他有了一些优势。他觉得相对来说自己更有创造力。“很多音乐人其实是没有想法的,他们还是在不停地模仿,不停地做别人做过的东西。”
但文凭问题仍旧是潘正这样的学生们面临的最大问题,所以很多人只能借助学习社区与美国的大学的关系去出国留学,然后拿到一个文凭再回到国内立足。
随着这些年来各种留学机构的兴起,“海归”的含金量越来越低,这种“出国涮水”的方式拿到的学历文凭的竞争力也严重下降。而且,出国也需要一定的经济基础,虽然“先锋”能够提供一部分助学金,但出国的出路仍旧是对于经济条件稍好一些的家庭才更合适。
潘正自己曾经有出国留学的机会,但他放弃了。他解释说,现在美国的教育,尤其是大学教育已经很产业化了,大部分学校都被资本裹挟,通俗的说就是用金钱和时间来换学历。而他选择做音乐,对于学历的要求并不是硬指标,他更想把时间倾注在音乐上。
“先锋的学习环境很令人羡慕,但出来以后的竞争也挺残酷”。所以,他觉得,像“先锋”这样的的新型教育并不适合大多数人,它只是给了学生们另一种选择,让那些急切想要选择与众不同道路的学生能够有一个归宿。高考的那种教育环境虽然内卷严重,但却相对公平,“我觉得只有所有人都能够富裕起来的时候,这种教育方式才会大众化。”
(文中受访者均为化名)
原标题:Qing听丨被“散养”的孩子:一个非典型教育样本的探讨
【免责声明】上游新闻客户端未标有“来源:上游新闻-重庆晨报”或“上游新闻LOGO、水印的文字、图片、音频视”等稿件均为转载稿。如转载稿涉及版权等问题,请联系上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