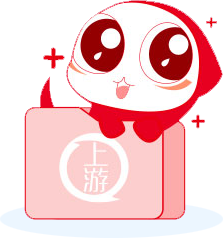

“三大步,跑得快,肥料往到农村带…”重庆城曾有20多个粪码头?
红岩春秋号消息
沿街收粪人
“倒尿罐——”
每天蒙蒙亮,巷子里准会响起一阵吆喝,嗓门不大,但格外清脆。不一会儿,接二连三的木板门声响起,走出一个个头发蓬松的女人,或睡眼惺忪的小女孩,或蹒跚的小脚婆婆。她们提着或端着一只只瓦尿罐,朝吆喝人旁边的木粪桶走去……这是20世纪70年代川江边小县城的一幅市井生活图。

老重庆民俗漫画“倒罐子”(张明志/绘)
那时候,一家大小挤在平房里,即或是住在两三层的楼房,一样没有卫生间。由于离公共厕所较远,夜晚要方便,家家户户都备有尿罐。我母亲在邮电局当话务员,经常上夜班,家里倒尿罐的活自然落在了大妹妹身上。大妹妹长得漂亮,喜欢打扮,又爱面子,讨厌又臭又脏的尿罐。每次清洗尿罐时,她要么用开水烫去臭气,要么拿竹刷把狠狠地戳,捣坏了好几个,没少挨骂。
重庆城的人更爱面子。下午的时候,上班上学的人都不在家,街上行人又少,收粪人这才出门收粪。他们一般不直呼“倒尿罐”,而是喊“倒罐子啰!”“倒桶!倒桶!”我们巷子的波儿奶奶年轻时就住在重庆城,她给我们讲,1949年前重庆城挑粪的粪夫要穿号衣,他们白天不准上街挑粪,粪桶不能装得太满,还要盖个木盖子。
沿街收粪人是郊区农民,在什么都缺的年代,他们把粪便当成宝。小时候,我在乡下看三爸给地里的菜淋肥,他淋的是清汤汤的猪粪水,边淋边对我说:“要是有城里的粪就安逸了。”过去,重庆城把城市粪便当肥料管理,设有专门的肥料管理所和公司,属事业单位,市里的城肥领导小组则由副市长当组长。
我们巷子的那个收粪人姓向,是一个50岁左右的男人,中等个子,脸瘦削,光头上扎裹着一圈白布帕子,冬天用以取暖,夏天用来揩汗。他家在江对岸七八百米高的水磨梁子上,生产队派他来城里收粪。每天鸡叫第二遍就出门,坐最早一班轮渡到县城。收满一挑粪后他便往回挑,过了渡,一直爬上坡,临近晌午才到家。这么辛苦,就为一挑粪。他说:“城里的粪便肥,回去后还要与猪粪、水掺和后才淋庄稼。”
一天清晨,巷子里新来了一位收粪人,大家都认为是给老向打替的,也没多问,纷纷倒了尿罐就回屋了。不一会儿老向来了,比平时晚了点,哪知粪已被人冒收,他心痛得快哭了。
卖钱的粪肥
20世纪70年代末,一个大年三十的晚上,天空飘着绵绵细雨,地上湿漉漉的,很冷。在重庆街巷,一名大学生模样的年轻人正快步往家赶,当他路过离家不远的一座公厕时,看见那里蜷缩着一个守粪农民。农民双眼直盯着粪池,麻木的神情似乎忘了这是除夕夜。年轻人为之一振,同情、怜悯、感慨……复杂的情感一一袭来。他后来创作了《守粪农民》的油画,数易其稿,最后画成了《父亲》。这个年轻人叫罗中立,后来成为四川美术学院的院长。
一幅《父亲》,绘出时代的一个剪影。与“粪肥”有关的往事,不胜枚举。
川江沿岸城镇的公厕,按计划分配给近郊农村生产队用肥,重点是蔬菜队。队上一般安排年老体弱的社员照守,以防止其他队社员“偷粪”。有些城镇的公厕不固定分给哪个队,而是由各生产队轮流挑,以10天或半月为期限。城里单位、厂矿的厕所,要有熟人介绍才能挑。

担粪的农民(陶灵/摄)
我们巷子有个下乡知青,小时候他的衣服口袋里常装着炒豌豆当零食,大家给他取诨名叫“豌豆”。临下乡时,他通过父亲的关系,把单位的一座厕所包给了自己落户的生产队挑粪,因此立了大功,当上了生产队的保管员。
重庆一些郊县及邻近的广安等地,不属取用城里粪肥的范围,有一段时间严重缺肥,近百个公社的社员便来重庆城里“抢粪”。他们不分白天黑夜,自己上厕所捞取,每天进进出出几千人次,粪车粪桶随处可见,粪便四处泼洒,导致街巷里污秽不堪,臭气熏天。重庆城立即采取措施,实行“城肥供应证”和“准运单”办法,才控制和禁止了“抢粪”。
这里,不妨赘述。重庆城中由机构来管理粪便清运工作由来已久。
清朝时期,厕所被叫作“茅司”,公厕被称为“官茅司”。 巴县知县聘了专人来管理重庆城官茅司的粪便清运。重庆建市后,由公安局管理官茅司,后公安局改名为警察局,一直负责或配合卫生局管理官茅司及街道卫生。当时市民捡了死老鼠也要交到警察局,每只奖励5分钱。
抗战期间,重庆城有两类茅司——官茅司和保甲茅司。当时,由于人口激增,公厕又被炸,如厕极为困难。于是,政府传令镇长、保长,发动民间力量修建公厕,并准许人们卖草纸和收取如厕费用,每人每次2分。
重庆城厕所最多的时候有200多座保甲茅司,由粪商雇人清运粪便。而官茅司的粪便则由粪帮清运,但最终都卖到近郊的农村当肥料。粪商、粪头、粪霸由此纷纷出现。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重庆城有个“五花帮”,专门做运粪、卖粪的工作,每挑粪卖2至4角钱不等,还向居民收取倒罐费。
20世纪80年代初,我刚参加工作时,单位厕所的粪肥以每年500元卖给郊区蔬菜队。每到年底,蔬菜队队长会准时来交下一年的粪钱,单位老邹负责这件事。
粪码头储粪
粪便当肥料时,公厕还没建沼气池,用肥的生产队随时来人挑。人们将粪肥一趟一趟地挑到江边码头,并在岸上挖了大坑储存,其坑壁用三合土敷平,不渗漏。每过十几天,生产队便来船来人,把粪肥运回去。由于这些储粪坑装卸时又脏又臭,影响环境,于是专门设立了粪码头。重庆朝天门、望龙门、菜园坝和临江门、千厮门、牛角沱等江边,多时有20多个粪码头,每年运粪肥近10万吨。
然而,重庆城区公厕的粪是不用人挑到粪码头的,而是用人力车拉。两只胶轮的木板车上,安了一个很大的卧式扁木桶用于装粪。由于重庆到处是坡,下坡时,掏粪工便将双手用力压住粪板车拉扛,使车尾翘起来,与扁木桶的重量持平,仿如跷跷板似的一路狂奔。待车速飞快时,他一屁股歪坐在一侧的拉杠上,脚尖不时点地,控制车速和方向,不一会儿就到了码头。岸边有一个U形木滑槽架到江边,在此拔出扁木桶底的塞子,粪便就哗啦啦地流到了坑里。这个拉粪板车的过程被称为“三大步”。

老重庆民俗漫画“三大步”(张明志/绘)
生产队的粪船是木船,拆了船舱之间的堵(舱隔板)后,便成了一个大舱,这样装得多些。我们巷子的那个知青“豌豆”,他队上的粪船从县城一回来,全队社员就要出工,把船上的粪挑到庄稼地边的粪坑。一天正遇下雨,“豌豆”挑着一担粪,从粪船的跳板往岸上走,突然脚下一滑,掉进江里,粪桶扣了下来。粪水倾泻一空,他根本不敢凫出水面,而是埋头钻进深水里,游了一大圈才爬上岸,结果还是一身的粪臭。挑粪的社员乐得哈哈大笑。尽管如此,队上的青壮劳力,包括“豌豆”,还是喜欢挑粪。因为工分最高,一天能挣12分,值4角多钱。
船舱的粪当天必须挑完,挑完后还需将船清洗干净,不然会严重腐蚀木船舱板。可生产队从江边到山顶都有庄稼地,空着手走上山顶都要一两个小时,再怎么努力,一天时间也不能将船上的粪全挑上去。于是,他们又在河边挖了几个大坑储粪,慢慢转挑。
又快过年了,一天,买我们单位粪肥的那个蔬菜队队长来了,找到老邹,说:“明年这粪,我们不挑了!”老邹犯傻了,粪没人挑,茅坑满了咋办?那时又没建沼气池。好说歹说,不卖一分钱,请蔬菜队帮忙挑走。念其多年的供肥关系,队长答应了。
过了一年,蔬菜队长又来了,说:“现在包产到户,我也派不动社员来挑粪了,你们另想办法吧!”老邹很灵光,说:“那每年给你们500元,算是社员的工钱,怎么样?”
我也不知道他们商量结果怎样。年底,我拿着调令离开了家乡小县城。
后来,城市粪便不再当肥料,所有的厕所都建了沼气池、化粪池,现在是生化池了。
原标题:城记 | “三大步,跑得快,肥料往到农村带……”如民谣所述,重庆城曾经真的有20多个粪码头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