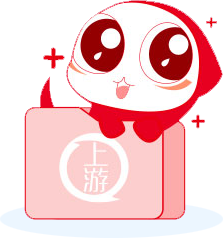

为聋哑人打官司 这个重庆小伙走红网络成全国唯一手语律师

△在手语律师的道路上,33岁的唐帅或许将不再是一个人。
上观新闻消息,“实在不好意思,能不能让我先眯半小时?”唐帅困得抬不起眼皮,声音越来越轻。
长年累月,唐帅靠着一根根烟和一杯杯浓茶抵抗汹涌而来的困意,这次却失了效。刚从看守所回到律师事务所的他,前一夜只睡了3小时。平均每天睡眠时间仅有4-5小时,连续3年没有周末,常常熬到办公楼里只剩他一人,这是被多家媒体称作“全国唯一手语律师”唐帅的日常。
从2006年成为手语翻译到如今的执业手语律师,唐帅在这条路上走了12年。这个十一假期,他依旧没能休息。办公桌边几摞厚厚的蓝色封皮卷宗,他得趁着假期看完。接下来,受各地律师协会的邀请,他将在全国演讲,主题为“社会担当与责任”。
今年火了之后,唐帅已接受过300多家媒体的采访。他说,他不喜欢“网红”这个词,更不想当“唯一”。
9月,事务所的一位聋人姑娘通过了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的客观题考试。如果10月的主观题考试也顺利通过,她将可能成为第一位聋人律师。这意味着,在手语律师的道路上,33岁的唐帅将不再是一个人。
直言已患上采访恐惧症的唐帅,仍在一次次接受媒体采访。“我希望有更多人关注聋人群体,让他们不被社会抛下。”唐帅深知,他的努力如同杯水车薪,但他仍然愿意做那道光,哪怕微弱。
无声的世界
△唐帅(右二)作为重庆律师代表,参加律协举办的人才训练营。 由受访者提供
多数时候,在工作中,唐帅的视频对话都是无声的。
戴着框架眼镜,头发微卷,一身浅棕色针织外套的唐帅微皱眉头,紧盯前方竖着的手机屏幕,双手不停比划。屏幕中,一名聋人正在咨询法律问题。除了普通话和重庆话,手语也是唐帅在工作中最熟练的语言。
实际上,唐帅最初并没想过会成为手语律师。尽管,他出生于聋人家庭。
旁人难以想象,4岁之前的唐帅,和父母不曾有过丝毫交流。一心巴望孩子过上正常人生活的父母,将他送到外婆家,隔绝于手语世界外。直到如今,唐帅的父母也依然不知他在何处上过学,学校大门往哪边开。
直到4岁那年,唐帅见父亲因患阑尾炎痛得在病床上打滚,但医生没法与之沟通,难以在第一时间诊断病情,唐帅只能无能为力地看着父亲的汗一点点浸湿了衣被。
“外婆因此专门找我谈话,她告诉我,如果不能跟父母沟通,又怎么能照顾父母?”还在学前班的唐帅,偷偷学起了手语。他的学习场所,是父母工作的金属加工厂。
唐帅最先学会的手语是“爸爸妈妈”。300多名工厂员工里有200多位聋人,“我一出现,他们就问我,爸爸妈妈呢?”唐帅儿时小脸圆乎乎,一头自然卷,好似洋娃娃,小酒窝格外招人疼,“叔叔阿姨喜欢逗我,常常拿着热好的饭菜给我吃。”
在反反复复的比划互动中,唐帅将一个个词熟记于心。更难得的是,学手语对他而言,毫不费劲,简直是过目不忘。
然而,偷学手语的唐帅被父母发现。为了不让他再去工厂,父亲借来电子琴,逼他在放学后练习弹琴。
父亲的阻拦并没有让唐帅停下。5岁时,唐帅就在工厂的职工大会上,坐在厂长旁边,成了小翻译。他一度很自豪,“这么小就轻松掌握了手语,因此我在那里社会地位还挺高”。
可自尊心却在一次交流中被重重打击。远嫁的阿姨来家中做客,“那个阿姨问我,你会不会交流?”唐帅伸出双手,给记者一点点演示“会不会”和“交流”的区别,“短短的一句话,就有两处和重庆的手语完全不一样。”
唐帅下决心要掌握手语的各地方言。从读小学起,几乎每个周末,他都揣上小本和笔,蹲守在重庆地标解放碑、朝天门,“只要看到拿手比划的人,我就上前”。那些年,重庆旅游业兴起,吸引了一批批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
在街头遇到主动学手语的非残疾小孩,对聋人来说,是件无比稀奇的事,人人都乐意聊。唐帅通常拉上他们聊十几分钟,遇上看不懂的,就拿出本子让对方在纸上写。有些格外热心的游客,还请唐帅吃饭、做导游,一聊就是2、3个小时。这种“守株待兔”的学手语方法,唐帅一直坚持至高中。
手语特长为他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工作机会。2006年起,唐帅为重庆各区公安机关的刑事案做手语翻译,一干就是7年,处理过近千件聋人案子。2007年,他通过自考进入西南政法大学法学专业,在2年半里修满了4年的所有学分。2012年,他成为全年级第一位通过司考的学生,获得法律执业资格证书。
唐帅终究没能像父母期望的那样,远离聋人,反而将自己和这个群体越绑越紧,再难分开。
荒漠中的水
当手语翻译的那几年,在聋人群体里,唐帅一度被认为是“最难攻克的人”。
他第一次参与聋人刑事案的翻译,只花了40分钟,对面的12名犯罪分子就主动招供。而此前,3名手语翻译用了十几个小时,也毫无进展。
甚至很多人传言,唐帅有“催眠术”,只要犯了罪的聋人在他手上,一定会招。
有个例子,唐帅总要讲给来访记者听。一次协助审讯一名聋人小男孩,这男孩从小在家没人管,饿到走投无路,杀了同村的老奶奶。男孩没上过学,也不会手语,唐帅就守在看守所,与男孩同吃同住好几天。终于,男孩在唐帅面前一步步重演了犯罪过程,还主动伸手,做出让唐帅拷手铐的动作。
“哪有什么催眠术?不过是把自己放在与聋人平等的位置上。”唐帅摇了摇头,“实际上,有时因为维权无路,一些聋人对司法有仇视心理。”
声名远扬的他,渐渐也被外地警方请去协助办案。他愈发体会到聋人群体在法律面前的无知与无助,更促使他走上执业律师的路。
湖南一名法官告诉过唐帅一句话,让他难以忘怀:“在涉及聋人的刑事案里,审判官往往不是法官,不是律师,不是检察官,而是手语翻译。”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在法庭上讯问聋人犯罪嫌疑人,要有专业翻译人员参与。唐帅介绍,一般司法机关会聘请特殊教育专业的手语老师,每次耗资上千元。但由于自然手语和普通话手语的区别,手语老师并不能完全正确地理解聋人的意思,看不懂时索性忽略而过或是翻错,甚至有时遇上连手语都不太会的聋人,只能猜表情。
唐帅曾在庭审上直接指出手语翻译偷工减料,对方羞红了脸。一个手势的差别,在日常交流中可能无伤大雅,但在刑事案中,犯罪嫌疑人面临的或许就是多年牢狱,重至死刑。
恐怕再没有哪位律师比唐帅更能感同身受,他理解这个群体的苦。他的父母1993年就双双下岗,唐帅凭借勤工俭学才勉强高中毕业。他放弃高考后,北漂打工,睡过公交车站,卖过衣服,还经营过酒吧,给自己一点点攒来了读大学的费用。
“很多时候,聋人就是被遗忘的群体。”他总想着能帮就帮,最多时,家里住了7、8位聋人。他给这些聋人每人5000元,还添置了卖手抓饼的推车,后来卫生整治,又把他们送去玩具厂上班。唐帅说,为了帮助聋人,他已陆续花费300多万元。
但更多的聋人,长年处于自生自灭的状态,仿佛社会的“局外人”。一次参与询问一名不满16岁的聋人少女时,唐帅觉得不对劲,医生检查后才发现,少女浑身都是被烟头烫过的痕迹。唐帅至今清晰记得,他和警察把少女送回家时,带着一堆慰问品和钱,却遭到她家人劈头盖脸的质问;“把她送回来干什么?你们养她吗?”没过几天,女孩又被送回偷盗团伙。
“社会和家庭欠他们的,该如何去还?”唐帅不由自主,用手敲了敲桌子,“在审判聋人案件时,最难的,就是罚、情和理。”
他告诉记者,聋人的世界往往简单,非黑即白,因此常走极端,一方面是由于法律意识淡薄,另一方面是圈子窄,文化水平也不高,更容易上当。
就在唐帅成为手语翻译的2006年,据第二次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资料,听力残疾者占残疾人的13.07%,总数超过2000多万。
在唐帅看来,这些仿佛身处社会荒漠的聋人,需要有人送水。
“手把手吃糖”
△事务所的办公室里,聋人助理和实习生在工作。 张凌云 摄
采访间,唐帅的电话和微信一直没断过。找他的人太多了。
256G容量的新款手机,唐帅拿到手没多久,就卡到几乎用不了。他有两个微信号,好友人数都已添至上限。看他的微信好友申请记录,手指飞速,滑了5分钟才滑到底。
今年年初的一天,他的微信突然在几小时内收到上万条好友申请,还被拉入上百个微信维权群,挨个仔细询问才发现,他们都是一起全国聋人庞氏骗局案的受害者。
“因为沟通上的问题,处理聋人的案件通常都要花费普通人3倍甚至更多的时间。”唐帅说,几乎每天,事务所工作人员都要帮助聋人向公安机关报案、整理笔录和证据,一位聋人就要花上3-5个小时,复杂案件则耗时数日。
四面八方涌来的疑问,时常让唐帅无奈至极——“律师和法官有什么区别?”“怎么才能办离婚?”他开始在重庆大渡口区给聋人做普法讲座,1-2个月1次,每次至少来了四五十位,年龄从十多岁到70多岁不等,多时达上百人。讲座结束后,他常被聋人围住。他们挤成一圈,久久不愿散开。问题很多,却大多与法律无关。他们问唐帅多大了,有没有结婚……在他们眼里,能见到一位交流无阻的非残疾人,实为罕见。
普法有效:年初的庞氏骗局案,在大渡口区,无一位聋人被骗。
唐帅告诉记者,从他接触手语翻译至今,聋人犯罪手段发生了巨大变化。十来年前,案件以偷盗、抢劫为主,而今,多数变成了更难察觉、侦破的金融诈骗。
经过社会调查收集了聋人最关心的法律问题之后,唐帅专为聋人拍摄了几期普法小视频。视频里有“两个唐帅”,一个用口语讲述,一个用手语实时介绍。画面中间则是不断变化的动画,比如用狼以高额回报欺骗兔子来科普庞氏骗局。他给普法栏目命名为“手把手吃糖”。“一是我姓唐,和糖同音,更方便聋人记住;二是希望这个普法视频能像糖一样,让人轻松接受并消化。”
为了帮助更多人,他还自掏腰包,投入200多万元开发了一款APP。构想简单,“你问我答”,事务所的律师上线解答聋人的法律问题。不久,唐帅发现他想得太简单,颇感无力,“很多人最高只有初中水平,连手语都不会的也大有人在,他们看不懂回答,也不知道该怎么问……”苦苦支撑了一年多,唐帅无奈放弃,转向微信公众号。
帮众律师的公众号里,聋人可以通过视频用手语在线询问。单次咨询39.9元,每次持续2小时,这是根据重庆司法局最低服务收费标准计算的成本费。事务所的律师,也为聋人上门服务,但从未收费。“如果要上门服务,那这个家庭一定非常困难,怎么可能还去收费?”唐帅说。
目前事务所处理的案件中,聋人相关案子占到30%。只要聋人找上门,唐帅一定会接。“真的不能再多了。每一个聋人案子,就要好几个普通案子去补。感觉有种‘劫富济贫’的意思。”唐帅坦言,“绝大多数根本出不起请律师的钱,每四五十个案子里可能才会有一个按照正常标准交费。”
今年的大渡口区人代会上,唐帅作为区人大代表,提交了一份建立手语翻译协会的议案。他希望吸纳更多精通自然手语的翻译人员,促成国内手语翻译的标准化。
他总觉得,可以为聋人做的还有许多。
被选中的人
“案子太多忙不过来,我试过让律师们都来学手语。”唐帅说,他自己花钱,请手语老师每周来所里上手语课。大家起初信心满满,半年后,唐帅做了测试,才不得不承认,这条路行不通。并非人人都如他当年,一学就会。学得最好的也只能比划几个词,一到对话,全懵了。
在最焦虑的日子里,唐帅曾整夜整夜地失眠。睡不着时,一部纪念邓小平的纪录片点醒了他:“‘港人治港’这个词反复在我脑海中播放。为何不能让聋人学习法律,参与聋人的法律案件?”
他立刻在全国聋人和高校圈里发布信息,招聘聋人助理。应聘者有七八十位,他精选出5位。“我本想着让这些助理做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就够了。”唐帅承认,他起初有过疑虑,并没想过能走多远。
这5位毕业于重庆师范大学特殊教育专业的聋人,其中邱福林因小时候注射青霉素而近乎失聪,幸运的是,残存的些许听力让他学会说话;还有一人与邱福林类似,在掌握手语的同时也有一定说话能力;另外3人则完完全全必须通过手语交流。
学习法律,无疑是从零开始。唐帅给每人都买了全套教材,让他们边工作边学习,所里的律师便是老师。大多时候他们通过幻灯片教学,其余时候看书自学。
5名助理的主要工作之一,是视频帮助聋人解答问题。眼下,邱福林的手机里也有上百个聋人维权群。有时下班路上,他会接到聋人打来的视频电话,“在下班时间找来,一定是很紧急的,必须接。只能一手举手机,一手比手语”。
两个月后,这些年轻人出乎意料地渐入轨道。唐帅大胆决定,让他们参加司考。
今年,事务所又来了一批特殊教育专业的聋人实习生。办公室里,大多数时候都极其安静,因为这里一大半均为聋人。
今年,唐帅还尝试在全国范围内招聘手语翻译界的牛人,未来能够配合律师处理案件。来应聘者不少,最远有来自内蒙古的手语翻译。经过反复面试,唐帅在众多应聘者里选出2位。他的要求很高,这些手语翻译要和他一样,精通各地手语方言。
毕竟,找到唐帅的人越来越多,也不再局限于国内。他刚刚接手了一个日本华侨的案子,还有印度的聋人找来。即使放眼全世界,在做手语律师的道路上,唐帅也是先行者。
“我没有前人可以借鉴,只能不断地试错和探索。”唐帅坦言,这么多年,不是没有想过放弃。“好像老天就是选中了我,这么容易掌握了手语。每一次我熬不下去,第二天就立马有聋人找上门,求我帮忙。”他认真看向记者,“的的确确是每一次。”
唐帅把这些巧合看成是天意。他说,这种非常人的极致工作状态,他不知还能坚持多久,但至少现在,他要对得起对他有所期望的聋人,对得起自己,对得起初心。
初心是什么?或许就是夜深人静时,整栋楼里那盏唯一亮着的灯。
原标题:走红网络的全国唯一手语律师唐帅,并非聋人,办公室却极安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