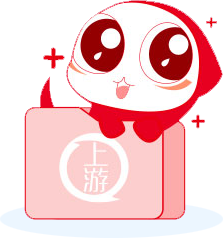

林语堂的抗战岁月 在重庆躲避日机空袭照片曝光
澎湃新闻消息,来抗战话题很热,学界研究有很大进步,媒体也很关注。我也凑个热闹,讲一个人的抗战故事——他的战场主要不在中国;他用的武器不是弹药,而是一支笔,一支写英文的笔——希望可以扩展我们审视抗战的全球视野。
我个人非常赞同中国抗战历时十四年,而不只是八年。中国抗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部分,世界史也应如此写。可惜,世界史欧洲中心主义还是根深蒂固,不仅认为“九一八事变”不是世界大战的起点,“七七事变”也不算,都说“二战”是1939年至1945年,中国人也跟着说。起码可以说广义的抗战十四年,狭义的抗战八年。“九一八”的时候林语堂在英国,次年回国后创办《论语》等刊物,在文坛掀起一股幽默清风,这都是广义抗战背景下的产物。特别有两篇调侃时任日本外相广田君的小品,那真是奇文。
但这里还是讲狭义的抗战阶段。这又可以分三个阶段:“七七事变”到珍珠港事件美国参战,再到盟军诺曼底登陆,再到两颗原子弹结束战争。三个阶段的焦点、议题都不一样,我这里只讲前两个阶段。
我们知道,林语堂因《吾国与吾民》一书在美国一举成名,他的书商兼朋友华尔希、赛珍珠夫妇邀请他赴美。1936年林语堂一家赴美后又写了另一部更为畅销的书《生活的艺术》。
我们先看一下战时林语堂的足迹:
1936年8—1938年2月:美国,纽约(1937年8月,古巴度假)
1938年3月—1939年7月:法国,芒东镇/巴黎
1939年8月—1940年3月:美国,纽约
1940年5月—8月:中国,重庆
1940年9月—1943年9月:美国,洛杉矶/纽约
1943年9月—1944年3月:中国
1944年3月—1948年7月:美国,纽约
林语堂本来打算在美国待一两年,写一本哲学书,即《生活的艺术》,如有可能的话再到欧洲住一段时间。现在抗战全面爆发,书还没写完,但林语堂决心已定:回国投入抗战。当时林语堂的美国朋友华尔希、赛珍珠等人对这种“爱国热忱”非常不以为然,认为在这个时候,他应该留在美国,向美国人讲解中国,以此为中国发声。还有读者主动给出版商写信,询问林语堂的去向,是否安全。
但林语堂不听,坚持要亲身回国参战。《生活的艺术》写完出版后,他便离开纽约,试图经欧洲返国。结果在欧洲滞留了一年,撰写小说《京华烟云》。次年8月,欧洲战场乌云密布。林语堂在巴黎待不下去了,又转回纽约,处理《京华烟云》的出版事宜。次年3月,林语堂安排好以“普通人”的身份,全家一起乘海轮回国。可当时林语堂已经是国际知名作家,媒体追踪他的一举一动——一到重庆就有媒体报道,躲避日机轰炸的照片立即被登出。蒋介石和宋美龄也马上接见他,从此他们保持着通信联系。

林语堂(右起第三位)一行在重庆躲避日机空袭,1941年。左起第三位是林语堂长女林如斯。台北林语堂故居藏。
林语堂就自己应以何种方式抗战求助蒋宋。他们明智地决定:到美国为抗战发声,比在重庆躲炸弹有用得多。于是林语堂又回到美国,作为中国的“民间声音”,虽然是以“蒋介石侍卫室官员”的身份拿的外交签证。
我们可以从林语堂在抗战期间扮演的不同角色来看这一个人的抗战:
第一,林语堂是个“记者”,给《纽约时报》等美国报刊撰写时事报道,第一时间通报中国情况,阐述中国的“民间声音”。
第二,林语堂在美国的成功在于推介中国文化,被誉为“中国哲学家”。抗战全面爆发后,他运用其文化资本,用艺术手法(小说创作)呈现中国人的抗战形象,同时着重阐释一个“现代中国”。
第三,他是一位后殖民批评家,号召运用中西智慧共同创建一个新的文明。
第四,担当“国师”的角色,给蒋介石建言。
第五,担任中美文化使者的角色,给中美两国老百姓做信使。
一、战时记者
“七七事变”后不久,全球媒体聚焦中国战事。8月《生活的艺术》完稿,林语堂到古巴度假,《纽约时报》发电报追来约稿请他谈谈中国时局。《纽时》的意思是要这位“中国的哲学家”谈谈中国人会如何运用自己的哲理坦然接受被征服的事实,或许将来再在“文化上”做功夫。林语堂和《纽时》反复来回电报,最后一口拒绝,坚称这次中国人会战,哪怕是用自己的身体去堵敌人的枪口。给出的理由是:中国民族主义的兴起、中国人民的士气、蒋介石的领导,以及打持久战中国拥有辽阔疆土的优势。在此际,中国有林语堂这个“民间人士”在《纽约时报》发声,其作用真是金不换。林语堂自“九一八”以来,一直是主战派。他并不是不懂“中国有长程哲学,却没有短程炸弹”,但他认为,一个民族的精气神更为重要,战争的输赢并非完全由炸弹的数量来决定。因为没有炸弹,便使劲压制民族主义情绪,不如放开一搏,用空间换时间,打持久战,“只要战争打成僵局,中国就实际上赢了。”但这需要中国人民付出巨大的牺牲,敢于“坚壁清野”,才能耗得住。当然,外援也是至关重要的,中国的抗战是世界大战的一部分。
林语堂还在重庆时,便给《纽约时报》发了一封快报,揭露日机轰炸的残忍。林语堂说,这些轰炸显示“日本人竭尽全力要摧毁中国人的财产、让中国人胆寒”——他们达到了前一个目的,但没有达到第二个目的。星期二上午,轰炸后的浓烟未消,林语堂上街逛了一逛,看到有商铺已经在街上摆出瓷器在卖。林语堂写道:“这儿摆的不是中国的瓷器,而是中国人的胆量。”他确信:“战争一定会赢,靠的就是这种中国胆。”
为了争取美国舆论,林语堂经常以“读者来信”的方式《纽约时报》写信,比如就美国不断给日本输送原油一事便写过好几次,以表抗议。珍珠港事件前夕,美日之间曾有秘密高层会谈,美国倒向日本并非不可能。林语堂为此大声疾呼。林语堂及时向《纽约时报》写信,以“一个中国普通老百姓——他现在是远东最重要的个体”的身份,阐述“中国的民间意见”。林语堂警告,日本此时的谈判只可能是策略性的,任何出卖行为都会遭到四万万中国人的唾弃,他们在这场战争中已经付出了无法想象的牺牲。华盛顿的外交家最好清楚了解这一中国民间立场,除非日本完全撤出中国,一切方案都会无效。
1941年11月25日,美国书籍销售商协会和纽约《先驱论坛报》在纽约阿斯特酒店举办“读书与作者”午宴,林语堂应邀作演讲。林语堂在演说中说,他感到很“困惑”,中国的抗战究竟是不是为民主或民主国家而战,“因为此时民主国家都还没决定到底要不要战”。林语堂告诫,日本人说的话、日本天皇签的字和希特勒说的话和签的字一样可靠,美国必须准备好和日本开战。“林语堂明确表示,美国已处于和日本交战前夜,他敦促美国人不要再三心二意,而是要接受这个冷酷的事实。”

林语堂1941年在纽约“读书与作者”午宴上发言。台北林语堂故居藏。
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那天,林语堂受邀到亨利·卢斯夫妇家参加午宴。卢斯当然一向支持中华民国。卢斯的传记作者斯旺博格这样描述当天午宴时宾客听到这一突发新闻时的情景:
参加家宴聚会的包括希恩、美国驻莫斯科大使斯坦哈特、林语堂博士、考尔斯、凯斯和《生活》杂志的桑代克。下午两点半,主人和二十二位嘉宾各就各位,午宴开始。卢斯家有个家规,吃饭时不接任何电话。然而,吃甜点时,有个电话打进来,管家觉得此事非同小可,便把信息写在纸上,放在小盘里递给餐桌上坐着的卢斯夫人。她看了一眼,随即用汤匙敲了敲玻璃杯。
“所有孤立主义者和姑息者,请听着,”她说,“日本人轰炸了珍珠港。”
现场一片骚动,惊讶,大家都抢着去听电台、打电话,想获取更多细节。宾客中只有一人神情镇定,一动没动。林语堂先致歉—他得把甜点吃完了,然后说:“瞧,这种事早就注定的啦。”
二、“中国哲学家”
林语堂在美国以“中国哲学家”的形象为美国中产阶级读者阐释“中国智慧”而家喻户晓。抗战全面爆发后,林语堂利用这一文化资本,竭力阐述一个“现代的中国”,以纠正《纽约时报》那种中国人只会“哲学地”接受日本统治的观念。
《吾国吾民》1939年再版时,林语堂写了一篇长文——《新中国的诞生》,作为该书第十章,庄台公司还同时发行单行本。该文一开始便提出核心问题:“我们古老的文化能够拯救我们吗?”林语堂的回答非常干脆:不行,“只有现代化会救中国。”“中国别无选择,只能走向现代。‘现代性’不请自来,”林语堂如此解释抗战之前中国的现代化过程。
林语堂特别强调,当代中国已经不再是一个“文明”,而是一个民族/国家,爱国主义情感高涨。
日本的武器弹药、军事实力远远超过中国,但日本要征服的是一个现代的、具有强大的民族认同感的中国。日本政客扬言要用坦克摆平反日情绪,林语堂讥讽道:任何一个头脑清醒的人都不会想用武力来扫除某种情感。
为了突显中国老百姓在抗战中的爱国精神,林语堂还特别指出中国抗战中“最振奋人心的场景”——战时大合唱。当时最为流行的一首歌叫《义勇军进行曲》,聂耳作曲,田汉填词,林语堂把它译成了英文。当然,这就是我们现在的国歌。
要把“文化中国”和“战时中国”两个迥异的形象相结合,并不是件易事。林语堂的策略之一便是用中国文化和人民的温良恭俭、可亲可爱来衬托日本军队的残酷和野蛮。于是,他创作了两部史诗式的抗战小说:《京华烟云》、《风声鹤唳》,用艺术的形式,从文化的角度,为中国抗战摇旗呐喊。
《京华烟云》扉页写道:“本小说写于1938年8月至1939年8月,谨此献给英勇的中国战士,他们用自己的生命,为我们子孙后代的自由,而战。”但小说并不是直接描述战争本身,而是着重描绘战争的现代历史背景。用长达八百多页巨幅勾勒出现代中国的图画,强调新旧文化的现代转型,以调和多姿多彩的中国生活方式和血腥的战争场面之间的紧张。
小说一共有三十多位女性人物,从传统型到现代型,或介于两者之间,从激进叛逆的黛云到古典优雅的曼娘。曼娘是传统女性的典范,一生恪守旧的礼俗,但小说的情节安排赋予曼娘一个关键作用——由她来决定中国该不该进行抗战:
“你觉得中国应该和日本打吗?”木兰问道。
“如果像这样发展下去,还不如打一仗,”曼娘说。
“怎么能让阿轩赤手空拳和鬼子打呢?”木兰记得她爸说过:“你问曼娘。如果曼娘说中国必须战,那中国就会胜。如果曼娘说中国不能打,那中国就会败。”
“你认为中国可以和日本一战?”木兰又问道,一个字一个字说得很慢。
“不管中国愿不愿意,都必须去战。”
好了,曼娘把话说了!
抗战一打就意味着中国老百姓要付出巨大的牺牲,而小说中曼娘的死正是这种牺牲的悲壮象征。
另一部小说《风声鹤唳》,其文学历史价值在于:该部小说第一次纪录、揭露并谴责了日军在“南京大屠杀”中所犯下的罪孽。正如林语堂指出,造成“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一次迁移”的原因并非战场上的恐怖(诸如空袭炸弹或枪林弹雨),而是由于日军攻占南京后那些丧尽天良的行为。
林语堂进而把日军的大屠杀和“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张献忠四川大屠杀相比拟。林语堂评介说,两者都极其疯狂、极其变态,不过有一点不同:张献忠“没有一边屠杀老百姓,一边还嚷着要建立‘新秩序’。他杀别人,也清楚知道自己会被别人杀掉”。
三、后殖民批评家
珍珠港事件后,美国参战,中国的抗战局面完全纳入世界大战格局。可是中国战场并没有受到重视。二战实际上也是二十世纪思想意识形态领域的缠斗,除了西家的法西、东家的普罗,还有“白人”的帝国主义、种族主义、殖民主义——以丘吉尔为代表。林语堂称之为“现代病”,对此集中火力猛批,并希望战后东西方能够共建一个“新文明”。
此时,林语堂在国际舞台上为印度独立大声疾呼。
如果印度人不能独立自由,他们为什么要为英殖民者卖命——难道是为了自己继续被殖民统治?林语堂指出,这场战争已经使殖民逻辑变得十分荒唐,他呼吁英国人“别再自欺欺人了”。
1942年8月6日,林语堂和众多名流参加于纽约市民会议厅举行的集会,引用美国历史说:“甘地是个傻瓜,因为他要争取的就是华盛顿为之奋斗的——为他的国家从英国获得自由和独立……对印度的不公就像以前英国对美国殖民地和爱尔兰殖民地的不公一模一样。
现在美国人自由了,他们忘了没有获得自由的民族对自由有多么向往。印度问题就是这么简单。”
德国人和日本人都公然宣称自己的种族歧视政策,但如果我们认为“只有纳粹才有种族优越感”,那也是一种幻觉。林语堂希望美国能够带头唤醒全世界,为全世界各民族的平等摇旗呐喊,只有如此,“这场战争才会逐步转变成为道义和精神原则而战,‘种族优越感’也就迟早会消灭。”
1943年9月,林语堂被选为美国印度联盟名誉主席。林语堂给联盟主席辛格(J. J. Singh)致信接受这一“非同寻常的荣誉”,并再次阐明其对印度的立场:
我坚信,印度的自由是我们大家共同的责任,因为印度的自由和世界的自由不可分割。这个世界不能一半自由一半被奴役。
我知道印度有自己的民族问题和困难,就像中国和其他国家一样。但我要每一个印度人都有为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的自由。解决自己国家的问题的政治自由的机会都被剥夺了,这是何等的羞辱。这是你们要争取的首要权利——解决自己问题的权利,如果你们得不到这个权利,其他权利对你们来说都是没意义的。我无条件支持印度的自由,我愿意向全世界宣告我的立场。
1942年美国圣诞季节书市推出林语堂选编的《中国印度之智慧》一书,大为畅销,一时出版社都没有纸张来印,因为战时美国有纸张限额。林语堂的“东方智慧”让当时美国变得“洛阳纸贵”了。
林语堂自己却认为《啼笑皆非》乃其最重要的作品。该书尝试让东方智慧作为资源,对战时政治以及由“科学唯物主义”(特别是所谓的“地缘政治学”)统领的西方文化现代性展开批评。
十九世纪帝国主义兴起,白人征服了全世界,那是“因为白人有枪,亚洲人没有”。丘吉尔可以不让印度独立,但丘吉尔摆脱不了报应。假如西方精英和决策者拒绝承认这种历史潮流,那么,林语堂说得很直白:他们就是在为第三次世界大战播种,那将是一场恐怖的、白人对全世界有色人种的大战。
当今世界急需一种和平哲学,可是在二十世纪文化中是找不到的——林语堂称之为“道德上的恶性肿瘤”。“所有导致战争的根源——权力平衡术、强权逻辑、贸易、种族歧视——一个不少,原封不动。”二十世纪西方文化把人理解为经济人。和平的问题,或者说为什么无法思考和平的问题,就是起源于这种经济至上思维模式。
当今世界没人谈和平哲学,国际关系领域的主流话语只讲霸权和武力,美其名曰“地缘政治学”,林语堂称之为“伪科学”、“血腥地球学”。
“地缘政治学”正是纳粹的指导思想,希特勒《我的奋斗》一书正是诠释德国地缘政治学大师卡尔·豪斯霍弗尔(Karl Haushofer)教授的理论。但豪斯霍弗尔其实并不是地缘政治学的创始人,这个“荣誉”要归英国人麦金德(Halford MacKinder)。林语堂惊讶地发现,在1942年,这个臭名昭著的纳粹意识形态居然是最受美国大学教授欢迎的理论,并通过他们深深影响美国公共舆论和政策。
林语堂称这种地缘政治学为“道德卖淫”,和纳粹意识形态如出一辙,对世界和平遗害无穷。针对地缘政治学赤裸裸地崇尚强权逻辑,林语堂请出老子给与反击。如:“夫佳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恶之,故有道者不处。”“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为上。”
《中国印度之智慧》“中国智慧”部分有一长篇“引言”,以一段诗文结尾,对弗洛伊德主义竭尽讽刺挖苦,并呼吁东西文明相会共建新文明:
我们的心灵和身体再也没有隐私;
这帮精神历史的学者撕掉了我们身上的遮羞布,戳破所有神秘,
把我们赤裸裸、战战兢兢的灵魂丢进灶房间,把厕所变成了公共画廊;
他们让爱情祛魅、让浪漫之酒变酸,拔掉傲骨的羽毛,让其在光天化日下赤裸人类神圣的内在心灵,被抛出神殿,代之以臭烘烘的利比多。
人性的概念被颠覆、被糟蹋。屁股从人体中打掉,支架不住;必定得垮。
现代知识已经支离破碎,在其废墟上一个新世界必须重建,必须由东西方共建。
四、“国师”
林语堂第一次回国后和蒋介石、宋美龄建立了个人关系,有信件显示,林语堂是最早策划宋美龄访美的。他曾写信敦促宋美龄接受访美邀请。
美国参战后,整个策略是欧洲优先(先救英国),蒋介石派了熊式辉将军率领中国军事代表团赴美参与同盟国的战略策划,结果被冷落,基本无所事事。林语堂在美国作为中国的民间发言人发声,但对国民政府当时的外交非常不满,而时任驻美大使是胡适。
林语堂在给华尔西的一封信中发泄自己的不满:
……就是整个曹锟时代北京政府的心理在作怪。宋子文在中国谁都不怕得罪,可是在美国那样谨小慎微,生怕得罪美国政府,哪里敢把中国当成平等的同盟国,只顾着到处磕头,只是搞定了三十架飞机(还是明年才能交货),那个千恩万谢啊。我们的外交家在这里慷慨儒雅,而我们十七八岁的小伙子在付出自己的生命,我们坐在这儿唱高调儿。我每次和人讲起这事,往往一下就火冒三丈,控制不住,甚至当着夏(××)的面也大发雷霆。美国在许可证制度下每月给日本输出成千上万吨原油,却忽视中国,到底是谁的责任?为什么中国会被遗忘?胡适敢抗议吗?如果我们自己把自己当成被殖民的人,那也不要怪别人把你当成殖民地的人,这些人就是被阉割了的殖民地人,都有白人情结。要是中国人自己不能摆脱这种心理,不以平等者自居,那有谁会平等待你呢?和人民太脱节了,就是这些人的糟糕之处……
我知道我在这个星期天《纽约时报》上写的区区小文已经要得罪胡适了,可我管得了这么多?我相信,你和赛珍珠可以做点功夫,比中国人自己做效果要好多了。我们可以做个游戏,你去试试,让胡适或宋子文做个公开呼吁,给中国多要几架飞机。你还不把他们吓死。
于是林语堂直接给蒋介石上书,第一次上书后得到蒋的鼓励,“请多指教”,于是他又写了几次,主旨就是要摆脱被殖民心理,进行“革命外交”,扮演了“国师”的角色。比如,林语堂“指教”道:外交就是“布迷阵之道”,宋子文要访美,他应该先路经莫斯科转一下,即使他在苏联什么事也没有。
五、文化使者
林语堂在美国不是高谈阔论中国哲学、儒家智慧,而是真正扮演文化使者的角色。这里举两个例子。
1941年1月20日,美国罗斯福总统第三届任期宣誓就职,国家广播公司(NBC)为此做了一个特别节目“全国万众一心”,邀请包括林语堂在内的几位国际知名人士共同探讨。面对千千万万美国听众,林语堂如此说:“今天我们庆祝美国的民主盛典,我能想到的最恰当的颂词是:孔子两千五百年前梦想的民主与社会公义正在今天的美国逐步实现,一个和平、自由、人人享有公平正义的梦想。”
1943年9月22日,林语堂离开美国第二次回到战时中国,走之前,他上哥伦比亚广播电台做节目,向听众说再见,并同时盛邀美国听众以个人名义给中国人写信,以增进两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由林语堂把这些信亲自带到中国。林语堂的呼吁得到美国听众热烈的响应,他收到很多来信,最后带了六百封到中国。以下挑选几封信的段落,以见证中美关系史上罕见的“民间亲善交流”。
马里昂·阿尔特曼(Marion Altman):
……我们只能希望这个多灾多难的阶段马上就会结束,我们可以在较为和平的环境中发现对方。我们时刻心系你的同胞。我们也会力尽所能,提供一切可能的援助。请转告他们……
约瑟夫·古德伯格(Joseph Goldberg):
……你回到你的祖国后,请告诉你的同胞:北美人民和他们心连心、肩并肩。中国应该做的(等他们能做的时候)是:派一些学者过来,在我们的学校、大学和公共机构给我们讲解中国文化,多给我们讲一些中国人的生活方式……
约翰·莱利 (John H. Riley):请把我的名字也写上。等你回到中国后,请去看一下我的儿子,他叫弗朗西斯·莱利(Francis X. Riley),美国陆军航空队中尉。你告诉他他老爸说的:给我狠狠地打日本鬼子,要他们加倍偿还他们给中国人造成的痛苦。我儿子现在在中国帮助你们的宏伟大业。

原标题:文章报国:林语堂的抗战岁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