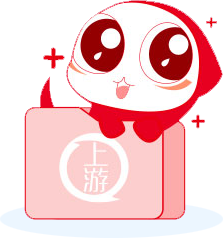

重庆珍档丨九旬老人曾任重庆新华印刷厂厂长:上街发《大公报》号外,我特别自豪

△《大公报》号外长这个样子。
今年90岁的戴光斗先生曾任重庆新华印刷厂厂长,他祖籍广西桂林,1942年进入因抗战撤至桂林才一年的大公报社当印刷学徒。1944年9月12日,印制桂林大撤退前《大公报》最后一期报纸后,随报社最后一批员工逃往重庆。1949年后,戴光斗随大公报社印刷厂并入新成立的重庆新华印刷厂,完成过中共中央党刊《红旗》杂志在重庆和北京同时印发、7个月内印制十卷本《巴金选集》并同时上市等不可能的任务,颇多建树。我们将用三期专栏打望老爷子传奇般的印务生涯。
桂林
小时候,戴光斗想不到有一天会到重庆来。老家桂林山清水秀,是一座父亲用双脚丈量的小城,“我老汉做小生意,挑担卖油,当时桂林只有象鼻山上有一个发电厂,除了有点路灯,老百姓基本上点煤油灯。父亲在阳桥、桂南路南边这一带卖,做生意做得还比较好,大家都很信识他。抗战以后煤油紧张,不许民间买卖,就改成卖菜油了。”
戴光斗从小就爱唱歌。“有个教音乐的桃老师对我影响特别大,她齐耳短发,短的衣服,有点像解放装。第一首歌就教《保卫黄河》。她跟其他的音乐老师不同,一上课就把歌词写在黑板上,先讲意义,然后才教谱,再唱,大家都很喜欢她。我特别喜欢唱歌,每次儿童节合唱,她都把我弄去当领唱,还带我们几个她喜欢的孩子,去看新安旅行团、厦门儿童工作剧艺团、七七剧艺团排演节目。我现在想,这个老师可能是个进步分子。”
后来因为家里困难,跟大哥、二哥一样,戴光斗失学去当学徒。“在进大公报社印刷厂之前,我进了一家小厂达德,五一节,厂里接了一个4开套色画报,用石印来印的,在石板上铺开,用棕刷几刷几刷就印出来了。老板叫我送到桂西路客户家,我一看打收条的那个人,就是桃老师,我们两人都愣住了。她问我怎么不上学了?我说家里实在是供不起了,只有出来做学徒。她也很难受,最后送了我两本书:一本抗日歌曲,一本小学教师用的语文教材。叫我一定要学文化,人不学文化没有出息的,‘抗日歌曲你要好好唱,能够鼓舞人的士气。,讲得我眼泪巴沙的,我走了很远,回头看,她都一直站在门口把我看到。”
桃老师还教了戴光斗一个唱歌练嗓的绝招,后来到重庆,还真管用。“她说你的嗓子很可贵,要好好保护。你要练嗓子,就到河边去,听流滩的水声,那个声音是不变的,用低音去合,它也合得起;用中音和高音去和,也和得起。到了重庆,李子坎有个拦河堤坎,听得到水声,我就在上面练嗓。”
报馆
1942年,经大哥介绍,戴光斗进入大公报社。“哥哥先在大公报社印刷厂上班,我进去之后,薪水是19块钱,在当时算是高的了。”
桂林大公报馆的环境相当好。“报社来建馆的是王文彬,他是发行人,找了国民党部队的一个营房办报,是七星岩的后山,门口一道狭窄的山峡,是一块天然的防空地带,飞机在上面根本看不见。大门是用桂林那种山石垒的四四方方的门,一条路直通里面6、70米,就是一根旗杆,左边是季鸾堂,再里面就是胡霖(胡政之)公馆。当时报馆有8、9部国产的对开平板机,报纸送进城是人挑,没通车,后来宪兵团才修了一条简易公路,叫宪五路。”
民国著名报人吴鼎昌、张季鸾、胡政之是《大公报》开山三巨头。他们主持的大公报,氛围更好。“凭良心说,大公报还是比较民主的。吴鼎昌当了贵州省主席后,就不兼大公报社的社长了,因为大公报讲一个‘不私不党’。平时根本不分哪个是职员哪个是工人,人事上也不搞裙带关系,很多编辑、记者都是从练习生培养的。他们发新闻稿到排字房来和我们工人的接触是很融洽的:这个版子怎么拼,这个稿子摆不下了,怎么办?怎么挤,我们那个铅条有二分条三分条,把条抽薄一点,文章就可以挤,就可以插一条短新闻进去。编辑、记者穿中山服的比较多,穿西装的不多,好像没有穿长衫的。我们进报馆当学徒,一人发了一套中山服,伙食也好。”
季鸾堂是大公报的精神空间。“我进报馆时,张季鸾已经死了,大公报在任何地方的礼堂都叫季鸾堂,就是为了纪念大公报的元老张季鸾。职员活动、食堂都在那里,桂林大公报组织的职工夜校也在里面,所有的文化用具,都是报馆买。语文、历史、外语,都请的专业教师。外语就是外文编辑黎秀石的夫人汪克柔教,他们都是燕京大学毕业的。当时我才12岁,是失学儿童。大公报人的社会责任感相当强,记得在开学典礼上,经理金城夫说:‘很多家长都把自己很好的孩子送到我们这里来,我们要是放任不管的话,就会让有些人带坏了!我不但对不起这些娃儿,也对不起别个的家长,更对不起社会。’‘带坏了’他指的是报社里面还有一部分勤杂人员,有的是国民党的兵痞下来的。金经理这些话我听了非常感动。这是我读过的最好的学校。”
号外
《大公报》一般一日出对开一张,四个版,有的时候再出个加张,就是六个版。“有时还出个号外,就是有大事情了。日本人打湘桂的时候,我们有时候也打点胜仗,真假我们就搞不清楚了,就发号外。《大公报》的号外有一个特点,不收钱,但是也不发给报贩子,就由报馆的职工拿出去散发,我也是最积极的一个,哇,打了胜仗了,抓起一叠号外就夹起跑。”
从大公报馆一直跑,经过六合路,跑过漓江大桥进城,到桂东路,桂林最繁华的地区。“桂东路绸庄、金店特别多;桂西路就是文化街,龙门出版社、商务印书馆、正中书局就在这里。发给别人看,别人抓去看,我相当自豪。报贩子也在吼,狗日的不拿给我们,他们拿去就要卖钱。所以大公报为了把好新闻尽快让老百姓知道,不收钱,就用大公报的职工拿去发。但也是自愿的,你愿去就去,不去也没人说你。号外就是16开大小,平时版面一半的一半,一般就几行字,我军又什么又什么。为什么我对发号外这个事情这么积极呢?因为抗战时有个说法,叫政治的重庆,文化的桂林,桂林出版社特别多,戏剧团体也多。所有文艺界文化界的人,大部分都要经过桂林停留,那个时候就演了《抓壮丁》的,我就喜欢这些。”
发号外的时候,戴光斗的衣服都遭别人抓抢时撕烂了!“当然主要是有些报贩子在抢,但我心里还是很舒坦,衣服抓烂了,我也觉得不可惜,就觉得很自豪。一来是我们的军队打赢了,二来打赢了的消息,是我印出来的。”
文/图片翻拍 上游新闻·重庆晨报记者 马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