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舒舒,原名舒玲敏,女,80后,重庆市作家协会会员、秀山县作家协会会员,现居秀山。重庆市“第一届中青年作家高级研修班(小说)”学员、重庆文学院第五届创作员。以小说创作为主。创作题材多涉及社会基层生活、乡村生活。有作品散见于《小说月报·原创版》《红岩》《红豆》《重庆日报》《重庆晚报》《梵净山》《夜郎文学》《散文家》《酉水》《秀·SHOW》等报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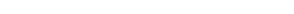
舒舒:文学是心中的光
(本期访谈主持人:陈泰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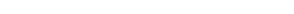
上游文化:舒舒,你好!据我所知,你没有固定的工作,还要供两个孩子上学,至少目前又还算不上专业作家或职业写作者,生存和写作是你必须同时面对的两个问题。那么,你在生存和写作的关系中产生过困惑吗?最终又是什么促使你将写作延续下去,并走到今天的?
舒舒:在很多人的意识中,总认为生存与写作是相悖的。因为绝大多数写作者为了生存不能兼顾写作,而写作需要时间和静心,微薄的收入无法满足生存的需求。事实确实如此,有许多写作者确实也因为生存而放弃了写作。曾经也有人如此暗示过,我亦受此影响。但最近我才领悟到,生存是生存,写作是写作。写作和生存就像左手与右手,处理得好,相得益彰,处理不好,手忙脚乱。一般情况下,左手端碗,右手拿筷,有什么问题?没有任何问题。生存和写作单放在一边都是不容易的。但为什么总有人说是为了生存而放弃写作?因为有人把生存的不容易,推在写作的头上。同理,也有人将写作的不容易推在生存的头上。都是给懒惰和放弃找借口和台阶。我很庆幸自己认清了这个概念,否则,生存得不容易,我也会说是为了写作才搞得如此糟糕的。写作可不背这样的锅。这就像我们总寻找真爱,但却不明白,只有经得住时间和困难考验的才是真爱。
关于我在写作路上是怎么走到今天的?我认为生命有着某种神秘的牵引性,是一种潜意识的行为,它是按照种子最初的遗传形态,根据潜意识的某种暗示而运行的。侧重点不同,显示出的天赋和能量也就不同。就像一台电脑,想要获得更多的数据就必须读取数据库里的信息,如果不懂代码,就无法打开数据库。要打开数据库,唯一的途径只有学习更高层次的代码。这代码是什么?代码就是自我向内探索的方法和途径。我很感谢自己没有放弃寻找打开文学之门的代码,并持之以恒。我遵从于内心的指引。虽然生活也曾捉襟见肘,但我从未将写作视为生活的负担。写作于我一直是心灵的慰藉,帮助我陪伴我渡过生命中的一次次难关。我甚至想过,若不会写作,会是什么样?是否还存在于这个世界?生活的铁爪贯穿躯体,黑夜的鬼怪浸入灵魂啃噬。我虽一直用灿烂的笑容掩盖生活猛烈撞击的伤痕,但留下的后遗症却一直被文字默默疗养。我很庆幸还能写作。写作不仅让我与生活和解,与自己和解,原谅伤害我的人,更是自我内在的修炼。不是我将写作延续下去,而是写作延续了我生命的深度和广度。
上游文化:你今年年初发表在《红豆》杂志的短篇小说《大雪封山》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篇幅不长,叙述流畅,内容反映了当下老人赡养和医疗问题,也揭示了两代人对待生命和归宿的不同观念和矛盾冲突,从中透射出一种克制而哀婉的腔调,让人读后总心怀戚戚。你是怎么找到这种基调的?
舒舒:《大雪封山》是我加入重庆文学院第五届创作员“桃李班”的第一篇作业,得到张者老师的指导,和师兄师姐师妹们提出的宝贵的修改意见和建议。后来,有幸得江北区女作家何霜姐姐的组稿,推荐到《红豆》杂志。编辑张凯老师看了稿子后,指出不足,又进行了修改。这篇稿子让我学到了很多,以前没有注意到的细节、角色转换、场景描写等,都让我有了新的深刻认识。这种认识在以后的写作中,会起着重要的作用。
至于小说创作中如何找到这种哀婉的腔调,或许是与我自身的经历有关。2015年失去父亲后,对于涉及父亲的作品,就总有一种“子欲养而亲不待”的痛感。小说的人物情感,带有作者的情感和对世界的认知,并将这种感知通过人物的语言、动作传达。所以,我亦无可避免。如果读者能从《大雪封山》感受到这种哀婉,这不仅是我的情感的传达,亦是读者内心深处潜藏的、不为人知的情感共鸣。文字是抚慰心灵的良方,如果能给读者带来心灵上一丝温暖和安慰,这是我的荣幸。

▲2022年,舒舒在出租屋中创作《大雪封山》,该作品2023年刊发于《红豆》
上游文化:有人说每写一篇小说就是把自己放进小说场景中重新活一回,换句话说,就是小说中的人物或者人物群,有作者的影子,你有没有这种情况?
舒舒:这种情况对于我来说,叫做代入。就是把自己当成小说里的人,从心里走一遍人物的人生经历或心路历程。我认为这种代入是写作基本的、必需的要素。为什么有的人物形象很鲜明?有的很模糊?个人理解,应该就是代入感的层次深浅不一,关照点不同。当然,这种代入感也会带有作者自身的经历、喜恶等,在塑造人物的时候会将自己的情感、体验、认知等赋在人物的身上延展,并潜意识驱使或指挥人物代替自己活一次,活成与现实中不一样,或者是为现实中不如意的自己找到心里理想的彼岸,从而达到释放心里困惑和自我救赎的目的。
上游文化:中篇小说人物有一个性格发育的问题,请问你是如何处理的?短篇小说需不需要性格发育?
舒舒:哈哈,这个问题好辣嘴。个人理解,不论是中篇小说还是短篇小说,都有一个人物性格发育的过程。只不过中篇小说的人物性格发育相对来说有空间,而短篇小说的容纳空间几近于无。小说家毕飞宇曾经说过,短篇小说因为篇幅的问题,要在有限的字数里去写人,人物的性格是没有发育起来的。这就让很多写作者认为,短篇小说是不需要人物性格发育的。但我个人理解是,人物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性格。只不过,短篇小说没有篇幅来写人物性格发育的经过。这就形成了短篇小说不写人物性格发育,而直接到达人物性格。短篇小说的性格发育,我觉得不体现在文本里面,而在于作者对人物性格的塑造上,透过只言片语,是可以追溯到人物性格的发育过程的。
短篇小说是没有篇幅写人物性格的发育,长篇小说则可以缓慢而连贯的写,而介于长篇和短篇之间的中篇小说,既不能像长篇那样缓慢连贯写,又不能像短篇近于无,这就导致中篇小说只能通过场景、语言、对话、动作等渐次展开和侧面描述。要问在小说中如何更好地呈现人物性格发育,以我目前的创作,多从人物的出生环境、人生重大经历、情感挫折、以及人物接受教育程度、对世界的感知等方式呈现。小说中的人物与现实中的人物是一样的,虽不能完全呈现人物性格的发育过程,但也不能否认人物性格的独立性和完整性。因此,中篇小说的人物可以从多角度、多维度、多方面进行性格发育,也可从“前生”约略铺垫,也可从正在进行中的场景、对话、事件、动作等有意识发育。小说人物说什么话,有什么动作及目的,有人物自带的动机,这个动机是延续人物往下走的方向和线索,也是支撑人物存在的核心。

▲初中时期的舒舒开始写诗歌,《青春》在学校的一次朗诵比赛中获二等奖
上游文化:在你的多篇小说中,其主人公都透露着强烈的欲望,你自己也认为,你也是一个有着强烈欲望的人,那就请再谈谈你的作品中以及你自己在写作中的欲望问题。
舒舒:从常规理解,欲望是指为了达到某种目的而产生的想法,并在想法的基础上实施行动。所以,人生来就有欲望。对写作者来说,欲望其实比一般人都强烈,只不过极少有人正视自己的欲望、并承认。写作的欲望来源于人本身的“想”,由“想”生“欲”,由“欲”渴“望”。婴儿想吃奶是欲,看着奶是望,吃到奶是得。得不仅是得到,更是一种认同认可。人终其一生,寻找的就是认同认可。同理,写作者从“思”“到“写”至“完成”的过程,就是“想”至“认同认可”的过程,即是欲望萌芽至得到满足和释放的过程。从某种角度讲,欲望强到一定的程度,会蜕变成理想,会左右写作者在写作路上的坚持性和长久性。所以写作者中有的矢志不渝,有的坚韧不拔,有的大器晚成,当然也有放弃的。同理,小说中的人物,是作者赋予的生命,只要是生命,都会有欲望。小说中的人物欲望与现实中的人物欲望是同等的。只不过,小说中的人物欲望是被读者一眼看在眼中的,而现实中的人物欲望则隐藏于皮囊之下。写作者不仅是欲望的行动者、实施者,亦是欲望的解剖者和释放者。写作的过程,就是探索欲望、抒写欲望、完成欲望的过程,并在此基础上,找到精神上的平衡点和支撑点。
上游文化:有很长一段时间,你对红色题材创作产生过浓厚兴趣,投入了很多时间和极大的创作热情,继长篇小说《潜行》脱稿后,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一连写下了六个红色题材的中短篇,我想了解一下是什么激发了你的这种创作激情?而在创作中你又有着怎样的经验和感悟?
舒舒:这个念头来源于一本秀山党史资料,看了资料后,我对秀山二次解放感到好奇,又了解到秀山目前没有关于红色题材的文学作品,于是就产生了创作的冲动。当然,还有一层原因,就是想为秀山文旅做点力所能及的贡献,但现在看,这完全是我自不量力。我原计划将秀山解放战争历史分成四个中篇小说完成,小说分则独立成篇,合则故事延续、人物互相穿插。但《潜行》写好后,改来改去就改成了一部长篇小说,后续的部分就整理在中短篇小说集《穿过黑暗的黎明》中。创作方面其实也没有多少成熟的经验,除了现有的党史资料,就是用最传统的实地采访和田野调查方式去收集资料。我不过是将资料里面的故事根据自己的想象重新虚构、布局、人物塑造、代入性描写当时的局势和情节。保留原有的真实故事,也尽可能的复原其原有的重要人物和发生的事件线索。这好像不是什么秘诀,这是我在写作中的某种偷懒取巧行为,只不过是根据前人的描述,转述给读者而已。目的,让更多人了解秀山解放战争的艰难历程。

▲舒舒的多篇作品先后在《红岩》《小说月报原创版》《红豆》等杂志上刊发
上游文化:在长期写作中,你有没有遇到过瓶颈期?
舒舒:瓶颈期应该是我的常态。遇到瓶颈期,很迷茫,也很痛苦。但后来发现,每经历一次,似乎就有所提升。突然就意识到,瓶颈期并不是坏事,而是破壳,是自我突破和自我雕塑的关卡。闯过关卡,就会获得成长。所以,卡在瓶颈期时,我不会坐以待毙。因为我没时间耗在止步不前的困境里。我虽在初中时就尝试着开始写小说,但贫寒的家境根本没有机会让我在学校系统地学习。中专辍学后,就南下打工,为了所谓的爱情辗转到重庆。2004年,从重庆回秀山就闪电般结了婚,婚后就是家务和孩子。直到2014年,才有幸进入秀山作协,并在老师们的带领下开始写作。那时我已经33岁,早已过了追逐梦想的年纪。而再次提笔,仅仅是因为生活太压抑了,而写作让我找回了迷失的自己。两个年幼孩子的母亲,一份身兼数职、高强度的工作,婚姻中的一地鸡毛,让我很迷茫、很抑郁……但幸好,作协老师们一直鼓励我、指导我,推荐我参加重庆文学院的各种文学讲座及培训班学习。这对别人来说也许作用不大,但对我来说却意义非凡。所以,我比任何人都认真和努力。今日能有几篇作品与读者见面,是重庆作协、重庆文学院、秀山作协共同栽培出来的结果。
前两年,我经历了人生至暗时刻,不仅对写作灰心丧气,对生命也产生了质疑。我特别感谢张者老师,他在我最挫败、最灰暗的日子投来一束光,让我重新燃起对生命和写作的希望。没有在黑夜里走过漫长河堤的人,并不懂得这束光意味着什么。但对我来说,无异于第二次生命的重启。那段经历我现在几乎不敢想不敢碰,未来也许也不敢去轻易触碰。我是个惯于自我养伤的人,也是个心向阳光的人。只要有一点点微光,就会迎着光勇敢走下去。所以,我遇到瓶颈期,没有停滞,而是写,不停地写,写什么都可以,喜欢的不喜欢的,有意义的没意义的,写就完了。压力越大,写得就多;嘲笑越多,埋头写得越勤。后来我又发现,“写”真是一个克服瓶颈期最直接最有用的方法。
上游文化:在写作之初,你有想过为什么而写作吗?你觉得写作的最终意义是什么?
舒舒:我从三年级开始写日记,写,成了生活中的一个习惯。开心写,不开心也写,发生什么事了更要写。写是记录,也是对心情的纾解。虽有过作家的梦想,但感觉离我十万八千里,是遥不可及的幻境。所以,写作仅仅是因为习惯,是在压抑的生活中,寻求一丝自我安慰。婚后生活的不如意,让我重新提了笔,没有目标,没有想法,仅仅是为了寻求心灵上的快乐和安慰。但我们身处的环境是变化的。接触的人不同,思想也会随之变化。随着眼界的打开,产生许多此前没有的想法,承担本不属于自己的责任。这就像我儿子踢足球,自由自在的踢和有教练监督着踢,心理上还是有本质的区别。他问我:为什么将爱好当成任务后就不快乐了呢?写作亦是如此,一旦将写作在心里变成了责任和负担后,也就不快乐了。有段时间,我似乎不是为了快乐而写作。但我永远没有忘记写作的最初所求是快乐。为了能快乐写作,我放弃了许多东西。
写作的最终意义是什么?这是这两三年里我经常思考的问题,在现实和困境面前,认识到作为个人的无能为力,生命有时如此脆弱,有时又如此倔强。“快乐”和“意义”在心中发生了冲撞,一时觉得写作有意义,一时觉得毫无意义。后来看了一些哲学方面的书,也看一些心境修行方面的书,还看了一些天文科技方面的书。人就是如此,了解到的世界越多,也就越不快乐。但脑袋接收信号从来不是自己能决定的事情。总想用“思想内功”将万事万物融会贯通——其实我们是有这种能力的,将完全不同领域的东西互相联系、联想、并展开丰富的想象。胡思乱想可以让心不受局限地飞扬,就算身陷狭窄的空间和困境,但思绪却可以飞越浩瀚宇宙遨游。我喜欢神游其外的感觉,不必纠结生命和写作的意义是什么。这个问题没有答案,是我需要终其一生去探索和寻求的。
而在当下,我很庆幸得益于一些朋友在背后的引导和开解。朋友不经意的话特别治愈,他说写作被我们想复杂了,写作其本质就是呈现个人对世界的认识和表达。所以,写作的最终意义是自娱自乐,如果偶尔影响了别人,得到认可,那是意外。我很认同这番话。我写作最初的出发点,就是为了取悦自己,偶尔有人喜欢,并得到情感上的共鸣,那是意外的收获。但不得不承认,这种意外的收获,感觉实在太过美好,以至于在困境中,成为坚持走下去的动力。

▲访谈者(左)与受访者舒舒(右)于2023年2月在长寿区大洪湖采风
上游文化:到目前为止,你对自己的哪一篇作品最为满意?
舒舒:每篇小说都是我生活的痕迹和走过的心路历程。我个人偏爱《翡翠湖》。写《翡翠湖》的时间,是我第一次参加重庆文学院的培训后。那次培训一共七天时间,我几乎没有好好睡觉,一是选择环境,二是受老师们的思想冲击。白天上课全神贯注记笔记,晚上交流会后整理笔记,记录心得。回来后,一气呵成写了《翡翠湖》。这篇小说蕴积了我多年对写作的热爱。没有想过构思,也没有想过怎么写,就以最自然的角度切入,最舒服的语言叙述,写得很畅快,就像一条堵塞的河水,阀门一开,河水“哗”就涌了出来,仅仅两天就写完了。
曾经有人问我:培训有用没?我的答案是:有用的。当然,这得看人。比如经常听培训课的写作者,或许就没有什么大的收获。但我不一样,那时的我就像一张白纸。第一次在白纸上画的画,第一次在白纸上写的字,无论再难看,印象都最为深刻。所以,直到现在,我还记得《当代》文学院院长陈应松讲《如何将地域文化变成小说》的课。他讲了一段对我影响很深的话。这段话驱散了我心里一直困惑的迷雾,每次读,都很受益。分享出来,希望能对初学者有所助益。
“学者侧重关注于理性,作家关注于社会生活的折射面。因为作家写出的小说是虚构的。虚构是具有力量的,是神秘的。这种力量来自于虚构意境中的波及能力,拥有假设与虚构的外壳,是一种艺术手段,直指生存的最深层处。但是,我们有时却困惑于这种虚构的感觉。总认为虚构出来的东西不具有任何价值。质疑作为一个作家的存在感。所以,在现实创作中。很多作者都认识不到虚构的重要性。但同时,虚构写作又阻碍着写作者前进的脚步。因为它存在许多局限性,比如情感冲动、表达能力、虚构能力、想象能力等。学者与作家的关系就好比生产者与贩卖者的关系。学者是生产土特产的人,他们对本土文化进行考证、取证、辩证。而作家则把这些土特产拿来进行包装、转售,相当于二手商人。”
(图片均由受访者提供)
附:
舒舒佳作《大雪封山》(点击即可欣赏)。
编辑:朱阳夏
责编:陈泰湧
审核:冯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