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苇凡,本名李平,重庆合川人,教师。作品散见于《诗刊》《星星》《诗歌月刊》《红岩》《诗潮》《诗林》《中国诗歌》《绿风》《江南诗》《诗收获》等刊物,曾获东丽文学奖等。出版诗集《杯水记》《不思量集》等两部。
用诗歌的微光照到半米之外
(本期访谈主持人:陈泰湧)
上游文化:苇凡,请问你从事什么工作呢?
李苇凡:我是一名小学老师,是一位业余写作者,主要从事诗歌写作。
上游文化:作为语文教师,有人认为你的工作对写作会有促进作用,你同意这种说法吗?
李苇凡:因为每天跟语言文字打交道,所以大家都觉得语文教学跟写作是相通的,这种联想看似合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教学跟写作完全是两码事,二者几乎不在一个频道上,特别是在基础教育阶段当老师,或许写作对教学有一点点帮助,但这个因果关系没法颠倒——我觉得一位数学老师或者体育老师成为作家的概率,其实跟语文老师差不多吧。
为了撇清这种嫌疑,我更愿意是一名数学老师或者体育老师,或者去从事与此无关的工作,做一份跟写作反差很大的工作。我们知道,有些作家的职业跟语言文字一点也不沾边,比如卡瓦菲斯的长期工作是水利部的临时工,兼职股票交易所的经纪人;卡夫卡是保险公司职员;张二棍是地质工作者,成天满山跑;李松山干脆就是个放羊的。所以我觉得一个写作者其实跟他所从事的职业没有什么关系,反过来说,从事任何职业的人都有可能成为一位作家和诗人。
上游文化:翻开你最新出版的诗集《不思量集》,第一卷即是书写农村及童年生活的诗作,读来很是让人共情,请问把这个题材的作品安排在书的前面是有什么特殊的用意吗?
李苇凡:我出生在农村,长在农村,成年以后有过一段农村工作的经历,所以归根结底我是个乡下人。写自己最熟悉的题材,是最保险的,也是最方便的。在我的脑子里,那些人、那些物、那些事,活灵活现,历历在目,一抓一大把。当然,这也是一种涉嫌偷懒的做法。但是要把农村题材写好,也不容易。要写出新意,写得不落俗套,就更难。以前有些诗人在写乡村时,笔之所至都是所谓的回味、歌颂,甚至一些落后的、糟粕的东西也不例外,这是没有原则的。
而我所做的,只是记录。我写小镇,就是记录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小镇,我生活过的地方。我想重现记忆里的乡村,用笔去捕捉那些易逝的或者已逝的零星的生活片断,让那些过去的人物和场景在新的时间里复活。我想为我的乡村写一部简史,哪怕只是一个极简史,这算不算一种野心呢?
作为一种载体,诗歌可以见证历史。米沃什说:“诗歌的见证比新闻更可靠。”。当我不在了,我的后人或者没有这种经历的读者就可以根据我的记录去了解那个时代,去体验和理解我们那一代人的生活。所以它们应该被记录下来,否则我会遗憾。

上游文化:你刚刚说到了乡村生活与诗歌,能再讲讲童年与诗歌吗?
李苇凡:关于童年生活,我们都有这样的体验,越是近期发生的事,记忆却很模糊,越是久远的事,反而越清晰。几十年前的事还历历在目,说明那些经历对我们的影响还在起作用,并终将影响我们一生。就像我在诗中写道的:“那时我记性特别好/见过的人总是过目不忘/看过的书,誊抄过的课文/到现在还记得……一些频繁使用过的文字/在脑子里还留有深深的划痕。”
童年可以说是文学的源头或者文学的故乡,书写童年,很多作家乐此不疲,比如鲁迅、高尔基、萧红、林海音、琦君等等。童年是一个富矿,在人的一生中永远闪闪发光。
童年已成记忆,诸如上学路上和放学路上那些无限延长的晨昏;晚间我们大院子里几十个孩子蹦跳呼叫的热闹场景;清晨我在母鸡咯咯嗒咯咯嗒的叫声中醒来,它已在我枕头旁的草窝里产下一枚热乎乎的鸡蛋,那是我的早餐。如今都已经成为记忆。现在连那院子也被推土机铲平了。可能在以后的时代,那样的场景再也不会有了。那是我们那一代人人生中最重要的部分,值得用语言去重建。
上游文化:读你的诗,感觉有一种忧伤的基调,甚至有些沉重。我发现你有好些诗作是在探讨生与死的问题,关于这一点,你可以给我们讲讲吗?
李苇凡:文学或艺术作品所呈现出来的基调跟作者的个人气质有关,这也体现了一位作者的审美倾向。可能因为我本人比较喜欢安静和独处,无论是看书还是听音乐,很容易被一些忧伤的情绪所吸引,于是不知不觉影响到创作,这是我所乐见的,作品中呈现出的这种基调,正是作者真实情感的体现。
当然,我说的是作品的整体倾向。其实前人也有过相关的论述,《吹剑续录》里写道:“柳郎中词,只合十七八女郎,执红牙板,歌‘杨柳岸,晓风残月’。学士词,须关西大汉,铜琵琶,铁绰板,唱‘大江东去’”。
关于在诗中探讨生与死的问题,前段时间我和一个朋友也有过交流。人之一生,两件大事,即生,即死。对于中国人来说,死为忌,讳而避之。而对于写作者来说,不但不应避开,而且应自觉地对生死进行思考和书写,此是人生的重要命题。我自何处来,归何处去?人死之后是什么形态?死者的世界是什么样子?和生者的世界有何不同?这是我们常常追问的命题。
人生无常,是谓正常。人来到这个世界就是来体验生命的,生之终结便是死的开始。死者的世界到底是个什么世界?没有人回来向我们描述它,只有当我们去到那里才会知道。很多文学和艺术作品都在对此进行探讨和阐释,像电影《寻梦环游记》中描述的多姿多彩的亡灵世界,或者《镰仓物语》中,主人公死去的父母安静地生活的黄泉之国。我在想,在死与生的世界必定有一个秘密通道,可以让我们相互往来,交流。这个通道在哪里呢?它一定在我们大脑里,在我们的精神世界里。作家和诗人的工作,不是在寻找,就是在挖掘。因此在诗中,在文学作品中,呈现死亡是再正常不过了,这是文学永恒的主题。知死,即知生,明白死的意义,也是让我们更好地活着,珍惜生命,珍惜当下。

上游文化:你是怎么迈出诗歌创作第一步的?
李苇凡:很多人青年时代都有一个诗人梦,或多或少都写过诗。可能也没想过为什么写诗,或者是被诗歌所描述的境界所打动,或者是有想法需要表达。孔子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可能大家开始写作都是这样糊里糊涂,有的竟然写出了好诗,所以呀,每个人都有成为作家和诗人的潜力,只是后来,随着年龄渐长,我们的心开始变得粗糙起来。只有极少数人,还保持着一颗柔软、敏感的心,对世间万物依然充满好奇,充满热爱,和年轻时一样,我们把这颗心叫做初心。
我也是一样,开始写作的时候不会去问为什么,只是写出来而已。因为上师范嘛,学习没什么压力,总得找点什么来填充空余的时间,于是经常去阅览室,那时阅览室订了很多文学刊物,诗歌刊物也有好几种,像《诗刊》《星星》《诗神》这些,读了别人写的,心里痒痒的,跃跃欲试的,于是就尝试着写作,写出来居然发表了一些。
上游文化:从学生时代到现在,是什么让你在诗歌创作的道路上坚持了这么多年?
李苇凡:“坚持”,这个词让我很惭愧。上班后工作忙碌,然后是结婚,孩子出生,我的写作停下来了。是的,诗,写不下去了,一种具体的生活,让人投入了全部的精力。这一停,就是十年。十年,没有任何想要表达的欲望,连阅读也没有。我甚至和许多人一样,认为生活可以没有诗歌,诗歌的微光照不到半米远的地方。所以整个十年,只是活着,没有留下只言片语。
现在看来,并不是那么回事,说是为生活所困,只是为写不下去找一个理由。这里真的要澄清一下,我不想让生活来背这个黑锅,恰恰相反,我的家人和孩子为我的写作提供了动力。归根结底是懒惰,所有的理由都是为懒惰找借口。但是不能否认,生活的平淡琐碎真的能消磨一个人的志向,对,刚才说的,困于平淡琐碎之中,而写作,恰恰为铁板一块的生活打开一个出口,从平淡、重复、机械,甚至无助中走出来,哪怕只是短暂的出神——从物质的我进入精神的我。
诗是无用的,正因其无用,才让我们得以摆脱现实,摆脱功利,沉溺于一种不被干扰的形态之中。
而且我越来越发现,不是我需要写作,而是很多事物需要我把它写出来,比如故乡,比如亲情,比如友谊,比如一些卑微的事物,需要我去体察它,理解它,需要我用笔去呈现它的悲与喜,爱与痛。我越来越发现写作成了一种使命。这是我自己的事,谁也代替不了。
认识到这一点,我就又拿起了笔,重新开始写作。
上游文化:你的文学创作聚焦在诗歌上,有没有尝试过其他文体?有没有例如小说、散文之类的创作计划?
李苇凡:因为懒啊。写诗可以用很少的文字来容纳海量的信息,而且不择时间、环境,现在手机上就可以完成一首诗。小说和散文创作与之比起来,可是个重体力活。码字是很辛苦的,除了才华,还需要耐力毅力和体力。当然这是开玩笑。任何一种文体都需要投入极大的热情、时间和精力。选择哪种文体主要是看写作者的习惯或喜欢或适合使用哪种形式表达而已。其实对我来说,诗歌的写作也是很艰难的啊,而不是人们普遍认为的:你写一首诗是信手拈来嘛。世上之事就没有信手拈来一说,即便是李贺这样的天才诗人,也因为写作的殚精竭虑而早夭。就像我前面说的,如果怕吃苦,如果不勤奋,如果没有坚持不懈的精神,一下子就荒废了,而且一荒就是十年。
散文写作也很有意思,或者是更有意思。散文我也写过一些,朋友们说很好看,可能更多的是一种鼓励吧。
对于写小说,目前还没有这个计划,也许某一天,突然就写上了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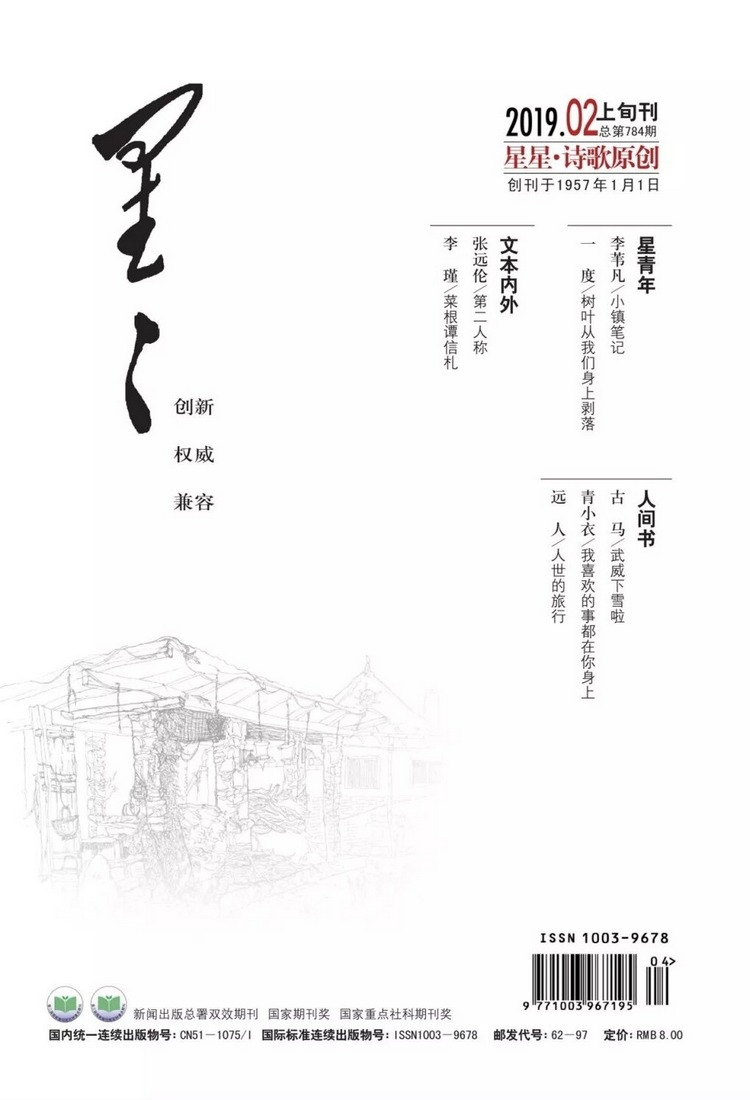
上游文化:一个教师的写作观念或许对学生不会产生直接的影响,但教师的阅读观念往往能给学生带来很直接很深远的影响,聊聊你的阅读吧?
李苇凡:最近有一个词叫“文化体力”。有人抱怨:上班族因为时间和精力被工作压榨殆尽,每天疲惫不堪,导致“文化体力”严重透支。体现在表达能力退化,词汇变得匮乏,看不进长文,只看得进娱乐垃圾。所以下班就只有打打手游,看看爽剧,哪里还读得进书啊。这种说法虽有些夸张,但还是有些道理的。
国庆期间我买了十几本书,有小说,有哲学,有诗集。过了一个月,只有两本书撕开了封皮,不过,我想总有一天我会把它们全部读完。
倒是有一本旧书,是一本袖珍书,放在我伸手可及的地方,随时都要拿来读一读。这本书是《唐诗三百首鉴赏词典》,傅德岷老师编的。这是我读过的遍数最多的一本书,可能有几百遍了吧。
上游文化:读古诗,对现代诗的写作有帮助吗?
李苇凡:当然。中国古代诗歌已经扎进每个中国人的基因里,也是现代白话诗的原乡。新诗最重要的标志就是它的现代性。古诗中有现代性吗?也是有的。
我最喜欢的是老杜和小李,即杜甫和李商隐。杜甫的广阔视角、人文关怀、以及选材的广泛性等都值得每一个写作者学习。杜甫沉郁深邃的诗歌气质是我最仰慕的,我不否认我的写作受到了杜诗的这种气质的影响。杜甫是格律诗的集大成者,可有些诗却平易质朴非常口语化。比如“至今大河北,化作虎与豺。”“老妻画纸为棋局,稚子敲针作钓钩。”“鹅儿黄似酒,对酒爱新鹅。”就像我们现在的白话诗,有时候我读一读,借以检测一下自己的诗是否太散文化或者太拖沓。李商隐“曾是寂寥金烬暗,断无消息石榴红。”“星沉海底当窗见,雨过河源隔座看。”在我看来仍是很现代的手法。那种语感和修辞,那种心理体验,那种幻灭感,其把握和呈现方式跟我们当今的写作别无二致。
上游文化:访谈的最后,给你出一道难题,请你选择一首你自己最满意的诗歌,并说出这首诗究竟哪里写得好。
李苇凡:这的确是一个难题。作品好不好不是作者本人说了算的,作者所做的工作只是把它完成。我自己比较喜欢《种菊》这一首。有一天我在浇花时突然想到这样一个题材:把菊花种在花盆里和把菊花种在纸上,然后试着把它写出来,写完之后稍作修改,便算完成。后来再读时,我发现这首诗自然顺畅,毫无雕琢感,语言的铺陈、跌宕,时空的辗转、腾挪,虚实之间所生发出来的歧义和诗意让我颇感意外,同时也贯彻了我对生命和生死的理解,于是不由自主就赞同了陆游“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的说法。
种菊
把磨出小洞的搪瓷盅,从母亲那儿要来,
种一棵野菊花,放在窗台上,
每天观察它,为它写一篇作文。
最为蓬勃好看的野菊花,长在村头的墓地里,
那是我背着大人,偷偷挖回来的。
现在我依然种菊,以一个现代人的身份,
把它种在城市的阳台。
把菊花种在花盆里不算什么,
要把它种在纸上,
用汉语自身的肥力去滋养它,使它呈现出全新的意义。
但事与愿违,
更多的时候,它似乎倾向于,
带有某种过去的信息,
以呼应我小时候,从墓地移栽来的那一棵。
那是死去的人,以另一种形式出现在这个世界上,
那是他能想到的,最美好的形式——
与我相识。

他们眼中的李苇凡和他的诗——
蒋登科(评论家、教授、重庆市作协副主席):在李苇凡的诗中,诗人对自己的情感体验、人生向往、生命价值表现出了明显的方向感。它们的本质都是安静,在沉思中获得安静,在安静中提升生活与生命的质量与人生境界。在他的作品中,我们几乎见不到直接的情绪宣泄,更见不到那种剑拔弩张的情感表达。对世界,对他人,诗人总是以一种温和的态度来打量,他不指责,不怨恨,更不愤怒,更多的只是反思自我,捕捉日常生活所具有的诗意,抒写内在的感悟与向往。我们不能说诗人心目中没有烦躁,没有苦恼,没有迷茫,但他善于将这些瞬时的、非本质的情绪从人生与诗歌之中剔除,从而通过艺术的创造获得一种具有普视性的人生观念。这种观念来自对生命的终极关怀,来自对表象的剥离和对本质的深入。从这个角度说,李苇凡的诗在视野上并不拘泥于具体可感的事物和生活现象。这些诗是开阔的,也是独特的。
张远伦(诗人、重庆市作协副主席):李苇凡的诗歌有着这个时代少有的隐逸气和家园情怀,在现代丛林法则的冰冷中散发着温情脉脉的追叙之光。诗人在对乡镇和小县城的叙写和回忆之中,找到了几乎被遗忘却一直在闪耀的人性和哲理。他常常描写那些在生命中具有穿透力的,附在思想深处的那些人和物,卑微而又自带灵光,然后用舒缓的语言节奏,层层叠叠地呈现他们,并进行深切的生命思考,大多宽阔深邃,是有层次感和纵深度的诗歌。物象与人的命运交织在一起,语言朴实而又意味深长,诗人善于寻找物象、细节和语言背后的意外之意,找到很强张力的留白或者潜台词,甚至找到词语和句子的歧义,这是一个优秀诗人的能力所在。诗人在意象的延展、叠加、层递和镂刻上很有功夫,这与语言内部较慢的节奏感相得益彰。
唐力(诗人、重庆文学院专业作家):李苇凡诗集《不思量集》以一个边界小镇为对象,由此展开了他个人的书写。这样的小镇是属于他的,带着他独特的印记。李苇凡的诗作是沉静的,在舒缓的叙述中,展开了一个小镇的风情。人物、场景、时令节气,草木动物,都在他笔下一一复活,展开一幅风情画卷,生活画卷,散发出记忆的气息,古旧而又温暖的气息。他表现一个微小却富有诗意的地方,实际上是以笔记的形式,记录小镇的生活史,从中使我们得以窥视生活的秘密。
王士强(诗人、诗评家、天津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李苇凡的诗具体、真实、细腻,有着来自泥土的温度、纹理和气息。这种具体性、在场性不仅在于他观察、体验的深入,更在于他对之的情感与认同。其所写多是一些“近乎无事”的小事,但它们又是有内在性和心灵性的,往往惊心动魄而又意味深长。那些具体而微的细节是极为真切而具有生命力的,可谓活色生香,具有很强的艺术力量。
刘清泉(诗人、沙坪坝区作协主席):我想谈到的是跨文体写作,这是一个技术手段问题,更是一个意识问题。李苇凡的不少诗,如《手语者》《光源》《病中吟》《夜宿小镇》等,有明显的“故事情节”。诗人驾驭着书写的进程,不仅语言是叙述性的,摒弃了起修饰作用的形容词和先入为主的情绪,而且诗中有小说所强调的“故事核”,讲缘起、重铺垫、埋伏笔,有转折,有高潮,还有出其不意的结局,呈现出与众不同的诗意。这是一种很有勇气很有价值的探索,可以给我们的现代诗写作带来许多新的启示。
大窗(诗人、九龙坡区作协主席):李苇凡的诗歌深藏人性和命运的奥秘,总有断断续续的神秘气息弥漫其间。他本能,沉静,细腻,敏感,悲悯,他书写平凡的快乐,琐碎卑微,直面苦难、生死,在看似平面铺叙的底层生活中,以及独有的缓慢推进的语言形式,渐渐渗透到你的满眼和灵魂,无疑,只有好的诗人才能带给读者这种震撼。在此意义上说,诗人李苇凡的工夫在诗内。
陈啊妮(诗评家):李苇凡的语言与他置身其中的生活环境是那么和谐,他的诗中始终隐隐振动着扣人心弦的拨动,那是来自生命细微处的触动与裂开,是诗人让那片恒温的土地散发的持久魅力,是诗之根系因为生命瞬间的打开而产生的深邃痴迷。李苇凡是安静而细腻的生活观察者,在他的诗中有憨直的真切,情感的滋养,以及不断渗透其中的厚重思索纠缠其中,诗人让他的生命现象与自我的日常体察达成了一种人文化的同构关怀,并且在不动声色中流露出犀利又清晰的思想共鸣。李苇凡的诗是在零度空间里冷抒情的高手,诗人纤细的审美使他的诗句在读完之后变得意味深长。
二两春光(诗人、评论家):李苇凡为人的谦虚低调,正暗合了他诗歌缓慢从容文气的气质。他喜欢不厌其烦地写细节和心绪,像慢镜头的推送,而且是两个层面的慢镜头,所以偶尔被人诟病为行文拖沓。其实不然,如果你在一个慵懒的下午,晒着阳光,文火煮茶,读他的诗,你会体会到诗和心性合而为一。他也时常写到生活中的种种疼痛,但从来没有那种呼天抢地的,而是像扎灸针行气,酥麻麻的胀痛。以上点滴,在他的诗中都能找到实证。
张丹(诗人、评论家、文学博士):为什么漫长的人生中,我们以为极为重要的事情到头来充满遗忘;而被选出的,只是一些发生过的小事或对事件的观看。我们发现,那种事物的趋势,暗示了我们的生命形态,隐喻了生死的永无终结:凡事只是不断向其他事物生发的过程。因此,我们是在回忆一些漫不经意的过程,完结之事(物)是从过程中被带了出来。这是我读李苇凡的新作生发的感受。这些诗中充满“旧物”:旧的搪瓷盅(《种菊》),旧的生命(《种菊》《夜宿小镇》《立冬》),旧的生产(《灌溉之诗》《樱桃》),旧的生存(《断竹颂》《雪》)。这些旧事物在诗人的修辞中不断被转喻换喻,联通着时间不断分叉的小径,将我们引向更多的现在和过去,更多的交叉处。仿佛一个人的现在,只是多种可能性中的一种。从李苇凡的诗中,我们看见了一个多义的现代心灵,也看见他生命的命题。

编辑:朱阳夏 责编:陈泰湧 审核:冯飞
【免责声明】上游新闻客户端未标有“来源:上游新闻”或“上游新闻LOGO、水印的文字、图片、音频、视频”等稿件均为转载稿。如转载稿涉及版权等问题,请 联系上游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