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隆玲琼,80后,重庆石柱人,现居重庆丰都,重庆市作协会员,重庆文学院第五届创作员,作品散见于《民族文学》《诗刊》《红岩》《星星》《诗潮》等刊物,有诗歌入选《中国诗歌》《汉诗三百首》等选本,获第八届重庆少数民族文学奖,出版诗集《你住几支路》。
隆玲琼:从“恶人谷”出发寻诗
(本期访谈主持人:陈泰湧)
上游文化:我是在2023年上游新闻承办的重庆市生态主题征文中,才了解到你是一名生态环境工作者,而在此之前我看到你发表了不少诗歌,如《前方到站通远门》《致2202》等,字里行间,还以为你是医生或者医务工作者,你遇到过这样的误解吗?
隆玲琼:是的。有不少人问过我这个问题,可能是因为之前写的诗中,医疗相关题材比较多或者相对显眼吧,相似的题材还有《通远门,另一扇门》《人身阑尾》等好几大组。这些都来自我在IVF术(编者注:IVF术俗称试管婴儿手术,通远门为重庆妇幼保健院附近的一个地标建筑)、阑尾切除术时的一些见闻感触。我没有医学专业的背景,哈哈,因为在IVF术中,这是一个比较漫长的医疗过程,感觉我们比医生要更清楚自己是什么状态,打的什么针,吃的什么药,什么时候要做什么检查,查什么指标,哪种数值算正常,然后在无数次的排队中跟姐妹们交流,那时候感觉差不多要成专家了,对了,感觉在医院就像是在“恶人谷”里一样,都是“高手”。当时感触也特别深,写的《试管五部曲》上了《红岩》中国诗集头条,后来写的同题材的,上了《诗刊》的双子星座,有一篇随笔,那个“待填补的漏洞”那篇就是那个时候写的。
一开始是写作尝试,后来逐渐产生了相应写作兴趣,后来的创作中我仍然将大量的医学术语放入诗歌中,比如IVF术中的进周、降调、雪诺酮、达必佳和腹腔镜中的单刃手术刀、光子治疗仪、按压痛,等等。工作与生活中的科学术语或者说行业术语,也更多进入到我的诗歌中,比如《热玛吉》《奇妙的多普勒》《噪声监测》这些。
词语是有纬度的,是一个多面体,每一面的词境都不一样,每个词语用在不同的诗句里会展示不同的界面,会有不同的美感。埃利蒂斯说:“我避开词的通常用法,我追求的是与词的日常用法背道而驰的东西。”而我将一些专业术语使用到诗歌中,是想让它们在和人体发生生理反应的同时,也介入心灵、介入精神。我觉得通过诗歌,它们能产生一种奇异的效果,从冰冷生硬变得温暖又神秘。
上游文化:你从小就爱写作吗,什么时候开始写诗,你认为写诗的意义在哪?
隆玲琼:嗯,是的,小学就最爱作文课,作文常被当作范文念。中学疯狂看琼瑶小说,看轰轰烈烈的爱;看池莉小说,读平民情怀人生之思。写过好几部手抄本小说在学校传阅,哈哈。写诗是从大学才开始的,当时受李清照、纳兰容若、仓央嘉措、徐志摩等的影响比较大,特喜欢写一些卿卿我我的唯美诗歌,也在《武陵都市报》《石柱报》等先后发过一些豆腐干,现在回头看,那时我还没有诗歌入门呢。
2013年,我向《星星诗刊》投了一组稿,没有中稿,但被邀请加入了星星诗歌群,接着又被群友拉进了另一个诗歌群,叫“恶人谷”,再被群友拉入了奔腾诗歌群,开始混迹网络,长期在“恶人谷”“奔腾诗歌论坛”发诗交流。从那时起,才算是真正开始现代诗歌写作。网络写作平台的价值争议很大,但对于我,确实是最重要的成长经历和舞台。在这段时间里,我结识了一些江湖诗歌野才,他们不显名于刊物,但对诗歌却异常严肃和真诚。在他们的帮助和那种诗歌环境的促进下,我从浅吟低唱的附庸风雅上挣脱了出来。所以,我真正开始诗歌写作的时间也就是十年的样子,但现在我觉得自己也还是一个诗歌新丁。
都说艺术高于生活,但艺术甚至做到还原生活、记载生活都很难,要怎么去高于呢?生活现场的丰富性和戏剧性,甚至超过了所有艺术的表述能力。我的诗歌紧贴着我的生活,我愿意像史蒂文森说的那样“住在诗里”,我乐于写诗,更乐于生活,我相信诗歌是可以不时调亮生活亮度的。

上游文化:你的诗集《你住几支路》入选了中国作协少数民族重点扶持项目和重庆市委宣传部、市作协重点扶持项目,这个书名有什么深意吗?
隆玲琼:嗯,入选扶持项目真的非常幸运,也非常感谢关注和关心着我的所有人。这个书名没有什么非常特别的用意,就是诗集中的一首诗。一开始,我想用的书名是《打开》(另一首诗的题目),我询问了几个关系比较紧密的诗友,他们都觉得“你住几支路”更新颖也更能综合体现我在这本诗集中的生活问答,于是就选了这个。
上游文化:你诗集的第一部分是脱贫攻坚主题,您是多久开始这类题材创作的?创作的初衷是什么?
隆玲琼:最初开始这类题材创作应该是在2018年,第一首诗歌是《你好,小麦》(后来刊发于《椰城》杂志)。记得那是一个早春,在去帮扶村的路上看见大片久违的小麦,因为太久不见,还特地向同行人确认了不是牧草。当时有一种欣喜、亲切和惊慌,感觉扎根心底的乡情怎么就这么模糊起来了呢?出于本能写下这首诗作为“记忆背叛的救赎”。持续这类诗歌创作是在2019年,当时大部分贫困户都已稳定脱贫,回首旧日寒困,亲睹新景象,作为一名身在山区的帮扶者和文学爱好者,我自然而然地参与了脱贫攻坚这场历史性大战的记录中。
上游文化:你写了多少首与脱贫攻坚相关的诗歌,这些诗歌的主要内容是什么?能不能选一两首来讲讲背后的故事。
隆玲琼:初稿百余首吧,诗集选了40来首,主要是以小叙事方式讲述自身参与扶贫工作的经历和感受。这些诗可能不是我诗歌里面最好的,但每一首背后都有真实的故事和人物支撑,都有直击我内心深处的触点。比如《路》那首,基本是实写:“李老伯”第一次跟我说有条种庄稼的小路需要解决的时候,我不是很上心,简单打捆统计上报,完全没理解到一条通往田间地头的小路对于一个每天往返于庄稼地的农民的意义,以至于让沉默寡言的他反复多次向我提出同一个困难,因此我写下了这首愧疚之诗。再如,消费扶贫时隆叔的一句“一棵种子就可以结出一树李子或者一堆红薯”,让我看到了农民对土地的认知与感恩,于是写了《他说种子与果实》;秦婶的一句“鸡鸭都是听得懂话的,不用抓,喊得拢”,让我联想到了乡村振兴的紧迫性与乡村人员流失的深层原因;走访时,向家老人一句“我们不会乱说话,你不用经常来”,让我看到了万千农妇的质朴与宽容和无数扶贫工作者的坚定与守护……
我一个同事的帮扶户只有父女两人,女儿是领养的,但养父特别喜欢,通过帮扶,女儿顺利上了大学,他又非常担心女儿这只凤凰飞出山沟沟就不回来了,每次去他都会说到女儿,每次这个60多岁的男人都要掉眼泪。类似情况还有很多,我们既不能阻止任何人对美好事物的追求,也没有理由让任何一个美丽院落成为空村。我肯定还会持续关注乡村振兴,关注时代发展。

上游文化:你有一对双胞胎孩子,也写了不少关于孩子的诗,你觉得写这个题材与其他题材有什么不一样,你希望孩子今后也写作吗?
隆玲琼:讲一件小往事吧,2019年我很幸运获得第八届重庆少数民族文学奖,得到消息时,我正在哄孩子们睡觉,放下电话我兴奋地对他们说:宝贝,妈妈获奖了,你们以后要乖,不调皮,给妈妈多点精力写诗好不好?孩子们睡眼蒙眬,但他们很干脆很响亮地答了一声:好!当时一岁半的他们当然不明白我说的获奖是什么,但他们的回应就是我写作的最强动力源,我写诗对于他们的现在显然还没有任何意义,但这就是我乐于与他们分享的无数快乐之一,这就够了。孩子一夜安稳不哭闹,第二天继续调皮捣蛋折腾我;我失眠一夜,第二天便继续忙碌生活琐事,仿佛我们之间的约定从未发生。孩子的懵懂和遗忘都让我欣慰,我不会为了写作,让我对孩子的爱做出让步,更不会在他们的成长过程中刻意往这方面引导,我们相互关联,也彼此成就,我爱他们,但不为他们制定某种未来。
我的工作之余全是孩子的时间,自然也会写出关于孩子的诗歌,我喜欢我写给孩子的诗歌,那里面有更为具体的爱。我希望我能像我的导师张远伦老师说的那样,微距般拍摄生活,感受生活,并获得关照孩子和孩子之外万物的能力。也希望大家能感受到这些诗歌中的细碎和爱和细小的人性之光。
上游文化:看你的诗歌,总给人一种一蹴而就的感觉,你写诗多是反复修改还是一气呵成?
隆玲琼:对于写作,我有严重的强迫症:前一首诗不完成,下一首就开不了头;如果觉得一首诗已经写完,就连个标点符号也不会改动。这让我的每首诗歌几乎都有明显的漏洞,可能是语言方面的也可能是逻辑方面的。才开始写诗的时候常常是一气呵成,现在会反复修改,但改诗对我来说真是很痛苦的事情,基本也要一气呵出半成的诗歌我才会修改,才能改成功,这可能跟我急性子有关。然后,我觉得自己也是个情绪化写作的人,有时写一堆,有时很久不动笔,最近也四五个月没写了。
上游文化:看你的写作和发表数量都不算少,对于诗歌写作,你有什么理想或者说愿望?
隆玲琼:其实我也没发表多少作品,2022年特别少,就在《诗刊》发了一组,2023年稍多点,这么多年公开发表的总共也就不到20万字。我写诗纯粹就是爱好,就是想写,没有想到过任何与成就有关的内容。如果非要说愿望,那就是,希望爱诗的人也被诗歌所爱。我纯粹地喜欢诗歌,但现在还说不上被诗喜爱和反哺,希望能够到达被诗哺育精神、提升自我的境界。

上游文化:现在,人们对诗歌的争议很大,特别是不写作的人,对诗歌甚至有一种偏见,你是怎么看待诗歌的?你想写出什么样的诗歌。
隆玲琼:怎么说呢,我的一位朋友说得很好,他说写诗就是身着盛装穿行在幽巷。这句话里有多重意思在,盛装既是诗歌的过去地位尊崇,也是精神上的高贵,也是说诗歌的技艺复杂丰富;幽巷首先是精神上的清寂独行,也是说当下诗歌的冷落孤欢,也对应着诗人在写作技巧上的曲折艰难。史蒂文森说过“诗歌必须最成功地抵抗智力”。我理解的抵抗智力首先是真诚,其次才是智性与理性的限制。诗歌中,实与虚可以打开边界阻隔,恣意传送出不可言和无力可言,这是很美妙的。我想写的诗歌就现在的想法来说,还是生活之诗和生命之诗,写什么大于怎么写,每一句静寂的表达,都应该有个体生命最有力的回响在内。
上游文化:作为一个非专职写作者,你当前或者未来的打算是什么?
隆玲琼:写诗是我的热爱,但不是我的主业。所以,我肯定还得首先做好本职工作。往大了说,我所从事的生态环境工作,同样的重要与紧迫,生态是一个大课题,也希望大家都关注生态;往小的说,我也要好好工作,努力上进,养家糊口;然后呢,我会继续坚持创作,坚持远离名利心,坚持生活得纯粹。
艾略特说过:“凡是诚实的诗人,对于自己的作品的永恒价值都不太有把握。他可能费尽一生而毫无所得”。我曾被这句话打击,又无数次被这句话深深抚慰。作为一个拙于虚构的人,我的写作大多取材于生活体验,每首诗背后都有不算小的一段时间和路程作支撑。诗有虚饰,但无伪善,我努力让自己写下的每一行字,都衡量着自己的诚实和良知。再大的题材都由个体在营造,每一个小小个体都是一个宏大空间的切入口。我想,我会找到和打开更远更宽厚的景深与写作空间,继续用更诚恳的写作态度,让我具体而独有。
上游新闻:可不可以选出一首你最喜欢的自己的诗,并加以解析。
隆玲琼:好啊,自己喜欢的还挺多的,自己的孩子嘛。我选两首吧,《敲窗的鸟》和《灰雁》,再用一段野渡的评,算是对这十年诗歌写作成长的一个小概括。其实主要是我不会写评论,也不会解析,他评得好,评到了我的心坎上,哈哈。
1.敲窗的鸟
咚,咚咚
它用尖尖的小嘴轻敲我的窗
一扇窗只响三下。我在最末端等它
它走过来,与我的手平行
可它不在我掌心。一块玻璃
阻止了它被我杂乱的掌纹绊倒
这个清晨,我们都紧闭着嘴,对视三秒后
它径直地飞走,落在另一扇窗台上
咚,咚咚
它继续一扇窗一扇窗地敲过去
2.灰雁呀
野芹遍地。灰雁呀——
我也有笨拙的翅膀,和宏亮而清脆的高音
教教我,怎么在迁徙中小心地歌唱

去天赋之外
——从《灰雁啊》说起
文/野渡(诗评人)
从《敲窗的鸟》到《灰雁啊》,隆玲琼度过了自己写作的十年,也从自己的青春时期写进了中年生活。大概十年前,隆玲琼刚开始写诗的时候,就展现了她的写作天赋,她从日常中取出现场进行再造和移植的能力是与生俱来的。在她的诗集《你住几支路》的序言中,我曾经评价她是一个“窥见了日常之外,神秘的通灵写作者”。她早期的诗作,大多都建立在这种透视寻常、无师自通的状态下,比如《打开》《遇见骆驼刺》《下水道》《水》等等。
诗意感知天赋对于诗人来说,甚至是高于语感天赋的属性,毕竟只有极少数诗人,把自己的诗歌魅力建立在纯粹的语感快乐上,能够不需要挖空心思去营构,自带着一个诗气空间,是令人羡慕不已的天分。也因此,很多具有诗意天赋的诗人,都沉浸在自己的天赋愉悦中,他们的诗,随写作时间增长的往往仅仅是语言成熟度,天赋即限制,即是写作的天花板,甚至随着嗅觉的衰退,写作中的灵性损耗会逐步降低他们的写作成色。
在隆玲琼的第二个写作阶段,她开始试着对天赋发起挑战,从自己驾轻就熟的灵性写作中跳了出来,去写一些“硬诗”,不管是纸张系列,还是医院系列和工作系列中,她都用发力重新建立“词物关系”的方式,把大量术语类的硬词带进自己的诗中,这对一个习惯了“柔顺、自然、清新”语境状态的作者来说,无疑是人为创造写作困难,对抗自己的写作习惯,如同一个人强行绑起自己的右手,去当一个左撇子。在每一首诗中,每用一个内容坚硬的新词,都需要敲开一次词的外壳,重建新的词意和语意连接,从修辞层面上说,这是技艺上的立巧,但对写作态度而言,却是一个弃巧取拙的过程,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她突破了自己的天赋瓶颈,从一个原生态诗人,向“丰富的诗人”蜕变。
几个月前,她发了一组去川西高原的游记诗作给我,在这一组中,《灰雁啊》这首诗,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首只有三行的短诗,不再是她前一阶段中,明显“执于语言之力”的那类作品,一首不描述复杂现场,从叙事文本回归到抒情文本,“手法老套,语言也不时髦的诗”,在这首诗中,语言素净利落,抒情气息却饱满而充裕,我甚至能在其中感受到一些大诗人的写作气度,比如国内的蓝蓝,国外的艾米莉狄金森等等。如果夸大一些说,这甚至可以是某类诗歌的样本状态,诗就应该是这样,或者得有一些这样的诗。在“我和灰雁”的瞬间交汇中,完成“雁我”之间的短暂又完整的融通,情绪的触发一即而中却又稍纵即逝,雁我相逢于一瞬,却交织出一串乃至无尽的生命旅程漩涡。
在这首诗中,隆玲琼明显已经触及到写作的另一个台阶,从有意和用力的“有招之诗”,向随意而发的“无招之诗”迈进,只有不执于力,才能尽展全力。
写作天赋是对写作者最好的天赐,但能破开天赋的屏障,打开天赋之外的写作空间,才能更显诗人的劳动价值。在写作过程中,用心力的不断输出去攀爬无形的阶梯,用下一首去找到下一步,显然比写出一首好诗,具有更多的意义和价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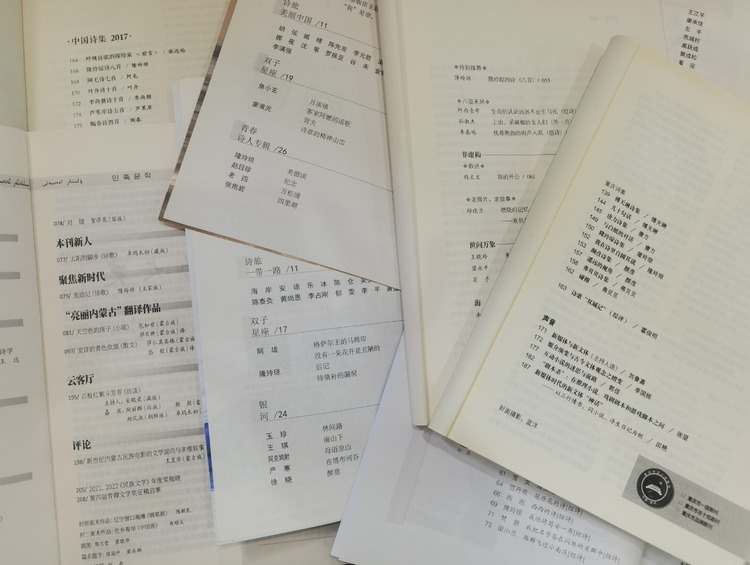
创作谈:我在诗里自圆其说
文/隆玲琼
1
透过半扇窗户进入的灯光,慢慢将整间屋子烘得昏黄而温暖。夜哭的孩子重新入睡,时针指向凌晨两点半,我却比在清晨还要清醒。这是众多日子中的一个日子、众多夜晚中的一个夜晚,我是众多数羊人中的一个数羊人。开始我有一群羊,后来有广袤的大草原,再后来羊群布满整个夜空……这情景如同艾米莉·狄金森笔下的《要造就一片草原》。不知是谁说过,写作是为了逃避,我有些赞同。如果今夜写诗,便是逃避我的羊群,我想把我的羊群赶进他人的帐篷或者夜空。
此刻,万籁俱寂如追忆,月明风轻似憧憬。
2
昨天去医院开出院证明,在外科接诊处碰到一个同事,很健谈和硬朗的一个人。他带着极力掩饰的痛楚说,胆囊有个结石,这次可能要做掉了。我问他怎么一个人来,他说开始不想挨刀子,媳妇正在路上,又特地补充了一句:“本来我一个人也行”。透过口罩我能看到他扭曲的表情,一个刚刚割掉阑尾的人特别能理解他的一边倾诉一边掩饰。我想,他要是也写诗,是否能通过一首诗来缓解部分疼痛;是否会在绞痛与放射性疼痛之间突然有了新的割舍观;是否会不假思索地说出:我一身虎胆竟然不敌几克胆固醇结晶体,不如摘掉。
生活,便是无数个这样自我佐证与自圆其说的白天,加上无数个数羊人与内心对话的夜晚吧。隔壁618的敲门声传进来,急促持久,迫使我从门缝看到一个穿着底裤的房客,如何让一扇为他关上的门重新再为他打开。唉,这个抱着臂膀自圆其说的旅居者。
3
有位朋友说,写作是星空下的孤独,诗人和上帝相等。写作的孤独即个性的出现,即创造的诞生。
是呀,写作的孤独者并不是脱离社会群体的消极自居者,而是从社会百态中提取自我的纯粹,从众声沸腾中抵达自我的安静。这种孤独因为心里有万物而柔软膨胀,像附着于蛋糕的奶油,蓬勃纯净,形全味甘;这种孤独因为远离喧嚣而陡峭立世,像孤松生于岩顶,身在空中,根深石内。
4
虽然写作的时日也不算短,但受制于天分和努力,我离一个诗人还有很大的差距,目前还没有自己诗歌特性甚至诗歌方向。陈东东说,一个诗人的三个时期分别是音乐、飨宴和冬雪。诗人的音乐是什么呢?一种适合自己,也专属于自己的发声方式,或者一个独特的音乐形式或构造?而哪种发音方式适合我的声线,哪种表现方式才适合你对我的阅知呢?我希望是紧贴生活的,纯粹的,是“写什么”大于“怎么写”的。
然后呢,期待飨宴和冬雪。
(隆玲琼:《我在诗里自圆其说》这篇创作谈是当时《红岩》在做成渝诗人专辑时约的稿,当时刚做了阑尾手术,感情也比较丰富,就写了《中年阑尾》一组诗交了,也写了这个随笔。)
相关链接:

编辑:朱阳夏 责编:陈泰湧 审核:冯飞
【免责声明】上游新闻客户端未标有“来源:上游新闻”或“上游新闻LOGO、水印的文字、图片、音频、视频”等稿件均为转载稿。如转载稿涉及版权等问题,请 联系上游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