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周年!感谢你我砥砺同行
编者按:
“文学新征程”是重庆文学院和上游新闻联合推出的一个栏目,旨在通过媒体平台将我们行进在文学道路上的重庆青年作家适度推一推,让更多的读者知道我们,认识我们,并在我们的创作故事和创作心得中得到一些启发和帮助,在文学的道路上再增加一些同行者。
该栏目每间周的星期三推出一篇,2023年5月31日推出第一篇,迄今已发表推送了26篇。根据一些读者和被访谈作家的建议,我们特在栏目推出一周年的这个时间点做一期特别策划:访谈者和被访谈者的位置调换一下,进行了一次“逆向访谈”,让本栏目的主持人成为26位作家的“拷问”对象,给大家一个“报仇”的机会。
由于本期被访谈者更多是以读者和作者身份接受访谈,故访谈内容不能完全代表上游新闻文化频道的观点,谨代表被访谈者个人对文学及文学现象的一些看法,限于视野及学识水平,难免有失偏颇。特此说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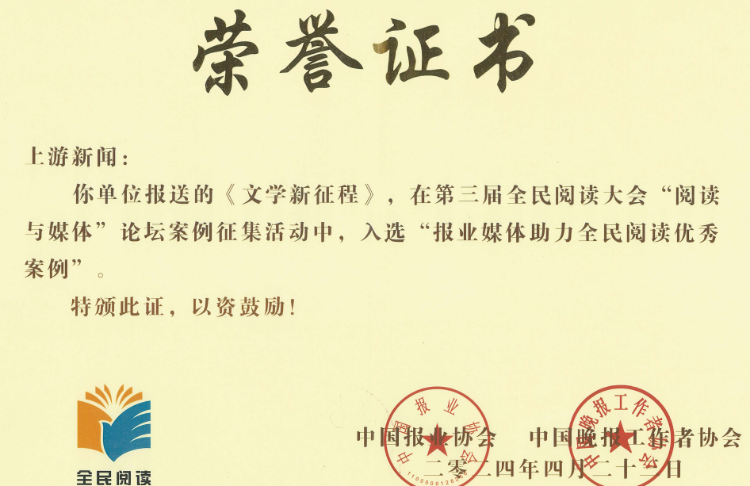
泥文——《获得与坚守》

泥文:我记得我的那个专访标题是《获得与坚守》,这个栏目在上游新闻坚持下来有了一年了,推出了那么多比我优秀的青年作家(我是老年了,感谢让我年轻延续了一下)。我想,那个标题也可以用在此时:在重庆文学院与上游新闻的加持下,你的“获得与坚守”也是有目共睹的(除开工作原因),面对写作与现实生活的意义,坚守与获得,你有没有觉得,文字与生活是互为牵强的事呢?如果在这个基点上展开,如今为文之人能不能算真文人?
陈泰湧:牵强?不,我个人的观点恰好相反,文字与生活恰好是一种相互的“救赎”。除开我的编辑工作,我也是一个写作者,是从写作中再一次寻找到生活的价值,少年时也曾豪情万丈,噫呼吁,“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可到中年才发现“满眼青山未得过,镜中无那鬓丝何”。人生不可重来,也再无机会去建大功立伟业。罢罢罢,只有文学是门槛最低的,入门永远都不嫌晚的。况且人生越多舛,越是文学的财富。人活一世,不能只给世界留下一声叹息吧!应该留下点有价值的东西,一本书、一首诗,所以文字与生活彼此成全,相互救赎。
只要不是文盲皆可称为文人,但是否是真文人那就难说了,这个“真”字很难,其实看一个为文之人是否“真”,读他们的文章即可,与是否发表、是否获奖无关,与作者的学历职业职位也无关,读者能从文章中读出是否有真情,读出是否有风骨,读者心中自有判断——无论古今!
晏菁——《紫雾里的守护星》

晏菁:很荣幸能够在“文学新征程”栏目当中去对写作进行更多的思考。其实,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我也感受到“文学新征程”带给我的一个关键词思考,那就是“传承”。无论是对于本土新人写作者的采访,又或者是资深写作者对于经验的传授,我觉得上游新闻“文学新征程”的栏目,非常注重对于写作新生力量的培养,以及对于写作经验和技巧的传授。在过去,我一直有着一种观念,那就是写作是一件绝对孤独的事,必须剪除那些与写作无关的部分,但在接受访谈之后,我也思考了很多,这种传承是否也意味着写作超越了自身的局限,开始与更多年轻力量一起成长?它对于我们写作者来说是必需的吗?请问你如何理解“传承”在我们写作行业当中所起到的作用?
陈泰湧:文学从来都不是凭空而来的,从儿时外婆讲的故事开始,应该就是对我们进行的文学启蒙,再后来我们大量的阅读,也是浸润在名家的字里行间,他们的语言、他们的思想,我们潜移默化地接受了传承。
重庆文学院的“高研班”和“创作员班”给了我很大的启发,以我个人体验来说,文学院给我指派了张者老师,对于小说的具体创作,我几乎没学到任何技法,但在和张者老师的日常交流中,他让我们同学之间互相评议,以及他对我创作中的一点点拨,真有拨云见月的感觉,是一个人独自去阅读独自去领悟独自去写作所不能得到的,这就是论“道”。后来,李燕燕老师又带领我从事非虚构领域的写作,有良师,让我少走好多的弯路。我就想,如果开设一个栏目,将我们正在文学道路上攀登的这一些年轻作家组织起来,让他们讲讲自己的文学经历,说说自己的创作心得,或许就能给更多的文学同行者以启发。其实,我就是最大的受益者,因为在做这个栏目的时候,我花了很多时间去思考,去感悟。文学本来就是一种思想的分享,文学是无私的,传承有很多种方式——不是人家不给,而是你有没有想好怎么去接。
舒舒——《文学是心中的光》

舒舒:一年,两个字,两个字却含了四季。有人在四季中走了。有人走进了四季。“文学新征程”用自己的方式,承载着看不见的文学使命,吸附更多走进四季的人,用文字涌泉、煮茶、交友、添香,促进文字与文字的碰撞、思想与思想的碰撞。很幸运,我在“文学新征程”上提前完成了“文学初”的小结,从而有了对人生、对文学新的思考:如何沉下来?如何静下来?沉是降落、向下、沉淀。静是平静、安静、宁静。请问你是否有过同感?如何调节心“内”“外”之间的“动”与“静”、“明”与“暗”?
陈泰湧:“松风庭院昼沉沉,颇惬浮生习静心。”从古至今所有的文人都渴望着内心宁静,都想有一方庭院,静静地写字。可是很难。在当今这个娱乐品类众多的当下,更难,在外界各种诱惑风起云涌的当下,非常难。在和这二十多位年轻作家的访谈中,我发现了这些优秀的文学攀登者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不刻意地去避世,而是积极地在书写生活。这是一种动和静相依相融的状态。他们在写作前有着强烈的书写冲动,这是动,一旦提笔,就融入到了文字世界中,这是静。换一种说法吧,他们也会渴望发表,但他们对写作的渴望要远大于发表的欲望,他们把欲望放在了文章中,他们保持着一种动和静的居间平衡。这或许就是我所访谈的这些年轻作家们,比其他写作者更优秀之处。
蔡晓安——《用文字照亮人生的路》

蔡晓安:对一般人来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已经很难了。你既是新闻人,又写了几部长篇小说,除此之外,还得著万言文,在既定而有限的时间内,你是如何做到在三者之间自由穿梭的?而且,我们都知道,新闻讲写实,一板一眼不能与事实有出入,而小说,却讲创新,讲虚构。这是两套思维方式。请问当你已经习惯了新闻的行文风格,再来写小说,会不会有产生困感的时候?
陈泰湧:写新闻是我的工作,写小说是我的生活,这样说吧,前者是大米饭,后者是鸡鸭鱼肉。我和很多写作者一样,都不是专业作家,必须得有一份职业来养家糊口,然后才能通过文学写作去追求“诗和远方”。新闻写作是一种应用文体,并非文学创作,另外,新闻写作只是这个工作的其中一步,前面还有选题、策划、采访,后面还有编辑等工作,它是一种综合能力的训练,通过长期的新闻写作训练,能让我对小说写作中选题的把握,素材的积累,文字的精炼产生积极的作用。比如最近出版的《小乾坤》就是一部反映重庆火锅人的小说,二十多年来我采访过上百位开火锅店的大小老板,看他们潮起潮落,这些观察也就成就了我的创作。而你所提到的困惑,对于刚刚从事文学创作时的我确实是存在的,但反复练习,不怕写废,有思考,有顿悟,现在已经“脱困”了,跳出这个困惑之后就发现文学领域足够宽阔,有无限的可能。其实,我更希望将新闻和文学这两者联系得更紧密一些,目前正在“非虚构”写作领域试水。
敖斯汀——《在时间中书写》

敖斯汀:时间过得真快!说出这句话,我感觉我有了老人才有的沧桑。写作某种程度上是抵抗时间,又在时间之上,虚构了时间。在我心中,你在生活压力和各种身份转换中偷取了时间。我知道你至少写好了三部虚构小说,为何又转向非虚构,你是向非虚构“逃亡”了吗?你觉得在我们所处的时代,虚构和非虚构,哪一种更有力量?为什么?
陈泰湧:写第一部长篇小说《白色救赎》时,我没想过能出版,甚至没有奢望能完成。那是人生中非常黯淡的一段时光,我觉得应该写点东西,毕竟写作是没有门槛的,越是困顿的时候越能迸发力量。写自己的亲身经历?总觉得差点什么。那就写理想中的我吧,或者说是我理想中的一个人物,于是就有了这部虚构小说。这部小说既是小说主人公的自我救赎,也是我的自我救赎。随后又写了《心杀》和《小乾坤》,在后面的写作中我发现有些题材不一定适合用小说来表达,或许非虚构可以尝试一下。我并不是“端水”,我是真的认为“虚构”与“非虚构”各有所长,都有自己的力量。就像一双筷子和一把餐刀,不能说哪种餐具更好,要看你是吃火锅还是吃牛排。我不是“逃亡”,而是想多吃一个菜。当然我也有一点“小九九”,写小说的高手太多,我不能一直依靠运气吧?非虚构写作目前正处于一个上升阶段,文学期刊对非虚构稿件的需求较大,高手又不是太多,相对容易发表,建议大家不妨多关注一下非虚构写作。
冯茜——《人生是一首长诗》

冯茜:我在近年的写作和阅读中发现:文学作品虽然多元丰富,样式也多,但同质化现象也很严重,题材局限,写法趋同。那么在这种现状里,作家是否需要一种探索的勇气呢?我们需要在哪些方面进行创新呢?而在创新同时,我们又要怎样守住我们好的传统呢?
陈泰湧:你问到一个编辑的伤心处了。我在日常编稿时发现好文章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能让人眼前一亮,“嘿,原来他是这样写的!”然而绝大多数的文章是看了开篇第一句,你就能知道这篇文章的最后一句,“啊,一幅画卷正徐徐展开!”小文章如此,大文章同样如此,很多编辑都有这种看稿看得想自杀的冲动。
这是很显性的,还有一种较隐性的,有些作者文笔不错,也能找到编辑的兴奋点,可你多看他的几篇文章,就发现今天张家大哥,明天李家大婶,还是一个套路。说好听点,就是没有新意,没有突破,说难听点就是自我抄袭。
作为一个写作者,最重要的是不断地创作。而这个“创”字,我的理解就是创造和创新,是不是一篇比一篇更好?哪怕失败也没关系,试错才是成功的亲妈嘛!如果一味地重复别人或重复自己,就算是发表了很多,又有什么意义呢?在微信群里朋友圈里炫耀一下数量而已,“也笑长安名利处,红尘半是马蹄翻”,有谁能记住你的文章,真心为你点赞呢?
如果要说守住传统,我觉得还是诸葛孔明先生那句说得好,“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守住真心,抛弃杂念,“由来不是求名者,唯待春风看牡丹。”我们一起静下心来好好写吧。
吴越——《想在人类的群星中留下姓名》

吴越:在我还是一个工科生的时候,学习和工作是一件有迹可循的事情:背几个公式,拿多少学分;打几个螺丝,挣多少工资;所有的步骤明晰,按部就班就是标准答案。但写作似乎不是这样的,提纲在写作的过程中一变再变,笔下的人物和事件总会“随机应变”,更像是大脑中的秩序与灵感在博弈,我常常会感到:文章没有结尾之前,我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我想知道,作为一名更成熟的作者,你是否会遇到同样的问题?这是写作的必然结果、必经之路,还是说,是一种需要去克服的坏习惯?
陈泰湧:先握个手,拥抱一下!感觉找到难友了!你读工科,我读医科,应该都是逻辑性很强的,但文学是个可以事后来总结规律,写作时却没有逻辑的东西。
我写第一部小说心里有一个故事梗概,信马由缰地写,写完了发现只有男主角的名字是我的预设,其他全变了。第二部稍微学聪明了,写之前学会了列提纲,然后写到一半的时候,我把后面的提纲重新写了一次。这种“随机应变”虽然给我们的写作在结果呈现方面带来了不少的阻碍,但我个人却很享受这个过程,我笔下的人物自己在呐喊,他们不愿被我来左右命运,他们要借我的笔写出自己的命运来,他们是活生生的,这是一种多么美妙的感觉啊!
我想,可能我预设的提纲是循规蹈矩的,但我内心却是不安分的,想要打破各种条条框框,嗯,这样的小说写出来一定是我内心最真切的,应该是最好看也最有感染力的。
就这样吧,你好像问错了人,没有问到成熟的写作者,但恭喜你,找到了共鸣。
熊那森——《写作是一团叛逆的冰》

熊那森:很高兴能够成为“文学新征程”栏目的一员,虽然我同时很羞愧。感谢文学院,感谢上游新闻。我常听你鼓励青年作者多写,给他们很多鼓励,包括我,首先我要对你这种大情怀表示敬意。还记得与你相识是在第一届中青年作家高研班,当时在食堂听你与人交流,侃侃而谈,觉得你是一个经历丰富、洞察力强且善于表达的人,心想你一定写了很多大作,但我没有查阅到。后来又有机缘一起学习,交流更多,发现你机智幽默,总是嘻嘻哈哈的,并不像一个正在严肃创作的人。我偶时还想,你的想法很多,看问题也很深,不写真是浪费啊,没想到,不久就看到《心杀》,接着你又出版《白色救赎》和《小乾坤》,我非常吃惊,也真高兴。后来听说你的很多作品其实是很早就完成,这么多年你是一直都在默默保持创作吗?你经历丰富,又具有新闻人的专业素养,一定有很多素材,你会特意整理素材吗,一般是如何搜集与整理的?作为编辑,你的眼光毒辣,要求很高,你对自己也是这样吗,平时会不会对自己的写作有不满意的时候,又如何面对?这些都是我想学习的地方,哈哈,谢谢。
陈泰湧:要说感谢,真是应该感谢重庆文学院给我们很多年轻的写作者搭建的学习和交流平台,第一届高研班据说还是张兵院长靠自己的人脉去读客拉来赞助才得以开班,也感谢上游新闻的各级领导对文化频道的支持、指导和厚爱,使得“文学新征程”这个栏目得以诞生和延续。
就创作而言,我个人认为写作只是临门一脚,更多的创作还是在我们日常对生活的体验和观察。只不过有些作者开场就踢进了球,就像你一样,非常年轻就发表了作品,得到了重庆文学奖,有一些作者要在加时赛甚至点球时才射门,同样很精彩。我算是下半场才进了球吧。如果现在将我们所做的“文学新征程”重新读一遍,你会发现我们所选择的访谈对象并不是以年龄划分,而是那些刚刚进球,尚未成为“球星”的一群人,其实我们就是想作一个“催化剂”,把我们这些文学“新实力”的创作经验分享出来,鼓励更多的人勇敢地拿起笔来,将自己的生活变成一篇篇精彩的文学作品。
为什么要做这样一个栏目,也是我在读高研班时就产生的想法,我是一个茫然行走在文学创作道路上的人,突然之间发现了这么多的同行者,大家都有共同的感想、困惑、追求和喜悦,俗话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将心比心吧,况且,赠人玫瑰手留余香。
虽然我也发表了几部作品,心里会有一点点小得意,但在和大家交流时才明白自己只不过是运气好而已,不断地职场体验,就是盘带、传球、再盘带,等观众都觉得太无聊了,想退场时,我瞎打瞎撞把自己想写的东西写出来了,把球踢进了球门,哦,是谁把球门挪到了我的前面?
我也会遐想,下一个进球能不能姿势更潇洒一点?
南风子——《为知了建造房屋的人》

南风子:你有多个职业领域的跨越经验,无疑为你的创作提供了独特的视角。作为一名跨越多个行业的创作者,这些多元的经历对你的写作带来了哪些助益?你已经成功创作了以医疗为背景的《白色救赎》和以美食为主题的《小乾坤》,那么在未来,是否考虑将更多其他行业的元素糅合进你的作品中呢?在创作这些涉及特定行业题材的长篇小说时,有哪些独到的写作心得?此外,我们注意到许多拥有新闻背景的作家在文坛上取得了显著成就。对此,我想探讨一下新闻素材与小说创作之间的联系。在创作过程中,您是如何巧妙平衡小说的故事性和文学性的呢?最后,我必须向重庆文学院和上游新闻表达我由衷的感谢,这个“文学新征程”为重庆的作家群体,特别是青年和基层作家,提供了宝贵的展示机会和平台。
陈泰湧:文学创作是极其神奇的。跨越多个行业,看上去很美,其实心里很苦,谁不想岁月静好呢?如果不进行文学创作,那以前的那些阅历就只能是“瞎折腾”,既然经历过,不妨就把这些经历当成财富——“塞翁失马”是一句听上去很舒服,很能自我安慰的话。
我有医疗等行业的职业经历,但我写的并不是行业小说,只不过以这些为背景,仍然是写人,写人心,写我们这个社会。当然,因为有这些职业经历,在创作中对人物的塑造、环境的营造都是有益的,更真实,真实感才能把读者带入进去,产生共情。我不仅当过医生,当过记者,还在杂技团干过,书店、出版社、画廊、博物馆等地方工作过,甚至开过心理咨询所、卖过高科技农药,这些职业体验中有很多打动我的东西,我希望能在今后的创作中慢慢用到它们,这样创作出来的作品至少不会太枯燥吧。
新闻写作和小说创作虽然都是驾驭文字,但这其实是两个不同的类别,前者是应用文体,是记叙现实,后者是创造一个世界,可以仔细思考,思考人性的复杂性、事件背后的复杂性,也有更大的自由度。“新闻结束的地方是文学出发的地方”,这既是指出了新闻和文学在时间场域的不同,也是我的一个状况,目前我主要转向文学创作和编辑工作,曾经的新闻训练仍然是有很大的帮助,比如对选题的把握,对素材的挖掘,对文字的精炼,对时间效率的把控。
另外,我注意到“非虚构”写作是一轮初升的太阳,恰好,新闻的训练和文学的练习如果用在非虚构写作上可能会产生更为美妙的味道,我想作些尝试。
王景云——《我的心是燃烧着的水》

王景云:不同的经历,给了你不同的人生体验。从中体悟到更深的人性和探究到事物的本质,使得你在虚构和非虚构写作上都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你在多行业中跋涉,不断地做出选择的同时,时光也在不知不觉中流逝。你每一次做出人生重要抉择时,是否会运用一种成本思维?比如:时间成本、机会成本、决策成本、沉没成本等等,毕竟对一个文学写作者来说,每一次选择都要权衡工作、生活与写作的时间与空间的各种关系,从而把握生活的主动权。另外八卦一下,读你的小说有诗意的语言贯穿始终,你的文章中也经常引用古人诗句,说明你是一个有诗意的人,今后有否打算涉猎诗歌这种文体?最后,感谢重庆文学院和上游新闻的“文学新征程”栏目,给我这个最最基层写作者提供了交流和展示的好平台。衷心感谢!
陈泰湧: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哪有那么多可以主动选择的机会哟,很多转折往往都是被迫的。但我觉得只有写作是可以由自己主动选择的,选择什么时候写,选择写什么,可以用写作来完成自我的救赎,弥补人生的缺憾,甚至还可以架构一个自己理想中的世界。也曾和一些朋友谈到过写作的沉没成本,写作我们固然希望有更好的结果,但创作的过程才是最有价值的,我并不认同没发表就是“沉没”,比如曹雪芹写《石头记》,从发表的角度而言,他那一生都是悲催的,可我们谁能说他的那一生是无意义的?写作本身就是意义之所在。
说到诗歌,在中学时代也曾写过一些,也发表过那么一两首。但我认为诗歌创作更需要天赋,而小说创作更青睐人生况味。多读诗是有好处的,可以让自己的语言变得更美,我现在不写诗,但是仍然爱读,只可惜现在读到的“分行”很多,诗很少,好诗更少,感觉现在的诗人们把激情用到了四处投稿和朋友圈的各种晒,用在创作上的精力太少了。仍然是那个观点,创作的过程才是最有价值的,用的精力越多,作品才会越好,才能少挨读者的骂。自勉,共勉。
萧星寒——《我把重庆写进科幻里》

萧星寒:你有没有觉得科幻出现在“文学新征程”是一件非常古怪的事情?长期以来,科幻都处于一个非常尴尬的境地。文学圈觉得你们科幻属于科普,科普圈则认为你们科幻是文学那边的,好比长了肉做的翅膀、在暗夜里飞的蝙蝠。你是如何看待这个问题呢?
陈泰湧:从我们邀请你做“文学新征程”的访谈嘉宾开始,就至少是充分表明了我们的态度,也代表了重庆文学院和上游新闻文化频道的观点,科幻也是文学,而且是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其后我们又邀请了罗琳和段子期两位科幻作家参与“文学新征程”,今后还会邀请更多的科幻作家来参与。
我至今都还记得小学时读到过的《小灵通漫游未来》《珊瑚岛上的死光》,这是文学的启蒙,也是科学的启蒙,如果这样的作品能“两栖”,在孩童心里同时播撒下文学和科学这两粒种子,这是多么美好的事呀!我不代表文学圈,也不代表科普圈,请允许我代表大读者和小读者这个“读者圈”,向你们道声“谢谢”!
李浩白——《不疯魔不成活的写作者》

李浩白:现在一部分文友从我的作品里替我引申发明出了一个“历史推理学”的新概念。我具体总结起来,认为“历史推理学”就是从已知的资料出发,尽量有广度、有深度地发掘和推断更多未知的真相。你对“历史推理学”有什么看法和建议?
陈泰湧:首先祝贺你“开宗立派”。
历史推理小说我简单地理解就是和科幻小说“背道而驰”,科幻小说是用当今人类的科学认知去设想未来,而历史推理小说则是用当代人类的科学认知和思想去重新演绎历史背景下的一个故事。不管是向南还是向北,读者喜欢看就是硬道理。
其实历史推理我们并不陌生,也不是你发明创造的,十多年前的《达芬奇密码》让很多中国的读者、观众“耳目一新”,江户川乱步奖被称为日本的历史推理的摇篮。所以,准确地说,历史推理的定义早就明确了:以历史上的真人真事为解谜对象的推理小说。目前国内也有很著名的历史推理小说,诸如《大医》《清明上河图密码》《长安的荔枝》等,当然,你的数十部作品几乎都是历史推理小说中的佳作,“开宗立派”之说是开玩笑,但说你是目前中国历史推理小说领域的领军人物之一,应该是准确的。
我非常喜欢读的一部小说叫《天下第一混乱》,各种搞笑的桥段,各种别出心裁的情节设计,我在哈哈大笑中竟然把中学没学懂的历史课全都补回来了。还是回到之前我谈到的那句话——好看就是硬道理。
刘云霞——《在疼痛中盛开的花朵》

刘云霞:对我的访谈《疼痛中开出的花朵》发表以后,陆续收到很多反馈。有重度抑郁患者给编辑留言,说找到了战胜自己的动力。这是写作的救赎。作为一位语文教师、兼职心理教师,同时也是一名写作爱好者,将爱好与职业融合,在救赎自己的同时给予读者力量,我很开心。我觉得自己常常处于一种矛盾之中,灵感乍起时,文思如泉涌,这个有意义,那个题材也不错。这个想写出来,那个也想写出来,我要写散文,我还要创作长篇。可是,一阵忙碌过后,再坐到书桌前,却沮丧地发现先前的灵感荡然无存,甚至觉得什么都不值得写,从而否定自己。这让人非常窘迫。想知道你是如何处理这个矛盾的呢?
陈泰湧:我也问过很多写作者,都有这样一个冲浪式的过程,先是觉得什么都可以写,然后一提笔就又觉得好像之前所想的没有那么有价值,甚至是写到半途然后废掉的。我也同样经历过这样一个过程,特别是写长篇小说,需要漫长的时间,那真是一种煎熬,写作中间还会面临工作、疾病、家庭关系等各种外界因素的影响。所谓成功者,不一定是最有才华跑得最快的人,但一定是能坚持跑到终点的人,咬咬牙,写完最重要!
经历过几本书的折腾后,我没有以前那么着急了,对于灵感也有了新的看法,所谓灵感,是触发我内心的那一点火花,是不是值得写,还需要静下心来,看看这个火花是不是这个社会的“痛点”,写作并不仅仅是个人情绪的宣泄,一定要做一点对社会有意义的事,不能去浪费纸张,出一堆送不出去的书吧?——爱护森林,作家有责!
当积蓄够了,写作的时候才会有情感的喷发,才会有创作中咬牙坚持下去的毅力。我一直想写一个题材,目前已经构思了两年了,仍然觉得忐忑,我想还会再花五六年、甚至十年的时间去思考,去积蓄素材,去酝酿情绪。我相信那会成为我最满意的作品。
但忆玲——《靠码字实现理想生活的网络作家样本》

但忆玲:很高兴成为上文学新征程的第一个网络作家,也因此而认识了很多喜欢文字创作的朋友。我喜欢把小说作者看成讲故事的人,无论是网络小说作者或传统小说作者,他们都在用心讲故事,你觉得网络小说跟传统小说是否有共通性?
陈泰湧:你这是设问句吧?答案显而易见噻。
我知道你所说的传统小说是指目前我们所谓的“纯文学”,对于不那么“纯”的,我们统称为“类型文学”,其实类型文学才是真正的“传统”文学。
从盘古开天讲起……我们从小听的故事,是口头文学吧?是一代一代传承下来的民间文学吧?等长大了一点点(其实是长了很多年以后),在茶馆里听说书,天天都是武松要打死老虎的时候,“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两个月过去了,老虎还没打死。时代发生变化,我们不泡茶馆了,拿起报纸看连载,于是金庸成了文学史上的巨擘,再然后,我们进入了网络时代……时代变了,载体变了,文学还是文学,读者还是读者。
如果非要把网络文学和纯文学来作对比,一个是“下里巴人”,一个是“阳春白雪”,都是音乐。有人喜欢听钢琴,我就喜欢听唢呐,那声音多震撼呀,不是进洞房就是搭灵堂,人生大事!音乐没有什么高雅和低俗之分,都有各自的听众,如果有人非要说自己才是高雅的,嗯,确实,啷个说都可以,那我也可以用“东施效颦”这个成语来赞美他——我就觉得这是一个褒义词。
李苇凡——《用诗歌的微光照到半米之外》

李苇凡:我读《白色救赎》,一天就读完了。书中展现的人物、事件和场景感觉很真实,我也经历过那个年代,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这种投入有利于更好地理解作者要表达的东西。我知道你是一位新闻工作者,跟新闻写作一样,小说的写作肯定也需要搜集资料,我想问的是,在虚构作品的写作过程中,在资料的选择和运用方面,你是如何协调生活的真实和文学的真实?从文本的呈现看,既要透露出真实,却又似有所隐瞒,就是西方理论所说的披着面纱的真实,如同一座冰山,你认为一部好的小说,其表面显露的东西和隐藏的部分有着怎样的尺度?是冰山的物理比例吗?
陈泰湧:邱华栋说过,“新闻结束的地方,是文学出发的地方。”社会这么庞大和复杂,现实也无比的庞大和复杂,我们所见的很多“新闻”已经远远超出了人们理智的想象。但文学有另一种力量,我们可以去探寻更幽深的人性,去改写现实中尚无法到达的结局,可以去重塑真善美。从这个角度而言,我认为写作不是一个冰山显露出多少比例的问题了,而是重塑,水是真实的,而冰山的形态是作家去塑造的,我们可以去塑造一座造型特异的冰山,这是我们显露出来的社会的一角,也是显露出作者内心的一角,但水,就是真实的世界,那是汪洋大海,也是作家的内心世界,很大。不是刻意地要去显露或隐瞒,而是不得不取舍,任何好的小说,真的就是“沧海一粟”。
蓝钥匙——《笨鸟的梦想是成为一棵树》

蓝钥匙:在阅读中,会发现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作品往往是“特殊”的角色和情节,人物身世成谜,要么背负深仇,要么经历非凡。但我们普通人,每天经历的都是油盐酱醋茶。故事缺乏激烈的冲突,就是小清新的岁月静好可以吗?写作者在创作中,如何从“小乾坤”里写出“大味道”呢?
陈泰湧:鲜衣怒马少年时!每一个人都曾有过英雄梦想,只不过被社会现实捶打之后,有的被塑型成了或“大卫”或“思想者”或“维纳斯”,有的被锤成了一摊泥。每个普通人都是有故事的,我曾经在一篇创作谈中提到过,“无论发达还是落魄。没有一个人是甘于平淡的,每一个人都是厚厚的一本书。最贵的(火锅)牛油其厚腻的味道也比不过任何一个小伙计的人生味道。”的确,我们普通人每天经历的都是柴米油盐酱醋茶,但一口锅一个碗却是装满了人间的喜怒哀乐悲苦愁。我完成的两部小说,有读者就批评说主人公没有“飘扬”起来,没有“功成名就”,“不过瘾”。是的,我就是写的小人物,他们都有英雄梦,但他们毕竟是和我们一样的普罗大众。我认为文学作品必然是要写出我们内心的那种欲望,“名垂青史、封侯拜相”是一种欲望,“封侯非我意,但愿海波平”也是一种欲望,“吃得开心睡得安稳”仍然是一种欲望。文学创作毕竟不是真正的人生,太平淡了就没有读者看了,会被读者骂的,如果我们能通过对“小人物”的书写,写出对人世的悲悯,对美好的向往,这个过程就是味道之所在,读者会与主人公共鸣。
石若轩——《文学评论AI化路径的逆行者》

石若轩:在访谈之前我看了你的《白色救赎》,其实我注意到无论是《白色救赎》还是近期的《小乾坤》,它们都具有显著的生活感,两部作品讲述的故事都是有机的,面对这两个故事的时候,我的阅读动力并不是情节,而是人物在情节中的反应。所以思考为何我写的小说中的人物都是共用同一张脸,为什么他们都是“躺”在故事里的?除了我对于故事情节的设计与想象几乎乏善可陈之外,这些人物缺少一种具有代表性且稳定的核心性格,多维的性格在各种精密情节中的内心与行为反应可能是避免故事脸谱化的方式之一。所以我好奇的是你在以往的创作过程中,倾注笔力最多的是哪些角色?你喜欢他们的性格吗,这些人物的性格是否有你自我性格的投射或是分身呢?
陈泰湧:我也很喜欢你的文字,我们的风格不一样,而且你在文学评论方面的造诣很深,是我想学却又学不会的。
《白色救赎》着力于医学生沈鲍鑫的成长及被社会捶打的故事,可以说是一部半自传体小说,《小乾坤》着眼于重庆火锅创业代言人张隐的成长和社会的变迁,这个人物也是我个人职业生涯不断变换的一个缩影,可以说都有我的影子,写作中我和主人公会一起笑会一起哭,同喜同悲。当然,我也创作了另一部医疗背景的心理悬疑中篇小说《心杀》,刻画的是数个女性角色,我个人认为也算是比较成功吧。
我写过的所有人物,哪怕是一个小小的只有绰号没有名字的龙套角色,其实在我的生活中都是有原型的,这或许就是年龄带给我的财富,也是这二三十年里各种职场折腾后的另一种收获吧——蓦然回首,那些我爱的人和我恨的人都被写进了小说中——一个人生忠告:千万别得罪那些写小说的人,否则“小说里面见”。哈哈!
韩路荣——《从“三无女孩”到耀眼的“女人花”》

韩路荣:你的微信名是B612行星,这个微信名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吗?还有就是我想把你问过我的一个问题也问你一下:请从一个新闻人的角度,你对网络文学怎么看?你觉得它未来的趋势是什么?
陈泰湧:“你夜里仰望天空,因为其中有一颗星上有我,因为其中有一颗星上有我在笑。对你来说,所有的星星仿佛都在笑,于是就有了会笑的星星。”我的微信名其实是一个“密码”,也是寻找朋友的“暗号”,如果你知道这是《小王子》一书中小王子所居住的星球,那就是“志同道合”的朋友,一定是有童心的人,肯定会是值得深交的朋友。童话就是这样,永葆童心的人一定是真诚和善良的。这也是我一直很喜欢看童话的理由。以前孩子还小的时候,我打着给他买书的名义给自己买了很多童话书,现在打着研究文学的名义,仍然在买童话书。不要以为一个上了年纪的大男人就不能喜欢童话了,“所有的大人都曾经是小孩,虽然,只有少数的人记得。”
对于网络文学,不可否认,门槛很低,只要会写字上网都能进入,但也正因为门槛低,进入者众,要想成名成家也就更艰辛,要经过更“血腥”的拼杀,大浪淘沙始见金,能在网络文学领域里成名成家的绝不会比传统文学领域来得轻松,至少在体力上的消耗就是一个门槛,而且其文字与读者的距离更亲近,很值得钦佩。另外就是“网络文学”对文学的普及作用,让文学不再是高高在上的阳春白雪,我记得有人说过,“书店的敌人不是网络,而是不读书”。
从量变到质变是客观规律,我个人认为,目前网络文学已经走过了最初的野蛮生长时代,无论是从资本的角度,还是从读者的角度,都已经聚焦到了质量上,对网络作家的要求也就更为残酷了!加油!
隆玲琼——《从“恶人谷”出发寻诗》

隆玲琼:一个好的写作者,需要保持内心的、对自己作品的挑剔,而不是总想着读者会怎么看;但一个好的写作者,也应该通过写作的方式来回馈读者。不少人在成名之后,写作中有了急于回馈读者的无形压力存在,往往写出一些粗粝质地的作品,很难再突破和提升。你觉得一个好的写作者,该如何保持自己的写作纯粹,一心专注于发现、思考、创造呢?
陈泰湧:你说的这种“粗粝质地作品”情况非常普遍,某些作者会炫耀一年在全国的报刊上发表了数百篇文章,我在工作中也会经常遇见,在邮箱里收稿时会发现一些作者每天都在投稿……这些作品或许文从字顺,或许钻研透了编辑部用稿的“时令”和“语调”元素,但这些是好作品吗?这些是好的写作者吗?其实业内对他们也有专门的称呼,“稿贩子”!褒义贬义不用细说了吧。其实真正成名了的作者,是非常爱惜羽毛的!他们或许笔耕不辍,但是否拿出来发表,绝对会三思而后行,不允许低劣的作品拿出来发表。当然,人上一百形形色色,也有少数不爱惜羽毛的,读者会送他们“烂书作家”称号,会遭到唾弃的。如何保持自己的写作纯粹,我认为,读者是要花时间花钱来读你的作品,一个好的写作者,不要自嗨,要敬畏文字,尊重读者,要对得起“天地良心”四个字。
罗琳——《用软幻想写硬现实》

罗琳:虽然我个人的关注点是发掘和繁荣本土幻想文学的创作,但是我还是想知道在现实题材方面创作较多的作者们,会怎么看幻想文学——特别是幻想中的重庆,甚至是幻想中的中国,跟现实会有什么样的联系。换而言之,我想知道更多幻想文学的读者和创作者之外的视角!
陈泰湧:打个比喻吧,现实生活就是平街层,新闻算得上是上了一层楼,可以通过新闻看到更多的真相,而现实题材的文学作品就是再上了一层楼,可以探寻更多的人性,那么,幻想文学或许就在第三层楼,看得见楼下的人,又少了一些现场的喧嚣和束缚,幻想作家们能看到的是更远的天际,看到的是浩渺的星空,在帮助我们寻找未来,以及构建一个理想的世界。在我看来,幻想文学是“无界”的,至于幻想题材是否用到重庆,是否用到中国,或许作家能更便捷地将这些现实中的地理特征和文化背景代入到小说中,会对我们的读者更多一些亲近感吧。我最喜欢的一部科幻小说是《北京折叠》,我喜欢它,与地域无关,作者郝景芳也只是因曾经租住在北京北五环外的城乡结合部而触发了创作的灵感,小说中所构建的那三个空间,其实与“北京”并无关系。
杨不寒——《一切写作都是基于语言的幻想》

杨不寒:交游,是一个作家生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文学新征程”这个系列访谈,想必也让你更深入和全面地了解到了重庆作家当下的创作情形。我想这是一种难得的经验。作为文学后生,我对重庆作家的基本情况还所知甚少,但是很高兴能从这个栏目中管窥一二。你是否愿意简单介绍一下,在你看来,相比于前辈,重庆九零后作家有那些值得注意的新质?这些新质是值得欣喜的,还是值得担忧的?
陈泰湧:因为做这个栏目,也让我对重庆新生代的作家们有了更多和更全面的了解,总的来说,新生代的作家们更低调,更务实,也更爱惜“羽毛”。这些年轻的作家们其创作能力有高有低,成名有早有晚,很多是作品上了全国的文学大刊,我们才一惊,“咦,又冲出来了一个重庆的年轻作家?”
这群年轻作家很低调,很谦逊,有正确的价值观,不会成天醉心于在报屁股上发一点豆腐块,公众号、美篇里发一堆文章,然后就成天在朋友圈和微信群里各种炫耀,以乞讨廉价且虚情假意的赞扬,当然,现实也决定了这群年轻人没有权力去利用关系发表各种渣渣稿件,这或许让他们的文学之路走得较为艰辛,但这又未尝不是一件好事?文学之路的跋涉是需要很多特质的,唯独忌不知天高地厚的自我陶醉。
总之,重庆的年轻作家群体在文学创作的道路上有些“闷声发大财”的感觉,他们是一面镜子,让我时时反省。
周睿智——《把灵魂从混沌中独立出来》

周睿智:你最近两年连续有长篇作品问世,请问你在文学创作上有野心吗?主要在那些方面?
陈泰湧:所谓野心,我所理解就是能力和目标不匹配。每个写作者都有野心,因为大家都有更远大的目标,也常常会在写作中挠破脑袋。
我一直都想着写一部有关川江的长篇小说,因为我的祖父曾经是川江上的大领江,尽管我和他从未见过面,但我的血脉里始终涌动着川江澎湃的波涛,可惜我现在还驾驭不了这个题材,力所不逮,目前的创作,就当作是为这部作品练笔吧。
要说近期的创作目标,那就是准备写一部儿童文学作品,其实我个人觉得,真正的作家最应该写的就是儿童文学作品,我们都从童年走过来,在那个时期接受到了文学的熏陶,感受到了这个世界的美,现在,是该我们“回礼”的时候了,每个作家都应该给我们的孩子创作出一部优秀的作品。
儿童文学是最纯净的,看着简单,其实我是尝试过的,要想写好是非常难的,作者的心里要纯净,文字要浅显和简练,说话要蹲下身子……唉,市面上有些东西打着儿童文学的旗号,拿腔拿调,板着面孔说教的,那不是儿童文学,那是弱智文学——读者不管年龄大小都是非常清醒的,只有作者自己是弱智而已。真正的一部好的儿童文学作品是能让孩子爱读,成人也爱读,能受益终身的,比如《小王子》。
段子期——《科幻给了我更辽阔的世界》

段子期:近期文学界兴起一些新的学术概念——“新南方写作”、“新北京作家群”等等,你如何看待文学与地域文化之间的关系,以及当代文学创作在重庆地区的现状和发展?我们有孕育出一个“新渝派写作”概念的可能吗?
陈泰湧: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不同的地域,其文化背景自然存在着差异,如果这个地方的优秀作者多了,优秀作品多了,自然就形成了一种群聚效应,会被放大,就会被学术界冠上一个新名词。例如“新渝派写作”的概念能否提出,能否被广泛认可,不是你我或哪一个行政部门提出来就行的,是必须靠一大帮“新渝派作者”和“新渝派作品”来共同堆砌,是需要时间来发酵的。这样说吧,我关注到酉阳、秀山等渝东南地区,这里的写作者们有着语言的天赋,是出大诗人的地方啊,巫山、奉节等地,那里的大山大水,那里的川江奔腾了上万年,远去的船工号子,消失的纤夫步道,还有大江截流的移民们,那是多么厚重的小说题材呀,还有“8D”梦幻般的中心城区,已经有很多重庆的科幻作家在享用这一得天独厚的创作资源了。资源有了,作家也有哇,现在重庆青年作家正大踏步地走在“文学新征程”上,目前还缺少一点什么?缺催化剂!扶持政策算是一种重要的催化剂吧,能加快时间的进程,但如果没有又会怎么样?催化剂不是化学反应的决定因素,缺了,大不了时间慢一点而已,化学反应仍然是会发生的,我相信“新渝派写作”这个概念会诞生(可能不一定叫这个名字),也会发出耀眼光芒的。
周宏翔——《希望小说比自己走得更远》

周宏翔:很荣幸成为“文学新征程”的一员,这里想说,因为每个人的审美都不太一致,对小说的理解也千差万别,但是在创作中,我依然很想知道对于小说的认知大家的差异性在哪里?就是什么样的小说在你眼中是好小说呢?李安导演在一次访谈里提到,真正打动人的电影其实不是故事,而是某个moment,令人难忘的一个片断。或者说,故事、文笔、结构、人物,如果都是重要元素,但最让你会心一击的是哪一个元素呢?
陈泰湧:每个作者不同的人生经历会决定他写出来的作品千差万别,同样一部作品,因为读者的人生经历不同,所以他们读出来的味道也是千差万别,但好作品肯定有一个共同特征,能打动大多数读者,能让读者跟着作家的笔或哭或笑,如果读者不能动情,那就是在看耍猴咧,作家就是那只猴,读者在看你怎么上蹿下跳闹笑话。
一部小说是一个整体,由很多重要元素交织而成,缺一皆为遗憾。如果一定要选择一个“元素”,我认为作为读者,对结构这些可能不会太过于注意,他们会关注什么?文学作品有两大永恒的主题,爱情和死亡,这也是我们这一生都逃不掉的,把这两个故事讲好——李安说的不是故事而是片断(moment,片刻,瞬间)——那就把爱情最炙热或最哀婉的那一个片断讲好,把死亡最痛彻心扉或长歌当哭的那一片断写好,写到极致,就会是一部“直击人心”的好作品。比如《白色救赎》就是谈论死亡,《小乾坤》就是谈论爱情,里面即有很多至情至性的moment,哈哈!我现在迷茫了,第三部又该写什么呢?
杨小霜——《我的躯壳里藏着一个孩童》

杨小霜:生活中大多数人都不是专职作家,或者说在没有成为专职作家之前,应当如何处理工作、生活与文学的矛盾?听说你的人生中曾有一段十分灰暗的日子,请问是文学让你重新“活”了过来吗?文学到底能带给一个普通人什么样的变化?
陈泰湧:对于非专职作家来说,文学不是你的一日三餐,你不靠它活命,但文学永远是我们的维生素,是我们的咖啡因,有了它,再苦再累,生活都有盼头都有寄托,人才可以不在生活的重压下变成行尸走肉。越是在至暗时刻,越应该抱有希望,因为文学是最没有门槛和“成本”的,当然,不是说只有提笔创作才算是文学,阅读,也是亲近文学的一种方式,看花开花落时,突然吟哦一句也是文学。这样说吧,在一个灰暗的世界里,亲近文学的人,哪怕他衣衫褴褛,食不果腹,但他的眼睛里一定会有光。有光就有希望,有希望,就一定会有未来。
谭建兰——《用锄头耕耘文字》

谭建兰:我在读《白色救赎》的时候,书中的每一个故事的结局和走向我都猜了,但是没有一个猜中,你给我们展现了一个很普通,但却并不平凡的主人公,人生可以无愧、坦然。但你在前面的访谈中又说过,“没有想过《白色救赎》这本书可以完成,也没有奢望能够出版。”我想问的是你如何坚持写完这本书的?另外,文学对于你,究竟是什么?
陈泰湧:我和你一样,没有接受过专业的写作训练,而且胆子大,上手就是整长篇,中途才发现自己眼高手低,驾驭不了。但这个时候又停不下笔了,感觉是小说中的人物在握住我的笔,想书写他们自己的命运。后来就咬咬牙,写吧,写完了又是非常艰辛地修改,这里得感谢很多前辈和文坛好友,他们给我提出了非常多的意见,有些照单全收,有些一时无法去改,但这些意见让我对第二部小说的创作积累了经验,少走了很多弯路。当然,第二部长篇小说自我感觉也写得更好了,更轻松了。
文学对于我,我以前说过,是“救赎”,现在,我会再加上一条,是“希望”。一个是对过去,一个是对未来。
本期被访谈者简介:
陈泰湧,重庆市作协会员,重庆市新闻媒体作协秘书长。鲁迅文学院四川作家创作培训班学员,重庆文学院“讴歌计划·特约作家”、第五届创作员。现任上游新闻文化频道负责人。出版有长篇小说《白色救赎》《小乾坤》等,并开设有随笔专栏。小说作品入选2023年度重庆市文艺创作重点资助项目,散文作品入选重庆市作家协会2023年度定点深入生活项目。长篇小说《小乾坤》被列入重庆市2024年度重大主题文艺创作项目。


编辑:朱阳夏 责编:陈泰湧 审核:冯飞
【免责声明】上游新闻客户端未标有“来源:上游新闻”或“上游新闻LOGO、水印的文字、图片、音频、视频”等稿件均为转载稿。如转载稿涉及版权等问题,请 联系上游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