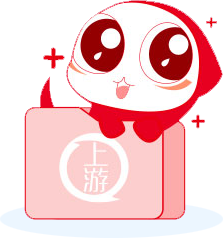

中国第一位女大使出生在重庆 曾被称为“啤酒大使”
今年,生于重庆巴县木洞镇的中国第一位女大使丁雪松(1918—2011)诞辰100周年。我们采访了其女儿郑小提并根据相关回忆史料,打望这位重庆女儿波澜壮阔的传奇生涯。雪松出身寒门,在重庆苦读、考进银行当小职员,抗日救亡时期,给报纸写火力凶猛的时评,1937年入党,被派往延安读抗大,任女生队队长,和朝鲜人——一代名歌《延安颂》以及后来中朝两国军歌的作者郑律成结为夫妇,1945年随夫赴朝任朝鲜劳动党中央侨务委员会秘书长。1950年经周恩来批准,经金日成同意,夫妇回国;1979年任中国驻荷兰王国特命全权大使,是中国第一位女大使。
木洞
跟父母的名字相比,郑小提的名字有点非传统。她说:“我出生时,我爸正在太行山区执行任务。我妈没有奶水养活我,就卖掉了父亲千辛万苦背到延安来的那把小提琴,买了一只羊,用羊奶喂我,所以就给我起名小提。”
1943年生于延安的郑小提是真资格的延河女儿。跟同代人都有三五个兄弟姐妹不同,她是父母的独生女,两岁时还随他们一起到朝鲜,5岁在平壤师从苏联专家学习钢琴。她1956年考上中音附中学钢琴,毕业后考上中音作曲系学作曲;1970年任总政歌舞团创作室创作员,1987年转业到中国旅游出版社音像部任音乐编辑,推出了崔健第一盒个人专辑《新长征路上的摇滚》。现在,郑小提以一个巴罗克室内合唱团团长的身份,活跃在首都音乐舞台上,还多次组织郑律成作品音乐会,也是韩国每年一届的“光州郑律成国际音乐节”组委会成员。
采访中,郑小提两次提到妈妈的老家——木洞镇。她说:“当年我妈妈就生在木洞一间临江老屋里,离重庆有90多里远,出生时取名丁孝芝,上学时改名丁正兰。她一出世,我外公丁开科已经患疗疮去世了。外公是个小商人,家里没什么积蓄,只留下年老体弱的祖母和妻儿老小五口之家,祖母成天捧着一个装着木炭的竹篓小瓦罐,驱除江边的潮气和寒冷。每天拂晓时分,都能听见江边传来纤夫们拉船喊川江号子的声音,我妈妈就是在雾蒙蒙的江边阴暗小屋里,伴随着川江号子度过童年的。”
全家靠丁雪松的母亲摆一个杂货摊和给人做点针线活来维持家用。“我妈妈从小就背上背篓带上皂角,跑到江边去帮母亲洗衣服。轮船开过来,浪花涌来,她抱起衣服就跑;浪子过了,又回去跪在石头上,一件一件搓洗。外婆看见她去洗衣服,就说:‘幺儿哟,莫再下水了,等幺婶忙完再去洗吧。’我外婆在她那一辈人中排行最末,按老家那边的称呼,我妈妈就叫她幺婶,而不是喊妈妈;我外婆喊我妈妈幺儿,这也是重庆那边的习惯,不管女儿、儿子,都是宝贝疙瘩,统称幺儿。”
河边儿女最愉快的游戏就是跑到江边去爬“梁山寨”。郑小提介绍,“那是一块横卧河滩的大石头,从一边爬上去,再从另一边光滑的斜坡上滑下,就像幼儿园的滑梯。在大石头上看着江边船来船往,大一点的船,我妈妈她们称呼其为洋船,心头老是在想:它们从哪里来?又到哪里去?想坐上洋船到外面去看看。想不到多年以后,妈妈真的实现了她小时候的念想,漂洋过海,当大使去了。”

1936年,丁雪松18岁时在重庆。
求学
丁雪松初中读的是自费的重庆文德女中。郑小提说:“我妈妈第一学期成绩很好,但因贫困遭到奚落和白眼。文德女中的学费和伙食费都很贵,同学都是有钱人家的小姐;女庶务也相当势利,见了富家女笑脸相迎,遇到穷学生,冷眼相看。由于妈妈的姐姐患结核去世,可能受到传染,我妈妈脖子上长了两个肿结,民间叫做瘰疠,医学上叫淋巴结核。因为营养不良,又怄了闷气,她脖子上的肿结越长越大,胀痛难忍。文德女中嫌贫爱富的风气,使她产生了强烈的逆反心理。放寒假了,我妈妈从朝天门码头坐船顺流而下回到家里,就发誓再也不上自费学校了。在家里待了一阵,打听到重庆有个免交伙食费的女子职校,她就在洪水期间,又坐小木船到朝天门上岸,去考了个名列前茅。”
女子职校虽然还是清苦,但她心情十分舒畅。“因为同学大多是穷苦人家的女孩,再也不见富家小姐和庶务的势利眼。她脖子上两处肿结,被我外婆逼着找江湖郎中开了刀以后,一直没有愈合,需要定期换药,所以只有穿着没有领子的上衣,一直穿了两年。稍一用力,伤口就绷得很痛。所以上体育课,同学打球、跑步,我妈妈只能眼巴巴地待在操场边上看。在两年时间里,她几乎没离开过校门,从不到热闹场所去耍。”
银行
女子职校分农、工、商三科,学期三年,丁雪松读的是商科。郑小提说:“1934年夏天,妈妈读到二年级,听同学们说重庆平民银行招收练习生,她在班上成绩相当好,经不住同学们劝,她去一考就中,才16岁。当时职校的学生能考进银行,大家都津津乐道;家里也高兴得不得了,外婆还特地派舅舅到重庆来看我妈。”
1934年秋天,丁雪松进了重庆最繁华的都邮街平民银行上班。“我妈觉得以前的名字太女儿气,就改成了雪松。银行的待遇比较好,见习生每月薪俸18元,年终还有奖金和分红,伙食也大大好于女职校。一旦营养加强,精神舒畅,我妈妈的身体很快好转,伤口逐渐愈合,一年后彻底复原。她当时能打网球、打乒乓,到郊外骑马,还跟年轻同事们学了几段京剧和川剧。”
丁雪松和金融界一帮热血青年都很关心时政,组织了球队、剧团和歌咏队,传看进步书刊,宣传抗日救亡。她还给本地重庆商会主办的报纸《商务日报》和《新蜀报》投稿。据丁雪松回忆录记载:1936年6月9日,华北危急,她在《商务日报·公共园地》副刊,用笔名雪萍发表了《在民族解放前什么美梦都会成为泡影》:“非洲小国阿比西尼亚(即现在的埃塞俄比亚)尚能抵抗意大利法西斯七个月之久,我们作为泱泱大国,竟将被一个区区的日本所征服,多么可耻!为什么老是不抵抗?如果一开始即抵抗日寇,何至于今日?”她对一些人的麻木不仁甚至醉生梦死的生活感到愤慨:“在民族未获得解放前,个人过安逸日子的想法只能成为幻想。”文章引起了很大的反响,还有读者来信表示从睡梦中惊醒,要用肩头担负起救亡的工作。”
当时,穿一身阴丹士林布短袖旗袍的丁雪松给同代热血青年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一位战友说:“在重庆这么闭塞的地方,一个女孩子能找到银行这样的职业,竟然还积极地在报纸上对职业青年的前途进行讨论,这有多么不容易。”她的言论和表现,也进入了白象街88号那边《新蜀报》主笔、地下党员——江津人漆鲁鱼的视线里。
入党
漆鲁鱼本是江津世家子弟,曾留日学医,1929年回国参加共产党,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被捕,出狱后被党派往江苏苏区任保健局局长。红军长征后,他留下来照顾受伤的陈毅,在战斗中被冲散,和组织失去联系,靠乞讨逃回江津老家,后来通过投稿成为《新蜀报》主笔。
丁雪松女儿郑小提说:“我妈妈曾经回忆,漆鲁鱼还常在白象街一个空店铺的楼上,对他们讲解党的基本知识;有一次还办过一个只有我妈妈和另一个同志参加的读书班,讲苏维埃运动史,时间是凌晨三点;有时晚饭后,他叫上我妈妈,到小什字马路上,装作逛街的样子,边走边对她进行党的基本知识的教育;有时在郊外无人处或地下室举行秘密集会,漆鲁鱼会压低声音教他们唱悲壮的《国际歌》,还唱其他革命歌曲。一听到这些歌,我妈妈他们就渴望到红军中去,到延安去。漆鲁鱼认为我妈妈忠诚可靠,十分信任她,就交一些秘密任务让她执行。1937年夏秋之交,一位老红军秘密路过重庆,我妈妈和另外一个同伴去文华街为他送车票和衣物,圆满地完成了任务。”
1937年10月,漆鲁鱼找到了党,恢复了关系和党籍,担任重庆市工委书记。郑小提说:“他找到了我妈妈,非常高兴地说重庆党组织恢复了,四川省工委同意以他为首组成中共重庆市工委,他还把上级批复的密信用碘酒显现出来给我妈妈看。他对我妈妈说:一年多来,你接受了考验,表现很突出,很优秀,现在组织上决定第一个发展你入党。我妈妈就在一个同志家的货栈楼上填写了入党申请书,又在另一个同志家里举行了入党宣誓仪式。我妈妈入党之日,也是她马上就要离开重庆之时:组织上决定让她和地下交通员温厚华去延安学习。”
温厚华原是巴县中学学生,当时在华通贸易公司当见习生,1949年后任新疆大学党委书记。他曾回忆:“我还记得雪松来找我的情形,她从打铜街来到道门口,满脸兴奋找到我,悄悄地问:漆夫子让我问你,有去延安的机会,你去不去?‘延安?’我欣喜若狂,向往已久了嘛!求之不得的机会,咋个不去?那时我和丁雪松很红,在救国会组织的活动中,我们经常抛头露面,走在前面,已经引起国民党的注意。”
去延安
从重庆到延安,行走路线是先到成都转干部关系,再从西安到延安。郑小提说:“转关系的信是用泔水写在一块白绸手帕上的,我妈妈就一针一线缝到丝棉旗袍的夹边里。漆鲁鱼告诉她到延安之后,要交给罗迈(即李维汉)。早在江西苏区时,漆鲁鱼和罗迈就很熟了。回到银行,我妈妈装着要回家探亲,请了假;对家中却是不辞而别,到延安后才写信通知家中已平安到达。一别就是十几年,离家时还不满20岁。直到1951年春,我妈妈作为新华社记者参加第一届赴朝慰问团回国后到各地宣讲,当再次见到她时,我妈妈已经是三十几岁的中年人了;她又见到了可敬的老领导漆鲁鱼,他当时任西南局宣传部出版局副局长,不久又调到北京任卫生部部长助理,后来调回四川任成都市副市长。”
1937年12月一个隆冬的夜晚,丁雪松和温厚华在两路口车场会合,登上去成都的长途敞篷汽车。“他们在成都转党的关系转了半个月后,找到车翻过秦岭山脉,终于到了西安,找到位于七贤庄一号的八路军办事处,见到了林伯渠,接上关系,再等到延安去的大卡车。一车装了二三十个青年人,他们互不认识,但都遵守地下工作的规矩,彼此也不交谈,所以车上气氛相当沉闷。但车过了洛川,翻过一道道山梁后,司机下来打招呼说:同志们,边区到了。这时大家才爆发了,唱啊、喊啊,到延安了!”

丁雪松
女生队
1938年1月要过春节的时候,丁雪松找到延安招待所报到。郑小提说:“我妈妈小心翼翼地把漆鲁鱼写给她的介绍信,从丝棉旗袍的夹缝中拆出来,转给了罗迈(李维汉),他当时是中央干部教育部副部长。妈妈被通知进中国抗日军政大学学习,给发了军装。她脱下呢子大衣、丝棉旗袍,穿上灰色棉军装,打上绑腿,系上皮带,转眼间就成了一名她一直向往的八路军女兵。”
丁雪松从重庆穿过去的丝棉旗袍,在延安就再也穿不出来了。“学校只发两季衣裳,夏天一身单军装,冬天一身棉军服,当中没有换季的衣服,手巧的学员就把棉花取出来,变成夹衣。谁如果带来多余的衣服,会无私地送给缺衣的同学。一旦得知某位学员要奉命到大后方工作,来自大城市的女学员会立刻捧出来时穿的旗袍、大衣,供她挑选。我妈妈的呢子大衣、丝棉旗袍,可能最后也就这样派上用场了。女生的生活更苦,我妈妈说,延河就成了她们的盥洗室,冬天敲开冰窟窿洗,夏天跳进河里冲。夏天的时候,几个女生相约到河边,先洗好下衣,晾到河滩上,人躲进河中泡着,等下衣干透,穿好再洗上衣。没有肥皂,就用石块在河边捶打衣服,或用草木灰过滤的碱水来洗。”郑小提说。
抗日军政大学创办于1936年6月1日,1937年第二期更名为抗大。前三期主要培训对象是红军中的高中级干部,每期人数都在1000人左右。从第三期开始,人数逐渐增多,平津革命青年大量涌入。郑小提介绍,“我妈妈赶上抗大第三期的末尾,这一期共有三个大队。第一、第二大队全是红军干部,第三大队是知识青年。当时,女知识青年比较少,就和女红军干部混合编成一个女生队,附属于第二大队。妈妈在抗大先后经历了第三期到第五期,为时一年半,直到抗大总校1939年夏天迁往前方,她又转到女子大学学习。大批知识青年涌入延安,抗大急需干部,从1938年4月第四期开始到1939年第五期,妈妈先后调任四大队女生队队长、五大队女生队队长、女生大队一队队长、五大队女生一队队长。”
同代人郭霁云在《梅洁枫丹》一文中曾回忆这位著名的“女生队长”:“在丁雪松带领下,女兵大队精神抖擞地进行着操练,丁雪松嗓音洪亮,口令干净利落。全体同志步伐整齐,进退有序,毛主席和中央首长看了我们的操练,都称赞地说,‘娘子军,真了不起啊!’丁雪松因此获得了‘女大侠’的绰号。”
八年
在延安,首长和普通学员穿着一模一样,男女没有明显的区别,一律穿着粗布军装。郑小提说,“抗大名为大学,实际上并没有像样的礼堂、教室,人人都住在窑洞里,好像回到了穴居时代,所以我妈妈他们听见早几期抗大同学开玩笑,彼此之间不称‘同学’,而称‘同洞’。有一次毛主席讲课对他们说:你们过着石器时代的生活,学习当代最先进的科学——马克思列宁主义。”
抗大理论课的教师阵容很豪华,著名的学者艾思奇、何恩敬、任白戈、徐懋庸、张庆孚都是教员。其中任白戈在上世纪60年代还担任过重庆市委书记。郑小提介绍,“抗大的大报告更为有名,真是近水楼台先得月,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彭德怀、贺龙、罗荣桓、彭真、博古等中央领导同志,都来抗大给我妈妈他们作过大报告。在露天会场,学员们把背包一放,席地而坐。”
2000年,丁雪松在回忆录中回首延安岁月时说:“在延安,我度过了难忘、极有意义的八年,在抗大、女大,经党的关怀、培养,我这个稚嫩的四川女孩增长了组织才干,成长为一个有独立工作能力的干部;经过军事生活和劳动的磨练,我的体格也健壮起来。在延安,我寻到了生死不渝的爱情,与郑律成结为终身伴侣。延安那八年是我一生中的一个重要历程,承先启后,为我未来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丁雪松郑律成和女儿郑小提
大使
丁雪松1938年穿着丝棉旗袍从重庆出发,到延安抗大脱下旗袍穿上军装后,直到1979年,才重披旗袍。丁雪松女儿郑小提说:“1979年4月11日,我妈妈派驻荷兰任大使,在大使馆举行上任招待会那天,她穿着一袭银灰色锦缎旗袍。西方敏感的新闻记者马上就注意到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外交人员服饰上的变化,在报道中特别注明一笔:老派的青蓝二色的毛式服装,被精细的中国丝绸代替了。”

△丁雪松在海边。
1982年5月,丁雪松换任丹麦大使,乘北欧航空公司客机飞赴丹麦首都哥本哈根。“玛格丽特二世在宫中举行隆重的宴会招待各国使节及配偶。各国男女使节携着他们盛装的夫人或大礼服的丈夫赴宴,我妈那天也是一身旗袍,是一袭银灰色织锦旗袍,上面用金丝蓝线织成龙凤图案,还配着白色高跟鞋,挎着缀有白珠的小提包。宴会结束的时候,侍从长在宫门送客的时候见到我妈就说:中国的服饰,雍容大方,今晚大使阁下的服装最为华贵。”
丁雪松是怎样出任大使的呢?“1978年夏天,她正要去青岛度假,她的上级、对外友协会长王炳南约她谈话。他对我妈说:你的工作将有变动,组织上可能派你出国当大使,先和你打个招呼,希望你思想上有个准备,认真考虑考虑。消息来得很突然,我妈妈没有思想准备,一时没向他表态。她有点为难,跟很多科班出生的职业外交官比起来,没有受过专业训练,外语也不行。当时我爸刚刚去世不久,1949年上级任命她为新华社驻朝鲜特派员,让她组建新华社平壤分社并任社长,1964年上级任命她为国务院外事办公室秘书长,最初她都有顾虑,我爸就给她打气,说叫你干你就干嘛!你是很能干的,准能干好。一想到我爸原来对她的这些鼓励,我妈妈心里又有底了,1979年2月5日欣然飞往海牙赴任。”
2月23日,丁雪松在海牙附近始建于1674年的苏斯代克王宫递交了国书。“那天,我妈妈在摩托车队的前后护卫下,乘着一辆古典式皇家轿车驶进王宫大门。下车后由一位身着军装的指挥官陪同,检阅了皇家仪杖队。随后,在宫廷典礼官的引导下拾级而上,步入接见大厅,荷兰女王朱丽安娜已经等在那里,我妈妈郑重地递上了国书,国书装在一只特大信封里,用盖着钢印的白色梅花边宣纸片封口。”
致歉
丁雪松在荷兰大使任上,促成了荷兰首相范阿赫特访华,这是近代史上荷兰在任首相第一次访问中国,访问很成功。还签署了两国经济技术合作协定和文化协定。中荷双方对此都表示相当满意。
但国际风云,瞬息万变。丁雪松后来在回忆录中谈到:“送走了荷兰首相,我留在国内休假,没想到就在这期间,发生荷兰向中国台湾出售潜艇的事件,使中荷关系出现变故,导致两国关系一度从大使级降为代办级。”
郑小提说:“我妈妈希望笼罩在中荷关系上的乌云尽快散去。1983年年底,荷兰内阁及其领导人公开声明:1981年批准出售两艘潜艇只是一次性交易,下不为例,还做出了不再向中国台湾出售武器的承诺,并重新确认1972年中荷建交所规定的各项原则。中荷两国的外交关系,从1984年2月1日起,由代办级再次恢复到大使级。1985年,荷兰前首相范阿赫特,就当年出售潜艇的错误决策,多次主动向我新任驻荷大使表示歉意。”
啤酒
丹麦首都哥本哈根东北部的长堤海岸,有一尊以安徒生童话《海的女儿》美人鱼为原型的青铜雕塑。1982年5月,丁雪松被任命为驻丹麦大使,飞赴哥本哈根,发现了这尊美人鱼的一个“秘密”。
郑小提说:“这事还得从北京当时的啤酒说起。原来当时国内啤酒产能不行,而且只有鲜啤,不便保存。街头巷尾,经常可以看到北京人抱着热水瓶、端着锅盆,顶着烈日在饭馆门前排长龙买鲜啤的场面。我妈就想,丹麦盛产啤酒,大家喝酒就像喝开水,我何不从中穿针引线,引进过来?她说干就干,终于促成中国和丹麦之间的啤酒合作项目,中国建成第一座年产10万吨的现代化啤酒厂——华都啤酒厂,就是今天我们熟悉的燕京啤酒的前身。北京市啤酒奇缺的问题终于解决,为此,丹麦啤酒厂老总诙谐地称我妈妈为’啤酒大使’”。
为引进丹麦啤酒的先进技术,丁雪松几度进出嘉士伯啤酒公司。“我妈妈才得知这座雕像的创意原来出自嘉士伯啤酒公司创始人卡尔·雅可布森。有一天,他在皇家剧院观看根据《海的女儿》改编的芭蕾舞,突发奇想:表达爱情和幸福的主题《海的女儿》,转换为过油画、舞蹈、音乐,唯独缺少雕像。于是他请著名雕塑家艾立克森,塑成美人鱼雕像,原件存放在嘉士伯啤酒公司,按原件放大一倍的复制品,赠给哥本哈根市,1913年正式安放在长堤的海边,成了丹麦的象征,全世界一个著名景点。”
在安徒生的童话中,海的女儿最后化为浪花和泡沫。重庆女儿丁雪松呢?2011年07月13日《人民日报》发消息:“原中国驻丹麦(兼冰岛)大使丁雪松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11年5月29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3岁。丁雪松是重庆巴南人……”
文、图片翻拍/上游新闻·重庆晨报记者 马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