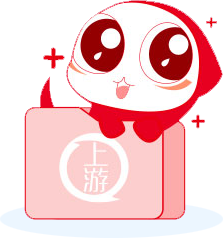

大历史|嚼槟榔,曾经是六朝名士风流的表现
槟榔在今天有点不登大雅之堂,而且我们已经知道嚼槟榔对健康有很大危害,但是在六朝的名士子弟之中却一度非常流行,刘穆之、萧嶷、任昉、陈庆之、庾信等名人都是嚼槟榔的行家里手。
六朝如梦嚼槟榔
晋室南渡后,汉人的政治中心迁移到建康,离岭南已经比较近了。建康的贵族士人不但熟悉了岭南的嚼食槟榔习俗,而且还开始模仿起这种异域习俗来。
到了南朝四代(宋、齐、梁、陈)时,江南的士族开始普遍嚼食槟榔,各种文学作品中不乏对槟榔的记载,可见当时嚼食槟榔已经不被认为是一种异域的、罕见的习俗,而是司空见惯的贵族日常。
当然,槟榔的种植不太可能越过南岭,居住在江东地区的士族所吃的很可能是干燥保存的槟榔。杨孚曾记载过保存槟榔的方法,当时也许已有类似于今天湘潭的干槟榔,但史籍中并没有翔实的记载。
经历长途运输的异域物产在古代通常都是非常昂贵的,因此南朝能够嚼食槟榔的人,除了岭南槟榔产区的人以外,其他地方的应该都是贵族或者富商。
从北朝的文献来看,北方贵族已经把南方贵族嚼食槟榔当作一种“吴俗”,并且有少数人开始效仿南朝人的这种“风雅”。当然,北方的槟榔更加稀少而珍贵。
佛教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槟榔在中国的流行。槟榔在印度的佛教中就是重要的供养物,伴随佛教在中国南北朝时期的大发展,槟榔也被士庶各阶层普遍认知。

印度槟榔是佛教的供养物
当时中国南北的信众都把槟榔当作一种重要的礼佛斋僧供养物,从而使槟榔成了跨越南北界限的重要贸易品。自南北朝时期起,槟榔不再被中原人视为一个需要介绍的异域植物,基本上从《异物志》这类书中退场。
《南史》中明确记载了槟榔在南朝士族中的流行情况:
穆之少时,家贫,诞节嗜酒食,不修拘检。好往妻兄家乞食,多见辱,不以为耻。其妻江嗣女,甚明识,每禁不令往。江氏后有庆会,属令勿来,穆之犹往。食毕,求槟榔,江氏兄弟戏之曰:“槟榔消食,君乃常饥,何忽须此?”妻复截发市肴馔,为其兄弟以饷穆之,自此不对穆之梳沐。及穆之为丹阳尹,将召妻兄弟,妻泣而稽颡以致谢。穆之曰:“本不匿怨,无所致忧!”及至醉,穆之乃令厨人以金盘贮槟榔一斛以进之。
刘穆之是南迁的北方士族,籍贯为东莞郡莒县(今山东莒县),是汉高祖刘邦的庶长子刘肥的后代。他世居京口(今江苏镇江),京口是北方士族南迁后聚集居住的地方,即著名的“北府兵”的根据地。
刘穆之与南朝刘宋开国皇帝刘裕都出身京口,且都早年贫微,两人关系密切,但并不是亲戚。(宋武帝刘裕是汉高祖刘邦之弟楚元王刘交的二十二世孙,按照中国传统文化,“五服”之内才算亲戚,刘穆之与刘裕两人早已出了“五服”,不是亲戚了。)
刘穆之屡次在刘裕出征时留守建康,总理朝廷内外事务,官至尚书左仆射(实权宰相)。刘穆之传虽见于《南史》《宋书》,但刘穆之在刘裕篡位前三年即已去世,并未做过一天刘宋的官,但他确实为刘裕取得大权立过头等的功劳。
这里说的是刘穆之年少时家贫,逢生日节庆时喜欢吃一点好东西,性格不拘小节,喜欢去妻舅家讨吃食,常遭到侮辱,他却不以为耻。刘穆之的妻子江氏很有见识,总是不让他去乞食,后来江家办聚会,妻子嘱咐刘穆之别去,但他还是去了。刘穆之吃完饭,还要槟榔吃,江氏兄弟戏谑他说:“槟榔是消食的,你经常饿肚子,要这东西何用?”妻子江氏把头发剪去卖了买菜肴,替她的兄弟请刘穆之吃饭,从此以后不对刘穆之梳洗打扮。
后来刘穆之做了丹阳尹,准备叫妻舅来(会餐),妻子哭着下跪(“稽颡”,即五体投地),想要辞谢(希望刘穆之对江氏兄弟宽宏)。刘穆之说:“本来就不记恨,何必烦恼!”到酒酣时,刘穆之让厨子用金盘捧出一斛槟榔供他们(江氏兄弟)享用。
刘穆之吃槟榔想必是成瘾的,饭都吃不饱,还要吃槟榔,可见槟榔在东晋末年已经是士族常用的嗜好品。著名的典故“一斛槟榔”或“金盘槟榔”的出处就在这里,常用来比喻早先贫微,后来发迹,不计前怨;或喻因贫困而遭戏弄。
斛是量米的容器,东晋时的一斛差不多相当于现在的二十升,现代大桶桶装水的容量大约就是二十升。这么大一盘槟榔放在江氏兄弟面前,能不让人惭愧吗?刘穆之的“不匿怨”大抵如此。
唐诗中用到“一斛槟榔”典故的有李白的《玉真公主别馆苦雨赠卫尉张卿二首》—“何时黄金盘,一斛荐槟榔”62;卢纶的《酬赵少尹戏示诸侄元阳等因以见赠》—“且请同观舞鸲鹆,何须竟哂食槟榔”。
《南史》中还有一则关于槟榔与孝道的故事:
(任)昉父遥,本性重槟榔,以为常饵,临终常求之,剖百许口,不得好者。昉亦所嗜好,深以为恨,遂终身不尝槟榔。
这里说的是关于孝的事情。任昉一生仕宋、齐、梁三代,以文章名重天下。他出身乐安任氏,母亲是闻喜裴氏,都是当时的高门大姓。
任昉父亲任遥喜欢吃槟榔,平时常吃。任遥临终前要吃槟榔,但是打开了百余个槟榔都找不到好的。任昉虽然也嗜好槟榔,但因为此事怀憾,终身再也不吃槟榔。
这里看得出南朝的士人不仅常吃槟榔,还要吃好槟榔。但是当年保存和运输槟榔并不容易,从岭南到江南的路上,也许有一多半的槟榔都要坏掉。任遥的运气更坏,打开了百多个槟榔都没有一个好的。
刘穆之和任昉都是北方南迁士族,两人不曾到岭南任官,因此吃槟榔的习惯肯定是在建康附近养成的,南朝士族普遍流行嚼槟榔应无疑义。
佛教推动槟榔大兴
南朝齐、梁时,关于槟榔的记载就更多了,南朝佛教的兴盛也助推了槟榔的流行。
例如“读书万卷,犹有今日”的焚书皇帝梁元帝萧绎,曾主编《金楼子》,其中记载“有寄槟榔与家人者,题为‘合’子,盖人一口也”。后世《三国演义》中写曹操题“一合酥”,杨修逞机灵,让大家一人一口分食,可能是受这则故事的启发。
槟榔要寄给家人,还要一人一口地分食,可见槟榔在南朝也算是珍品,价值颇高。
南齐萧氏宗室也有吃槟榔的习惯,在《齐书》中有体现:
嶷临终,召子子廉、子恪曰:“……三日施灵,唯香火、盘水、干饭、酒脯、槟榔而已。朔望菜食一盘,加以甘果,此外悉省。葬后除灵,可施吾常所乘舆扇伞。朔望时节,席地香火、盘水、酒脯、干饭、槟榔便足……棺器及墓中,勿用余物为后患也……后堂楼可安佛,供养外国二僧,余皆如旧。”
南齐宗室豫章王萧嶷要求在他死后以槟榔供奉,这是槟榔首次出现在中国人祭品中的记载。它的出现与萧齐宗室信奉佛教有关系。
一般来说,古代祭祀必须有祭牲,对亲王的祭祀更要用到少牢(羊和猪),信奉佛教的萧嶷在此特别嘱咐不要用祭牲,而用酒脯、槟榔代替。脯是肉干,在佛教概念中属于“三净肉”(不见杀、不闻杀、不疑为我而杀),槟榔则是佛教供养中常备的物品。
这段记载一来说明萧嶷生前很可能有吃槟榔的习惯,二来说明他企图用佛教祭祀来取代传统的华夏祭祀仪轨。
萧嶷在遗嘱中还提到了两件事情:一是薄葬,不要在棺椁中放置贵重的陪葬品,明面上说是为了避免被盗墓(后患),其实也是佛教的要求;二是要求家人继续供养外国二僧如故,萧嶷佛教信徒的身份显露无遗。

佛教要求佛寺边种“五树六花”槟榔树即其一
齐、梁两代帝室很喜欢赐槟榔给臣属,这是此前没有过的事情,可以证明萧氏皇室也喜欢吃槟榔。
现存多篇答谢赐槟榔的启文,有王僧孺的《谢赐干陁利所献槟榔启》曰:“窃以文轨一覃,充仞斯及,入侍请朔,航海梯山,献琛奉贡,充庖盈府,故其取题左赋,多述瑜书,萍实非甘,荔葩惭美。”庾肩吾的《谢赉槟榔启》曰:“形均绿竹,讵扫山坛,色譬青桐,不生空井,事逾紫柰,用兼芳菊,方为口实,永以蠲疴。”《谢东宫赉槟榔启》曰:“无劳朱实,兼荔支之五滋,能发红颜,类芙蓉之十酒,登玉案而上陈,出珠盘而下逮,泽深温柰,恩均含枣。”
齐、梁皇室赐槟榔,可见槟榔之物的确上得台面。不过皇室赐的槟榔并非常品,而是上佳的异域珍品,沈约得到的槟榔是交州产,王僧孺得到的槟榔则是干陁利产。
《梁书》中说:“干陁利国,在南海洲上。其俗与林邑、扶南略同,出班布、古贝、槟榔。槟榔特精好,为诸国之极。”干陁利国即Kandari,是苏门答腊岛的古名。
北朝对槟榔的爱与恨
南朝齐、梁吃槟榔的风气不但在南方盛行,还影响到了北朝。梁末陈初时的庾信有一首《忽见槟榔诗》:
绿房千子熟,紫穗百花开。
莫言行万里,曾经相识来。
庾信的家族是南朝非常显赫的高门—新野庾氏,其家“七世举秀才,五代有文集”,父亲是前面提到的曾得赐槟榔的庾肩吾。庾信40岁以前是南朝梁的重臣,40岁以后是西魏和北周的重臣,一生“穷南北之胜”。
这首《忽见槟榔诗》是在北朝时所作。“莫言行万里,曾经相识来。”庾信在北方偶然看到了南方流行的槟榔,睹物思情,满怀思乡之意。可见槟榔在北方是很罕见的物品,却是来自南方的庾信的旧相识。
这也是南北朝时期首次在北方出现槟榔的记载。唐代李嘉祐曾作《送裴宣城上元所居》—“泪向槟榔尽,身随鸿雁归”71。这首诗用的就是“庾信见槟榔”的典故。
北朝关于槟榔的记载不止见于庾信的诗,北魏贾思勰的《齐民要术》也收录了槟榔条目,不过是在附录的卷十中,这一卷专记“非中国物产者,聊以存其名目,记其怪异耳。爰及山泽草木任食,非人力所种者,悉附于此”,槟榔、荔枝、椰子、杨梅都在此列,贾思勰也明确指出这些东西是中原种植不了的,《齐民要术》作为一部农书,存其名目也就足够了。
槟榔条目引用了《与韩康伯笺》《南方草木状》《异物志》《林邑国记》《南州八郡志》《广州记》六种文献,没有贾氏的评述。也许贾思勰从来没有见过槟榔,只是在各种文献中得知此物,因此这段记载不能证明槟榔就出现在了北魏的土地上。
北朝另一份重要的历史文献《洛阳伽蓝记》中也出现过槟榔,是用来描述北朝人眼中的吴人形象的:
吴人之鬼,住居建康,小作冠帽,短制衣裳。自呼阿侬,语则阿傍。菰稗为饭,茗饮作浆。呷啜莼羹,唼嗍蟹黄。手把豆蔻,口嚼槟榔。乍至中土,思忆本乡。急手速去,还尔丹阳。
这段话是杨元慎(杨元慎,北魏术士,居于洛阳。杨衒之《洛阳伽蓝记》载其“善于解梦”,“元慎解梦,义出万途,随意会情,皆有神验”)对陈庆之说的。
时值六镇起义,北魏大乱,梁大通二年(公元528年),武帝萧衍遣陈庆之北伐,命其护送北魏宗室北海王元颢北归称帝。陈庆之率七千将士破三十二城,胜四十七战,所向无敌,攻克洛阳。
公元528年前后,当时陈庆之在洛阳生病,杨元慎去为他治病时说了这番话,意在劝陈庆之早日收兵回江南,让他“急手速去,还尔丹阳”。
杨元慎这里列举了六种吴人的习俗:
其一是以菰稗作饭吃,菰是茭白,菰稗就是茭白的籽实,也叫雕胡米,这种米在《礼记》中已有记载,种植菰稗不完全是吴俗,只是南方水乡种植得比较多。
其二是以喝茶代替喝酒浆,喝茶在唐代以后才从南方广泛传播到北方,确实是吴俗。
其三是吃莼羹。其四是吮吸蟹黄。莼羹和蟹黄这两道菜只有南方水乡之人才能吃到新鲜的,至今仍是三吴之地的佳肴。
其五是把玩豆蔻。其六是嚼食槟榔。豆蔻和槟榔这两种东西出自岭南,把玩豆蔻、嚼食槟榔也是当时吴人的日常。
杨元慎说这些话真实的意思是:吴人居住在卑湿之地,中原的高壤厚土不是给你们这些人住的,赶紧滚。这段话言语间极为无礼,是赤裸裸的地域歧视。、

陈庆之也嚼槟榔
其实地域歧视自古以来就史不绝书,举例而言,洛阳自汉魏以来,直至隋唐,一直是集中原经济文化荟萃之都会,《世说新语》中东吴陆机、蔡洪都在洛阳遭受过地域歧视。北方人对南方人的歧视直至北宋时仍然极为显著,譬如寇准对宋真宗所言的“南方下国,不宜冠多士”。
也多亏陈庆之是个儒将,颇有雅量,要是换个对象,杨元慎立刻就身首异处了。
唐代编纂的《三国典略》记录了西魏及北周、东魏及北齐、梁及陈的重要历史,三方历史的编年体史书也有关于槟榔的记录:
齐命通直散骑常侍辛德源聘于陈,陈遣主客蔡凝宴酬。因谈谑,手弄槟榔,乃曰:“顷闻北间有人为啖槟榔获罪,人间遂禁此物,定尔不德?”德源答曰:“此是天保初王尚书罪状辞耳,犹如李固被责,云胡粉饰貌,搔头弄姿。不闻汉世顿禁胡粉。”
这里说的是南陈的蔡凝接待北齐婚聘使者辛德源的事情。在宴席上,蔡凝一边手持槟榔玩弄,一边说:“听说北方有人因为吃槟榔获罪,民间禁槟榔,这是真的吗?”辛德源回答说:“这是天保(北齐文宣帝高洋年号,公元550—559年)初年王尚书的罪状上的说法而已,就好像东汉的李固获罪,罪状上说他用胡粉(产自西域的铅粉)饰貌,搔首弄姿,但没听说汉代禁胡粉。”
王尚书是仕官东魏北齐的王昕,字元景,王猛是其五世祖,北齐文宣帝高洋在天保初年裭夺其官职,天保十年再将王昕“斩于御前,投尸漳水”。高洋在斥责王昕的诏书中说他“伪赏宾郎之味,好咏轻薄之篇。自谓模拟伧楚,曲尽风制”。
王昕“雅好清言,词无浅俗”,是北朝名重一时的文人,在东魏时就已经做到正三品的荣衔金紫光禄大夫,他欣赏南朝文化,不但喜欢嚼槟榔,还喜欢咏南朝流行的新体诗(“轻薄之篇”),可谓全方位模拟南方的文化生活。
这桩事件透露出两个信息:
第一是北齐的高官中是有人吃槟榔的,不过,吃槟榔恐怕是比较次要的事情,关键在于吃槟榔代表了一种崇尚南朝奢靡浮华风气的倾向,也象征着来自南方的“文化污染”,所以才能作为王尚书的罪状;
第二是南朝中有北方禁止民间吃槟榔的传闻,这样的传闻恐怕不是空穴来风,想必有一定的根据。槟榔在北方是很昂贵的东西,又只在南方出产,北朝士族喜欢模仿南朝士族,南方嚼食槟榔的风气有蔓延到北方的趋势,如果吃槟榔的风气在北方流行起来,会导致财税流失到南朝,这对于北朝的军国大计是没有好处的,因此北朝的统治者不会希望槟榔传到北方。
在南北朝时期,北朝在大多数时间里都占据着军事上的优势,但在文化上却处于劣势。隋文帝统一南北朝以后,听到了来自建康的南朝音乐,便说:“此华夏正声也。昔因永嘉,流于江外,我受天明命,今复会同。”连统一了南北的皇帝也认定南朝的音乐是华夏正声,当时南北文化的地位可见一斑。
南朝梁元帝萧绎在江陵焚书时一次性毁灭了图书十四万卷,当时北周和北齐的官方藏书加在一起还不足两万卷,到了隋文帝的时候经过努力搜集,才使得官方藏书达到了三万卷。藏书数量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国家的文化实力,南朝在侯景之乱以前,文化上是领先于北朝的。
当时北朝的文化人对南朝的文学、艺术,乃至生活习惯都很向往,连南方士族嚼槟榔的习惯也要一并学习,于是才有了高洋斥责王昕的这条罪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