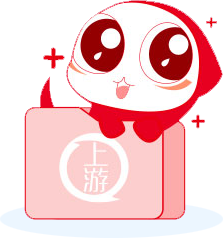

文史丨“山城棒棒军”竟然是因一部电视剧喊响全国,编剧为你讲述这部爆款背后的故事
“以后我们好好合作一把!”束导眯缝着眼睛望着我。
眯缝着眼睛是在使眼球聚光?导演都是习惯这样选角色看人?
我望着他的眼缝想,随口答应:要得嘛。
1993年寒冬腊月的一天,我与重庆电视台导演束一德在北京中央戏剧学院招待所偶遇。束导当时到北京,是为了完成新拍的电视剧《傻儿师长》后期事务。
在了解我有中央戏剧学院文学系研究生学历,在川剧团干过十余年,还有川剧原创获奖剧目的经历后,他对我说了这么一句话。
当时真是没有想到,这一句话会把我带入《山城棒棒军》。

《山城棒棒军》剧照
一
那时洪崖洞在搬迁,好多棒棒为省房租住在这里,我进屋之后无事一样,笑呵呵地先把烟满撒起,手上拿一支耳朵上还给他们“卡”一支,氛围整热和了,然后请“棒棒”们摆龙门阵。
大概一年后,束一德与制片主任陈文诗找到我,问我有没有创作打算。
我兴致勃勃地说坐长江索道看上新街而产生的灵感:一个大院,坡上是三层楼房,是住主人家的;坡下是平房,是住下人的。1949年后,坡上坡下颠覆式换位,两代人的恩怨情仇,会弄出一个好东西。
束一德听了就不歇气地摆脑壳:“你那个题材全国都有。我们重庆的‘棒棒’只有重庆才有,独一份!而且,只有现在而今眼目下才有!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你好生想一下!”
我听了一个激灵,但还是觉得茫然,就说,“等我想一下。”
陈文诗接口说:“你要快点想!一个轮周之内,你给我们一个答复。”
走出电视台,迎面走过来几个“棒棒”。看着他们,我突然脑筋急转弯:“棒棒”不都是农民吗?我出生在江津青泊乡,后来在白沙镇读小学读中学,三分之二的同学都是农民子弟。后来又下乡当知青等于就是当农民。再后来考进全称为“江津县农村川剧团”的剧团,长期到农村巡回演出,对农村对农民很熟悉而且有感觉。
于是,我立即回去对束一德和陈文诗说:“做《山城棒棒军》,我得行!”
束一德笑得粲然,说:“这就对了噻!”
我回应:“尽力而为。”
多年后,想起这段经历,我心头就暗自嘀咕:如果当时一根筋没有脑筋急转弯,硬是差点跟《山城棒棒军》失之交臂!
认真说起来,我最初学写剧本当编剧是被“逼上梁山”。1972年,我是凭一根笛子离开插队的农村考入剧团的,演样板戏搞音乐伴奏,吹竹笛、吹长笛都是吹主旋律,是乐队主力。后来,川剧全面恢复演传统戏。传统川剧笛子就靠边站了,仅是“下手琴师”偶尔兼行的无足轻重的乐器,这时候我在剧团就是干收门票、打幻灯字幕的杂务。
一直自视很高的我去打幻灯字幕心头是痛苦的,毕竟那是勤杂工干的事,而且还必须全神贯注,打哈欠都必须快点打,因为演员的唱词与字幕必须同步吻合,错了要挨观众斥骂。那时候幻灯机还比较原始,用大功率的灯泡做光源,演出结束时衣服都拧得出水。想到以后可能这样过一辈子,实在是心有不甘,有一天突发奇想,要让全剧团围着我转,只有当编剧写剧本!
但是,这打幻灯字幕的经历却使我因祸得福,为我以后的编剧写作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那几年演的都是川剧传统戏的经典,在反复全神贯注看戏的过程中,我注意到什么叫有戏,什么叫没得戏,我了解到观众喜欢看什么,不喜欢看什么,也学习感悟到一些川剧艺术的手法、手段和技巧。写《山城棒棒军》的时候,我大量借鉴川剧的一些手法和手段,甚至直接用到剧本创作当中,比如毛子跟王家英斗嘴吵架,梅老坎为平息冲突,替毛子向王家英“带话”的桥段,这个“带话”的桥段很有喜剧效果,就是借鉴川剧“牛掉尾”的手法。
尽管我对农民生活很熟悉,但对“棒棒”的生活还不了解。于是,抓紧时间老老实实地跟“棒棒”混热络了“补”生活。
当时,我在重庆市文化局创作室工作,住沧白路局机关内,离“棒棒”们杂居的洪崖洞很近。我不抽烟,每天晚上都买两包中档的“朝天门”烟揣在荷包里,去敲“棒棒”们的门。因为他们白天都出去找“业务”不得落屋,天黑了才回得来。
那时候洪崖洞处于拆迁前期,原住户大都搬迁,“棒棒”们住这里不交房租,都是几个同乡住在一起,好有个帮衬照应。这些房子厨房已不通天然气,煮饭炒菜烧煤油炉子,房内又没卫生间,几重气味综合,在屋里头吸口气都熏人。
但我进屋之后无事一样,笑呵呵地先把烟满撒起,手上拿一支耳朵上还给他们“卡”一支,氛围整热和了,然后,请“棒棒”们摆龙门阵。
“棒棒”们没有被采访的经历,你看我,我看你,老虎咬天——不晓得如何开口。我就问他们:“当‘棒棒’最高兴的事情是啥子?”这一下就使他们打开话匣子,抢话说了。
其中一个说他昨天在重百大楼,一个老大爷叫他背彩电回家,家在枇杷山,老大爷有点抠,说话还很冲,把运费砍到七块。他心头不安逸,也不讲价,背起就走。走拢枇杷山他就放下彩电,说,给你背拢了,七块钱。
老大爷说要背上楼,背到家里才给钱。
他说,你没说要上楼,七块钱是解放碑到枇杷山的价钱,上楼有上楼的价钱,一层楼两块。你家住七楼,总共要付二十一块。这七块钱的运费你不给的话我就把彩电背回去。老大爷无可奈何,只好要他搬上楼,最后一边给钱一边说:“你拿去吃药!”
这个“棒棒”接过钱就走,不是去药店而是直奔小面馆,欢欢喜喜地打牙祭,吃了一碗牛肉面。他有些得意地对我说:“平常时候都是吃一碗素面。”
我当时听了觉得很有戏,人物有性格有内心,还有画面。但落笔写的时候还是放弃了,觉得这样写出来有副作用,有违主题的展示,最后改为“梅老坎”给一家人修落水管,故意用砖头堵塞,然后“费力”地修好。而女主人的真诚、大方使他深受感动,接过工钱和女主人送他的衣物,走到僻静处,“梅老坎”打自己一耳光,算是对自己不良行为的否定。
接下来我又问他们当“棒棒”最不开心的事情是啥子。他们除了说半天都没找到一单“业务”不开心,说得最多的是孤身一人在城里头,时常想娃儿,实话实说,还要想娃儿他妈……我想,这的确是进城农民工带普遍性的问题,就叫他们说具体的,又给他们撒一支烟,耳朵上再“卡”一支。
叫他们说自己如何想娃儿他妈,都不好意思说。我就挑动他们互相“检举”。我这一招果然见效,没多久,其中一个就被其他人“检举”出来:端阳回家想跟媳妇亲近,结果藏在尼龙袜子里头的钱都遭媳妇清出来了,却没跟媳妇亲热成,三个娃儿像往常一样挤在妈妈床上睡起,不给老爸让地方。这个情节我基本上照单全收写上去了,只是给失望的“梅老坎”在最后加了一句台词:这跟不回来有啥子区别!
据说观众看这段戏时,有人笑得下颌骨脱臼!

当时的解放碑(剧照)
二
梅老坎和毛子人物关系借鉴了《堂吉诃德》,好人蛮牛牺牲是我的预谋。在党校招待所写了将近四个月才写完,手稿交重庆歌剧院打印室打印,打字员笑得打不下去。
1995年初春,我与束一德住进当时的四川省委第二党校(现重庆市委党校)招待所,开始进行《山城棒棒军》剧本创作。
我们把《山城棒棒军》定位为轻喜剧,喜剧效果主要是在人物性格与规定情境的错位中产生,而不是靠滑稽与“展言子儿”搞笑。首先是主题定位。改革开放初期,农民工开始进入城市打工,他们受到城市文化现代意识的冲击和影响,也对城里人的思想意识产生冲击和影响。恰好在几年前,我想给重庆话剧团写一个工业题材的话剧,曾经到重钢深入生活。有个特招进厂的知青,特长就是演节目、打篮球,奖状得了不少,但没学到技术,后来待岗了,靠卖盒饭起家,现在生意做得很大。于是,就设计了王达明(王窽窽音wǎng cuà cuà)及家人与王三爸这条线。写了王达明从下岗的失落,受到梅老坎等“棒棒”们吃苦耐劳精神的影响,开启新的人生。
人物设置上,出于特定的生活题材的考虑,既然要写一个“军”,宜用群像式的人物设置,以扇面展开生活真实,呈现出现实的脉动。当然,群像也有主次。如果说男一号是梅老坎,那么,男二号就是毛子。这两个人物的设置,是借鉴了《堂吉诃德》里堂吉诃德与侍从桑丘·潘沙的人物关系,毛子是作为梅老坎个性的反衬,如此更能产生喜剧效果。
由于是群像式的人物设置,情节的推进就不容易造成环环相扣起伏跌宕,带来的问题是二十集篇幅的故事节奏平缓,容易造成观众的审美疲劳。怎么解决这个问题?人物的生离死别最容易对观众造成情感冲击力,最好是拿一个观众认为最不该死去的人物作牺牲。梅老坎死不得,他死了后面的戏就没法戏了。跟梅老坎如影随形的毛子也死不得。只好让蛮牛去牺牲了。于是,在前面做足了好人蛮牛的铺垫,最后让蛮牛在救助老教授时见义勇为地牺牲,好多观众看到这里都泪眼婆娑,给电视台打电话,说蛮牛那么好一个人死了,接受不了……我是既感动又高兴,感动的是耿直的重庆观众对《山城棒棒军》的热爱与投入;高兴的是编剧预谋得逞,这部戏的情感高潮“推”上去了。
方言电视剧的语言是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如果只是简单地追求搞笑,重庆方言“言子儿”轻而易举就可以做到。我们在这个问题上很慎重,不在剧中“展言子儿”,除了少量适合在规定情境使用的方言歇后语,比如“你半斤花椒煮二两肉——麻嘎嘎(朒朒)”,“怀胎妇女过独木桥——挺(铤)而走险”,更多的是努力在人物个性语言上下功夫。比如梅老坎给主任医生搬家,搬运沙发时偶然拾得病人家属在手术前送的红包三千块钱,三千块钱在上个世纪90年代不是小钱,梅老坎不想交出去,第一次怀揣昧心钱走在街上,难免惴惴不安,碰巧迎面走来警察,更是胆战心惊禁不住有些发抖。警察关心询问:“棒棒,你怎么了?需不需要我们提供帮助?”梅老坎怎么回答我是反复推敲,最后写出这句台词:“你们走了……我,就好了!”
又比如梅老坎跟毛子介绍媳妇,说对方是寡妇,有娃儿,你跟她结婚,就可以捡现成,直接当爸爸。毛子说,“还是亲自当爸爸比直接当好些……”
在党校招待所奋战了将近四个月,《山城棒棒军》终于完稿。那时候都是手写,手稿交重庆歌剧院打印室打印,打字员笑得打不下去。我把这个情况给束一德讲了,束一德胸有成竹地说:“《山城棒棒军》,有了!”

《山城棒棒军》副导演、编剧王逸虹在该剧中扮演港商(右一)
三
我向导演束一德推荐庞祖云扮演梅老坎。梅老坎、毛子、蛮牛打扮成“棒棒”到大街上去体验生活,真正的“棒棒”对他们恶语相向,说他们抢生意。
一般情况下,编剧交稿就算完事了。为了熟悉电视剧拍摄制作流程,我提出要跟组。制片方同意我到剧组当副导演。剧组设在嘉陵江大桥北桥头不远的司法局招待所。建组后首要的事情就是选演员,这是副导演的职责之一。我记得不久前看过根据同名小说改编的方言电视剧《在其香居茶馆里》,有个角色是重庆川剧院的演员庞祖云扮演的,他有“小花脸”的喜剧功底,但很松弛,台词也没得戏曲腔调,就向束一德推荐他演梅老坎。束导没吱声。
后来,把庞祖云请到剧组,束导眯起眼睛盯了他一阵,又跟他聊了几句,就把梅老坎定了。
接着,又定了赵亮演毛子,王群英演蛮牛,仇小豹演巴倒烫,张新演王达明,罗德元演赵嘉陵,唐玉生演江疯子。赵亮是原成都军区战旗文工团的,他引荐了几个同事,又定了谢先丽演张淑慧,寻建建演王家英,陈丽娟演于芳……
最费周折的是胖妹的演员不好找,剧组都开拍戏了,还没定得下来。重庆城胖子女娃儿好找,能够演戏的胖子女娃儿难寻,最后,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有朋友说某旅行团有一个伶牙俐齿的胖妹导游,此人叫刘军,我们立即找来给束导看了,束导当场拍板:就她了!
导演束一德不是重庆人,是江浙一带的人。正因为不是重庆人,他对重庆文化特色的感觉远比司空见惯的重庆人更敏锐。之前在新疆石河子兵团文工团工作。到重庆电视台后,已经执导了《重庆崽儿》《傻儿师长》等脍炙人口的电视剧。
束一德受过严格的斯坦尼斯拉夫“体验派”戏剧理论体系的培训,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主张演员要沉浸在角色的情感之中,讲求演员与角色合二为一,进入“无我之境”,通过逼真的生活化的表演,再现生活。因此,束导要最早进组的庞祖云、赵亮、王群英等人打扮成“棒棒”,到大街上去体验生活找感觉。后来的结果证明,正是这“逼真的生活化的表演”,成为《山城棒棒军》得以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
这些伪装的“棒棒”上街之后竟然可以百分之百以假乱真,以至于真正的“棒棒”对他们恶语相向,说他们抢生意。
当时戏曲处于低谷,许多川剧团都“关停并转”了。庞祖云在观音桥碰见原江北区川剧团的一个女演员,她见他一身“棒棒”打扮,很是惊异,问道:“师哥?你这是啷个了?”
庞祖云就跟她“演戏”,带着哭腔说:“师妹嘞,师哥倒霉了,落难了,没得办法了哇,只有当‘棒棒’了……”女演员听了顿时泪如雨下。
庞祖云这才说实话:“我是逗起你耍的,我是要拍电视剧在找感觉,拍《山城棒棒军》嘞。”
女演员这才破涕为笑,对着他胸膛一阵乱拳,说:“你这个背时的庞祖云,你硬是一个小花脸!”

梅老坎和毛子(《山城棒棒军》视频截图)
四
我西装革履地扮演“港商”走进重庆宾馆,“毛子”给我搬行李。束导一声“开始”,我不晓得是怎么回事,立马周身僵硬,眼睛都不敢看镜头。后来看回放发现看不清我的脸。
1995年10月,《山城棒棒军》开机。为节省经费,许多群众角色,都由剧组人员客串,制片主任陈文诗以前是京剧演员,有表演经验,直接出演有名有姓的角色“陈凯”。管服装的赵刚演戏有瘾,在剧组客串过几个戏了,在《山城棒棒军》里客串孟小渝在歌乐山松林坡遇见的神经兮兮的路人甲。
看大家都在戏里露脸,我也想试一试。
有一天,陈文诗对我说:“你有扮相,也客串一把。”我连忙说:“要得!”
于是,新姑娘坐轿头一回拍电视,我西装革履地扮演“港商”,走进重庆宾馆,赵亮扮演的“毛子”给我搬行李。束导坐在监视器前面喊了一声“开始”,我不晓得是怎么回事,立马周身僵硬,眼睛都不敢看镜头。好不容易走完过场,把唯一的一句台词说出来:“我要住店,有房间吗?”
束导喊停!我以为要重来。束导又说:“过!换场景!”
我疑惑地看着束导,束导已经背转身去。
后来我看这段回放,镜头都是用的中景或远景,看不清我的脸。原来,有经验的摄像师为预防我这种怯场的“黄棒”群角临场出事,大都采取这种“不给脸”的方法。
我心有不甘,回房间关起门来做练习。然后对陈文诗说:“明天我再客串一把?”
陈文诗一笑,说:“你就算了,你有你要干的事。明天你要去火车站接演员……”
我清楚是明天上午拍这段戏,接演员的火车是下午到。
我跃跃欲试表演梦想,从此熄灭。
电视剧也是表演的艺术,演员根据人物的性格和规定情境的内心心理,赋予人物特定的动作表演展现出来。演员表演得好,特别是临场发挥得好,能够在剧本的基础上额外加戏。比如醉酒的梅老坎背醉酒的胖子上楼那场戏,剧本写的就只是梅老坎很费力地背胖子上楼,拍的时候,由于扮演胖子的演员比扮演梅老坎的庞祖云高许多,梅老坎一直是拖着胖子走,而且是费力不讨好。最后导演和演员商量改成梅老坎的脚盘在胖子腿上,梅老坎背胖子变成胖子背梅老坎,笑料暴增,效果倍增。
五
“今天打麻将只打齐八点钟,要看‘棒棒军’,看完了接着打。”《山城棒棒军》居然能够叫停麻将,这是我没有想到的。
我一直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等待《山城棒棒军》的播放,那是丑媳妇见公婆之前的内心焦虑。尽管我知道审片时,参与审看的领导和专家无一不拍手叫好。
1996年9月的一天,《山城棒棒军》正式播放。我不安地走出家门,沿着九尺坎、民族路、沧白路走了一圈,听见满街都是“棒棒,来哟……”,以及观众的笑声,心中石头才落下去了。后来,我到重庆肥皂厂招待所采风,在职工食堂吃晚饭时,听见一个退休职工给“麻友”们打招呼:“今天打麻将只打齐八点钟,要看‘棒棒军’,看完了接着打。”《山城棒棒军》居然能够叫停麻将,这是我没有想到的。还没想到《山城棒棒军》只是表现市井街巷普通人生活,没有展示高大上的英雄,后来也能够获得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或许正是接地气表现真实生动的普通人的生活,观众才觉得这部电视剧与他们的接触是零距离,更喜欢“棒棒”演员们。
有一次我与庞祖云上了一辆奥拓出租车。女司机看到庞祖云,顿时眼睛发亮,拿起对讲机就说:“报告大家一个好消息!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梅老坎现在坐在我车上!”
对讲机里立马嘈杂起来:“真的呀?是不是喔?”
女司机说:“不是‘蒸’(真)的,未必还是煮的?说完,她把对讲机递到庞祖云面前:我这些姊妹伙都喜欢你得很!你跟大家说两句!”
庞祖云呵呵一笑,说:“大家好!”
对讲机里传来一阵尖叫!
庞祖云把对讲机还给女司机:“你好生开车。”似乎觉得不应该让我受到冷落,庞祖云又说:“喔,给你介绍一下,他是编剧……”
女司机回头望我一眼,喔了一声。
车到较场口,庞祖云下车了,他刚要伸手掏钱,女司机就按住他的手不放,说:“我是绝不会收梅老坎车钱的!”
庞祖云下车后,又对女司机说:“请你把我们的大编剧送到沧白路文化局!”
女司机说:“没问题!梅老坎请放心!”
车到沧白路,我下车付钱,女司机笑眯眯地把钱收了。
我很淡然,坐车付钱,理所当然。何况,观众喜欢演员,还不是因为有这部剧吗?
《山城棒棒军》播出至今快27年了,重庆电视台经常重播,还有人要看。这使我感到欣慰。
登录豆瓣网,在这个年轻文艺青年的集散地,我看到了这么一条写于2022年11月17日的点评。
“这出上世纪的悲喜剧,对人性的刻画,众生的关怀。就像重庆和国家的变化一样,震撼人心。导演把镜头对准那个时候的众生,社会的底层。其中的人文关怀令人动容。剧中最后一幕,梅老坎喊着号子,和众人抬着重物爬梯坎。那‘重物’既是时代也是人生,是城市的发展,是生活的难题。他们负重前行爬坡上坎,爬出了社会的进步,进步中流淌着他们的血泪。他们是过去,也永远是现在。”
文/王逸虹 作者系二级教授、文化部优秀专家、原重庆作家协会副主席,代表作品电视剧《山城棒棒军》《邓小平在重庆》和话剧《朝天门》 本稿件版权归《重庆晨报》所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