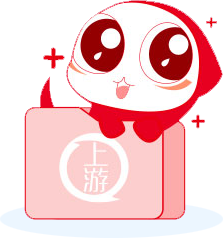

上游•互动丨“老码头杯”征文(4)丨大哥的喝酒史 - 文猛


大哥的喝酒史
文猛
多年前,我很不解大哥喜酒的理由,我很不解大哥总感叹“有朝一日时运转,天天喝酒当过年”。
大哥最痛苦的事情就是他没有好好喝过好好醉过。
著名的川鄂茶盐古道穿过我的家乡,古道旁边有古老的老码头酒坊,酒坊旁边是我们的家。闻着酒香长大,我们六个弟兄就大哥一人喝酒,显然这不是大哥宣扬喜酒的理由。
大哥比我大18岁,更远年代的大哥酒事我不清楚,我只知道上世纪80年代以前的乡村,刻骨铭心的记忆只有一个字:饿。醉是那个年代不敢奢想的最大幸福。于是,乡村酒事只能零零星星地呈现在乡村的红白喜事中。
大哥是我们家唯一的乡村红白喜事代言人,方圆百里中,只要有人家办喜事或丧事,大哥一定会去。不为贺喜或吊丧,就为奔赴一场酒事。
大哥自然要随礼。红布包袱装着半升玉米,家家一个样,回回一个样,家里没有更多拿得出手的礼品。早上,红布包袱挎在肩上,兴高采烈。傍晚,红布包袱捆在腰间,唱着他自己才懂的歌,仿佛一片落叶,在落日的余晖中向着家的方向飘荡……
忘了交代一个背景,大哥不断地出席一场一场乡村红白事,绝不是父母纵容大哥的酒嘴,大哥在乡村还有一个身份:支客师,就是负责张罗主家红白喜事那几天所有事务的支客师。
所有安排到位了,在乡村酒席进入尾声的时候,大哥这个支客师才可以上桌。酒碗在八个人面前端出一条粗白线条来,飘过大哥手中,白线条断了——酒没了。那些年代的主家都是一桌一瓶酒,不像今天能够敞开肚皮喝。等到后来,大家瞅准大哥往哪席走,那席准没人去。大哥也不客气,独自一桌菜一瓶酒,傍晚回家照样歌响步大脸更红霞……
我们为大哥的乡间酒态羞愧。
大哥的另一场酒事自然与老码头酒坊有关。说是酒坊,其实我们一直怀疑酒旗上那个“酒”字的笔画是否少些什么。填不饱肚子的年代,老码头酒坊酒锅里也没有太多的大米、高粱、糯米。红苕出来的时候,他们酿红苕酒。甘蔗出来的时候,他们酿甘蔗酒。地瓜出来的时候,他们酿地瓜酒。很有几年这些都没有多余的时候,听说山上的青杠藤可以酿酒,居然让那些藤藤叶叶煮进酒锅。这个时候,酒坊想到了大哥这个乡村酒仙,大哥的酒品在乡村是有说服力的,只是这个酒品与大哥的酒态没有多大的关系,就是品酒,就是端出那么一小杯让大哥说话。酒坊从来没有用碗给大哥端过酒,好在大哥只品酒,不品酒碗。
乡村不可能经常有红白喜事,酒坊不可能天天酿酒,乡村天空之下的大哥脸上无光,口中无歌,大哥就盼着家中来客,来了客人总会有预期的酒事。
事实上大哥的期盼很少有下文,一个十几张嘴巴的大家庭对于我们那些亲戚朋友来说,的确没有拜访的冲动。
1977年3月26日,我能够清楚地记住这个日子,是因为从那一天开始,我给自己树立了一个理想,长大了一定给大哥买一瓶像样的酒。
那天,表姐夫复员专门到我家。多年不见的表姐夫到来,让家中一下慌张起来。再穷,饭菜总能凑上一桌。贵客来了,酒成了全家最大的痛。青黄不接的季节,老码头酒坊早熄了酒灶。到乡场上去,哪个农村人家中有买酒的酒票。饭菜上桌了,大哥还在院中走过来走过去。母亲喊了几遍,大哥苦着一张脸进屋,大哥穿过父亲诊所的时候,突然眼前一亮,药柜上居然摆着一瓶酒精——
冷了开水,兑上酒精,大哥和表姐夫的酒事开始……
几碗过去,表姐夫开始对着大地无尽地倾吐哇哇哇地抒情——哇!大哥一旁大喊:“打到长耳巴一只!”哇!大哥数着:“打到长耳巴两只!”
数到打到长耳巴八只的时候,表姐夫从桌子上梭到地上,脸青面黑。
好在父亲出诊回到了家!
第二天我问大哥,昨天你们明明在喝酒,为什么说表姐夫打到了长耳巴?
大哥一脸地鄙视,说长耳巴还有一个名字叫什么,叫——兔。当这么多年兵,这么点酒就喝成那样?!
表姐夫气愤地从床上爬起来,说那还是一点酒,那可是大姑爷一整瓶酒精。
从此,大哥在家中再也找不到父亲藏酒精的地方。
1980年,农村土地承包责任制也让铅灰色的乡村有了花般一样的红润,乡里买上了放映机。谁做放映员?天天看电影?成为全乡最美的猜想。全乡把所有适合的人选都想过,唯独没有想到我大哥。只有我大哥想到了他自己。他给了两个理由:一是他是乡里小电厂的发电员,和放电影一样,都是“电”字辈的;二是他喝酒当支客师的口才适合放电影。
书记居然答应,显然书记看重的绝对不是大哥的酒名。
山上映山红盛开的时候,大哥从县里集中培训回来,书记要乡里的第一场电影在乡场上演,大哥说不行,县里书记说回去的第一场电影只能在自家门口演,万一演砸了好收场。
大哥这个乡村放映员的首秀在村校操场上开场啦!操场上挤满了人,山坡上挤满了人,学校屋顶上爬满了人,那部电影的名字很甜——《甜蜜的事业》。
银幕上现出两个大字:剧终。操场上的人没有一个要走,大哥说今晚的电影结束啦,明天在乡里演。大家这才起身,大人们却围在大哥身边,举着一个又一个空瓶子,指着挂在扁担上的电灯泡,央求大哥把扁担上的灯油倒一点,说这个点灯明亮。
大哥有哭的冲动。
今天我们总对那些炙手可热的人称为什么什么红。按照这个思路,大哥绝对是当年乡村的红人。乡村对有手艺的人都称师傅,唯独在大哥这里,称他为“文老大”。大哥在我们家排行老大,大哥在全县的放映员中确实也是老大。专业的考评术语我们不知道,至少有几手放映的绝活,让其他电影队让十里八乡不得不服这个老大:25秒的换片记录,精彩绝伦的电影解说,蒙着眼睛拆卸放映机,紧扣时事的幻灯宣传……当然还有一样更是让大家甘拜下风,那就是大哥理直气壮、气吞山河、惊天动地地喝酒。村里小媳妇甩脸子,小丈夫说文老大到村里啦,支书家的酒香就飘出来啦,小媳妇立刻漾出笑脸;村里小孩子哭闹不吃饭,大人们说文老大来啦,等会他光喝酒,不给你放打仗的电影,小孩立刻乖乖吃饭——大哥成为乡村最受欢迎的人,大家把家里能够拿得出来的好酒摆上,成就了当年大哥“有朝一日时运转,天天喝酒当过年”的理想高峰。
1989年10月,新中国成立40周年大庆的时候,大哥作为唯一的乡村放映员代表评为四川省文化系统劳动模范。晚上举办电影晚会,本来电影院早安排好一部新片。领导来啦,说今晚就放《一江春水向东流》,不上电影院,就露天电影,指明要大哥这个乡村放映员。当年的《一江春水向东流》是拍得比较艺术的一部电影,乡村放映时候必须加上放映员的解说,否则大家看不明白。按说在劳模这个层次这个场合是不用放映员解说的,显然领导看过大哥的劳模材料。
那绝对是大哥放映生涯最光辉的一幕。平时换片25秒,那天晚上他居然22秒就完成,平时对乡亲们解说,立刻调整为针对现场各个层次各个身份的观众解说,妙语连珠,诙谐调皮,雅的地方阳春白雪,俗的地方下里巴人。
领导什么也不说,只问一句:“有什么要求?”
喝酒!
大家异口同声!相处两三天,大家都知道大哥那点酒事。
1999年,电视机走进千家万户,电影不再是乡村最稀奇的东西,连当年的胶片放映机都派不上用场的时候,乡里决定解散电影队。听到这个消息,我们很为大哥高兴,我们经常用披星戴月来描述工作和生活的艰辛,其实这个词就是给我大哥的,披星戴月绝对是他几十年生活的常态,大哥总算可以在星空下睡个踏实的觉啦。
大哥回到家中,大嫂倒了酒,大哥连看都不看一眼,仰望着高远的星空……
我们为大哥担忧。
大哥的儿子大学毕业分配在某航空公司当机长,在海边给大哥买了房子,买了茅台酒,把大哥大嫂接过去。大哥把那些茅台酒全部摆在酒柜上,一瓶一瓶地摸过去,敲编钟一般,就是从不打开。大哥说人走远啦,家中地就闲啦,地闲了长草,人闲了难受,大哥的儿子只好在老家给大哥翻修了房子,摆满了大哥喜欢的酒……
大哥又成为了乡村支客师,他安排酒席,唯独不安排自己的酒,端着大大的茶缸,泡着浓浓的茶叶,看着别人喝酒。
家屋旁边的老码头酒坊又修了好几口大大的窖池,酒卖得很远很远,每当新酒出来,大碗大碗地请大哥品尝,大哥不喝,只闻……
2019年3月,区文化局局长来到大哥家中,捧出一本“新中国成立70周年改革开放40周年乡村放映员荣誉证书”,说国家不会忘记每一个人,国家记着你的奉献……
大哥换上崭新的衣服,挎上当年走村串户的放映包,气宇轩昂地走到乡场老街,大声喊着:“哪家有酒卖?哪家有酒卖?”
大哥醉啦!大哥的酒事又开始啦!

(作者系万州区作家协会主席)
版 面 欣 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