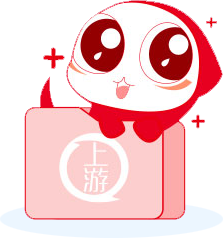

上游•夜雨丨我的老师那谁谁 - 冯茜

我的老师那谁谁
冯茜
我的老师是个文学人物。开始我并不知道,我当时是头脑冲动急于提高写作能力,稀里糊涂被人拉去拜师的,有病乱投医的那种。没想到拜对了,知道了老师的分量,吓了一跳,害怕了,想退缩,晚了。
从此我铁心跟老师学艺。我喜欢叫他师父,他也就称我为徒儿,有天我突然发现这种称呼显得我很像孙悟空,老师说:孙悟空好啊,那猴子机灵。他很满意我是猴子,因为可以使他像唐僧。不过没绷几天他就现了原形。
他的原形大致是这样的:脑子快,观念新,不摆谱,不着调,信口开河,口若悬河;六十多岁,常以八十自居,对万物好奇,胡思乱想,不爱请客;幽默机趣,自以为是,恃才而不勤奋,睿智偏要佯拙;练达稳重,老谋深算,孩子气,容易骗;瘦高个儿,假内向,喜孤独,好热闹,一言不合,一地鸡毛;清高,淡泊,食肉,豪饮,抢红包没手气,银发。
很显然,这种原形要想化装成唐僧那可是相当吃力,唐僧累他也累。所以,老师索性亮出他那集乱七八糟矛盾于一身的范儿,让人看到的,反而是本质上的纯净。我也纳闷,复杂的七色光混合在一起,为什么发出的居然是白光?
在外形上,老师属于老同志里帅得没边的那种,他自己好像没感觉。有次我忍不住对他说:师父你应该当演员。谁知他真当过演员。他说起以前在部队宣传队里,曾经有位战友帅得那才叫一个惊天动地。我问他:有你帅吗?他顺口说:那怎么可能!忽然意识到露了马脚,想了想又说:我俩风格不同,他主要演坏人,呵呵坏帅坏帅的。这种夸法我也是服了。
某天我拿文章向他请教,他对开头的一段不满意,他说:一篇文章的开头首当其冲,乃重中之重,正所谓文章争一起。这就好比一个人的脑袋,下雨天没带伞,只要脑袋被淋湿了,人就会有一种落汤鸡的感觉,而只要设法让脑袋不淋雨,整个人的精神面貌就不一样了。
说罢,他掏出一顶帽子戴在头上走到雨中去。那顶帽子他戴了十九年,平时装在随身包里,所以他的头部一直没淋过雨。我再看看我那篇文章,确实有点儿像落汤鸡。
另一次我又拿一篇文章给他看,他的评价是:这文章的腰身太臃肿,要减肥,不要有肉就往身上贴。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嘛,现在你去把它饿死。另外,文章的腿部也过粗了,一个美女上下一般粗好看吗?你这篇胖文章只适合放在唐朝,还有现在大洋洲的南澳。
我赶紧查了一下,南澳那地方集中了大洋洲一多半的胖子。所幸他没提到汤加,汤加全是胖子。结果这篇文章被他打回四次,我还哭了一场,直到删得瘦骨嶙峋,他才一拍桌子说:过了!唉,文章跟女人一样,要想减个肥真不容易。
老师经常带我去参加各种文学活动。我发现场合不同,他的风格也随之而变化。在有些场合他谈吐风雅,略带几句糙话;而进入另一些真性情的聚会,他也变得粗犷豪放,却又不失风雅。他告诉我,一个写作者应该有较强的适应能力,要随遇而安,不能格格不入,也不能失控无度。雅和俗的极致本是互相转化的,所谓大俗即大雅,大雅即大俗;而人的胸怀必须足够大,才能大而化之。作文亦同此理。
顺便谈谈老师的那个随身包。我只见他从包里掏出过那顶十九年的帽子,还有一回掏出过一副墨镜来耍酷,就再没见掏出过什么了,不知为啥那么重。为了尊师重教,我常抢着帮他背包,然后他就像一个移动摄像头随时监视着我。他说包里有身份证,如果弄丢了,他马上就会变成一个没有身份的人。
有一次我觉得包实在太重,问他能否放在车子后备厢里,锁好了保证不会被偷。他反问我:要是车被偷了怎么办?我说:我丢了车,你丢了身份证,咱俩扯平了。他说:那不一样,车丢了还可以再买。我说:身份证丢了也可以补办。他说:补办身份证要花钱。我说:买车更要花钱。他看了我一会儿,说:你知道补办身份证是什么感觉吗?那好比死而复生。
玩笑式的诡辩总是他赢,但我却能感觉到文学的意味。老师似乎在提醒自己,当然也在提醒我,面对这个千变万化的世界,要时时记得自己是谁,更不能弄丢了自己。
昨天开完会送老师回家,他下车后忽然又转身问我:那次我到底收你当徒弟没有?我说:好像是收了。他又问:你当时喝酒了吗?我说:喝了,我喝了好几杯。他说:那就是收了好几次。
他站在街头,银发飘飘,卓然不群,像站在李白的诗里: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
我突然不想叫他师父了,今后就叫他三千丈先生。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
版 面 欣 赏


还没评论 快来说两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