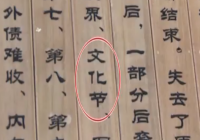冯雪峰(左一)与鲁迅两家合影
冯雪峰,原名冯福春,生于浙江义乌南乡神坛村——明将戚继光招募“义乌兵”的山村。这位冯家长孙尚在孩童时期就上山放牛了,以后下地干各种农活,9岁才放下牛鞭进学堂,因为祖父决定世代不识一字的家庭应该出一位能写会算的后代。很快,冯福春展露天性,学习刻苦,成绩优异。祖父喜形于色,将孙子写过的每一页纸片都精心收藏:“弄脏字纸要遭雷劈的!”为防读书人一般都有的“离心力”,祖父早早为长孙领来一位13岁的童养媳,想将孙子牢牢拴在自己身边以求发家致富。不料,此媳妇后来品行不端,不久便被遣送回娘家。
小学毕业后,家里不同意升学,认为能学会算术足矣,少年冯福春不干,他以替富家同学当“枪手”的代价,换取前往金华县城的路费与食宿。果然,他以第一名的枪手成绩,为这位同学考入金华中学;再以第二名的成绩,为自己考入了金华的浙江第七师范学校。由于师范有官费津贴,加上长孙成绩确属上佳,祖父宽恕了他的这一“自考”。
【丁玲:“我最纪念的是也频,而最怀念的是雪峰”】
1919年,“五四”风潮刮至金华小城,浙江七师发生罢课学潮,冯福春乃领头人,被开除学籍。随即,他改名为冯雪峰(那时没有户口簿与身份证,改名异常简单),瞒着家里,带着同学凑给他的17元钱,赴省会杭州。这一举动出乎祖父和父亲的意料之外,父亲气得折断了牛鞭。冯雪峰考入杭州的浙江一师,得到陈望道、叶圣陶、朱自清等名师教诲。在朱自清指导下,冯雪峰与柔石、潘谟华、魏金枝等同学成立了“晨光文学社”。1922年春,他与一师同学潘谟华、汪静之及应修人又成立了“湖畔诗社”。
1925年初,冯雪峰赴京,拿着潘谟华的听课证,成为北大旁听生,从而开始了与鲁迅的接触。这一时期,他一边在故宫博物院打工,一边充当校对与家教,仍时有断炊之虞,不得不经常向未名社借点小钱,但有借必还。1927年6月,冯雪峰加入中共,约半年后南下,在上海从事地下秘密工作,同年底经柔石介绍正式结识鲁迅,很快,他便与鲁迅、柔石一起着手筹备左联。
1933年深秋,时任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部长的冯雪峰,刚出门就被特务盯上。冯雪峰故意走到人声热闹的北四川路,快到海宁路时,他回头一把扭住特务,大呼:“绑票!绑票!”并动手殴打起来。特务猝不及防,惊愕未定,雪峰趁路人围观,巡捕未到之时,从人群中溜走。不久,他又差点闯进一位已被捕者的家,幸亏那家房东的娘姨(保姆)在后门暗示,再次脱险。由于在上海已无法立足,冯雪峰奉命经福建进入江西苏区,任中央党校教务主任、副校长,苏区政府中候委。
1927年冬,经朋友王三辛介绍,冯雪峰结识了刚写完《莎菲女士的日记》的丁玲,负责教她日文。当时北京的左倾知青纷纷南下,都去了火热的大革命第一线。冯、丁囿于各种条件,留在了北京,十分寂寞。两人相遇后,日语只教了一天就停止了,开始畅谈国事与文学。丁玲被冯雪峰的见识和谈吐所折服,迅速地爱上了他。不久,雪峰南下,丁玲也与胡也频去了南方。胡牺牲后,丁玲接编左联机关刊物《北斗》,成了左联书记冯雪峰的下属。
丁玲在延安时,有人曾问她:“你最怀念什么人?”她答道:“我最纪念的是也频,而最怀念的是雪峰。”丁玲承认:“这(指冯)是我第一次看上的人。”后来在《不是情书》一文中再说:“我自己知道,从我的心上,在过去的历史中,我真真的只追求一个男人,只有这个男人燃烧过我的心……”
丁玲这些形诸笔墨的情爱痕迹,难以擦拭,“丁陈集团”案发后,冯雪峰与丁玲的这层“历史关系”,也就成了掰扯不清的“暧昧”,当决定打倒冯雪峰时,他与丁玲的这一“历史关系”也就成了一支利箭。
一次批斗会上,冯雪峰、丁玲被先后喝令起立。一向耿介拔俗的冯雪峰低头站立,泣而无泪;“莎菲女士”丁玲则伫立哽咽,泪如泉涌。双双被划为右派后,两人形同陌路,从此再未见面。
【上饶的生死一线】
1937年7月,冯雪峰上南京会见中共代表团,代表团领导分别为王明、周恩来、博古。那天,博古给了冯雪峰一份《中国工农红军将士为卢沟桥事迹告全国民众书》,雪峰看到内有“服从蒋委员长”“信奉三民主义”,勃然大怒,向博古拍了桌子,指着鼻子骂他是“新官僚”。显然,在这历史弯折处,对于取消苏维埃政权、改编红军、服从国府,冯雪峰的思想未能及时转过弯来。
冯的妻子曾这样评价丈夫:“性子急,又容易兴奋。”其他人也说他“脾气躁,爱骂人”。1936年,冯曾甩过楼适夷的稿子:“这样的文章,一条条理也没有,论据不结实,怎么能拿去发表呢?”甚至指责:“你去日本学习了三年,简直什么也没有学到嘛!”(王培元《在朝内166号与前辈魂灵相遇》,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年版)冯雪峰身上典型的诗人气质与艺术家做派,得罪了不少人,因此呛水政海,似成必然。
故而,到1937年9月中旬,一气之下的冯给潘汉年写信请假,发了“浙东人的老脾气”(鲁迅语)。行前,他对胡愈之说:“他们要投降,我不投降。我再也不干了,我要回家乡去。”又对楼适夷说:“他们有些人一心想当国民党的新官,我可不干。”“党错了,鲁迅是对的。” 胡愈之找到潘汉年探问究竟,潘答:“雪峰这样子不对,谈判还未成功,怎么就说是投降呢?这是中央的事情,他是共产党员,怎能自己说跑就跑掉,组织纪律呢?他说再也不干了,他不干什么?不干共产党吗?!”几年后,当冯雪峰从上饶集中营保释赴渝,周恩来专门找他谈话,说他与博古的争论观点是正确的,符合中央对白区工作的政策方针,但因此闹意见回老家写小说,则不应该。
1937年12月20日,冯雪峰回乡隐居,专心写红军长征题材的长篇小说《卢代之死》,3年后大致成稿,共50余万字。不久,黄源通过李一氓向东南局书记项英提出建议,认为不应让冯雪峰这样重要的人物独自留在家乡义乌。项英接受了建议,电金华邵荃麟,转请雪峰来新四军部,但雪峰拒绝了。多年后,黄源问他何以不接受邀请,冯笑笑答道:“我在中央苏区早认识项英同志的。”黄源意会,便未再问下去。
冯雪峰失去与党组织的联系近两年,这种无组织、无纪律的任性使气,乃是导致中共领导层对其印象不佳的一个重要原因。1957年被打倒时,自是一大罪状,他检讨说:“得意时在党之上,不得意时在党之外。”
1941年初皖南事变后,形势开始恶化。1941年2月26日,金华宪兵根据冯雪峰与金华某左翼杂志社的通信,循迹进入义乌神坛村逮捕了冯。由于冯事前有所准备,转移了文件刊物,身份未曾暴露。审讯中,他复名冯福春,自称是商务印书馆研究历史的“先生”,并拒绝登报声明与中共或新四军无干系。随后,他被押入上饶集中营茅家岭禁闭所,《卢代之死》手稿就此失落,再未找回。
在狱中,冯雪峰先是染上了回归热(一种急性传染病,临床特点为周期性高热伴全身疼痛等),若非难友出钱买来十几盒606针剂,他必死无疑——狱中先后有四五十位难友染病归西。不久,冯再得肋膜炎,由难友外科医生毛鹏仙操刀放脓,手术时只有一把刻章小刀、一碗清水,没有药物,更无麻醉。因无条件消毒,术后伤口久久不能愈合,继而又感染上肋骨结核。消息传至上海再传至延安,毛泽东、陈云于1942年得知,马上致电重庆的周恩来、董必武,几经曲折,最终于年底由宦乡出面保外就病,限期3个月回狱。特务头子张超批示:“三月后病愈不回,唯保人是问。”冯当然未再回去。后来,冯雪峰将这段经历写成了电影剧本《上饶集中营》,1951年由上海电影制片厂改编拍摄成影片。
【与毛泽东畅谈鲁迅】
冯雪峰与毛泽东的关系,可追溯至“湖畔”时期。1925年,远在广州的毛泽东读到《湖畔》诗集,跟人打听冯雪峰的下落,托人捎话,说他很喜欢《湖畔》与冯的诗作,希望冯能到南方与他一起工作,以诗会友。
1934年初,冯雪峰进入中央苏区,此时正值毛泽东赋闲不得志,便与冯时常上饭馆吃饭聊天,通宵长谈,谈论的主题经常围绕鲁迅。当时中央有人提议请鲁迅来苏区当人民教育委员,毛说:“这些人,真是一点不了解鲁迅。”冯雪峰告诉毛,鲁迅读过毛词《西江月·井冈山》,认为他有“山大王”气概,毛泽东哈哈大笑。1934年10月中央红军撤离,部署甚为混乱,中央并未通知毛泽东,还是冯雪峰经过毛的住处,催促他随军转移。长征途中,毛多次派人将弄到手的纸烟送给冯。
1936年4月,受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的指派,冯以中央特派员身份衔命回沪,任务是建立电台,联络中断多年的上海地下党组织,开展左翼文化运动。抵沪不久,他即找到毛澤东两个散落的儿子(毛岸英、毛岸青),派人将他们经巴黎转送莫斯科。他受鲁迅委托,将鲁迅所编的瞿秋白《海上述林》送给毛、周,并“先斩后奏”地用鲁迅的稿费买了火腿、香烟及十几条长围巾送给中共首长,以御西北高原烈风。火腿、香烟一到西安就被“瓜分”掉了,只有围巾最后送到。(冯雪峰与鲁迅的关系,陈望道评曰:“弟子而以某种思想学说影响他的老师的,古今中外,颇不乏人。雪峰对于鲁迅,便是一个现成的例子。”)
因冯雪峰抵沪后,并没有积极去找周扬、夏衍等“失群孤雁”(他们长期与中央失去联系),而是先找了鲁迅,先见了胡风,不久便被卷入“两个口号”的论争,从此与周、夏等人结下梁子,成为冯后来之所以摔大跟斗的又一历史原因。评家有云,此事为冯的后半辈子“埋下了一颗定时炸弹”——1957年8月17日,王府井大街中国文联大楼小礼堂,中国作协党组扩大会议上,文化部副部长夏衍抛出一篇“爆炸性发言”,指责冯挟鲁迅对他们进行“政治陷害”,同时揭发冯在陕北赴沪途中,附有任务寻找一支与中央失去联系的游击队,由于冯拒不执行,致使该队伍被国民党全部消灭。到上海后,又曾企图将夏衍扭送租界巡捕房治罪。此时,冯20余年的老部下楼适夷信以为真地站起来,指责冯欺骗自己,号啕大哭起来;许广平也发言怒斥冯。(楼适夷《为了回忆,为了团结》,《鲁迅研究动态》1980年第2期)
1945年秋,毛泽东赴重庆谈判时会见了冯雪峰,夸赞他的杂文集《乡风与巿风》与诗集《真实之歌》,说是好几年没看到这样的好作品了。就在这一时期,冯雪峰在重庆发表长文《论民主革命的文艺运动》,观点与毛泽东《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有明显分歧,当时就被认为是“反对毛主席的”。后在《新华日报》副刊,冯又以笔名“画室”发表杂文《题外的话》,其中写道:“研究或评价具体作品,用什么抽象的‘政治性和‘艺术性的代数式的说法,可说是什么都弄糟了。如果这样地去指导创作,则更坏。”“对于作品不仅不要将艺术的价值和它的社会的政治的意义分开,并且更不能从艺术的体现之外去求社会的政治的价值。”被认为是对《讲话》的挑战。周恩来找到他谈心,冯虽然不再赞赏胡风的“主观战斗精神”,但思想上并未彻底认错服输。1950年代初,他多次指出建国后的创作太落后,现实主义特别薄弱,作品真实性非常低,公式化、概念化的问题十分严重。
1954年,毛泽东发动《红楼梦》研究批判运动,担任《文艺报》主编的冯被定调为“压制新生力量”,说他用贵族老爷式态度对付文艺青年——事实是冯热情接待了李希凡、蓝翎,辞别时送至大门外,替他们叫了三轮车,并付了车钱。
冯雪峰不得不先后在《人民日报》《文艺报》发表检讨,内有一句“反马克思列宁主义”,领袖看后非常不满。1954年12月31日,毛将冯的诗作和寓言等转给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彭真、彭德怀、陈毅、陆定一等阅读,拿着其中一篇文章对胡乔木说:“冯雪峰的‘湖畔诗写得很好,怎么文章写得这么坏?”
【为保党籍,违心改注】
1957年,冯雪峰成为文艺界“头号大右派”。批冯的“主战场”在中国作协,冯任社长的人民文学出版社则“配合作战”。8月12日,一位文化部副部长亲临人文社动员,号召全社对冯雪峰进行斗争。不到一个月内,人文社召开了七次全社批斗大会,冯出席第一次与最后一次。1957年8月27日,《人民日报》头版通栏宣布冯雪峰:“三十年来一贯的反党分子”,冯被钉上了耻辱柱。
为了保住党籍,冯雪峰听从作协党组书记邵荃麟的劝告,在1950年代版《鲁迅全集》“答徐懋庸信”的注释中留下一笔:“鲁迅当时在病中,他的答复是冯雪峰执笔拟稿的,他在这篇文章中对于当时领导‘左联工作的一些党员作家采取了宗派主义的态度,做了一些不符合事实的指责。”这一妥协使冯雪峰悔恨终生——因为这并非事实。对此,巴金曾有叙述:“(我)赶到科学印刷所去,读了正在排版中的文章,是许广平同志的手抄稿,上面还有鲁迅先生亲笔修改的手迹。是他自动地起草,为了照顾先生的身体,可是先生改得不少。”(巴金《随想录》第1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冯违心改注,极度痛苦,整夜失眠,胃疼得厉害。他以为如此这般按周扬的口径做了一切,便可保住党籍,然而,作协并未兑现承诺。1958年4月,冯雪峰被开除党籍,撤销本兼各职: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兼总编、中国作协副主席、全国文联常委、全国人大代表等,从副部级连降三级,最终被安排做人文社的普通编辑。不久,他又主动让出崇文门内苏州胡同21号独院(按规定冯一家仍可单独住在那儿),搬入东单北新桥草场胡同27号大杂院集体宿舍,最后祖孙三代蜷居20平米小屋,直到去世。
落难后,作家牛汉曾多次去看他,只见冯枯坐办公室,暗处饮泣,并泣诉自己“被说服”的过程。为证清白,他多次想投昆明湖,但考虑孩子尚小,妻子无谋生条件,自己无论如何得撑着活下去,他相信能活到历史洗净身上污水的那一天。
冯雪峰将自己一部有关长征的长篇小说手稿锁入箱子。1961年11月,《人民日报》通报摘去“右帽”,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将这部长征小说端放案头。不久,他被告知:可以写作,但像二万五千里长征这样伟大的革命题材,他不适宜写。这一次,冯雪峰没有把稿子锁回箱子里去,而是将它投入炉火之中,付之一炬。在这些日子里,他的头发也从两鬓花白到满头皆白。虽然准许他写历史题材太平天国的小说,但《小天堂》最终胎死腹中。至于其它写作路子,亦被一一堵塞,写评论不可能,写寓言更易遭曲解。
1964年,冯雪峰上河南林县参加四清,只能使用化名“冯诚之”。“文革”中,他头上有三顶帽子:摘帽右派、叛徒、修正主义分子。他先入牛棚,后发配文化部湖北咸宁向阳湖干校,种过菜、挖过渠、锄过草、插过秧、放过鸭、扫过厕所。
霜重色愈浓,时穷节乃现。“文革”伊始,冯的“对立面”就进了秦城监狱,他有许多机会在各种“外调”中进行“合理报复”。“文革”中,冯雪峰最麻烦的是对付各种外调,写了超过百万字的交代材料。因怕记忆出错或每次写材料有出入,他还专门搞了一份“交代底稿”(后载《新文学史料》1979年第2期)。冯雪峰没有趁机翻案,未对整过自己的周扬、夏衍落井下石,而是实事求是且自揽部分责任。周扬在狱中看到冯的这份材料,出狱后第一个去看的就是“老对头”冯雪峰,周扬激动得抱住冯痛哭。
冯雪峰生命的最后20年,没有发表任何作品(不能发表),临终最大的遗憾是未能恢复党籍,“希望有重新回到党内的一天”。从1958年4月开除党籍,冯就开始谋求回到党内。1960年他甚至去找了对他作了“爆炸性发言”的夏衍,承认过去有错误,要求回到党的怀抱,这让夏衍很是感动。(夏衍《一些早该忘却而未能忘却的往事》,《文学评论》1980年第1期)
【冤屈得以昭雪】
1976年1月31日,冯雪峰死于肺癌。2月7日下午,亲属及不足十人的生前好友向遗体告别,反右时曾向冯投过石头的楼适夷,偷偷地在他的遗体前放了一束鲜花。按当时规定,冯的遗体不准进八宝山,只能上北京东郊火葬场。2月16日,姚文元下令“不见报,不致悼词,一百至二百人规模”,于八宝山草草举行悄无声息的追悼会——没有悼词,没有一句大声说的话,只有三项程序:哀乐、默哀、结束,然后绕骨灰盒一周。出席者有茅盾、胡愈之、楚图南、李一氓、宦乡、周海婴,以及上饶集中营难友吴大琨、陈子谷、邵宇等。
三年后,冯雪峰的冤屈得以昭雪。1979年春,人民文学出版社党委讨论平反事宜,新改组的党委会众口一词:“早就该改正了,这还有什么可讨论的!”党委会很快开成“冯雪峰追思会”。较之当年的七次批斗,数次研讨,平反程序则快得多。冯雪峰念念不忘的党籍,自然也得以恢复了。随后,中组部正式批准《关于冯雪峰同志右派问题的改正决定》。
但冯的追悼会却难产,足足筹备了半年有余。因特意安排在文代会期间,故有千余人出席,文化部部长朱穆之致悼词。而之所以需要筹备如此长时间,据说是一位重量级人物不同意中央已认定的悼词(人文社、出版局两级党委通过),言如果发表这样的悼词,追悼会前他要先发表批判雪峰的文章。惹引“麻烦”的那段悼词是:“冯雪峰同志接受党中央的委派,从陕北回到上海,沟通了党和鲁迅的关系,捍卫了作为文化斗争主将鲁迅的光辉旗帜。”
为照顾这位文艺界领导人的“体面”,由中央负责人修改为:“冯雪峰同志接受党中央的委派,从陕北回到上海,传达了党中央的各项方针政策以后,使鲁迅加深了对党中央、对毛泽东同志的敬仰和依赖。”
一望可知,旧日嫌隙仍在发酸。说来说去,就是要将冯雪峰与鲁迅分开,不能让冯雪峰沾了鲁迅的光。今人看来,两段文字并无实质性差别,何至于需要“修改”大半年?事实上,冯雪峰在上海的前后活动仅著名的就有:一为协助李立三、陈赓去见鲁迅;二是安排瞿秋白驻沪期间与鲁迅的联系;三为方志敏遗信、遗稿的转交;四为丁玲联系赴陕事宜;五是斯诺访陕的联络安排。何以就不能给一句“捍卫了文化主将鲁迅的旗帜”?
1979年11月17日,为冯雪峰补开的追悼会如期举行。此时,人们回忆起冯身上许多“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本色”。如冯雪峰异常俭朴,傲上谦下,堂堂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周恩来指定给冯雪峰配备一辆小轿车(人民、美术、教育等大社社长均无),他却很少坐,只有上中南海开会等重要活动例外。平常戴一顶大草帽,雇一辆三轮车上下班。如遇雨天坐小汽车回家,到胡同口便会下车,因为路窄,他怕车轮溅泥于行人。行政部门买了一台电风扇,送到他家,立即退回;为公家办事,请客吃饭,如由他个人出面,一定是自己付账。1957年,反右运动开始不久,巴金去看望冯雪峰,冯拉他去新侨饭店楼下的大同酒家吃饭,巴金回忆:“雪峰虽然做主人,却拿着菜单毫无办法,这说明他平日很少进馆子。他那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在重庆时就传开了。”
可惜,这些“追认”,冯雪峰已经听不到了。
原标题:风雨冯雪峰
【免责声明】上游新闻客户端未标有“来源:上游新闻-重庆晨报”或“上游新闻LOGO、水印的文字、图片、音频视频等稿件均为转载稿。如转载稿涉及版权等问题,请与上游新闻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