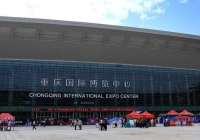澎湃新闻消息,“澎湃新闻·艺术评论”(www.thepaper.cn)今晨获悉,知名画家黄永厚于8月7日晚19点在安徽合肥去世,享年91岁。刘海粟曾评价黄永厚说:“文真、字古、画奇。”朱屺瞻则说:“画这种画要读好多书。”用画笔来思考,关注心灵,关注当下,关注社会问题,是黄永厚画作的美学特征。
黄永厚与杂文家陈四益曾在《读书》等杂志开辟文画专栏,针贬时弊,影响极大。
黄永厚与其哥哥黄永玉同是知名画家,但风格却有较大不同。据业内人士介绍,兄弟俩曾有十多年不相往来,后来终于和好,其中一言难尽。黄永厚身上的文人气更重。
作为画家、作家,黄永厚从来不愿意当一件工具,哪怕是一件金光闪闪的工具。这是黄永厚在画上喜欢题写长跋的一个理由。长跋,是黄永厚观察现实,反思自己的过程,是黄永厚不甘沉沦,拒绝媚俗的表现。

画家黄永厚(1928——2018)
8月7日晚十点多,画家黄永厚家人发出泣告:
家父黄永厚老先生于8月7日19点仙逝
黄河
黄风安 泣告

老友相聚,左起:许麟庐、黄苗子、黄 永玉、黄永厚
黄永厚生于1928年,土家族,湖南凤凰人。在黄家排行第二,早年因其兄长黄永玉离乡求学而承担起了黄家“长子”的责任,后又因画过抗战宣传画而应召当兵,入过军校,做过中尉;新中国成立后,由哥哥黄永玉介绍,考入中央美术学院读书。 1960年,从央美毕业后去了安徽合肥工业大学执教。黄永厚藏书、读书甚丰,属于中国画中的“文人画”派,其作品除少量山水、花卉外,大都取材于历史题材和民间传说中的人物。曾在画作中题“尽似古人,要我何用”以自况。刘海粟曾评价黄永厚说:“文真、字古、画奇。”朱屺瞻则说:“画这种画要读好多书。”用画笔来思考,关注心灵,关注当下,关注社会问题,是黄永厚画作的美学特征。
 黄永厚画作《聊斋人物》
黄永厚画作《聊斋人物》
他曾说,“画家就不是社会人吗?不闻不问那把砍刀就不会砍到画家脖子上了?要讲读书,《论语》、《庄子》、《史记》都管不到这个份上来,你得另想办法去找书来读,读读报评听听高明如何评价。我的画就像当前的时评,我不做旁观者。要起哄那是不用学习的,最近我读勒庞的《乌合之众》就是从这本书里照自己的影子。你看看,有几个人逃出‘乌合之众’?尤其像我这样当兵出身的人,可以说是天生的由人支使的料。”
一位学者对“澎湃新闻”表示,黄永厚先生特别喜欢《世说新语》,画过不少关于《世说新语》的题材。他曾说:“想达到《世说新语》的味道,很难。明清小品,像张岱那种,写得多好。这个社会让人体会不到快乐的生活,体会不到诗意。假如你们写不出像李义山这样的东西,怨不得你们,生活所逼。我们极容易做奴隶,以前做极权政治的奴隶,现在做钱的奴隶。”

黄永厚先生作品《阮籍》
面对画坛流行“钱多人傻”之象,黄永厚依然保有古风。他说:“这个世界没有谁对不起我。但我一点也不吸引眼球,讲话绝对语不惊人。”而黄永玉在为他写的《晨钟暮鼓八十年》中说:“他的画风就是在几十年精神和物质极度奇幻的压力下形成的。我称之为‘幽姿’,是陆游词中的那句‘幽姿不入少年场’的意思。无家国之痛,得不出这种画风的答案。陆游的读者,永厚的观众,对二者理解多深,得到的痛苦也有多深,排解不掉,抚慰不了。”
中国作家书画院常务副院长张瑞田说,黄永厚先生是一位有思想、有激情、有正义感的画家、作家。他在北京居住期间,屡屡拜访,衡文论艺,受益多多。

黄永厚先生作品
张瑞田认为,作为画家和作家,黄永厚的画品、文才,出其右者寡矣,“依我的目光来看,黄永厚是画家中文人,是文人中的画家,因此,他的画作,处处可见机趣、禅思,他的文章,字字映现学识、哲理。常常在《书屋》《读书》等杂志拜读黄永厚文配画的作品。画放达、清冷,文沉重、深刻,体现阅历,洞见卓识。作为画家、作家,黄永厚从来不愿意当一件工具,哪怕是一件金光闪闪的工具。这是黄永厚在画上喜欢题写长跋的一个理由。长跋,是黄永厚观察现实,反思自己的过程,是黄永厚不甘沉沦,拒绝媚俗的表现。”
黄永厚的学生陈远说:“这些天 ,一直在想,等天气凉快一些就过去看望老人家,不想竟接到噩耗,手一直抖,不愿相信这是真的。这个教我自由的老头于8月7日晚7时走了,十年师弟,情如父子,8月8日我要去合肥送老爷子最后一程。”
出版人李怀宇追忆说,黄永厚当年在北京郊区通州的家颇为简朴,大别于黄永玉同处通州的豪宅“万荷堂”。一进门,但见黄永玉的字:“翻你东西的人肯定是个天才,你要想法赶快把他轰走。”进了客厅,一眼看出黄永玉的画,相似的题材我曾在范用家见过两幅,这一幅的题字为:“除却借书沽酒外,更无一事扰公卿。吾家老二有此风骨神韵。”两边有一对联,乃是聂绀弩的诗句:“中年多隐痛,垂老淡虚名。”黄永玉、黄永厚曾有近20年不相往来,后来兄弟和好,一言难尽。

黄永厚先生作品《 板桥》
《开卷》主编董宁文说,上月还在与雷电先生电话中说秋天一道去合肥看望病中的黄老。那次电话中主要谈到黄老的近况以及前几年大病之后的恢复情况,心情颇为沉重,“拜识黄老多年,惠我良多,是我心中一位响当当的长者,愿老人安息。”
杂文家陈四益此前曾撰文回忆他与黄永厚在《读书》杂志等的文画合作缘起:黄永厚是黄永玉先生的二弟,相差四岁,也是一位著名的画家。他们老黄家的人都很有个性。认识黄先生出于偶然,是一位朋友邀我一同去探访的。他从安徽到北京,住在紫竹桥的中国画研究院。看他的画,很有个性。同他交谈,人如其画,个性彰显。他说到高兴处,就会畅怀大笑。说到他的画,他会突然来了兴致:“怎么样,来一张!”话音未落,已起身铺纸、提笔,画将起来,“同他的合作,从《聊斋索图》始。是他先画了几幅从《聊斋》中找出的画题,叫《聊斋索图》。我从他的画中又生发出一些意思,或同、或异,有时还唱唱对台戏。后来,他又画了竹林七贤图,每图都有一段题跋。我觉得他的竹林七贤图,自出手眼,很有启发,但是图上的题跋毕竟字数有限,不易为人理解,便自作主张,为每幅图作了一篇文章,每篇二三千字,寄给黄先生看了,他非常高兴,于是,就在《瞭望》上刊载。因为画了竹林七贤,我就想接着再谈《世说新语》,黄先生一口允诺为每篇作图,我当然喜出望外。后来结集为《魏晋风度》。又后来,湖南《书屋》约稿,我问黄先生是否有意一起来谈谈《儒林外史》,于是又有了后来在《书屋》连续刊登的《错读儒林》。”

黄永厚先生作品 《文长画气盛》
“到了2006年,丁聪先生患病,我同丁聪先生的合作不能不中断。起先,因为读者有一两期看不到这个专栏,便来函询问《读书》:是不是陈、丁二位遇到了麻烦?编者怕引起误解,问我是否可以请另一位画家继续。于是,便征求黄先生的意见,是否愿意把这个专栏接下来。黄先生同我的合作也已二十年,相互了解,便笑道:你当初跟一个七十岁的老头跑了第一棒,现在又找个八十岁的老头跑第二棒,这算什么事儿啊。依旧爽快地答应了。《读书·诗话画》的专栏,在停了两期后又继续了。只是‘丁画’改成了‘黄画’,文的风格未变,图的风格则由丁聪先生的工笔写真,换为黄永厚先生的彩墨写意了。同黄先生合作的文图,后来结集为《忽然想到》。这样,我和黄先生合作的图文,已出版的计有《聊斋索图》《错读儒林》《魏晋风度》《忽然想到》等。”
延伸阅读
暮鼓晨钟八十年
文/黄永玉

黄永玉手稿
二弟永厚要出版画集,后来又不出了。问侄儿黄何,他也没说出个道理;及至见到二弟,我劝他还是出一本好,他同意了。
在画画上,他的主张是很鲜明的。有的人画了一辈子画,却不明白他的主张何在?一个画画的人主张是很重要的。没有主张,画什么画。
当然有些人的画其实并不怎么样,却也一天到晚四处乱宣主张,其目的只是怕人不知道他的画好,那点苦心也就算到头了。
所以我觉得出一本画册最是让人了解自己主张的好办法,什么话都不用说了,它可以坦诚的让人看透肚肠心肝——吃的什么料?喝过多少墨水?发挥过什么光景?施展的什么招式?
毛泽东到苏联找斯大林订条约,主题是“既好看,又好吃”;托尔斯泰当面称赞契科夫的文章是“又好看,又有用”。两个大人物都提到文化上虚和实的东西。好多年前在农村搞“四清”,也提到“喝稀的,吃干的”两个政治概念,喻指精神和物质的紧密关系。
虽然说画画是件既用脑又用手的快乐行当,倒也真是历尽了寒冰的死亡地带得以重见天日。几十年来,人们溷滞于混乱的逻辑生活中。“深入生活”,得到的回报是沉重的沉默;“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有了发言权的彭德怀却招来厄运,“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真要关心起来,却又叶公好龙似的令人害怕。哲学上范畴的破坏,文艺上“载道”和“言志”的文体功能变成了对立的阶级斗争之武器。柳宗元《江雪》诗云:“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衰笠翁,独钓寒江雪。”在此景象中,垂钓的剩下郭沫若、浩然……间或还有两三两个海豚式的文艺人物在海中时冒时没“划”着“时代”创作“刹那牌”经典。

黄永厚先生作品
厚弟也近80了,我们都哈哈笑笑着说,从未以美学指导过自己的创作。美学中从毕达哥拉斯、柏拉图、康德、黑格尔,到马克思、列宁、朱光潜……从未提起过。人打生下地来,什么时候感受到第一次“美”的?谁都没有丝毫关注过这个伟大的命题。人自己包括美学家自己何时懂得美的?感知尚无着落,倒不如《孟子》中那四字黑话“食色性也”解馋多多,美学家不谈美在人身上的起始,要他何用?
厚弟几十年来的画作,选择的是一条“幽姿”的道路。我们的一位世伯、南社诗人田名瑜的一首诗谈凤凰文化的头一句就说“兰蕙深谷中”,指的就是这种气质。
说一件众所不知的有趣小事。八十多年前,我们家那时从湘西凤凰老西门坡搬回文星街旧居没几年。厚弟刚诞生不久,斜街对面文庙祭孔,我小小年纪,躬逢其盛。演礼完毕,父亲荣幸的分到一两斤从“牺牲”架上割下来的新鲜猪肉,回到古椿书屋,要家人抱起永厚二弟,让他用小舌头舔了一下孔庙捧来的这块灵物,说是这么非同寻常的一舔,对他将来文化上的成长是有奇妙的好处的。
想想当年,这对儿夫妇对于文化的执着热衷,是一个多么温馨的场面!他们那时的世界好纯洁,满是充满着书卷的芳香……
过不了几年,湘西的政治变幻,这一切都崩溃了。家父谋事远走他乡,由家母承担的供养五个男孩和祖母的生活担子。我有幸跟着堂叔到福建厦门集美中学读书,算是跨进天堂,而遥远的那块惶惶人间,在十二岁的幼小心灵中,只懂得用眼泪伴着想念,认准那是个触摸不着的无边迷茫的苦海。
我也寄了些小书小画册给弟弟们,没想到二弟竟然在院子大照壁墙上画起画来,他才几岁大,孤零零一个人爬在梯子上高空作业,这到底是鬼使神差还是孔夫子他老人家显灵?当然引来了年纪一大把的本地的文人雅士、伯叔婶娘们额手赞美。物质上的匮乏,却给祖母、母亲带来精神上的满足,每天欢悦的接待一拨又一拨的参观者。有了文化光彩的孩子,任何时空都会被人另眼相看的。几百年的古椿书屋又有了继续的香火,真怪!

黄永厚先生九岁时的壁画
湘西老一代的军人传统,地方部队总是有义务寄养一批候补的小文人小作家。名义上是当兵。其实一根枪也没摸过,一回操也没上过,在部队里跟着伯伯叔叔们厮混,跟着部队四处游走。表叔沈从文如此,永厚二弟也是如此。
二弟在“江防队”(这到底是个什么部队,我至今也不能明白)有机会做专业美术工作,和我当年在演剧队的工作性质完全一样,读书、写字、画画、自己培养自己。我们兄弟,加上以后跟上来的永光四弟,命运里都让画画这条索子紧紧缠住,不得开交。
说苦,百年来哪一个中国人不苦?苦透了!这里不说它了。
在兄弟中,永厚老二最苦。他小时候多病,有一回几乎死掉。因为发高烧已经卷进了芭蕉叶里了,又活过来;病坏了耳朵,家里叫他“老二聋子”,影响了发育;又叫他“矮子老二”,后来长大,他既不聋也不矮,在我们兄弟中最漂亮最潇洒,很多人说他长得像周总理。成年后,他的负担最重,孩子多,病痛繁,朋友却老是传颂他助人为乐的出奇而荒唐的慷慨逸事,于是家里又给他起个“二潮神”(神经病的意思)的名字。
他的画风就是在几十年精神和物质极度奇幻的压力下形成的,我称之为“幽姿”,是陆游词中那句“幽姿不入少年场”的意思。无家国之痛,得不出这种画风的答案。陆游的读者,永厚的观众,对二者的理解多深,得到的痛苦也有多深,排解不了,抚慰不了。
“幽姿不入少年场”自然是不趋附、不迎合,而且不羡慕为人了解。
徐渭、八大、梵高活在当时几曾为人了解、认识?因为他们深刻,他们坚硬,一口咬不下,十口嚼不烂,必须有好牙口、好眼力、好胃口才够格招架,并且很费时间,所以幽姿不免寂寞,以至如明星之光年,施惠于遥远的后世。
听忠厚的朋友常常提起某个伟人着时读过不少书,出口成章,很有学问。我总是微笑着表示不以为然。我说他读的书我都读过,我读过几十年他没有读过的外国翻译书,他根本就不可能读到,论读书,我起码比他多一倍。“文革”期间,他像发现新大陆似的大谈《飘》,大谈《红与黑》,津津有味,还要以此教育别人。说老实话,那不过是我的少年读物,没什么好牛皮的!他还特别喜欢大谈知识分子最没学问的话。一个人有没有学问,怎么可能由他一个人说了算呢?
真正称得上读书人的,应该像钱钟书、陈寅恪、吴宓、叶公超、翁独健、林庚、钱穆、朱光潜……这些夫子,系统巩固,条理清楚,记性又好,在他们面前,我们连“孺子”的资格也够不上的。
要是站在画家的位置上,说起读书学问,除了以后活着的年月还要读书之外,也算够用了,不是学问家,要那么多学问干嘛?老记那么多干嘛?
学问家读书,有点、线、面的系统,我们的知识是从书本上一路打着滚儿过来的,像乾隆的批示一样,我们只够“知道了”的水平。但比后来的首长在公文上打圆圈却是负责认真多多。画画,不可无学问前后照应。二弟的笔墨里就有许多书本学问,用的很高明,很恰当,变成了画中的灵魂命脉,演绎的不仅仅是独奏,而且是多层次的交响。
画家像个牧人,有时牧羊,有时牧马,有时牧牛,有时牧老虎。只要调度有方,捭阖适度,牧什么都没有问题的,甚至高兴起来,骑在老虎背上奔驰一场也未必为不可。做个牧人不容易,上千只鸭子赶进荡里,汪洋一片也有招不回来的时候。
文化上有不少奇怪的现象,可以意会,可以感觉得到。要说出道理却很费气力,有的简直说不出道理。比如说京剧有余叔岩、有言菊朋、有奚啸伯,更有周信芳。余叔岩某个阶段曾倒过嗓子,那唱法几乎是一边夹着痰的嘶喊,一边弄出珍贵的从容情感:宋公明打坐在乌——龙——院,莫不是,阿——妈——呢,打骂不仁?那一个“阿——妈——呢”已经是卡在喉咙里出不来了,嗳!就那点声嘶力竭挣扎于喉咙间的微弱信息,不知倾倒了多少当年追星族的梦魂?从音乐庙堂发声学的角度来看,这简直是笑话。说言菊朋,说周信芳,说儒雅到极致的奚啸伯,莫不都有各自的高超境界。

黄永厚先生作品《 颜驷当官》
画,也有各型各号的门槛,外国如此,中国也是如此。我想外国印象派以后的发展变化直到今天,恐怕习惯于写生主义的很多欣赏者都掉了队,都老了,现象如此,实际情况正如中国老话所云,“老的不去,新的不来”。不习惯不要紧,我就是四五十年代的胃口特别好的年轻人,是一个既喜欢老京剧又拥护前卫艺术的八十已过的欣赏者。
你问我为什么喜欢八大?喜欢突鲁斯拉德莱克?喜欢米罗和毕加索?喜欢勃罗克?我能意会。要说,如果给我时间或许也能说得出一点道理,但是,为什么你有权利要我说出道理?有的艺术根本就是毋需说明道理的,比如音乐,比如中国写意画,比如前卫艺术!
一个艺术家到了成熟阶段已经不存在好不好的问题了,只看观众个人爱好,喜不喜欢,比如说我喜欢买一点齐白石的话,却很少收藏黄宾虹的画;不是黄宾虹的画不好,只是我不喜欢。
梅兰芳和程砚秋,我听的是梅兰芳;没人敢造谣说我黄某人曾经说过程砚秋不好。
有人说多少个齐白石抵不上一个鲁迅,这似乎是在说十八个李逵打不过一个张飞的意思。张飞和李逵如活在一个历史时期,倒是可以约个时间过过招论论高低的。他们比武的可能性的基础是因为他们同是武人。
鲁迅和齐白石虽都是文化巨人。革命思想方面,鲁迅了不起,但鲁迅不会画画。齐白石画画画的好革命的道理却谈不上。两个人在各自的领域里各有成就,比是不好比的,就好像盐和糖都于人有益,可谁都不会说二十五斤零四两的糖比不上一斤盐。
厚弟的人物,常作悲凉萧瑟,让观者心情沉重,也时见厚重鲁莽如铁牛之类,夹带着难以琢磨的幽默点染,这恐怕就要算到父母的遗传因子账上了,父亲在这方面的才情影响过他的表弟沈从文,(《沈从文小说集》序,人民文学出版社),自己的儿子自然不在话下。
二弟明年就八十了,尔我兄弟在年龄上几乎是你追我赶,套用一句胡风先生的诗题作口号吧——“时间,前进呀!”
2006年12月31日晨3时半。香港山之半居。
黄永厚:除却借书沽酒外,更无一事扰公卿
文/陈远
“除却借书沽酒外,更无一事扰公卿,吾家老二有此风骨神韵。”这是一位大画家哥哥给同样是大画家的弟弟在一幅画上的题跋。
哥哥是黄永玉,弟弟是黄永厚。这个题跋,除了说这位黄家老二的风骨之外,还透露了另外一个信息:喜欢书。在圈内,比他晚的晚辈都管这个可爱的黄家老二直呼“黄老头”,同样,黄老头喜欢书在圈内也是人所共知。在他的住宅里,和卧室有一墙之隔的就是他的书房,连着书房的,则是他的画室。
画画的也是读书人
1985年,57岁的黄永厚来到了北京,当时没有条件,在朋友家串来串去。中间住了很多地方,也有过自己的房子,一居室。“当时书房起居室都在一起,画画也是,那就让我感到很美妙了。”后来条件好一些之后,黄永厚在通州潞河医院附近买了自己的房子,85平米,起居室、客厅、书房终于分了家。在那里住了五六年,才搬到了现在住的地方。
“我其实没有多少书,线装书更是没有。我在《瞭望》上画聊斋的时候,陈四益的一个老师问我,画聊斋用的什么本子?哎呀,这让我惭愧的不得了,我说:“什么本子?不加注不断句的版本我都不会看。‘后来陈四益的老师送了我一套线装书,他说是最好的《聊斋》版本。我读书,没有那么大的本事,一般都读选本。比较全的是那套唐宋元明清的历代笔记,过去我隔壁的邻居送我的。他是研究经济的,那一次,我第一次从他那里借了一套诺斯写的经济学著作。黄永玉看了说,你一天到晚都看什么?你又不懂。我说正因为不懂我才看,懂了我还读它干什么?”

黄永厚先生画作《桃源难觅》
“我读书不是读给别人看的,我是给自己读的。”这个老头的叙述其实充满了陷阱,他自己说书少,读书也少。但是看看他的书架,虽然没有珍本奇本,但是从政治学到经济学,乃至当今文化领域内每一本受到关注的书,都在其中。随手抽出一本,从头到尾,朱笔勾勾划划,写满蝇头小字,都是老爷子的读书心得。当今号称读书人的人不可谓不多,但大多是为稻粮谋,“给自己读的”,可谓少之又少。单凭这份洒脱,就难得。老头是画画的,他读的这些书,让他的画与当今画坛的画风有了迥然不同的风格,他的画,字比画上的笔墨还多,密密麻麻,每一幅画都传达一个思想,每一个思想都与当下的问题息息相关。“我是画画的,也是个文化人嘛。要说画画的不是文化人,恐怕任何画家都不会高兴。但是自己有几滴几两墨水自己要清楚啊。如果我要在画里表达什么思想,要是说得不对,多丢人现眼。但是如果画山水,抄抄唐诗宋词不读书也没有关系,人家不读书也是应该的,因为要练笔墨嘛!”
“我的画人家挑剔笔墨我都不在乎,但是我为我能在画中表达清楚意思这一点很得意。”当年老爷子在上海虹桥公园办画展,一个苏州花鸟画家走过去问:“在画上写这么多字也叫中国画吗?”这事正好被写意大师朱屺瞻碰上了,他回答说:“是中国画,这种画上百年没人画了,要读很多书……”
曾为王小波大哭一场
“我第一次买书是小时候当兵的时候,是一本王云五的字典。当时花了很大的工夫去背字典。结果工夫都白花了,因为中国的汉字要成句才好记。后来部队到了广州,我买了大量的书,见到书就买。当时已经是解放军的天下了,我买了一本《马克思主义与文艺》,我几乎能背下来。”1954年,黄永厚到了中央工艺美院读书,那个时期黄永厚买的书也打上了当时时代的烙印。
“一到北京,我就买了一本余秋雨批判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书,还买了别林斯基选集,看了这些书,知道苏联有几个斯基都了不起。那时候我基本上就不买美术方面的书。这些书我一直保存到‘文革’,结果成了我的罪状。”黄永厚的罪状之一是说“洛蒙罗索夫是伟大的诗人。”黄永厚为此一头雾水:“洛蒙罗索夫是谁啊?我没有看过他的书啊!”一问才知道,洛蒙罗索夫是俄国的大化学家,批判黄永厚的那些人把洛蒙罗索夫和莱蒙托夫给弄混了。
1956年,从中央美院毕业之后,黄永厚到了广州。在那里,“我买了一套中学文学课文。从初中到高中,一直从诗经讲到鲁迅。

黄永厚先生作品
跟那套书配套的还有教师辅导材料,我同时看了下来,我的一点基础就从那套书来的。后来到了“文革”,流行的是北大五五级编的文学史。我认认真真地读了。我的文学观点,基本都是从那里来的。后来我又买到了《中国历代文论选》、《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我画《宋玉对楚襄王问》时用的典故,就是从这里面来的。别人都以为我写画跋不用思考,随手拈来,我说可没那本事,我都是现买现卖,读了之后有点感触,马上画出来。我不像别人,家学渊源、书香门第。但是我能活学活用,读了这个,能想到那个。我也不像别人一样,有个很大的文库,有需要,我就去买,我的书,都是这么一点点积累起来的。”
“我读书也跟风。钱钟书的《管锥编》,一出版我就买了,还画了很多画。王小波的书,也是一出来我就买了,买了很多套,送人。买王小波的书是因为在《东方》杂志上看到书的介绍,我马上就去买了,没多久,王小波去世了,我大哭了一场,虽然我不认识他。从图书馆偷过书“因为看书评买书,有时候还上当。”老头儿一说这个,我俩就大笑起来。有一次老爷子在报纸上看到一本书的介绍,老爷子立马打电话给我:“我看到一本好书,你帮我买一下。”我去书店按照老头儿说的版本找到了一本书,内容很差。
我很疑惑,老爷子怎么会看这样的书?给老爷子打电话汇报:“书买到了,哪天给您送过去。”老爷子兴冲冲地问:“怎么样?不错吧?”我不好扫老人的兴,我说:“回头您自己看。”等给老爷子送过去之后,老头儿一翻:“上当了。”这样的事,老头儿没少碰上。说买书,这算好玩的事儿之一。
“还有些好玩儿的。我说给你听听。“文革”后期,图书馆都关了。但是《论语》我就是那个时候读的。我给你看看,就是这本,中华书局版的。当时是用来批判孔子的。本来当时《论语》是属于封资修,不许读的。但是这是《〈论语〉批注》,可以放心大胆地读,观点我不去管它,只看内容,哈哈。《论语》之前我从来没有读过,真正下工夫就是在‘文革’期间,之后我的很多画都用到它。要问我画的是哪个版本的《论语》,就是这个。说好玩的事,这算一个。”“还有这本,汤因比的《历史研究》,是我从图书馆里偷出来的,哪个图书馆我不告诉你,人家会找我算账的。”老头儿说到这里又笑了,其实“文革”中的陈年旧事,谁也不会找他算账了。“那时候我在合肥工大教书,去图书馆,在那里发现了一本这样的书,我一看,很有意思。揣在我的衣服里就带出来了,那时候没人管的。”
大丈夫不从俗流
按说一个画家的书房,摆满的应该是艺术绘画类的书籍,但是环目望去,黄永厚的书房里这一类的书甚至不够书架的一个格子,都是他的画家朋友送的,稀稀疏疏地摆在那里。“那一类的书,不要看。现在的画家们作画、论评家评画,一讲我的老师是谁谁谁,这一笔像谁谁谁。’
“艺术是创作嘛,你看看李可染什么时候说过他的作品像谁?我最近看书看到天津的大冯给一个大画家提意见:你的画风总是那样。那个大画家说:我变了,人家就不认识我了。我敢说,你要是总是按照一个套路写东西你肯定会难过,但是画家不难过。那一类的书,我看它做什么?我画画也绝对不去借鉴他们,但是我是中国人,我就处在这样一个传统当中,一天到晚能不受到他们的影响吗?” 这是没有办法的事。”跟书架的那些书相比,黄永厚的书房根别人的不同之处是挂满了名人字画,刘海粟、范增、黄永玉、黄苗子等等。这样的书房,有点像样儿,也有点不像样儿,这种风格,正像刘海粟给黄永厚的一幅字上写的:大丈夫不从俗流。这个不从俗流的老头儿,把书房装在了他的脑子里,画入了他的画中。
原标题:91岁画家黄永厚辞世:所画如时评,不做旁观者
【免责声明】上游新闻客户端未标有“来源:上游新闻-重庆晨报”或“上游新闻LOGO、水印的文字、图片、音频视频等稿件均为转载稿。如转载稿涉及版权等问题,请与上游新闻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