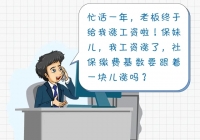“猪仔”契约华工一般指在国外从事体力劳动的中国人,是海外华侨的重要组成部分。清代华工出国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在鸦片战争前,主要是自愿结伙出洋谋生,大多分布在东南亚,人数较少;从鸦片战争到清末,几乎全是被西方殖民主义者拐掠、贩卖的契约华工,分布在世界各地。
19世纪去东南亚的华工,累计至少在七百万人以上,人数估计十倍于前一阶段。华工绝大多数是闽南人,也有少数粤东人。
华工出国的原因
福建和广东沿海地区,地狭人稠。破产的农村劳动力国内无处容身。而当时的南洋,地广人稀,土地肥沃,地下资源丰富。闽粤两省同南洋仅一水之隔,得“贸易风”之便,又有海外同族、同乡的招引,两省“过剩”人口便相继到南洋谋生。16、17世纪,西方殖民主义者相继侵入东南亚。他们为独占东南亚,不允许华人从事独立的经商活动,迫使华人只能充当中介商和开发其殖民地的劳工。随着殖民地的不断开发,去南洋的华工日益增多。
清代前期的南洋华工
清初已有大批华南沿海居民出国,以去爪哇岛各地的人数为最多。17世纪下半叶,爪哇岛上共有五万名中国人,绝大多数是体力劳动者。1710年,仅巴达维亚市(Batavia,今印度尼西亚雅加达)即有十万中国人。华工有自由雇工,也有由船户贩来的押身抵债者,名为“新唐”或“新客”(“新客”一词,1683年已在巴达维亚出现)。“新客”在偿债劳动中,对雇主有人身隶属关系。
1740年,荷兰殖民主义者为了消灭华人的经济优势,在巴达维亚曾屠杀华人一万多人。爪哇华工即转往苏门答腊、婆罗洲(今加里曼丹)和廖内群岛等地。他们或组成带有村社性质的劳动组合“公司”,向当地酋长交纳租税,领地采金,或从事农垦、捕鱼、放牧、种菜、种茶、伐木、造屋、造船和筑路等劳动。在西婆罗洲,这样的“公司”共有18个。著名的如东万律的“兰芳公司”(1777年成立),盛时有华工三四万人。
除组织生产外,还按天地会的模式组成自治、自卫的集体,名为“兰芳大总制”,公推罗芳伯为“大唐客长”,实行朴素的民主体制。“公司”成员曾发展到三十万人(包括当地居民)。荷兰殖民军曾多次袭击婆罗洲的“公司”,均被击退。1854年,大港等公司先后被荷兰殖民军消灭。1865年,“兰芳公司”亦被荷兰殖民当局撤销。
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英国为在马来亚进行殖民扩张,曾以授地招垦、贷款补助等诱饵,鼓励和罗致中国人前往开发。19世纪20年代,半岛西部各土邦的锡矿已有几万名华工。
槟城和新加坡的原始森林很快就被华工开辟无遗。随后转向半岛内陆柔佛、雪兰莪和霹雳等土邦。华工向当地苏丹纳租领地开发,称为“港主制”。他们在当地自建村镇,柔佛境内聚居达数千家,柔佛邦的二十九条河流的两岸,几乎全是华工开垦的种植园。海峡殖民地的三个港口(主要是新加坡)成为华工不断向半岛内陆推进的据点。
华工
从鸦片战争到清末,分布于世界各地的华工几乎全是被强迫签订契约的,通称为契约华工。主要分为欠债劳工和契约劳工两种。前者是同华人“客头”或包工头订约的债奴,后者是同白人雇主订约的契约奴隶。这两种契约华工可分为四种不同类型:
1)南洋的“猪仔”华工。
欠债劳工的一种。1800年槟城出现出售立约劳动一年的华工,售价由十至十五元增至三十元,称为“卖猪仔”。“卖猪仔”一词,在中国文献中最早见于道光七年(1827)刊行的张心泰著《粤游小志》。当时以新加坡和槟城为中心的“卖猪仔”活动便逐渐兴盛起来。
鸦片战争后,在槟城、新加坡、厦门、汕头、香港、澳门等地都设有专门拐贩、囚禁“猪仔”的客馆,俗称“猪仔馆”。各地“猪仔馆”关系密切,贿通官府,上下其手,迫害华工。
“卖猪仔”的利润丰厚,新加坡的售价常在百元以上,而成本不过二十元,华工本人所得不过十元,盈利由“猪仔”头和拐贩等层层分润。华工要为这笔身价付出为期三年的债奴劳动。“猪仔”有“新客”、“老客”之分。到年终结帐时积欠未清,只得续约,是为“新客”。还清了欠债的“猪仔”,如继续立约劳动,称为“老客”,每月可得工资五至六元。
从19世纪70年代起,英国和荷兰加强了对东南亚的经济扩张,南洋的“猪仔”迅猛增加,多数在马来半岛,一部分在苏门答腊的种植园和锡矿上劳动。从1800年到1914年英属马来联邦政府宣布废止“猪仔”制为止,入境华人累计近八百万人,其中“猪仔”至少占80%。南洋的“猪仔”大多数是从厦门、汕头和海南岛去的。在20世纪最初十年,去马来亚的“猪仔”年均二十万人,1913年达二十七万人。
从1864年起,荷属苏门答腊需要华工种植烟叶、开发锡矿,每年约自新加坡转贩一万六千名“猪仔”,引起英国殖民当局的干预。1877年,英殖民当局决定在新加坡设立华民政务公司,控制“猪仔”贩卖,减少中间环节,降低成本,同时防止荷属苏门答腊的转贩。
荷兰殖民当局不得不转向中国,从“猪仔”的源地汕头和香港直接设馆招募。汕头所设“元兴洋行”,专门拐贩“猪仔”供应苏门答腊岛,由德商好时洋行包揽承运。从1888年到1931年,共拐去三十多万人,连同过去从新加坡转贩的人数,共约六十万人。
拐去的“猪仔”主要用于扩大开发,但其中相当大的一部分是填补死去“猪仔”的空额。早期马来华工年均死亡率为50%。到20世纪20年代初,年均死亡率仍高达20%。苏门答腊岛东部地区“猪仔”年均死亡率为50%。无数的“猪仔”为这些殖民地的种植园、矿山及各项生产事业的开发和当地的经济繁荣付出了血汗和生命的代价。估计从1800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去东南亚的华工累计在一千万人以上。
2)拉丁美洲等地的契约苦力。
1838年英国废除了殖民地的奴隶制度,英属西印度群岛的甘蔗种植园因黑奴走散,劳动力短缺,生产陷于瘫痪,迫切需要引进外来劳工。这时的秘鲁和古巴也因英美大量投资开发,苦于廉价劳动力不足。
鸦片战争后,1846年,曾兼任葡萄牙、西班牙、荷兰驻厦门领事的英国的投机商德滴首先在厦门开设德记洋行,亦称卖人行,雇用几百名打手和拐子,用付给“人头钱”的办法收买歹徒拐来的苦力,把他们囚禁在巴拉坑 (Baracoon,葡语,即收容所),用暴力强迫他们签订到远洋劳动八年的卖身契约,并在苦力胸前打上烙印,以S、P、C三字分别代表去夏威夷、秘鲁和古巴,然后押送上船出国。
这种贩卖人口的勾当,暴利惊人,而且华工劳动效率又高,当时在英属圭亚那用五百名黑奴生产的糖,在古巴只需一百九十名契约苦力。一名黑奴的价格为一千元,而一名契约苦力才四百元。因此,英、葡、西等国的苦力贩子在汕头、澳门大肆掳掠华工。
从华南到拉丁美洲,需航行三个月至半年。在漫长的海途中,气候酷热,成百上千的苦力被锁禁底舱,生活条件极为恶劣,去古巴的苦力船海上死亡率曾高达45%。成为名副其实的“海上浮动地狱”。处于绝境的苦力,曾多次聚众暴动,从1847年到1872年,见于记载的这类事件共达五十二起,多数取得胜利,夺船返航。
当被镇压下去时,苦力往往采取破釜沉舟的办法,与敌人同归于尽。据估计,从1845年到1875年被掠贩到拉丁美洲和大洋洲的契约苦力不下五十万人。其中古巴和秘鲁分别为十四万三千和十二万人。绝大多数是从澳门掠去的。
古巴和秘鲁原来都是西班牙殖民地,以虐待华工著称于世。清政府在19世纪80年代,曾先后派陈兰彬和容闳分赴古巴和秘鲁进行调查。陈兰彬在名为《古巴华工事务各节》的报告中附有一千六百名苦力的控诉,详述苦力身受和目睹雇主残酷凌虐的事实。报告公布后,举世震惊,国际正义舆论曾痛加指责。
3)去美国的”赊单工”。
欠债劳工的一种。“赊单”,粤语,指赊欠船票。“赊单工”专指从香港贩往旧金山的欠债华工。
1849年,上海英商祥盛洋行掠买二百名契约苦力,装美国船“亚马森”号运往旧金山,每人的船票、伙食和杂费共一百二十五元,由祥盛垫付,签订契约到美做工,按月在工资内扣还。1850~1851年,香港开始拐贩欠债华工到旧金山。为了监督华工履行契约,收回垫款本息,安排华工劳动,在旧金山的广东各属同乡会(即会馆)很快成为联系业务、控制华工的机构。
“赊单工”几乎全是从香港输往美国的。拐匪以暴力强迫华工见官诳称“自愿”、“自费”出国,取得美国领事签证,打着“自由旅客”招牌,前往美国。1855年香港英国当局别有用心地炮制了一个“中国乘客法案”,装出要改善华工运输条件,实际从未付诸实施。
“赊单工”到达旧金山,先到会馆报到,随即在包工头带领和监督下,编队到指定工地劳动。美国雇主付给华工的工资,仅及白人工资的半数,而且全部交给会馆头人,头人除克扣和勒索垫款本息外,还从生活消费以及诱烟、诱赌等方面剥削华工。
19世纪中期,美国从事运载华工的航运业得到十倍的暴利。从香港到旧金山的航运成本每人只需五元,而票价却在五十元以上。专门载运华工的“太平洋邮船公司”,每年还从政府领取五百万美元的津贴。这家轮船公司同华商会馆订有口头协议,华工乘船回国,必须持有会馆的证明,否则不售船票。
华工从踏上美国国土之日起,就受到白人种族主义者的排斥和凌虐。西部各地排华风潮踵接,华工没有任何保障。美国修建从东到西、横贯美国全境的中央太平洋铁路时,因工程险阻,劳工短缺,曾同中国签订招募华工的条约。数以万计的华工在筑路中牺牲了生命,可是在这条对美国经济发展具有划时代作用的铁路建成后,庆祝通车典礼,却不让华工参加,并把他们全部解雇。事隔不久,由于遭到周期性的经济危机袭击,美国各地出现劳动力过剩,排华活动亦更加炽烈,屠杀、焚掠、殴辱和驱赶华工的惨案达二百余起。
1882年美国政府背信弃义宣布废约并严禁华工入境,去美国的“赊单工”就此结束。据估计,从1849~1882年,去美国的华工共约三十万人。他们对美国西部的繁荣,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4)“合法”招募的契约华工。
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英法联军攻占了广州。1859年,广州拐架苦力的暴行十分猖獗,激起群众自发惩治拐匪的行动。英占领军当局为控制局势,由占领军行政委员巴夏礼出面,向广东巡抚柏贵施加压力,迫使出示准许民人自愿出洋作工,到英国招工公所报名。第一批为圭亚那招去了契约华工三百人,每名成本(包括运费六十元)仅一百十七元,而当时加勒比海地区契约华工的售价为四百元,此举为种植园主省去八万五千元。这是所谓“合法化”招工的前奏。
1860年英法联军攻陷北京,迫签《北京条约》,强使清政府“同意”华人自愿出洋做工。但是自愿应募者寥寥无几。结果,招工馆还是用人头钱向拐匪收买苦力。从1860年到清末,英、法、西、美、秘、荷、德等国都曾先后同中国政府签订招工章程、条约,假“合法”招工之名,行“合法”掳掠之实,具体事例不胜枚举。
八国联军进犯北京之后,并不缺少劳动力的南非金矿财团亦趁机在华北招募廉价华工,因为这要比在当地招募黑人劳工合算得多。南非在华北招工的主要代理人是后来当上美国三十一届总统的胡佛。当时他在天津开平矿务局任工程师,汉名胡华。他在伦敦组织了一个空头的“中国工程矿务公司”同南非特兰士瓦矿业公会签订合同,取得包揽在华招工的专利权。所有联系招工的具体事务均由开平代办(此时开平已落到英国财团手里)。所谓代理招工,无非是假手洋行、买办、奸商、拐匪、人贩等层层立约,分途拐架,按期如数交人。这些招工人员取得天津关道“保工局”颁发的执照,深入内地,肆行掳掠,胡佛因此发了横财。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有二十多万华工被沙俄招往欧洲战区和西伯利亚森林等地,担负最粗重、最危险的工作。在赴欧途中和战地,一万多名华工在炮火中牺牲。沙俄以“待遇优厚”诳骗华工,实际上不仅不给工资,而且挨冻受饿。华工在一次反抗中打死镇压华工的七名俄兵。俄军派兵增援,把三百名起义华工全部枪杀。在西线俄军战场上死去的华工达七千人。十月革命爆发后,大批华工加入红军和城市赤卫队。
【免责声明】上游新闻客户端未标有“来源:上游新闻-重庆晨报”或“上游新闻LOGO、水印的文字、图片、音频视频等稿件均为转载稿。如转载稿涉及版权等问题,请与上游新闻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