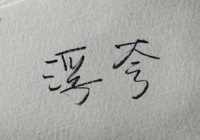拥有600万粉丝的三炮,是靠“土”和“叛逆”走红网络的。在激荡着乡村非主流风的配乐中,他和同伴戴着鲜艳的杀马特假发在村头尬舞,骑着改装过的家用摩托车在山路上翘车头,把柴房当KTV自嗨,在发廊用瓦刀染头发……
这些都是《叛逆少年》中的场景。一年多前,三炮开始在快手上发布这个用手机拍出的系列搞笑短片,很快,这个初中没毕业、曾在广东打工的农村青年,成了快手广西第二大网红。
在广西上林县塘红乡,他家贴着瓷砖的小楼快成了旅游景点。每到周末,总有十几岁的农村少年结伴骑着摩托车寻过来。有的希望三炮收自己为徒,有的追星般偷拍几张照片后悄悄溜走。一个贵州少年骑了50多天单车过来,只为瞧上一眼。
如今,和三炮一样放弃打工、返乡拍段子的年轻人越来越多。“打工是不可能打工的,这辈子都不可能打工的。”正如这个在快手上被翻拍了无数次的段子所喻示的,三炮和他在农村的追随者们都在渴求一种新的人生自由——不打工。

塘红乡F8合影
留守青年
6月的一天上午,三炮家的后院里,上万只蚕慵懒卧在层层叠叠的桑叶上,许久不见动弹。院外蝉鸣不已。
塘红乡车别庄仅剩的3个留在家乡的年轻人——《叛逆少年》里的三炮、表哥和疼叔,正在酣睡,网络的世界昼夜颠倒。
在现实中,他们是堂兄弟,一起长大,一起外出打工,如今一起在老家拍段子。有人戏称他们是“留守青年”。但和父辈共同生活的他们,更像活在另一个平行时空里。
三炮的父母早已出门采桑叶。儿子走红的网络世界,似乎与他们无关。街上每隔两天有集市,兜售簸箕之类的农具,买卖者几乎都是中老年人。
下午三四点,阳光不再那么刺眼,车别庄突然闹腾起来。
玩快手的年轻人醒了。公路上传来机车轰鸣声,同样留守塘红乡的蓝城、大表哥、小马林、大卫和阿蓝陆续到来。在一片片红色裸砖楼房中,三炮家的黄色小楼格外显眼,它是少数外墙贴了瓷砖、所有楼层都装了门窗的房子。方圆几十里,这是年轻人最密集的地方。
大家直呼网名,几乎全是95后,清一色穿网购的T恤衫,脚下是粘着泥的拖鞋。
客厅台式机35英寸的曲面屏亮了,大表哥坐在电脑前的转椅上,身体跟着音乐节拍摇晃,不时打着响指。
拍段子是一天中最重要的工作。想出搞笑的梗最难,灵感可能源自任何地方。听到一段魔性的音乐,想起电影中某段经典台词,或是瞥见门口快要散架的黑色28杠自行车、扔在院中一角的大红色编织袋……一个关于打工或返乡的段子就此诞生。
三炮坐在小板凳上沉思了一会儿,决定拍一个模仿《流星花园》F4耍酷的段子。他和表哥、小马林戴上拉直的斜刘海假发,大表哥套上暗红色西装,踩上7块钱一双的黄色塑料凉鞋。他们要扮演刚从广东打工归来、在村里风光无限的年轻人。
4个人拖着帆布拉杆箱,手插裤子口袋,一边沿着村口公路漫步,一边面无表情地望向跟拍的手机镜头。大表哥从西装口袋缓缓掏出一把塑料小梳,向上捋了捋头发,漫不经心地将梳子朝脑后一抛,留给镜头一个不羁的白眼。
在村口来回走了近10遍,三炮总算觉得“那种感觉到了”。拍完后,头发蓬乱的他坐在家门口垃圾堆旁的钢管上,低头用手机自带的软件剪辑视频。几年里,他用这个软件鼓捣出了上千个作品。
和其他人一样,初中没毕业的三炮说不出这个只有英文名的软件叫什么,只知道它的图标是一颗星星。
这个不到一分钟的段子最终在快手上收获了超过400万播放量,20万个赞。
有人称三炮是“快手周星驰”。对他拍的《叛逆少年》系列,有网友评价“笑得不能自理”“大片即视感”“演技比一些小鲜肉好多了”“拍摄和剪辑相当专业”。
“都是本色出演。”三炮笑了笑。这帮农村青年从未接受过任何专业的表演训练。在拍段子之前,他们在广东操作冲压机、做模具、打包装、炸鸡块、修车……
四五年前,他们从未想过,有一天,他们会成为网红。

酱爆出场时做出三指冲天的经典手势
自由之路
在《叛逆少年》中,几乎每个角色都个性鲜明。
三炮是穿着校服的初中生,呆傻木讷,总被人欺负;表哥是个护弟狂魔,老实中带点闷骚气质;大表哥是个非主流忧郁青年,经常陷入伤感回忆中;酱爆痞里痞气,天不怕地不怕,就怕阿妈打电话;小马林是车神,骑摩托车会翘头,每次出场都引发女生尖叫;疼叔则是当年叱咤塘红的老车神,如今退隐江湖,走村串户卖豆腐。
从广东打工归来的大表哥,带来了令人艳羡的“贵族气息”——他留着鲜红杀马特发型,穿着用别针拢住裤裆的西裤,身上挂着泛光的铁链,在村里坚持说普通话。他还使劲将两个表弟往时髦的路上推,带他们喝“不加奶的珍珠奶茶”,去乡里的野狼沙龙做头发。
一天,大表哥挥舞着铁链,教两个表弟“吸引异性的舞蹈”,蹲在树林中暗中观察的酱爆闪了出来。
他喊着周星驰电影中的经典台词登场:“在捏个moment,我酱爆感觉到,我要爆呃!”
“你是哪个厂的?”音乐骤停,身上满是水泥的大表哥扔掉铁链。
“天城五金厂,3号车间,580吨冲压机,操作员,酱爆呃!”身穿带毛领的天蓝色西装、留着紫色杀马特发型的酱爆缓缓仰起头,竖起大拇指、食指和小拇指。
“酱爆?!”三炮和表哥同时瞪大了眼。
天色渐暗,山间树林飘荡着黑黢黢的影。酱爆用三只手指伸进上衣口袋,夹出手机,搁在地上作舞台灯光。他走近大表哥,冷冷地说,“如果我没有猜错,你的口袋里还有半斤水泥。”
大表哥咬了咬嘴唇,狠狠地将口袋中的水泥一把把砸向地面,一场斗舞在尘土飞扬中开始。
莫名的台词、夸张的表演、怀旧的配乐,让这段农村尬舞极具魔幻现实色彩。很多人不知道,这段无厘头剧情并非完全虚构。

大表哥从广东打工归来
有一次直播,三炮做出酱爆三根指头冲天的经典手势,问他们,“这是什么意思?”
屏幕上弹出一条条“摇滚”“耍酷”等回答。三炮不断摇头。
这个手势源于真实的打工经历。
初二,三炮辍学了,他“也想出去打工”。
那些沾染了城市气息、衣着洋气,说话夹杂着普通话、给村里孩子买糖的打工者,对小山村的少年来说闪着奇异的光芒。村里老人种田一年的收入赶不上他们打工一个月。读小学时,三炮家还是土房子,有一次他洗澡时,整面墙“哐地”倒了下来。那时,他吃得最多的是猪油拌饭,很少见到肉。
出去打工意味着,有钱,能做自己想做的事。初中时,三炮迷上网络,QQ空间背景是一片黑,签名是无头无尾的句子,夹着符号堆砌的“火星文”。他的头发快到肩膀,斜刘海几乎遮住半边脸,自以为相当“飘逸”。但他最羡慕表哥的发型,后面不是塌下来的,而是向上飞起的爆炸头,三炮一直想弄个一样的,却苦于没钱烫发根。
蓝城是酱爆的扮演者,他比三炮高一届,少年时他迷上了音乐。在网吧一边打游戏,一边戴着大耳机听歌,当尖锐颤栗的电音、语速飞快的说唱从耳机中传出,他瞬间感觉电流击遍全身。
塘红乡没有KTV,蓝城和几个同学请病假跑去县城。几十公里的路,坑坑洼洼,他们骑着摩托车硬挺挺地驶过。唱歌的钱,是前一周吃泡面攒出来的。他喜欢点周杰伦的歌。唱完歌,几个男生挤在小宾馆30块一晚的房间里,第二天赶回学校。
初中两年,无心学习的三炮没买过一支笔,实在要写字就找同桌借。平时上课,他总趴在桌上睡觉。
初二下学期,三炮离开了学校,退学手续都没办。疼叔算是个循规蹈矩的学生,他原本想上高中,但中考分数还不到总分一半。家里供不起他读职校,只好放弃。在他的班上,仅仅两人升入了县城的普通高中。
大多数人选择辍学去广东打工。临近中考时,老师会苦口婆心地给学生打电话,劝他们回来参加中考。大卫回来拿了个初中毕业证,毕竟有些工厂招聘要求提高了。
真正进厂后,三炮才发现,靠打工通往自由,只是一个农村少年的幻梦。

疼叔的父母住在山上,每日放羊养猪
天城五金厂、冲压机和杀马特
三炮的工作是给产品打包装。每天工作11个小时,除了上厕所,一刻不能离开工位。他有点后悔辍学,“打工比上学辛苦得多”。
更难耐的是无聊和压抑。人成为机器的一部分,人类的肢体是它们延长的终端。每天,三炮的手重复着同一套动作,每过一小会儿,他就困得不行,头几乎要砸到桌上。
他开始学抽烟解闷。只有利用上厕所的5分钟,抽上一支烟,他才感觉自己获得了片刻的逃离。
蓝城去了老爸打工的厂,后来老爸在佛山办了个小作坊——天城五金厂。蓝城带着从前的同班同学大表哥,投向了这个日后蒙上神奇光晕的地方。
但在现实中的天城五金厂,工作庸常得几乎让人忘了自身的存在。车间生产锁具,比农村的厨房大不了多少。大表哥是冲压机操作员,每天重复三个动作上千次——左手将材料放入模具,右手调整,最后脚踩用两根手指踏板,几吨重的冲床哗地压下来,一个金属制品初步成型。
因为工作太无趣,蓝城在车间摆了个音箱,放DJ舞曲,他将音量开到最大,一边操作机器,一边摇晃身体。
一天,意外险些发生——大表哥差点没从机器里取出左手,一个指甲砰地断成两半。
小马林也差点因走神出事。他在另一家工厂操作机器,将标志印在产品包装上。有一次他没把产品放上去,把自个的手搁上去了,幸好是个小型机器,否则几根手指已经没了。
几年后拍《叛逆少年》,三炮没怎么想就设计出了冲压机操作员酱爆出场的标志性动作——三根竖起的手指。在他对工厂的记忆中,断指相当普遍,身边有朋友缺了好几根指头。
“很多人以为是很high的感觉,很酷,其实在厂里待过的人一眼就能看出来,我想表达的是手指被机器压断了。仔细看镜头,酱爆拿手机是用三根手指去夹的。”在直播间,三炮不停对粉丝强调,“在厂里上班的朋友们一定要小心啊!”
在工厂的压抑氛围中,蓝城见到了很多“杀马特”。他们非常在意外表,“想让别人觉得自己是最独特的”。这些年轻人穿着颜色鲜艳的西装,留着斜刘海和爆炸头,脚上是尖皮鞋,却做着“很脏很脏的工作”。
大家打招呼永远是同一句话:“你是哪个厂的?”比较工厂的大小、操作的机器、伙食有没有肉,成了这些打工青年虚荣心的膨化剂。
下了班,三炮认识了同乡的蓝城、小马林,一起玩摩托车,在水坝上翘头、飙车。
他们都自视“爱车如命”。摩托车是改装过的:卸了车头,这样玩翘头更轻便;加装了排气管,跑起来声音更响。塘红到佛山600公里,为了把摩托车从老家弄过来,他们冒雨骑了15个小时,期间还被警察逮住罚款。
镇上的杀马特们更浮夸,除了加装排气管,还在摩托车上缠着五颜六色的彩灯,连车轮的轴上都缠着。虽然车很拉风,但其实他们车技一般,三炮挺鄙视。《叛逆少年》中那辆缠满彩灯、贴着5块车牌、装着8根排气管的鬼火摩托车,就是为了嘲讽他们而设计的。
玩车久了,三炮开始渴望拍下和朋友玩车的日常。买一部拍视频效果不错的苹果手机,是他打工时最大的心愿。
刚来广东一年多时,他曾因买手机被骗过。那时他还是个木讷的“厂仔”,花300元在路边买了部“来路不明的苹果4S手机”。回宿舍后,他才发现手机开不了机。折腾了一周,他不肯放弃,将手机放在水里泡,用厂里的电容笔测试屏幕,用螺丝刀拧开后盖,直到他看到了一块黑乎乎的铁板,他才彻底醒悟——对方给他掉包成了模型机。
最终,即便厌倦了工厂,经常辞工的三炮入不敷出,他还是借钱买了部真正的苹果5S。他没想到,手机改变了他的命运。

三炮家的黄色小楼在塘红乡车别庄格外显眼
从打工者到网红
最初玩快手的时候,三炮没想过靠它挣钱。
刚开始只是下班后拍拍炫车技的场景,他们在佛山拍了一年多,目睹着快手从gif时代升级到短视频时代。
随着粉丝增加,广告商找上门来。都是几十块钱的小广告,让他们在视频下面贴上微商的联系方式,有祛痘的、有卖面膜的,展示3天就可以删掉。蓝城接过15元一条的广告,小马林甚至接过10元一条的。
这几个年轻人逐渐意识到,在这个新崛起的流量平台上,粉丝就是钱。
拍多了摩托车,担心粉丝审美疲劳,他们开始尝试加入一些搞笑的故事情节。最初没什么创意,几乎每个视频结尾,三炮总被一脚踹下水坝。
每次从水里爬起来,三炮都会头疼发晕,但他觉得,只要剧情需要,一切牺牲都是值得的。跳水的次数多了,他发现“涨粉很快”。
尽管拍段子挣的钱不多,难以维持生计,但这几个年轻人觉得比打工强多了。几乎每个人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关键是自由”。
在天城五金厂只干了几个月,蓝城就待不下去了。老爸每个月只给他发300元工资,这位创业者还是老一辈人的观念——“反正等我老了,我的钱都是你的钱”。另一点也让蓝城极不适应,晚上出去和朋友玩,老爸经常管着他。
他逃一般地离开父母。过年时亲戚们问他:“以后准备干什么,不可能老是打工吧?”
“我想当明星。”蓝城说。他想唱歌,想上电视。
“神经病。”亲戚瞪他。他们所谈论的“不打工”,是去学一门技术,以后在厂里不用打杂,而是当师傅。
家人送蓝城去学做模具,他学了几个月不干了;他跑去炸鸡汉堡店当厨师,用小本子偷偷记下配方和机器型号,为以后自己开店做准备;汉堡店倒闭后,他去加油站当服务生,白天拍视频,晚上上班;专心拍段子前,他终于自己开了家网店,做DIY手机美容。
2015年年底,蓝城和三炮、小马林回到老家过年。喧闹的时刻过去,年轻人几乎都走了,塘红乡恢复了平日的空寂,他们却留了下来。
“在外面生活成本太高,要租房要吃饭,在家管吃管住。”三炮决定在家拍段子,才18岁的他已欠下好几万元。
这几个年轻人戴上假发,演老头、演女人、演杀马特,在村里跳泥潭、骑摩托,拿着手机到处拍来拍去,几乎没人明白他们在干什么。
在小马林的爸妈眼里,他们就像疯子一样,既不种地也不出去打工,“整天依依妖妖的(广西方言,形容不正经)”。
他们开始在家拍段子时,表哥正在山上扛木头,一天挣108元;疼叔还在广东修车,晚上老板打电话随叫随到;阿蓝在工地上搬砖、开吊机,他觉得工地比流水线上有意思,无聊时至少还能玩玩泥巴。
三炮让他们也加入,可疼叔觉得三炮没干正经事儿——每天晚上不睡觉,成天捧着手机。
直到诧异地看着三炮一点点还清欠款,甚至手头变得宽裕,疼叔终于意识到,网络世界里或许藏着生活的另一种可能。
加入的人越来越多,他们的创作力变得惊人,每天能拍出六七个段子。几个人的想法一碰撞,一个点子就蹦出来了。
三炮的粉丝量快速涨到了100万,不过,之后的上升路又变得相当缓慢。
几乎所有主播都在拼命争夺有限的关注度。三炮目睹过各种噱头的炒作:刚开始流行约架,一言不合拍桌子,学社会大哥叫嚣“风里雨里,我在高速路口等你”。还有一段时间流行自虐,有人把头埋在沙坑里,有人鞭炮炸裤裆,还有些人“东吃西吃”,对着镜头面无表情地咬下老鼠的头,嚼碎,吞下。
在用户平均学历不超过高中、多半来自农村或三四线城市的快手平台上,人们能看到形形色色的农村主播。许多段子手给自己打上标签“全村人的希望”,评论区经常出现“不嫌弃农村的点赞”。
三炮很难说服自己去炒作,“附近很多人会看到自己的视频”。
在玩了3年快手后,他做出一个尝试,开始拍搞笑长视频。与小段子相比,长视频要求更强的编剧能力,但它更适合讲故事。
从一开始,三炮就想好了系列视频的主题。叛逆少年,就是他自己,也是千千万万的农村普通少年。
成为下一个三炮
事实证明,三炮选对了路。
为了拍出好段子,三炮习惯了晚上不睡觉,漫无目的地看视频、看电影,从中找灵感,学镜头的连接,周星驰有的电影他看了几十遍。一起做后期的大表哥积累了上百个歌单,精心挑选每一首配乐。有时为了实现画面需要的“五毛钱特效”,大表哥会用手指一根根在手机上画5个小时。
《叛逆少年》拍了一年多,长度加起来接近一部90分钟电影。三炮的粉丝量一年内翻了五六倍。那些炒作约架、自虐、喊麦的主播,几乎都已被快手平台封禁。
6月的一天下午,3个00后少年骑摩托车来到了三炮家门外。他们来自几十公里外的邻镇,穿着拖鞋,留着蘑菇头,怯生生地蹲在围栏外。
这是他们第三次来了。他们能脱口说出三炮家什么时候贴的瓷砖,也能一眼认出《叛逆少年》中每个角色对应的演员。
对这几个男孩来说,三炮是唯一的偶像,“喜欢他视频里那种感觉,那就是我的生活”。说起电视上那些影视明星,他们摇了摇头,“不喜欢,离自己太远了”。
3个男孩中,一个初二辍学,正在跟师傅学印刷,以后想开个打印店。另外两个还在读初三,一个打算毕业后去学理发,一个计划读职高。
他们也渴望像三炮一样拍段子,过上和父母不一样的生活,“以后不打工”。有一个男孩甚至给自己列出时间表,5年内要像三炮那样成功。
随着粉丝越来越多,三炮也开始注意对未成年人的影响。视频中出现飙车剧情,他会加上“经过加速处理,请勿模仿”的提示。在直播间,三炮经常强调未成年人禁止给他送礼物。看到疑似小孩给他刷礼物,他会问,“你是不是还没成年啊?你加我微信,我把钱退给你。”
高考前一天,三炮和伙伴们在山间公路上拍视频。明晃晃的太阳下,镜头里,他用不标准的普通话调侃道:“六月高考不努力,七月工地做兄dei啊,兄弟们,高考加油!”
三炮身上年少成名、摆脱打工的光环,除了吸引一大群农村少年,也吸引着其他尚未成名的段子手。
短短两周,三炮家来了几批外县的快手团队。他们大多一边做小生意,一边拍段子,“从小有当演员的梦想,虽然现实不允许,但至少能在快手上当当戏精”。
他们来三炮家观摩学习、一起拍段子,顺便涨涨粉丝。有人总结,三炮家门前简直是块宝地,无论在这里拍点什么,都有相当概率上热门。
三炮家成了车别庄最热闹的地方。三炮的姑姑喜欢来这里小坐,和陌生的客人们聊天。她记得,今年大年初五,三炮家的小楼里、院子中甚至围栏外都站满了年轻人。村里归来的打工者、广西几大有名的快手团队、慕名而来的粉丝们欢聚一堂,他们尽情地吃饭、喝酒、谈天说地。
那一刻,在人声鼎沸中,三炮的姑姑有种感觉,这个曾因外出打工冷清沉寂的村庄恢复了她童年时的那种生气。
就算网络消失了,也不可能再去打工
村民们逐渐习惯了这群举止怪异的年轻人。三炮周末去村小学拍片,一个六年级的女孩从虚掩的门缝中瞥见了他们,拽着妹妹飞快地跑来围观拍摄;她们的父亲也好奇地戴上了紫色杀马特假发,拿起手机自拍。
没人认为他们不务正业了。靠着拍段子挣的钱,年轻人都装修了老家的房子,给自己买了车,三炮还给父母换了辆面包车,方便他们去收桑叶。
可对这群段子手来说,不安的心态并没有消失。即便是家乡,一样的云,一样的天空,看久了还是会腻的。
“我们现在就是原地踏步。”蓝城有强烈的危机感。团队中最有主见的他,似乎预见,网络带给他们的东西终有一天会衰减、甚至消失。
无论儿子的收入如何增加,他们的父母都坚持和从前一样辛苦劳作,养蚕、放羊、养猪、跑三轮、开大巴车。在他们眼中,孩子依靠网络的生活根本不可持续。
为了抵御这种风险,年轻人也努力在现实世界中拥有谋生能力:蓝城在卖潮鞋,疼叔在卖黑头贴,三炮即将在县城开个奶茶店。他和朋友从网上买回一箱箱材料,每天跟着课程学习做奶茶。
和从前不同的是,他们希望未来依靠灵活的头脑谋生。疼叔很笃定,“就算网络消失了,我也不可能再去打工的。 ”
蓝城坚持要转型。他张罗着成立了工作室,他们将不再是一个松散的团队,而是一个有组织的公司,在利益分配上会有更具体的约定。
蓝城还看到,他们要摆脱角色的束缚。《叛逆少年》系列给他们带来了关注,却也让他们陷在固化的角色里。在粉丝心中,三炮似乎永远都是村里那个穿着校服的初中生,疼叔是戴着秃顶假发的老头,大表哥是红发杀马特。
看到他们过得比以前好了,总有粉丝评论,“你们飘了,不像农村人了。”
三炮恰恰感觉自己“拉了”,人气掉了。虽然粉丝数还在稳定上涨,但是播放量没达到他的期望值。与俊男靓女的主播相比,他直播时的打赏并不高。
有时他觉得自己“很土”。去南宁参加盛大的广西网红聚会,三炮穿着白色字母T恤就去了,疼叔甚至拖鞋都没换。站在舞台上,身着礼服裙的主持人介绍三炮是“广西知名农村段子手”,与其他网红相比,他显得拘束,没说几句话。
在塘红农村老家,他们平日更加随性。三炮会在地上找没抽完的烟头,点燃了继续抽。表哥会帮亲戚杀猪,疼叔会在朋友盖房子时拎灰递砖。拍完段子,想吃鱼了,几个人径直跳下蓝城家的泥塘。
从前他们并不在意自己土,快手粉丝正是喜欢他们的土气。可去往更开阔的平台时,他们开始对自己的形象感到不满。在新浪微博上,三炮只有10万粉丝,其他人只有几千粉丝,对他们来说,这个平台“太高大上了”。
几个月前,蓝城去掉了快手名中的“酱爆”,只剩下他真实姓名中的“蓝城”两字。他对粉丝宣告:“酱爆已经死了。”
为了学说唱,他开始用手机软件学英文单词。他嫌老家太闭塞,没几个人知道潮鞋,懂嘻哈,县城酒吧里放的音乐都是“土嗨”。他要努力变酷。
“不能老是绑在一个地方。” 蓝城说。
三炮也想过,“以后做大了可能去外面发展”。
去年冬天,几个年轻人头一回去了北京,头一回见到下雪。一家网络音乐制作公司邀请蓝城去录歌,机票住宿自理,发行后也没有收益。他毫不迟疑地接受了邀请,带上喜欢民谣的疼叔和以后想当DJ的大表哥。第一次坐飞机前,蓝城给自己买了2000元阿迪达斯的衣服和鞋。去了北京后,3个男孩挤在200多元一晚的快捷酒店里。
尽管录的歌不是自己喜欢的风格,但蓝城觉得至少离梦想近了一步。封面图片中的他们,搭配的不再是杀马特假发、凉鞋和摩托车,而是吉他、鸭舌帽和格子衬衫。
许多粉丝并不适应这种变化,感叹“贵族气质消失了”。从打工者到农村段子手,再到网络歌手,蓝城还渴望去掉头衔中“网络”二字。他最新发行的说唱歌曲就叫《做自己》,歌里唱着:“人生只有一次,没重启,这次我想做自己。”
(部分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原标题:当网红,打工是不可能的
【免责声明】上游新闻客户端未标有“来源:上游新闻-重庆晨报”或“上游新闻LOGO、水印的文字、图片、音频视频等稿件均为转载稿。如转载稿涉及版权等问题,请与上游新闻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