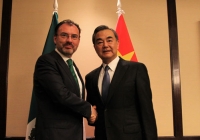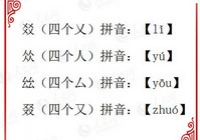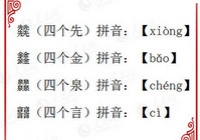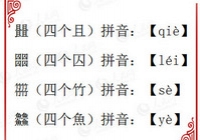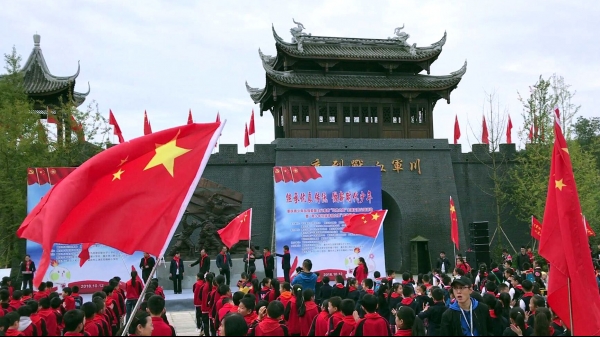△小苇在老茶馆阳台上,下面是童家溪入江口和江岸湿地。
2012年,从日本千叶大学留学归国的环境设计学博士谷光灿女士(网名小苇),在重庆大学建筑城规学院任教,从事风景园林遗产保护的教学和研究。当她回到老家同兴古镇,坐在家里开的望江茶馆里,看到小时候清流映带的嘉陵江岸,垃圾围镇、苇丛凋敝,她坐不住了,发起了一场从捡垃圾开始的美岸湿地保护志愿者公益活动。这是一个古镇女儿的芳心,也是一位环境设计学者的行动。
九岁前
小苇父母开的老茶馆,坐落在同兴古镇老码头上。童家溪在茶馆护坡下面的湿地上划出一道新月弧形,汇入嘉陵江,把右岸当地人称青龙嘴的浅丘,切出一个漂亮的岬角,伸出江中,苇丛依依,绿得正好。最后一坡江边梯坎边缘刻有水位标志,最低刻到175就没有了,这个季节,河面还在175水位之下约10米开外。
我跟着小苇在镇中河街闲逛,路边的楼房上也刷着水位标志,最高标到197,那可能是1981年重庆百年一遇大洪水的记忆。我们右手边,江景透过破败的民居豁口和黄葛树枝桠,连绵不断。她指着一处老屋前的花说:“指甲花,9岁前我家门前的花坛里有一排。”
那个“9岁前的家”,有指甲花的家,对小苇影响深远。
她说:“2016年我还画过一幅画,名字叫《小苇九岁前的家》,画的山里头我妈妈原来小学那边的房子。最近几年,不知道是不是年龄渐长的原因,对逝去的,以及正在逝去的一切有特别想挽留的情绪。那天早上,突然就想起很早以前住过的家,禁不住眼泪往外流,立马掏出钢笔来画,那是九岁前的家,后来父母工作调动就离开那里了。但是我还是深深地怀念着它。待我几十年后再去寻找,却发现它已经不在,小聚落的格局没有了,我感到深深的失落。”
小苇他们搞环境设计的职业习惯,但凡碰到几间东倒西歪的民居,就称之为“聚落”。那么这个“九岁前的家”,有什么东西“聚落”在她心中呢?“我记得北面是盐婆婆的家。小的时候以为姓‘盐’,但是现在感觉可能是姓‘颜’或者是‘严’。她人很慈祥,我和妹妹总是去吃她家的饭,甚至吃猪儿的食,是那种小红薯,还蛮香蛮甜的。我记得我偷过盐婆婆柜子里的老首饰,很漂亮,从抽屉里拿出戴头上玩,玩玩就不见了,好可惜是不是?盐婆婆有一大架葡萄,我们也吃过许多许多。”
家的西面住着邻居孙孃孃,就不这么好耍了。“她是一个泼妇,横得不得了,大家都怕她。有一年,她耍起横来,一把抓起农药瓶子就喝,毫无悬念她死了。”
家里面最重要的东西,就是老爸的两个蜂箱。“我最喜欢看蜜蜂在太阳底下从蜂箱口爬进飞出。听说蜜蜂进出前要跳八字舞,我观察了很久,也没看到。蜂箱对面较矮的墙里,就是盐婆婆的猪圈,是茅草搭的房子。房子北面有棵树干很粗的树,好像是槐树,有一年蜂王爬出蜂箱来到树干上,旁边聚集了很多蜜蜂。”
那里没有童家溪,小苇只能在大木盆里洗澡。“妈妈的卷卷头淋雨打湿,她就在门口梳头;爸爸在饭桌那里教学生算术,我就用小黑板画仙女的画。记得常常晚上从外面看露天电影回来,我一躺上床就舒服地睡了,还记得满屋子都是来看黑白电视的邻居,还有爸爸弄来的一个很大很大的收音机。爸爸和朋友在最里面的房间里摇蜂蜜的样子,很好笑,他们都戴着绿纱帽子,我们却蹿来蹿去,蜜蜂并不蛰我们。蜂箱那个房间光线最好,父母给人介绍对象就安排在那里,我和妹妹偷偷跑去看那两个人正在交谈的样子。”
那个蜂箱房间,也是最黑离父母最远的房间。“小时候每次去那个房间,都好害怕,门口的灯绳,拉一下就跑,灯亮了好一阵才进去。所以那个时候好盼望长大,盼望能不怕黑,终于有一天我很欣慰自己长大了,因为再也不怕黑屋子了。可是现在,我是这么怀念童年,怀念那些干净的空气,清亮的水,纯真的心……”
老茶馆
刘禹芬老师可能是志愿者团队中小苇最贴身的助手,没办法,她就是小苇小时候烫过“卷卷头”、栽过指甲花的妈妈。她1971年调到童家溪镇教书,1984年又到同兴小学教书,大半生的活动轨迹,好像就是为了向现在这个同兴老茶馆靠近。他们家2002年盘下来这个茶馆,见证了同兴水运老码头最后的繁华。
她说:“当时我们这边和河对门都没搞开发,渡口还没拆,渡船划过去划过来。对面的人不过河到礼嘉赶场,要翻个坡,很高;过河到我们同兴赶场,一过河就是街,很方便,所以过来的人拥挤得不得了。渡口外面还有卖羊子卖猪的,我们茶馆是渡口打头第一家(下面也有一家,但是有时候没开),1、4、7赶场,人多了根本接待不了,晚上这里面都遭买菜的堆满了,早上又出去卖。有一回我买菜从那边坎上过来,脚板都没落地,踩都踩不下去,一路挤过来,相当于是遭抬过来的。”
这个码头最早的繁华,是因煤而起。小苇说:“这个茶馆有100多年啦,原来叫望江茶馆。我们老汉很喜欢这个茶馆,我小时候经常来这里喊他回去吃饭。河滩这一片原来都是栈房、钱庄,是比较繁盛的煤码头,那边磁器口是瓷器码头,这里是离中梁山最近的一个河湾,从中梁山过来的煤,很快就能到河边通过水运下走,这也是它形成一个繁盛码头的原因之一。”
“小时候河滩上芦苇很多,我们同兴小学还在河滩上野炊,直接舀河水来煮饭。于是我就给自己取了个网名叫小苇。”但2012年,小苇从日本留学回来,差点把老茶馆卖了。“刚开始有一个反复,旧地重游,觉得它有点破败,像这个镇一样,就想把它卖了。但后来又有些舍不得的东西,说不清楚,就觉得该做点事情来把它改变。”
捡垃圾
改变是从捡垃圾开始的。中国人传统上觉得好像河边就是垃圾站,几乎所有的乡土河边,都是垃圾成堆。小苇说:“习惯往自己外面扔,好像水一冲,就不关自己的事了,最先我做的事情就是想把我们茶馆下面的垃圾捡了,我一个人也捡不干净,想发动大家的力量。第一批人就是我的大学同事跟学生,还有朋友圈的一些朋友;我妈也喊了一些镇上的人,这是最初的骨架。”
垃圾捡起来,最先是收到街上的垃圾桶。“马上就被人说啦,清洁工有意见。我们就用双手提到镇上的大垃圾站去,就搁平了。这个码头是镇上的休闲之地,春天从上午起,夏天从傍晚起,人特别多,遛弯儿、游泳、消食。镇上新开了一个店子的包装袋,我在河滩上就看到了。到河边来耍的人,他不停地丢,你得不停地捡,还得不停地宣传。他还是慢慢就会被感染,现在好多了。”
芦苇也恢复起来了。“芦苇本来是不需要种的,但河边有些地,镇上有些人开垦来种菜,就把芦苇割了!这事本来是违法的,但是没有人管,也就无所谓啦。我去说,还被人扔过石头的,但扔我石头的人,后来也转变得很好啦。加上政府后来明令禁止,那些菜地全部都收了,芦苇也就长好了。”
小苇妈妈拿着老伴刚刚在茶馆画的一张画过来说:“现在就是原生态,任芦苇自己长,它不用施肥,自己长,到了明年端午节的时候,你来看,长得好得很。因为涨水之后,那个泥很肥沃,只要有根儿,它就长。芦苇多了,白鹤就来了。你看,老爷子刚刚画了一张白鹤,好好看!”
文/图上游新闻·重庆晨报记者 马拉
【免责声明】上游新闻客户端未标有“来源:上游新闻-重庆晨报”或“上游新闻LOGO、水印的文字、图片、音频视频等稿件均为转载稿。如转载稿涉及版权等问题,请与上游新闻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