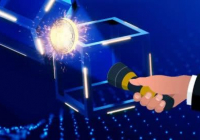很多人认为,重庆是一个很奇怪的地方:被四川、贵州、陕西、湖北、湖南这些白酒大省、强省围了一圈,自己却没有什么拿得出手的历史名酒。所以历来,重庆都被称为是中西部产酒区的白酒凹地。
于是,一些酒圈的朋友得出结论,重庆这地方,没有从历史中散发出来的浓郁酒香,所以开不出名酒的花朵。连很多重庆本土业界人士,也被误导了,悲观地以为,重庆酒史是一部苍白的历史。
但是,本文要告诉大家的是:重庆历史上不但出酒,而且在相当长时间内,重庆白酒的产量和品质在全川都名列第一。
重庆酒业的衰落,只是近年的事情。
01
最早的重庆酒
三峡博物馆里存有的先秦的重庆酒器,据说最早的是公元前841年,爵、卣、觚、尊等不同形制的都有。这个时代,已经是西周(前1046—前771年)后期了。
巴人和我们现代重庆人一样,也是移民迁徙过来的。巴人很像游牧民族,他们的巴国,就是一个不停迁徙的部落国家(严格地说,还不能称为国家)。殷周时期,巴人大约在汉水中上游和大巴山一带,经过上千年的播迁转移,转来转去,终于在春秋后期或者战国初期转到了现在的重庆及周边地区。
三峡博物馆里面的巴人酒器,在国内的早期酒器中,算是晚出的了。不过,重庆周边,尤其是从重庆境内的长江沿岸附近,很多新石器时期的遗址里面,出土了各种坛坛罐罐。如果这处遗址附近有个酒厂,你也大可说你家的酒早在新石器时代就有了,不信?有坛坛罐罐为证。天知道这些坛坛罐罐是干什么用的?说是用来盛酒的,也无法反驳——国内很多名酒,就是这样干的。
因此,不少文章这样论证:发现某处遗迹有坛坛罐罐,长得和后世的酒器有几分相似,就一口咬定这是酒器,然后推论说那个时候就已经出现酒了;甚至还有专家单凭有粮窖、有谷物出土,就铁口神断,认定有酒了——理由是,有了疑似酒器,或者有了酿酒原料,就一定会有酒。这样的专家逻辑十分强大。
其实,真要确认一个地方在某个时候开始产酒,应该用一个套装来证明:同时代的饮酒器、储酒器、酿酒器(发酵器、过滤器)成套出土。其实,这些新石器时代或者夏商时代的疑似酒器,大多是一种盛装液体的容器,除了可以盛酒,还可以盛兽乳、果汁、米浆、清水等等,没有配套的储酒、酿酒器皿出现,就不能确切证明酒的出现。
当然,三峡博物馆的周朝巴人酒器,那确实是酒器,因为这个时代,确确实实出现了酒。周朝,已经出现了为周王专门管理酒的官,叫“酒正”。酒正,负责掌管两件事:酒之政令管理和按标准培训酿酒员工。《周礼·天官·冢宰》:“酒正,掌酒之政令,以式法授酒材。”

在三峡地区发掘的古铜色觚
最早提到巴地一带产酒的书籍,是《华阳国志》。《华阳国志》里面有两处提到巴地的酒。一处是在一首诗里面:
川崖惟平,其稼多黍;
旨酒嘉谷,可以养父;
野为阜丘,彼稷多有;
嘉谷旨酒,可以养母。
很多酒文化专家据此认为,这首诗有明显的诗经小雅风格,它证明,巴地早在周朝就开始酿酒了。
《华阳国志》第二个关于巴地产酒的记录,是一个传说故事:秦昭王时期(前306—前251),在秦、巴、蜀、汉交界处——大约是现在的陕西南部和重庆东北部一带——出现虎患。其中有一头白虎尤其厉害,经常跟着一群老虎到处游荡。秦国高价募人杀虎。三位朐忍(现云阳)的巴人勇士以白竹弓射杀白虎——这个故事,《后汉书》里面也有记载,可信度较高——但是狡猾的秦人却欺负巴人勇士没有文化,舍不得兑现当初的承诺,只和朐忍一带的巴人部落签了个不平等条约,其中一条:“秦犯夷,输黄龙(当做珑)一双,夷犯秦,输清酒一钟。”
关于这个故事,史学家有多种解读,不过关于“清酒”一词,则基本上没有异议——这是巴地当时出产的一款好酒,名气都传到了秦国。
请大家注意一点,其时已是秦昭王时代。这时,巴国早已被秦昭王的老爸秦惠王派司马错灭了(《古文观止》从《战国策》一书摘录了《司马错论伐蜀》一文,讲的就是这次灭蜀兼灭巴的战役,事在公元前316年)。没有了巴国,被秦国改设巴郡的巴地,应该是秦国的属地了,为什么秦国还要和这些巴人立盟约?而且这种盟约,看上去更像是国与国之间的关系。
不过,不管怎么样,巴人那个时候出酒,而且出好酒,这是大概率事件。
清酒,在古代语境里面,就是好酒的代名词。那个时候酿酒,多以各种谷物为原料,且都是直接发酵。发酵后,原料和酒液混在一起,尤其有白色的淀粉物质和酒液混在一起,酒体发白浑浊,怎么都过滤不干净,所以劣酒就被称为浊酒或者白酒(这个白,指酒的颜色,和现在的白酒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好酒,则因为颜色清澈,被称为清酒。
巴人善酿酒,出产颜色透明的清酒,为秦人所喜欢,所以在盟约中就规定,如果巴人侵犯了秦人,也不要你们赔钱了,直接拿酒来。
这款让秦人垂涎的清酒,叫什么名字?用什么原料以什么方法酿造出来的?又是怎么达到清酒品质的?这些都无考。
02
巴乡清——西南最早的酒品牌
重庆这块土地上,最早留下名字的酒,叫巴乡清。为我们留下巴乡清记录的,有两本书。
一本是郦道元的《水经·江水注》,里面有这样一句:
江水又径鱼复县(即现在的奉节县)……有鱼复尉戍此。江之左岸有巴乡村,村人善酿,故俗称巴乡清。郡出名酒。
另一本书是西晋司马彪的《续汉书》,该书“郡国志”等八志被补入《后汉书》。“郡国志”里面,记载了东汉时期的地理分布,其中也有关于巴乡清的记录:“南山峡峡西八十里有巴乡村,善酿酒,故俗称巴乡村酒也”(转引自《重庆通史》第二章)——书里把巴乡清,叫做“巴乡村酒”。
前文记录的朐忍勇士射杀白虎,也发生在云阳。被秦国看上的清酒,也是来自于朐忍。朐忍,就是现在的云阳。
云阳的酒,不但从秦昭王时代到西晋,都赫赫有名,直到宋朝,也闻名遐迩。诗人范成大在《夔州竹枝词》中说:“云安酒浓曲米贱,家家扶得醉人归。”
在整个西南地区,经济最发达的是川西平原,这里有最早最完备的国家组织——历代蜀王朝。据扬雄《蜀王本纪》记载,整个传承次序是“蚕丛、柏濩(huò)、鱼凫、蒲泽、开明”。
西南地区最早的酒的记录,就出现在开明九世(约前436—前406)。《华阳国志》记载,“(开明九世)始立宗庙,以酒为醴”。任乃强教授认为是“改从汉语”,意思是以前是蜀语,现在用汉语“醴”来称呼酒。我认为这种解释不一定确切。
《礼记》等书均记载,醴是酒的一种。《尚书·说命下》:“若作酒醴,尔惟曲糵。”明人宋应星《天工开物·卷下》:“古来曲造酒,糵造醴。后世厌醴味薄,遂至失传。”曲是酒曲,糵是霉化的谷芽,二者都可以酿酒,区别是:酒曲的发酵力强,可以酿出度数稍微高一点的酒,而糵的发酵力很弱,只能酿出酒气淡薄的醴。
汉代以后,就没有醴的记录了。有专家说,醴就是现在的醪糟或者啤酒。可惜,专家又错了。醪糟其实也是酒曲所酿,啤酒则是直接用麦芽本身发酵酿造,而醴不同于此两者,是用带有霉菌的谷芽(麦芽、稻米芽等)作为酒化媒介,以谷物酿成。

在商周时代,醴通礼,主要用于祭祀。
开明王朝“以酒为醴”,其本意,应是他们没有酿醴的技术,而是把酒作为醴来使用,用于宗庙祭祀。并非仅仅是一个名词翻译那么简单。
开明时期有酒,而且,一直到秦汉时期,蜀地都有酿酒的传统,规模还不小。成都及其附近,陆续出土了不少有酿酒、饮酒、卖酒场景的汉砖,但是,却没有从先秦直到汉唐一直传下来的名酒传承记录。
这和云阳的清酒完全不同。云阳的清酒,在秦昭王时期已经闻名,然后一代代传了下来,到东汉、西晋时期,以云阳巴乡村出的清酒最为有名,并有专属名称“巴乡清”或者“巴乡村酒”,已经形成了现代意义的品牌。
那么,什么是品牌呢?
品牌就是,某个产品用于区隔其他同类产品的专属名称。
从古籍上看,汉以前,没有查到中国酒业有单个产品的专属名称。汉代,典籍或者出土文物上,大量出现某类产品的类别名称。比如,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竹简有“米酒”字样,此外还有椒酒(花椒酒)、桂酒(桂皮酒,不是桂花酒)、柏酒(柏树叶酒)、菊花酒等特色酒。这些都不是品牌,而是品类名称。椒酒、桂酒这类酒,早在战国时期,就已经出现。
带有品牌性质的汉代名酒,则有“会稽稻米清”(《周礼注疏》卷五,东汉马融注)、宜城醪(《周礼·天官冢宰》东汉郑玄注有“泛泛然,如今之宜城醪矣”)等等。曹植《酒赋》也提到“宜城醪醴”和“苍梧缥清”。宜城醪,大约是一种近似醪糟的酒,酒和酒滓混在一起,而“缥清”,则是指清酒。西晋左思的《蜀都赋》里面,记录成都有“清醥”酒,缥清和清醥,都是一回事,指清酒这个种类,也不是品牌。
所以,我们完全可以说,巴乡清或者巴乡村酒,是整个西南地区的唯一一款从先秦一直传承到宋朝的名酒品牌。
这样的酒品牌,放眼全国也是极其稀少的。
03
唐宋时期的重庆酒
唐宋时期,是四川经济最为发达的两个朝代。经济强则酒业强,这期间,四川,尤其是川西成都一带,酒业进入了最发达的旺盛期,而重庆,则因地理位置偏僻,酒业明显不如成都一带。
唐宋二朝,重庆一带见诸记载的酒有:
云安曲米春 杜甫《拨闷》诗:闻道云安曲米春,才倾一盏即醺人。范成大也有《夔州竹枝词》记载曲米春酒,但是范成大在他的《石湖诗集》卷19《夔州纪事》中说:“云安曲米春自唐以来称之。今夔酒乃不佳。”——云安,即云阳县。这里的酿酒传统,从秦朝一直保持到唐宋。到宋朝,曲米春酒的品质已经不行了,后来,这款酒便从历史中消失了。
忠州引藤酒 即现在的咂酒,把酿酒的原料(米、麦、青稞、高粱等)放在坛中,加酒曲搅拌,然后密封发酵。成熟后,加开水或清水,以竹管插入吸饮。唐宋时,则是用一根中空的藤枝,插在酒坛中吸而饮之。白居易在忠州(现忠县)时,就喝过这款酒。他在忠州写过《春至》一诗,诗中有“闲拈蕉叶题诗咏,闷取藤枝引酒尝”的诗句。
唐朝忠州也有烧酒。白居易的《荔枝楼对酒》诗云:
荔枝新熟鸡冠色,
烧酒初开琥珀香。
欲摘一枝倾一盏,
西楼无客共谁尝?
这里需要再次强调一下,唐朝的烧酒和现在的烧酒是两回事。唐诗中,除了白居易写的忠州烧酒以外,还有晚唐诗人雍陶在《到成都后记途中经历》一诗中,有“自到成都烧酒熟”一句。很多人,据此得出唐朝已有高度蒸馏酒的结论。
但是,王赛时先生在其所著的《中国酒史》中,对此持异议。经考证,他认为,白居易和雍陶以及其他同时代诗人笔下的“烧酒”,其“烧”字,指的是“一种加热处理的工艺”,是为了防止酒内细菌生长的低温烧制灭菌法,类似近代西方传过来的“巴氏灭菌法”,即加热到60摄氏度左右,并保持一段时间,以此灭杀细菌。经过这种方法处理过的酒,就叫“烧酒”。
而今天的烧酒,则是蒸馏白酒的民间俗称,主要指高粱酒,在四川重庆一带,则指小曲高粱酒,这和唐朝烧酒根本是两个东西。
那么,唐朝成都、忠州一带的烧酒,又是用什么酿的呢?
那时的烧酒,其实就是普通的谷物发酵酒,一般是用糯米,也叫酿米(孙思邈《千金要方》卷36中有“酿米一斗,水七斗,好曲末二斗”的文字)、酒米。
把煮到不同程度的糯米、水、曲药,按照不同比例混在一起,放入一口瓮内,上面覆以苫布竹垫等密封。发酵期则长短不一,短的七八天,长的一个季节。比较差的浊酒,发酵时间就短,品质好的清酒,发酵时间就长。
为了避免酒发酸,古人可谓绞尽脑汁。发酵要结束时,往酒里撒石灰,中和酸度就是其中一个办法。
发酵成熟后,进入榨酒或者滤酒环节。
榨酒,就是把刚刚发酵成熟的酒糟,放入特制的槽床,压取酒液。李白有“吴姬压酒劝客尝”、罗隐有“夜槽压酒银船满”,此外很多诗人都有类似的描述。
滤酒,就是直接把酒糟放在竹编的过滤器里面,慢慢滴漏过滤。也可以先滴漏后压榨。经过压榨或过滤后的酒,就是生酒,可以喝了。不过这种酒容易坏,所以,聪明的唐人就想出了烧酒灭菌之法。
除了上述几款酒,宋人张能成的《酒名记》一书中,还记录了几款重庆的酒:
夔州:法醹、法酝
合州:金波、长春
当然,这本书里面还记录了同时期四川其他地方的名酒,如成都、梓州、果州、剑州、阆州、渠州、汉州的酒;同时还记录了全国很多地方的一大堆名酒。
不过夔州的这两种酒,我怀疑其实就是同一种酒的不同档次。《齐民要术》有“法酒”一章。法酒,就是按照官府规定的操作流程酿的酒,这酒谈不上很好,但是也不会很差,大约中规中矩。法酝,就是按照法酒的规范酿的酒,比较普通;法醹,应该就是比较好的酒了,醹者,酒体醇厚也。夔州这地方,当时是川东中心城市,所以出产按照官府规范操作的好酒。《酒名记》里面,还有叫法酒和法清的酒名,也有不少叫什么醹和什么酝的酒,想来其命名套路,和夔州的法醹、法酝差不多。
而合州的金波和长春,是宋朝比较常见的酒名。《酒名记》里面,就有7款叫金波的酒。
接下来,简单地回答两个问题。
一、为什么唐宋时期的重庆酒,远不如四川酒品种多、名气大?
二、为什么重庆酒集中在三峡一带,此外也就合川有两款?
首先,唐宋时期,巴蜀两地,蜀地经济远超重庆一带,当时的重庆,因为山高林密,舟楫不便,开发相当不够。纵观酒史,我们会发现,好酒、名酒多出于富人集中的区域或者商品的主要贸易流通区域。所以,巴蜀两地相比较,自然好酒名酒就多出在蜀地。
《宋会要辑稿·食货·酒曲杂录》记载,宋神宗熙宁十年(1077年)之前,四川酒务(相当于国营专酿专卖垄断机构)数量共417处,而整个夔州路仅在渝州、万州、忠州和大宁监4地设有7处酒务,简直微不足道。从课额(即规定的上交利税)看,渝州4处酒务,仅上交1736贯;万州1处酒务,上交1347贯;忠州1处酒务,也是上交1736贯;大宁监1处酒务,课额只有区区421贯。
而仅仅合州一个地方,就有9处酒务,课额高达80837贯,可见当时合州酒业相当发达。昌州(现荣昌、大足、永川一带)和渝州一样,有4处酒务,但是课额却高达10451贯。可见,当时的渝西和渝北酒业,明显比其他地方发达。
到熙宁十年,干脆把夔州路的酒务全部废掉,不再设酒务。后来时废时兴,总体上,重庆范围的酒业,除了奉节、云阳、合川、荣昌这一东一西,其他地方大多不怎么样。
第二个问题的答案也差不多,川东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长期在夔州(治所在现在的奉节),直到南宋末期,因为抗蒙战事的需要,先是把川东政治中心,再是把全川的政治中心,先后移驻重庆,这个时候起,重庆的地位才逐步提升。因此,川东的名酒,也就长期在奉节云阳一带,而合州(现合川)一带,地形相对平坦,易于发展农业,当时是川东地区仅次于夔州的经济文化次中心,所以,合川也有好酒出现。
和四川比较一下。熙宁十年前,夔州路7处酒务,岁课额总数仅5240贯,加上合州和昌州,20处酒务,也不过岁课96528贯。整个川峡四路,酒务多达417处,岁课220余万贯,包括合州昌州在内的现重庆境内,岁课额不到当时川峡四路总额的二十二分之一,差距非常之大。
为什么单独以熙宁十年为界?因为这一年四川发生了一件大事。过去四川内部主要以铁钱为主,这一年全部换为币值更高的铜钱(铜钱和铁钱的比率,大约为一比十,即一枚铜钱可换十枚铁钱)。同时,这一年干脆免掉了穷兮兮的夔州路的酒税。
到1130年,绵竹人张浚主政四川期间,重用善于理财的遂宁人赵开,以其担任负责全川财政管理的川陕随军转运使,在全川推出著名的“隔槽法”。
所谓隔槽法,就是政府不但垄断酒曲供应,还把所有的酿酒器具全部收归官有。酿酒之户自己带米去官府的官营酒厂酿酒,官府提供酒曲和酿酒器具。
凡一石米输钱三千,并头子费用二十二。其酿之多寡,惟钱是视,不限数也。
意思是,你拿一石米来,交酿酒费3000文,以及杂费22文,至于你要酿多少,随便!交钱就行。这个政策一下来,四川酒税立马达到有史以来最高点。
行隔槽法的当年(1130年),四川岁课增到690万缗(缗就是贯,值1000文),到宋孝宗(1163—1189)时,据《宋史·葛郏传(卷385)》记载,“通四川酒课遂至五百余万缗”。这期间,夔州路也实行了隔槽法,但是岁收只有42900缗,简直微不足道。所以,26年后(1156年),夔州路又废除了隔槽法,并取消酒禁和酒课。
04
高粱酒来了
中国酒的历史,从酿酒技艺角度,可分为两个阶段:发酵酒阶段和蒸馏酒阶段,也可以从原料角度,分为米酒(不是黄酒。早期米酒,还不能称为黄酒。即便到后期,黄酒也只是米酒的一个种类)时代和烧酒时代。
当然,在米酒阶段,也有葡萄酒等其他果酒出现,而在高粱酒阶段,亦有糟烧、麦烧等烧酒和黄酒、果酒等并存,但是,就整个中国的主体酒业而言,无疑是米酒(发酵酒)和高粱酒(蒸馏酒)分别主宰了两个时期。
关于蒸馏酒的起源,学界说法很多,有汉朝起源说、南北朝起源说、唐朝起源说、宋朝起源说、辽金起源说、元朝起源说等等,但多持元朝起源说。
其实,就算蒸馏酒在唐宋就有了,也一定是极其少量,没有流行。种种资料、典籍都表明,蒸馏酒并没有进入唐宋时期人们的日常饮酒清单,反之,从元以后,蒸馏酒大行其道,清朝开始进入第一个高峰期,1949年后进入第二个高峰期。
蒸馏酒,一开始的原料是黄酒、黄酒酒糟和米,然后高粱开始被使用,很快,高粱就取代糯米、大米,成为蒸馏酒的主体原料。
中国高粱,是一个很魔幻的物种。中国高粱的起源,存在多种说法。简言之,一说是外国传入,源头是东非,经中东、印度,于二三世纪时传入中国;二说是中国也是高粱的独立起源地之一,大量考古表明,至少5000多年前,中国就有高粱实物;三说是二者并存,外国传入的高粱和中国本土高粱同时并存。
高粱一词,最早在唐朝陆德明的《经典释文·尔雅》中出现,然后惊鸿一瞥,消失不见,直到元朝才再次现身。
中国古人称高粱,多使用“蜀黍”一词,而这个词, 则是在《齐民要术》最后一卷(卷10)中出现。这一卷主要记录各种奇闻,“聊以存其名目,记其怪异耳”,里面从《博物志》中转载了一句话:“地三年种蜀黍,其后七年多蛇”,这个很魔幻的记录,就是蜀黍的首次现身。这个蜀黍,就是高粱。
后面还有一个词,特别值得关注:巴禾。巴禾,也是高粱——“扬禾,……此中国巴禾——木稷也”。木稷,是高粱的古代别名。
我个人觉得高粱的“国外双起源说”比较靠谱。
按照这种理论,中国北方高粱,起源于非洲,其中一支从北方传入黄河流域。现在黄河流域一带还有“风落高粱”、“拟高粱”,就是其过渡形态,再逐步演化成中国高粱的北方种。
而另一支,则从西南进入中国,最早在四川、重庆一带种植,然后才扩展到西南为主的其他地方。
中国的北方和南方两种高粱,在其成分结构上,有着明显的不同,这也有力支撑了中国高粱的两个起源说。
从高粱的这两个名字:蜀黍、巴禾,可以恰恰看出和四川、重庆的联系。蜀、巴两字清晰地指出了源头。有的学者认为,蜀黍的蜀,古义是“高大”的意思,所以,蜀黍应该是“高大的黍”,也就是高粱。这种解释太牵强,为了证明高粱是纯种国产,非要绕这么大一个圈子,连古义都冒出来了,也真难为这些专家了。凭什么说“蜀黍”的蜀,不是应用更广泛的四川的蜀,偏要是几乎没有人使用的“高大”那个蜀?这种词义选择的理由是什么?显然,这更多的是一种臆断。
如果仅仅一个蜀黍,还可能有那么一点点歧义,那么巴禾一词和蜀黍同时被《齐民要术》在同一卷里先后记下来,就有更强的指向性——中国高粱,最早的栽种地之一就是巴蜀之地,而且巴蜀两处都有,所以既叫蜀黍,又叫巴禾。
蒸馏酒诞生于元末,理由很充分,逻辑也自洽。元末,突然出现很多关于蒸馏酒的记录,这些记录,彼此为证,清楚明白。最起码,从元末开始,中国蒸馏酒正式登上了老百姓的酒桌,并得到相当程度的推广。
元代,四川酒业并不发达,在全国属于落后省份。《元史·食货志》记录了元朝各地的酒课(即酒税收入),总数为47万锭(元制,50两为一锭),其中四川行省仅为7590锭20两,连总数的零头都不到,旁边的湖广行省是58000多锭,北边的陕西行省也有11000多锭。
和宋朝时期四川的酒业昌盛相比,简直是天上地下。其原因就是宋末元初,四川是宋元作战的主战场之一,蒙古人在四川大屠杀,全川被打得稀巴烂,民生凋敝,人口锐减,以至于四川经济在整个元朝都没有恢复元气,酒业当然也不例外。
明朝,是中国酒业大转型时代,各种蒸馏酒出现,高粱酒也开始正式登上舞台。
从宋末开始,重庆的政治地位在四川区域内上升明显。宋末,因宋元大战,重庆成为四川抗元指挥中心。到明朝中叶,重庆和成都、泸州一起,成为全国30多个主要城市之一。
据万历六年(1578年)统计,重庆府20个州县另5个土司的田赋粮额为34.5万石,占全川总额三分之一。而平原地带的成都府,31个州县仅16.6万石,连重庆的一半都不到。重庆已经成为全川经济最发达的地区。
但是,整个明朝,重庆没有名酒传承下来(全川同时期也没有全国性或者全川性名酒),连久负盛名的云安曲米酒也黯然消失。
明朝,除了洪武年间有过短暂禁酒,270年间,都彻底放开了酒禁,实行了和前朝完全不同的政策,即不再搞酒、曲的专营,而是只对酒、曲收税,交税就可以自由经营。重庆不少地方,都有上交酒税的记录,如《江津县志》记载,白沙镇在明朝嘉靖年间就有上交酒税。
明朝的发达经济圈,主要在京杭大运河两岸和两端,这个区域诞生了不少名酒。
明朝酒种的分布,大约是北方烧酒、南方黄酒。从明朝中叶开始,在整个北方,蒸馏酒开始替代黄酒成为主力酒种。明朝的蒸馏酒,还是糟烧、米烧为主,高粱大规模取代稻米,应该是清初。
李时珍《本草纲目·谷部》:
蜀黍,俗名蜀秫、芦穄、高粱,不甚经见,而今北方最多。……有二种:粘者可和糯秫酿酒、作饵,不粘者可以作糕煮粥……其谷壳浸水色红,可以红酒。
洪光住在《中国酿酒科技发展史》中据此推断:由此可见,高粱生产之发展始见于16世纪以后,产区南方少而北方多,始用高粱酿酒至晚已见于明朝。
事实上,元朝虽然也出现过高粱的记录(如《农书》),但是没有高粱可以酿酒的文字,可见,高粱至少在元朝,还没有成为酿酒原料。
当然,李时珍的这句话,也只表明,明朝使用糯米酿酒时,同时开始将高粱掺杂使用,然后,高粱才逐步独立出来,成为糯米的候补物。
05
烧酒时代,重庆称王
四川以及重庆民间,从清朝开始,一般用“烧酒”一词指代小曲高粱酒。大曲高粱酒,则一般统称大曲酒。大曲高粱酒,严格地说,发源于明末清初,兴起于清末民初,流行于抗战时期,极盛时代,则是1949年以后。
在1949年以前,整个重庆都是小曲高粱酒(烧酒)的天下,大曲酒,无论销量、受欢迎程度,都位列小曲高粱酒之下。
但是,大曲酒的出现,使中国蒸馏酒从单一口感的小曲高粱酒一统天下,有了向多种香型演进的基础,现在我们喝到的几乎所有香型(小曲清香型除外),都是在原始大曲酒基础上发展而来的。
经过明末清初的大混战、大屠杀,重庆、四川人口锐减,经济又一次倒退到零点。直到湖广填四川大移民的展开,再到乾隆中期,四川的人口、耕地、田赋才恢复到明朝万历年间的水平,酿酒业才开始复苏。
也就是这个时候,四川第一次出现了“大曲酒”的记载。乾隆时期的进士、罗江(现德阳罗江县)人李调元在其所编的《函海》中记载“绵竹清露,大曲酒是也”。
乾隆时期,也有关于重庆酒的记载。四川学政吴省钦于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曾到忠县,有诗:“巴人酒熟糟满罂,山荞畬粟皆酒兵”,意思是,忠州这地方的巴人,酒熟了,酒糟填满陶罐(罂即陶罐)——这显然描述的是咂酒,他感叹,这里山上的荞麦、火烧野田里的粟米,都可以酿酒。他还记录:“今忠人以杂粮治酒,酿成,(以藤管)置其中吸之,谓之咂酒”。
但是,重庆不只有咂酒,还有烧酒。
重庆江津那时就以烧酒闻名,还有移民因为酿酒发了大财。据江津《刘氏家谱》记载,他们的入川始祖刘秀标,祖籍广东兴宁,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年仅14岁就因家贫入川,寻找先行入川的兄长刘秀桂。刘秀标先到江津为人家放牛,存了一点钱就去永川寻兄。好不容易找到哥哥,哥哥却因当石匠受伤,正愁无钱医治。刘秀标把当了三年放牛娃存的4000文,全部用于给哥哥医病。钱用光了,两兄弟只好乞讨度日。吉人自有天相,这一日,正在乞讨的刘秀标被一个前来探亲的远房亲戚发现,亲戚当即赠给他8000文钱,劝他们以此做点小生意。刘秀标就来到江津,和另一个同乡开起了槽坊酿酒,就此发了大财。
乾隆时期,江津白沙已经出现了槽坊街。白沙镇志记录,这条长约500米的街道上,几乎全是酿酒作坊。放眼整个四川,这条酿酒一条街,可以说是全川最早的“酿酒作坊产业园”。
川渝两地酒业的发达,与清朝的政策有关。历史资料显示,直到光绪三十年(1904年)以前,全川在整个清朝都不征酒税。《四川财政考·酒税考》记载:
川省初无酒税之法,酒类列入货厘增收。
指四川不单设酒税,而是把酒作为普通货物,只计征少量营业税。
有些地方会私下征收少量规钱,量都不大,所以酿酒贩酒有大利。这也是这期间四川酒业大发展的重要原因。
民国《新修合川志》卷5:
向产包谷、高粱两种,多用以煮酒。历无酒税……旧时惟秋成之日,汛署奉知州札,下乡查酢房烧烤,小有规费,约钱400文为止。后汛署裁革无此款。光绪三十年始有税,数不可考。
民国《南川县志》卷4“食货”:
(南川县)初无酒税。凶岁禁酒,捕厅查槽坊,例缴酿具,秋熟后解禁发还。
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袁世凯北洋练兵,为筹集军费,特在直隶开征酒税,税额为每百斤1600文,次年,根据朝廷统一部署,四川总督锡良仿袁世凯例,为练四川新军开征酒税。不过,四川开征的酒税比较低,高档酒(大曲酒、仿绍酒)每斤8文,每百斤才800文,烧酒等每斤4文,每百斤仅400文,而且,这笔税钱,还明文规定可以加到售价上去,对生产者基本上没有影响。酒税开征以后,最多的一年,收税90万两,而这之前,一年从酒业收取的税收(普通税)还不到2万两。
《光绪东华续录》记载:
查川省烟酒正厘,光绪二十四年解到司库者记银二万两。
请注意,这还是烟酒两项一共的厘金。
在加税以后,周询《蜀海丛谈》记载:
川省田膏土沃,民物殷富,出酒数多,槽坊到处皆是,私家烤酒尤众。……以江津、泸州、什邡、绵竹等处产酒之区,收数为最旺。每年全省收银约在九十万两上下……彼时川省每年应出酒在二万万斤以上,漏税者尚不在内也。
从这个数据可以看出,川省酒产量超过2亿斤,已居全国第一。
其实,锡良这次征税,清廷给四川下达的任务,只有50万两。没想到,四川只给一斤酒加4文到8文,比直隶的税率低得多,收的税却一不小心就差点比上级的要求翻了一番。只能说四川酒业太发达了。
清末这次征税,也为我们了解清末重庆酒业打开了一扇窗口,通过税额换算,我们发现:重庆江津的烧酒产量,居然全川第一,而且是长期第一。
民国《江津县志》卷5专门有“酒税”一节,据记录,光绪三十年所报税额为135000贯,次年确定为85000贯,按85000贯这个税额折算,当年江津全县产酒量高达1416万多斤(见《四川酒文化与社会经济研究》一书中《清代四川酿酒业的发展》一文。作者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李映发),位列全川第一。
槽坊数量也可佐证。民国《泸县志·食货》记载,泸县(辖区差不多即后来的泸州。清朝没有泸州,只有泸县,现在的泸州是1950年成立的)全县有600多户“白烧糟户”(即烧酒酿酒作坊),而民国《江津县志》卷12记载,江津仅白沙一个镇,就有300多槽坊,已经相当于全泸州的一半体量了。
以产酒著称的中江县,“县属城乡烧锅三百余座”(民国《中江县志·赋税》);酿酒业兴盛的渠县,“实有酢户六百八十余家”(见光绪三十二年六月二十八日《成都日报》);四川中部的富顺县,也有491家糟户(民国《富顺县志·食货·征権》)。
从前引的四川部分旧县志记录看,那时的泸州、绵竹等地,无论是酒坊数量,还是产酒量,都并不出色,宜宾的酿酒业更加落后。如渠县就有680多家酒坊,并不比泸县少。如果以县域为比较单位,重庆江津无论是酒坊数,还是产酒数,在相当长时间内都是全川第一。
据张学君(曾任四川省志编委会副总编、编审)研究,清末四川,各县的大酒坊,一年产量不过万斤左右,小酒坊则只有区区2000斤左右(见《四川酒文化与社会经济研究》一书中《清代四川酒业的几个问题》一文)。我们把江津的每个酒坊平均年产都设为上限1万斤,江津县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全县共产酒1416万斤,那么,此年度江津全县共有酒坊最少是1416个,或者相当多酒坊产量远不止1万斤。

泡粮工艺
小曲高粱酒(即现在的小曲清香型白酒),是中国蒸馏酒前期的主流产品。而且直到清末民初,小曲高粱酒都是重庆、四川市场上的主流产品。民国以前,重庆没有大曲酒的酿造记录,现在重庆的几乎所有大曲酒生产厂家,都是民国以后陆续从泸州等地引进的技术。所以,小曲高粱酒,实际上是重庆本土一直以来的强势传统酒种。
在小曲高粱酒时代,整个清朝,全川销售的白酒,超过95%都是小曲高粱酒——《四川商业志》说这个比例到民国时还不低于90%。而大曲酒,到清末都没有形成气候。
大曲高粱酒可能最早出现在明朝,清初开始受到部分人追捧。但是,大曲酒的前期发展非常缓慢,以泸州为例,民国元年(1912年)以前,泸县600多个酒坊,只有10个酒坊酿造大曲酒,窖池仅50口,年产量只有微不足道的240吨。而且大多数是在酿造小曲高粱酒的同时,顺带酿造一点大曲酒,真正专业只酿大曲酒的酒坊,只有两三家。这期间, 以江津白沙高粱酒为代表的重庆小曲高粱白酒,上销成都等地,下销宜昌、沙市,成为当时的主力酒品。
江津高粱酒不但产量大,而且品质好。1909年出版的《成都通览》中,在记录川西部分县份的畅销产品时,都把“白沙烧酒”单独罗列上去。而且,和同时期其他城市的小曲高粱酒比较,白沙烧酒的售价明显要贵一个档次。其他地区的烧酒(小曲高粱酒)每斤售价40文左右,白沙烧酒售价则在50文以上。
06
重庆酒的巅峰时刻
抗战前,从1912年(民国元年)到1935年,由于军阀混战,军阀横征暴敛,川酒的出产量大幅下降。
据《四川省糖酒志·征求意见稿》记载,1938年全川29个税务所(分所)统计,这年全川酒产量152994124斤(一亿五千两百多万斤),比清末的2亿斤,下滑了30%左右。
这期间,川渝两地市场上的白酒,主体依然是小曲高粱酒(烧酒)。当时的川渝,一共有六个白酒核心产区,其总产量超过8000万斤,占全川总产量55%以上。其中,重庆—江津产区的酒产量达到2500万斤,内江—资中产区1500万斤、泸县—隆昌产区1300万斤、资阳—简阳产区1000万斤、万县—忠县产区934万斤、渠县—广安产区930万斤。
这六大核心产区,重庆占两个,而重庆—江津产区以2500万斤产量,位居全川首位,继续领跑全川酒类市场。
这个数据无疑颠覆了过去我们关于川酒发展历史的认识。过去我们长期认为,重庆酒在川酒中占比甚低,甚至微不足道,一谈到川酒,就是泸州、宜宾和绵竹三大产区。其实,如前所述,川酒(四川白酒)的发展,分为小曲和大曲两个阶段,在小曲高粱酒阶段,也就是民国期间(1949年以前),重庆酒才是川酒之王。
1949年以后,川渝两地在政府支持下,主营大曲高粱酒的国企越来越多、越来越大——如果我们仔细考察西南地区大曲酒的兴盛史,我们会发现,不管是茅台,还是五粮液、泸州老窖、剑南春等,都是在国营期间成为巨无霸的。在这样的背景下,小曲高粱酒逐步式微,也是可以理解的。
让我们继续回到1938年,把这一年重庆各地的酒产量列个表,考察一下那时重庆酒在川酒中的真实地位。

从上表可以很明显地看出,1938年,重庆7个税务所的酒产量占到全川29个税务所总产量的近三分之一,是当之无愧的全川第一。
而在重庆的4800万斤酒产量中,重庆—江津产区(2500万斤)又占了一半以上(民国时期的数据,有的还认为,单是江津酒就超过2000万斤)。而江津的酒产量,在清末就已经突破1400万斤,占了重庆—江津这个核心产区产量的一大半。
实际上,这个表显示的只是上税的数量,还有大量的民间私酿没有上税。据估计,这期间全川的酒产量不低于10万吨,重庆酒产量应该不低于3万吨。
民国时期,四川酒,包括重庆酒也有几起几落。
民国初年,军阀大战。尤其是1918—1935年期间的防区制,把全川各地分别划给各军阀,由其在辖区自收自支,给全川乃至重庆民间经济带来严重摧残。
由于酒税在各地税务收入中算是一个大类,各地军阀纷纷给酒业课以重税。这方面的记载史不绝书:
因受防区制之影响,白沙以产酒有名,遂为防军觊窥。烟酒税局,恒于重税之外,不时科以罚金,因此各槽坊有相继而倒闭者,有移往他埠以避苛税者,于是一落千丈。
民国十年,其存者八十余家,民国十七八年仅四十余家。(见《四川经济月刊》1936年第6卷6期,《成渝路沿线经济概观(6)江津》)
1933年,刘湘统一全川后,包括江津在内的重庆经济得到长足发展,被摧残的江津酒业开始恢复,并得到发展。其中,江津白沙的小曲高粱酒,名气非常大。就连涪陵“本地制酒,悉以包谷为原料,品质不良,且无大宗制造。故一般所需之饮酒,皆由江津输入。江津产酒,系以高粱蒸制者,品质甚佳”(平汉铁路经济调查组:《涪陵经济调查》,《平汉丛刊》第3种1937年版,第83页)。
为了保证酒的生产,白沙把周边的高粱都搜空了。据1938—1944年成渝沿线19县高粱产量统计,凡年产量9万石以上的,都是产酒大县。其中江津高粱产量最高,42万市石(1市石约合当时的156市斤),产酒2000万斤以上,泸县年产高粱30万石,产酒约1400万斤。
高粱为农人所极重视之农产物,每年出产,本镇约二万石以上,因水运之便利,上自朱家沱、松溉、石门等处,下游至油溪以上之货,均各集中于白沙。(《江津调查》,《四川经济月刊》1936年第6卷第6期,第17—18页)
到30年代中期:
(江津白沙烧酒)十分之八九俱运销远地,上至洪雅嘉定,下至涪丰忠万,以及嘉陵江上游之合川三汇,黔省之贵阳、赤水、桐梓、遵义,均撑出白沙烧酒之招牌,人争购之。(《江津调查》,《四川经济月刊》1936年)
1937年交通部邮政总局出版的《中国通邮地方物产志》(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中记录,江津白沙酒每年有230万斤运销贵州省。这说明,曾经凋敝的江津小曲高粱酒,又恢复甚至超过了清末的高峰产量。
尤其是抗战时期,整个四川酒业不但没有和其他经济产业一样受到很大的负面影响,反而得到长足发展。1944年,全川出酒量达到22万吨,不但达到1949年以前最高水平,而且这个纪录一直保持到1978年。
据四川省银行经济研究处1945年对成渝公路沿线1943、1944年白酒产量的研究结果(1945年5月公布,《成渝路区之经济地理与经济建设》,第66—67页,四川省档案馆藏),成渝沿线的16个县中,属于重庆的有巴县、江津、永川、荣昌、大足、璧山6个县。成渝沿线年产量超过1000万斤的有4个县,分别是:
江津(3200万斤)
巴县(1800万斤)
泸县(1400万斤)
永川(1300万斤)
其中3个县都是重庆辖区——这有力证明了重庆曾经在四川酒业中的龙头地位。
不过这个研究,只计算了白酒。而江津当时还有广柑酒、柑橘酒和葡萄酒。1942年,只刘有光的“利农农产贮造股份有限公司”就生产广柑酒5万瓶,在接待来华访问的美国副总统华莱士时,这款广柑酒被作为接待用酒,受到华莱士的好评。
这个发展,一个重要的原因是酒业的近代化进程。尤其是重庆,拥有西南第一的金融资本、盐业资本和商业资本,这三大资本在抗战期间进军酒业。
以1940年成立的重庆大川酒行股份有限公司为例,这家公司的发起股东,除了少量酒业从业者,大部分是商业资本家、金融资本家和盐业资本家,在他们的雄厚资本介入下,大川酒行很快就打进成都市场,成为仅次于允丰正的黄酒生产商。
在重庆,因大量外地人口涌进,白酒销售也达到历史顶峰。泸州大曲酒年产量的一半被重庆市场消化,经销绵竹大曲的“恒泰丰”商行在邹容路开业,不到半年就享誉战时首都。绵竹大曲的生意,好到主动去报纸刊登“谢客”广告——请大家暂时不要来排队买酒了。同时实行“晚开门,早关门,价格略高”的销售策略。为了抢货,本地一些分销商甚至提前一年打款。
除了外地大曲酒畅销,本地酒也很受欢迎。
创始于1919年的渝北土沱酒,在北碚、渝北等地风靡一时,江津白沙酒则占据了重庆绝大多数餐馆。
四川老作家李华飞在《四川烹饪》杂志曾经有过一个名为“食客随笔”的系列文章,第五篇《郭老吃赊账》一文,称郭沫若抗战时期在国防部第三厅任职时,经常在旁边“星临轩”回民牛肉店吃牛肉,同时“外加二两白沙干酒”。在第七篇《烽火渝州话三店》中,记录了当时下半城大什字街口一家人称“毛帽子”的小店,李华飞时任《新民晚报》的副刊编辑,经常约三四朋友去这家小店饱口福。这家店的泡酒很有名,取名“越陈越香”。李华飞老人家写道:“河街毛宅后屋挖有5个坑,下置能容10斤的酒坛,灌满江津白沙干酒,用小纱布袋装着蜜金钱橘、冬瓜片、冰佛手,再将广柑皮去瓤,泡浮酒面,经半月掏出,香、甜、浅黄,入口韵味无穷,每晚仅售一坛。”
1938年重庆酒业同业公会统计,(重庆市)全市消耗干酒一项,每月在一千担以上,以重量记,平均共有十万余斤。……此外,曲酒消耗,每月也有数百缸。(1938年《四川月报》12卷5、6合期,第196页,《重庆酒业调查》)
从这个数据看,抗战初期的重庆主城,仅仅是酒业公会会员,每年销售小曲高粱酒(干酒)就达到近200万斤。
抗战胜利后,由于国民经济在内战时期的崩溃,重庆酒业受到严重冲击,酒企纷纷破产。整个四川酒产量,从1944年的22万吨高峰,到1949年,快速下滑到只有5万吨。
重庆酒业也受到巨大冲击,战乱后,1950年全年的产量也只有13811吨。
原标题:重庆酒曾经长期排在西南第一,这才是历史真相!
【免责声明】上游新闻客户端未标有“来源:上游新闻-重庆晨报”或“上游新闻LOGO、水印的文字、图片、音频视频等稿件均为转载稿。如转载稿涉及版权等问题,请与上游新闻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