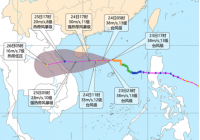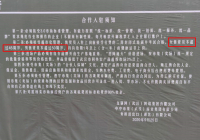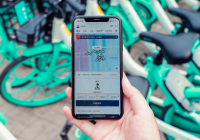1982年10月,老舍夫人胡絜青先生带着女儿舒济、女婿王端来到北碚,重访抗战时期的居所。按当时有关人员所指,走拢一看,连说不是。北碚区政府接待人员赶紧汇报,请来了区里的文史专家李萱华,马上落实。李萱华请胡絜青先生描述了老舍旧居的外形,相对位置,确定该在区委大院里,左找右找,用了两天,对了!区政协这栋小楼,完全符合。再请胡先生来看,连说:“就是这里!就是这里!你们看,这棵树也是当年那棵树!”这棵树有什么特点呢?树倒没啥特点,是棵普通的洋槐树,但种树的坑,其实是一个炸弹坑。

老舍在北碚寓所前
这里那时是北碚的中心,现在是北碚老城的中心,但在初建时,是郊区,北碚的新村。一位杨先生修的别墅小楼。从美国归来的林语堂到了北碚,那是1940年5月,正是轰炸期间,林语堂一家没住几天,就躲到缙云山石华寺去了。也是万幸,第三次轰炸时,小楼旁落下一棵炸弹,房屋小受损伤。林语堂也无心继续在北碚,甚至说在中国久待,立即安排再次出国,连刚买的别墅都来不及卖,干脆送人了!送给谁呢?一个组织,抗敌文协。
1938年在武汉,当时的全国军事政治文化中心,由数十个作家发起,成立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老舍被推举为常务理事兼总务主任,相当于秘书长。这个协会在1938年底也转移到了重庆。因为复旦迁到北碚东阳,逐渐的,在北碚有了30多个成员,于是1940年初成立文协北碚分会,办公处租在中山路上庐,没有会议室,显得很小气,林语堂就慷慨地雪中送炭了。
老舍1938年底来重庆,是到处飘起的,因为母亲年高,没能出逃,夫人胡絜青只得带着孩子,在北京照顾。老舍孤身一人,又有名气,哪点都可以住下,也哪点都在住,到过北碚很多次,但他主要住在陈家桥,冯玉祥的公馆,其实也就是一个农家小院。
1943年6月,老舍全家搬进了文协这栋小楼。当然,所谓全家也就一个人,所谓财产也就衣物。此前为指导文协工作,包括成立分会,与他人合作创作话剧,老舍来过多次北碚,也在这栋小楼住过。

老舍一家在北碚寓所前,男孩是舒乙
其实老舍到此,只是想暂时长住,写一部中篇小说,反映抗战的《火葬》,先是收不住笔,写成了长篇,又因吃的米太糟糕,患了盲肠炎。在江苏医学院附属医院做手术时,花了超长的时间,四个小时,按梁实秋的回忆,据赵清阁说,
其中找盲肠都花了一个多小时。因为老舍又患有胃下垂,盲肠被挤到左边了。术后老舍昏迷了10多个小时才醒来,还长时间发高烧,说胡话。在医院护理他的,是老向的夫人陈璧如和萧伯青,老舍昏迷中还一连串地喊出乌龟……等等奇怪的名词,不知道说的是什么。陈璧如回家向老向说后,老向就笑了,老舍喊的是小时候在北京读书时一些同学的外号。老向是比老舍低一年级的同学,所以知道。
老舍住了半个月的院,出来只能回到文协楼上休养,又来了重大消息:夫人胡絜青带着孩子到重庆了。原来,这年夏,老舍的母亲过世,胡絜青处理好后事,才带着三个孩子逃出北京,辗转曲折用了50多天,11月初才走到重庆。这个因战争分离六年的家庭在北碚团圆了,也真正是老舍一家定居北碚。
这里住着四户人,楼上有老舍,老向,萧伯青,楼下一大间会议室,是文协分会正式的办公处,一间独屋,住着萧亦五,“丘八作家”,他是一个伤兵,打日本时把右腿打断了,杵着双拐走路。
有了固定居所,老舍当然该是满意的,小洋楼,虽说遭受过炸弹威胁,但破损都已修复,连那弹坑,也将就种上一颗洋槐树,多舒适的环境!老舍在此,早起打太极拳,上午写作,中间翻扑克牌当休息。午饭后午睡,下午或写作,或访友,晚上则是与孩子们玩,甚至可以白天看了英文版小说,晚上就用北京话讲给朋友们听。
可是,浪漫总是那么容易被生活击败。
老舍没有固定收入,全凭稿费挣钱,胡絜青在北碚由梁实秋介绍进了教科书编委会,每月一石米,要养一家五口,后来还添了个老幺,那是多么艰难!
才经历了“大手术”的老舍,接下来得不到多少补充,还要坚持把《火葬》写完,所以老毛病贫血又犯了,时常头昏眼花,就干脆把自己的住房,就是楼上两间大屋,命名为头昏斋,发表于1944年初的杂文《假如我有一箱子画》的落款,就是北碚之头昏斋。这是因为胡絜青是齐白石的弟子,她到了重庆,便有传言,说她带了一大箱子齐白石的画,有几百幅之多,老舍发达了。这杂文既回击传言,又调侃自己,还可换点稿费改善生活,很不错!
但叫头昏斋只是一时兴起,对这栋小楼认识更深刻后,老舍用得最多的名字是多鼠斋。
当时这里只有两栋住房,很荒凉,蚊子多,青蛙多,老鼠更多,满楼乱窜,甚至不怕人,因此老舍命名为多鼠斋,老舍还写了一组12篇杂文《多鼠斋杂谈》在重庆《新民晚刊》“西方夜谈”上连续发表。这名字,没有一点雅意,所以难为人知。
其实,胡絜青是带了巨大的财富到北碚的,远远大于齐白石的几百幅画。
胡絜青到了北碚,前来慰问的人很多,胡絜青给他们细细讲北京的情形,老舍静静地在一旁听。《火葬》完稿后,老舍的酝酿也有了眉目,开始了《四世同堂》的创作。
《四世同堂》的主要情节和情感,均是来自于胡絜青的描述,这不是巨大的财富么?当然,这财富是属于中国。属于全世界的。
在北碚,在多鼠斋,老舍完成了《四世同堂》的前两部惶惑和偷生,1946年赴美国讲学,在美国完成了第三部饥荒。而胡絜青带着四个孩子,在北碚呆到了1950年才返回北京。

舒乙与李萱华在北碚老舍纪念馆
所以多鼠斋现在正式的名称是四世同堂纪念馆。
老舍的儿子舒乙有这样的回忆:
这里住着四户人,楼上有老舍,老向,萧伯青。楼下一间独屋,是萧亦五,他是一个伤兵,“丘八作家”,打日本时把右腿打断了,杵着双拐走路。他有一把从日军手里缴获的指挥刀。因为地方偏僻,晚上常有小偷光顾,一个响动,我们就喊有小偷,萧亦五听到,提着指挥刀,蹬蹬蹬地走出来追,他还没出门,小偷早已无影无踪了。这里热天时蛇也多,经常晚上摊在去厕所的路上,我们几姊妹上厕所,发现就喊叫,萧亦五又是提着指挥刀追出来。他是我们这家小人物的保护神。
老舍隔壁住着老向,老舍对老向并不喜欢,一屋两头坐,也很少到老向家去,可以说从没去过。有一次老向的岳父来了,老向总想把他撵起走,老舍知道后,到他家拍桌子打巴掌,狠狠骂了老向一顿。这算到过一次老向家。
当时北碚住着三老,老舍,老向,老谈(何容,又名谈易,故称老谈),都搞抗日通俗文学,很有成效。
我们一家到北碚后,生活很困难,老舍无职业,靠写作吃饭,母亲在国立编译馆工作,每月一石米。这米中多稗子,吃了不消化,很容易得盲肠炎,父亲和母亲都得过盲肠炎,父亲开刀,有胃下垂,身体很坏,腰伸不直,杵有手杖。他外出,母亲就派我在后跟着,国民党特务要抓他,如有意外,我就赶回家向母亲报告。他每天写作后,就要打太极拳。《火葬》和《四世同堂》就诞生于此。当时他很想念北京。我刚来北碚时,同他睡在一起,晚上喜欢撒尿,北京说撒尿叫尿泡。我晚上喊:“我要尿泡!”他听了感觉很亲切,连续多天碰着来人就说:“这小子很憨,晚上还要尿泡。”
在北碚期间,老舍戒了烟,戒了酒,连茶也终于戒了,都是因为养家需要用钱。只有肉不用戒,因为早就常常三月不知肉味了。经常有人来看他,这时那箱子衣服就起大作用了,每次来远客要吃饭,就翻一件衣服去卖。郭沫若,冯玉祥均来过。这里通向蔡锷路是一条羊肠小道,冯玉祥身高体胖,要两人扶着才能走下来。但孩子们最欢迎的还是冯玉祥来,因为他从不打空手,每次都要带点米面啥的来。
老舍在这里的照片还有两张,一张是在这门前照的全家福,另一张是他一个人靠在树边照的。这颗树是栽在1940年7月31日日本飞机轰炸这间屋的弹坑里的,是一颗洋槐树。
晚间休息时,就一块打纸牌,纸作的麻将牌,还很认真,经常输得哭。
1944年,日本人打到贵州,重庆很乱,萧伯青问老舍怎么办,老舍说北边那滚滚嘉陵江,就是我的归宿。后来他的死,就是这句话的延伸。
原标题:书说北碚:从头昏斋到多鼠斋,从林语堂到老舍
【免责声明】上游新闻客户端未标有“来源:上游新闻-重庆晨报”或“上游新闻LOGO、水印的文字、图片、音频视频等稿件均为转载稿。如转载稿涉及版权等问题,请与上游新闻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