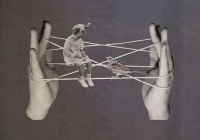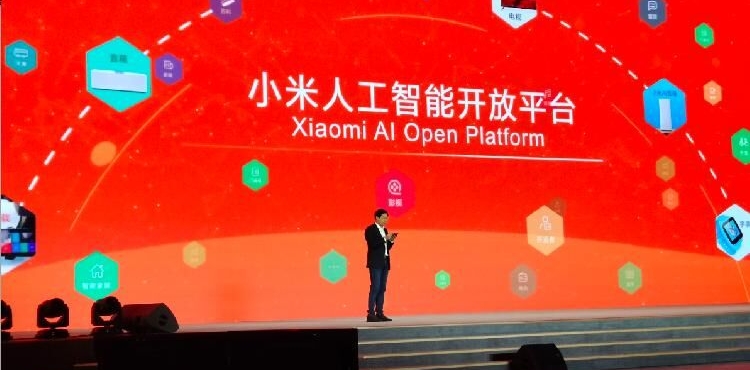刘慈欣认为,人类存在的意义在于向外拓展。人类应该不断地向宇宙深处扩张自己的生存空间,不断地向宇宙彰显自己的存在,这本身就是意义。我们如今却沉溺于信息技术的安乐窝中,变得越来越内向。
美国东部时间2018年11月8日晚,由亚瑟·克拉克基金会(Arthur C. Clarke Foundation)主办的2018年度克拉克奖颁奖仪式及晚宴,在美国华盛顿特区的西德尼·哈曼剧院(Sidney Harman Hall)举行,刘慈欣被授予了2018年度克拉克想象力服务社会奖(Clarke Award for Imagination in Service to Society),以表彰其在科幻小说创作领域做出的贡献。

刘慈欣领取克拉克奖后的演讲现场。
刘慈欣曾凭借科幻小说《三体》,成为第一个拿到“雨果奖”最佳长篇小说奖的亚洲作家。同年,《纽约客》专栏作家约瑟华·罗斯曼(Joshua Rothman)将刘慈欣誉为“中国的亚瑟·克拉克”。亚瑟·克拉克(1917-2008)是英国著名科幻作家和发明家,与艾萨克·阿西莫夫、罗伯特·海因莱并称为二十世纪三大科幻小说家。克拉克最知名的科幻小说作品是《2001太空漫游》,此书由著名导演斯坦利·库布里克于1968年拍摄成同名电影,并成为科幻电影经典。
作为刘慈欣访美行程的一部分,在领奖后的第二天晚上7点,刘慈欣在美国华盛顿特区的政治与散文(Politics and Prose)书店,和《华盛顿邮报》科幻小说书评编辑伊夫狄恩·梅森(Everdeen Mason)举行了对谈。伊夫狄恩·梅森本身是一个科幻迷,她每个月都会在《华盛顿邮报》的科幻专栏上,点评这个月新出的科幻小说。他们广泛地交流了对女性的看法、东西方的科幻小说的异同、科技与文学的关系还有对人类未来的看法。刘慈欣也透露了他对他笔下人物的看法,以及对人类沉溺于信息技术的担忧。
在刘慈欣的小说里,是男是女并不重要
刘慈欣对女性角色的描写,一直以来都会被女性主义者们诟病。比如《三体》系列里的女性角色就很脸谱化。故事会经常因为某些女性人物的“女性特质”,比如非理性、泛滥的爱心等而走向悲剧,反而男性角色则显得很理性,最后往往是男性英雄拯救了被女性毁灭的世界。伊夫狄恩·梅森就问刘慈欣,这是否意味着自己的一种女性观?

刘慈欣与伊夫狄恩·梅森在政治与散文书店的对谈现场,王玉琪摄。
刘慈欣则表示,其实自己根本就没有想过性别问题。他写小说的第一步,是先想象未来科学技术的样态,之后才能产生故事,最后才产生人物。他甚至认为,人物在小说中的地位并不重要,这在小说创作中可能不是一个很正确的做法,但在科幻小说中会比较常见。
比如《三体3:死神永生》中的程心,最初设定是男性,之后才改为女性。刘慈欣认为,其实男性和女性的行为方式并没有什么大的不同,在他的小说里,人物是男性还是女性,这并不重要。从科学的角度来看,男女并没有什么大的差别,如果有差别,也更多是后天的而非先天的。比如《球状闪电》里的女主人公林云,就非常积极进取,而不是被动的形象。
那么为什么在《球状闪电》中,要选择以陈博士的视角,来讲述女主角林云的故事呢?是不是意味着刘慈欣无法代入女性的视角?刘慈欣表示,这只是方便讲故事罢了。另外,林云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英雄人物,她有着很多性格缺陷,比如她痴迷于武器。从第三人称的角度来描写她,这会让这个人物显得更加客观可信。

《球状闪电》
作者: 刘慈欣
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5年6月
东西方的科幻小说有什么异同?
伊夫狄恩·梅森认为,最近中国有许多优秀的科幻作家涌现出来,比如郝景芳、韩松、宝树等。其中,刘慈欣在这个领域树立了榜样,功不可没。刘慈欣则认为,这本质上是一个文化话语权的问题。最近进入西方视野的新中国科幻小说,不一定是受他的小说刺激出来的,而是因为他的成功,中国科幻从而能够进入西方人的视野,受到了更多关注。因此许多优秀作者的作品,有机会被翻译成英语,从而被西方认识。
西方读者往往会关注中国科幻小说里的“中国性”,刘慈欣认为,其实中国和西方的科幻小说大同小异,科幻小说是跨国界的。科幻小说比其他的文学体裁,更容易能被不同国家、不同文化的人理解。因此我们经常能看到,在各国的科幻小说中,人类都经常作为一个整体出现。而且科幻小说的主题,也是全人类共同关心的主题,比如外星人入侵和乌托邦等。
当然,不同还是有的。因为美国科幻小说有比较浓的基督教文化背景,所以克隆人、人造生命等题材,在美国科幻小说中比较敏感。美国科幻作家和读者都会郑重其事地对待这些伦理议题。而在中国,这些有关于人造生命、克隆人的作品就不会显得那么重要。
中国的科幻小说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一些影响,比如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中国人会比较倾向于 “天人合一”,而不是像西方,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建立在对抗与征服上的。
刘慈欣举了他《流浪地球》的例子,这部小说被改编成了电影,并且即将上映。《流浪地球》主要讲述了一个在太阳发生灾变时,人类如何逃生的故事。如果这是西方人写的,人类肯定会倾向于坐着飞船逃生。但是在小说里,人类选择把整个地球推进到无垠的太空中,以这种方式逃离太阳系。这种选择或多或少地受到了中国文化的影响,这是一种人与家园、与大地无法割舍的情结。

电影《流浪地球》剧照
科幻小说里的文学性和科学性,孰轻孰重?
科幻是科学和文学的结合,但是读者往往关注的是科学幻想的那部分,那么小说的文学性到底在科幻小说里有多重要呢?刘慈欣透露道,说到了文学,俄罗斯文学影响他最深,尤其是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排在第二位是科幻作家亚瑟·克拉克,第三位是写《一九八四》的乔治·奥威尔。不过,刘慈欣表示,其实自己不是因为热爱文学才写作的,而是因为热爱科学幻想才写作的,科幻小说中的文学性并不重要。
因为令刘慈欣沉迷的是科学幻想,所以他在写作时,对笔下的人物并没有代入感,也没有特别喜欢的角色。他认为,人物在小说只是符号,比如程心只是一个象征着正义的符号而已。刘慈欣表示,自己虽然说不上来喜欢哪个角色,但是可以明确地说出讨厌谁。林云就是刘慈欣不喜欢的角色,因为她的侵略性太强了;章北海也是一个令刘慈欣恐怖的角色,因为章北海会为了达到目的而不择手段。有读者可能会喜欢章北海,误认为刘慈欣也喜欢他,甚至推崇他这种做事方式,但其实并不是这样的。
谈到科学,刘慈欣则显示出了巨大的热情。他在自己的作品中会试图去表达,人类在面临宇宙的浩渺时,一种类似宗教般的敬畏。他认为,这种宗教般的敬畏感是科幻小说的核心精神。因为像物理学,本身就蕴含着巨大的想象力,令他痴迷和敬畏。他说:“物理学本身就是一部科幻小说,只不过物理学的想象力是通过方程式表达的”。刘慈欣所做的只是抽取物理学中的一部分,构造出能被广大读者理解的故事。
比如,在《球状闪电》小说中,球状闪电被解释为像西瓜一样大的基本粒子,在宏观上呈现量子行为。其实这种解释不是接近真实情况的,但是,把这种解释写进小说是很有意义的。因为小说把量子力学这种微观的东西宏观化了,能让读者更真切地感受到物理学这种疯狂的想象力。
刘慈欣补充道,自己接下来想写一部和《三体》非常不同的作品。但是,由于现在科技已经越来越普遍、越来越失去神秘感了 ,写硬科幻小说,只会变得越来越难。
人类存在的意义在于向外拓展
科幻小说站在很高的位置去审视人性,关心全人类的命运。伊夫狄恩·梅森认为,在《三体》系列里面,刘慈欣似乎透露出对人性和人类命运的悲观看法,认为我们当下的人性注定会使我们的命运步入黑暗。
刘慈欣回应道,在自己大部分的作品里,其实人性在本质上并不黑暗。人性并不是永恒不变的,而是没有本质的,会随着自然和社会环境而变。在《三体》中,人性在面临灭顶之灾时,就会发生改变,如果拒绝改变,就会和环境产生冲突,这就会被环境淘汰。
所以,在未来,长期呆在太空的人类,会不会越来越不像地球上的人类?刘慈欣说,生物从海洋走向陆地后,陆地生物和海洋生物就变得完全不同。这同样会发生在人类进入太空之后。人的定义会随着科技的发展,和环境的变化而不断变化,而这种变化将会在接下来几十年里不断加速。
“这一点不管我们喜欢还是不喜欢,都一定会发生。”刘慈欣说,“我自己本来以为这种变化会发生在人类进行星际开拓的过程中。但现在看来,在人和机器在生理上不断地融合,人的定义就会发生变化。比如,手机已经成为人类的另一个器官了,只不过手机和人体暂时还没有生理上的连接而已。”

对谈现场的观众踊跃提问。
“人们可以天真地认为,自己能够坚守一种‘本真纯洁’的状态,但当‘人机结合’的时代真正到来时,这种坚守实际上是不可能的。这种改变是不可抗拒的。”刘慈欣补充道。
既然人性都是可以改变的,那么人类这种生物的存在的意义是什么呢?有什么价值是可以值得坚守的吗?刘慈欣则表示,生命到底是什么东西,这其实没有确切的答案。理查德·道金斯在《自私的基因》里说,生命只不过是基因的容器,这是一个让人绝望的定义,但这也是对的,不过在这个时代里,大多数人不能接受这个定义。
刘慈欣认为,人类存在的意义在于向外拓展。人类应该不断地向宇宙深处扩张自己的生存空间,不断地向宇宙彰显自己的存在,这本身就是意义。我们如今却沉溺于信息技术的安乐窝中,变得越来越内向。“这种内向发展到极致,世界就会变成这样一个图景:地球表面恢复了森林和草原,生命都很繁荣, 但是整个地球表面看不到一个人。同时,在某个地下室中,有一台超级电脑,在这台电脑里,生活着几百亿人,就像《黑客帝国》一样。这种图像一旦变成了现实,人类的生命将不具有任何意义。很不幸,人类正在朝着这个方向发展。”
刘慈欣认为,硅谷企业家埃隆·马斯克(Elon Musk)是人类的希望,这样的人越多越好。马斯克对星际空间的向往,以及把人类的存在扩展到其他星球的愿望,是人类很本源的欲望。但是,目前时代的主流还是在往内走,而不是向外扩张。刘慈欣认为,对星空和宇宙没有兴趣的文明,不会有长远的发展,不管他们在地球上多么繁荣。
当然,这种向外扩张是一种冒险。刘慈欣表示,不管在过去、现在还是将来,人类为了生存而牺牲自己是不可避免的。如果人类不去为了未来冒险,结果只是把更大的风险留给了子孙后代。人类的确很可能会在向外开拓的过程中死伤无数,但是如果不这么做,一旦地球发生了灭顶之灾,人类没有一个可以备份的世界,死的人只会更多。所以,探索和开拓过程中的牺牲,并不是人类可以选择的。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硕士生王玉琪提供现场速记整理,在此感谢。)
新京报记者 萧轶 实习记者 徐悦东
编辑 沈河西 校对 吴兴发
【免责声明】上游新闻客户端未标有“来源:上游新闻-重庆晨报”或“上游新闻LOGO、水印的文字、图片、音频视频等稿件均为转载稿。如转载稿涉及版权等问题,请与上游新闻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