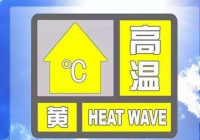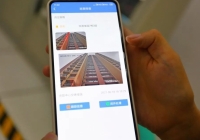在拉货三轮上入睡的农民工。(资料图片)视觉中国供图
中国青年报消息,困意随时会袭来,可能在吃饭时、上厕所时,甚至是跑步时。有人在梦境中把货车开进河沟,有人在车间突然睡着,被车床切掉手指。
能够调节睡眠和觉醒周期的下丘脑分泌素缺乏,是发生在身体内的第一个变化,接着,就像多米诺骨牌的倒下,他们的生活开始变得不受控制——白天会出现无法遏制的睡眠,晚上被接连不断的噩梦惊醒。
他们患上的疾病,被称为发作性睡病。目前人类已知的睡眠障碍疾病有90多种,发作性睡病是其中之一。和常人不同,他们只花几分钟甚至几秒就能入睡,入睡后也并非先出现非梦境睡眠、再出现梦境睡眠,而是从清醒直接跳进梦里。有人形容,白天“秒睡”时像“感官自动关机”,有人形容自己无意识的状态“像僵尸”。有时梦境就是上一秒真实环境的延伸,噩梦异常真实,是摸得着的恐怖。
把他们猛然淹没的困意,平均每三四个小时就会出现一次。到了晚上,噩梦和尖叫、冷汗、泪水一起到来,有时浑身无法动弹,“身体和心脏都像被湿毛巾裹住”。有些学生会在考试前的晚上吃安眠药,白天吃兴奋剂。
目前尚无关于发作性睡病权威的全球统计数据,据美国一个发作性睡病公益组织推算,全球约有300万人被这一无法根治、病因不明的睡眠障碍困扰。按照0.02%的人群发病率计算,我国约有70万患者,但目前只有不到5000人确诊,患者多出现日间嗜睡、睡眠瘫痪、睡眠幻觉、猝倒发作这四种典型症状。
由于睡眠质量差,患者往往需要把更多时间花在睡觉上。一位高三的患者说,同学每晚都学到凌晨一两点,而她只能晚上11点准时在焦虑中爬上床。午饭结束,一位推销员在同事都对着电脑冲业绩时,不得不趴在桌上睡午觉,否则下午会在老板眼前不受控地垂下脑袋。
他们有时会被贴上“懒惰”“不思进取”的标签。鲜有人知道,是“爱睡觉”这种病让他们失去了努力的机会。一位患者这样总结:“得了富贵病,没有富贵命。”有人把自己比作动画片里想学学不好、做事老出丑、被朋友欺负、被母亲责骂的大雄,“我就是大雄,但是我没有哆啦A梦,也没有静香。”
崩塌
困意袭来时,和身体本能斗争的痛苦常人难以理解。发作性睡病患者的主观体验和睡眠剥夺相似,一位父亲为了理解患病的儿子,曾经三天三夜不睡觉。接受中青报·中青网记者采访时他回忆,那时自己的意识“只能控制身体的20%”,走路无法走直线,分不清白天还是黑夜,“半边脸都被抽肿了还是迷糊的”。
中华医学会神经病学分会发布的《中国发作性睡病诊断与治疗指南》中提到,发作性睡病高发年龄段为8-12岁,它会让上一秒在课上积极回答问题的孩子,下一秒就鼾声大作。困意常在注意力高度集中时袭来,梦境比合眼到得还要早。
一位患者回忆自己上学时的无奈:一睁眼,黑板上的字全换了。为了保持清醒,他们在上课时“哪儿疼掐哪儿”,有人拿圆规把自己“扎成筛子”,有人用小夹子夹自己,醒来发现小拇指头都夹黑了。全都没用。
睡眠周期崩塌后,生活的不便接踵而至。出行是最容易发生尴尬的时候,乘公交地铁时,他们不敢坐下,害怕精神一放松,一不留神就会睡着坐过站。有男患者不小心倒在别人身上,直接被大嘴巴子呼醒;有人因为突然睡着手机一次次掉落,钢化膜摔碎了都懒得换新的。
睡眠与觉醒转换功能障碍诱发的猝倒也会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他们会在大笑、愤怒等情绪下出现局部骨骼肌无力,轻者面肌松弛,重者瘫倒在地。一位女患者在患病前爱美,爱开玩笑,“到哪儿都是中心”。现在她不敢走进人群,不再开心地大笑。有位母亲不敢抱女儿,怕一激动把孩子摔地上。害怕和女儿玩捉迷藏,“一开心就腿软,会在她面前倒下。”
多数患者习惯了独来独往。幼年患者在猝倒时会反复摸嘴唇、吐舌头、碾压手指,在学校里免不了成为异类。到了中学阶段,由于上课下课都在睡觉,他们很难有正常的社交。因为约会、打电话都会突然“消失”,有人在分手时被控诉最多的是“懒散”“没有责任心”。
一位患者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他曾在同事追问下说出犯困的原因,结果得到“看动物园里动物一样的眼神”。大部分时候,他们会用颈椎病、失眠、大脑供血不足中的任意一个遮掩过去。
从初中出现症状到现在,28岁的郑坤学会了闭嘴。领导总对他说,“像你这么大,我要打好几份工,根本没时间睡觉。态度不好就滚蛋。”刚毕业那会儿,他会直接说“老子不干了”。“现在不会了,工作不好找啊。”他只会低着头对老板说,“对对,我注意。”
注意也没用。患者白天必须定时小睡以维持清醒,但有次在外面跑业务,郑坤咬咬牙没午休。下午准备过马路的时候突然没了意识,耳边响起近在咫尺的刹车声,一抬头发现对面是红灯,自己站在马路中央。
他不会告诉朋友自己的病,因为这些年来,听他讲过的朋友眼里多是怀疑,嘴里多是羡慕。比起他,因为焦虑失眠的朋友能收获更多的同情。“别低头,皇冠会掉,别倾诉,朋友会笑。”他略带无奈地引用网上的段子。
患者们先迷失在比常人多几倍的梦里,再迷失在周围人的负面评价里,有人形容这个过程“像在无垠的雪地不停地往下陷落”。在知乎上,一个有关发作性睡病的问答下,最高赞留言写道:“这个病考验的是心理素质。”
弯路
如果无法确诊,患者将一直困在自我怀疑和自我责备中。22岁的周伟刚刚完成函授本科。他初中时发病,成绩从班里前十跌到倒数第十,没考上高中,上了中专。他在去年才确诊,“要是早知道这是病,早点吃上药,我可能现在就在大学校园里了。”
《中国发作性睡病诊断与治疗指南》中的统计数据显示,发作性睡病发病到确诊要2-10年。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睡眠中心主任韩芳见过太多被误诊的患者。除睡眠专科医生之外,其他科室的医生缺乏相关专业培训,难以在早期确诊这一罕见疾病。
很多人之前做过脑电波检查、血液检查、腿部肌肉测试、人格测试等“从头到脚”的检查,但被判断为一切正常。由于猝倒时产生局部肌无力,有人入睡前总出现恐怖幻觉,癫痫、抑郁症、精神分裂症也常见于部分患者早期的诊断中。
一位52岁的患者被当成抑郁症治了6年,吃了10多种药,去年一次体检,查出肝功能5项不合格,医生说是药物中毒。但因为剂量吃得大,已经形成药物依赖,“不吃就走不动路”,她只能加上护肝的药一起吃。直到在电视上看到有关发作性睡病的新闻,才决定去睡眠科做个检查。做完多导睡眠监测和多次小睡潜伏期试验,她被确诊为发作性睡病。
地方医院对发作性睡病诊断率较低,大部分患者都是通过查找资料“自我诊断”。一位高中生发现自己上课下课都会困,喝风油精也没用,上网一查,心里隐约觉得是发作性睡病。但县里医院说是抑郁症、市里医院说是癫痫,家人请的道士说她是被“附体”,一口“神水”喷在她脸上。她恳求家人带她到上海的大医院,“那是我最后一次机会”。在那里,她的判断被证实是对的。
有些人压抑了更久。一位母亲曾带着20多岁的儿子来找韩芳,儿子已经被当作精神分裂症治疗了5年。儿子心底一直不承认,但母亲不相信他的话。问诊时听见母亲说自己是精神分裂,堆积的愤怒突然爆发,抡着拳头就往母亲脑袋上砸。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门诊楼5层特需门诊前,家属们翻动着各种检测报告单和缴费单,腋下文件夹里厚厚一沓诊断结果记录着为孩子奔走的足迹。韩芳安抚过很多因为担心孩子学习焦头烂额的家属,“过分希望除根,渴望所谓特效药,容易被网上各种虚假信息欺骗。”有家长在10年里碰见不下10个骗子,“只要说能治好,我就去试。”
即便过了确诊这一关,治疗是患者面前的另一座大山。发作性睡病会终身伴随,现有药物只能缓解最影响患者生活的嗜睡和猝倒症状,想维持正常生活需要长期服用。这些药物属于国家一类管制精神药物,一次只能开7天的量,每次开药都要找有处方权的医生挂号。
一位新疆的单亲妈妈因为四处投医“欠了一屁股债”,跑遍新疆的医院无果,来到北京才确诊。每次开药都坐三天三夜的火车到北京,她要靠做房产中介还债,挣孩子的学费和医药费。她大部分时间都要工作,只能托人帮忙挂号带药,一次300元,相当于一盒药的价钱。
韩芳认为,“无药可用”也是诊疗难以规范化的原因。中国大陆尚未正式批准任何药物用于治疗发作性睡病,十几年来只有那几种促觉醒类药物和抗抑郁类药物能用于治疗,有些医院难下诊断、谨慎开药,也是因为超适应症用药存在较大风险。
中国睡眠研究会常务理事、北京宣武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詹淑琴从2005年开始接触发作性睡病患者,她认为,如果能早期发现、早期治疗,大部分患者能够恢复正常生活的七八成。除了药物干预,她建议患者经常运动,白天固定时间主动小睡,建立良好的作息规律。
她认为对病人的诊断和干预也要走出医院。患者回归社会面临的心理问题,是广大社会工作者需要关注的。有位31岁的患者找不到工作,不爱出门,买彩票、打游戏透支了家里银行卡。55岁的母亲不敢想以后,“我死都不瞑目啊”。
家庭是为患者提供心理支持的第一站。有患者因为父亲觉得自己意志力不够,和父亲见面就动手,3年没在一起生活过。有家属一看见孩子睡就大力把她拍醒,对别人说,“我每次看她睡觉,都想狠狠揍她。”在这些家属眼里,孩子的异常都可以总结为“不听话”,不能和别人提,提了“伤自尊”。詹淑琴有时感觉自己不是在治疗一个病,“是在治疗一个家庭”。
34岁的王明出来打工后,没再主动给父亲打过电话,一打电话就吵。有次他在家里坐着睡着了,父亲问“你怎么不忍着?”王明指出以前父亲阑尾炎,打了麻药还喊疼,“你当时怎么不忍着?”父亲一脸理直气壮说,“我那是病,你这算什么?”
3年前,王明加入一个708人的QQ病友群,后来退出了,因为看不惯群里“预期太高”的家长。“他们不停地折腾,什么针灸、拜佛,各种稀奇古怪的都要试一试”,身为患者的他光是看着,身上压力陡然增大,“他们就没从心底接受这是病,是治不好的病。”
被躺平
对患者的误解从家庭向外蔓延。网名“天空”的患者家属是一个QQ病友群的群主,13年来接触过1200个病患及家属,其中有很多因为老打瞌睡被学校退学的孩子,“人家就说你孩子不适合我们学校,你能咋办?”
周伟上初中时,老师经常给他家长打电话说他“学习态度不好”,一次班主任找家长谈话后,他休学了半年,没能继续学业。年轻时他还有些不服,去年确诊后,他觉得自己“变丧了”。检查结果显示,他下丘脑分泌素的量是正常人的十分之一,吃药也不可能较好地恢复。
“只能躺平。”初中后他就开始封闭自己,“也是一种恶性循环。你犯困,同学家长不理你,你内心软弱、不想和人接触,越来越宅,只能睡觉。到后来这个病变成自我放弃的借口了。”
他刚丢掉一份仓库管理员的工作。之前为了不让老板发现,他只能在推着车进仓库的途中眯一会儿,或者靠在仓库里的架子上,装作找东西。“让我睡5分钟就好”,但这5分钟毁了他的饭碗。
美国2018年的一项调查研究显示,每4个发作性睡病患者中就有1个曾因嗜睡问题被解雇或降职,68%的患者表示周围人并不认为他们患有疾病。
王明发病以来换了十几次工作。他曾在东莞的假发生产线上拿着烫板加工假发,后来因为总是睡着,手上被烫了好几个疤。离开东莞那天,他在出租车上又垂下脑袋,被司机叫醒时大脑还是懵的,手机、钱包、病例全落在车上就匆匆下了车。现在王明只能在家乡的小厂干,老板好说话,不会骂他懒,但工厂效益不好,去年10月到现在的工资还没发。
在病友群里,他发现很多病友是因病辍学去打工,却被不断辞退,其中包括外卖小哥、流水线工人、货车司机等体力劳动工作者。有人因为在工作中睡着摔断胳膊、切掉手指,只能换个地方继续干。有的病情严重的群友要靠捡破烂、啃老养活自己。
王明形容大家是“哑巴吃黄连”,老板撵人,一句“完不成任务量”就能堵住他们的嘴。“等我有钱了,我要拍一部《我不是睡神》。”他在QQ群里说。
发作性睡病患者组织“觉主家”负责人暴敏冬是一名患者,也是一位母亲。虽然女儿有时会不满妈妈老睡觉,不能陪她玩,但女儿总会在妈妈睡觉时给她盖上被子。女儿知道妈妈生病了,很累,“她眼里没有什么该是病,什么不该是病。”
她做过保险顾问,见客户前,她要提前到约定地点趴着睡会儿,走后,她还要趴着补觉,“不然咖啡厅都走不出”。很多患者都会在重要活动前睡上一个小时,“但在我做这些规划时,它已经在影响我的生活了。如果我是一个正常人,我不用为怕睡着而提前做准备。”
“我们就业面非常非常窄”,病友群里大家的共识是不要从事高危险性、高集中度、高精确性的工作。群主天空的儿子喜欢舰艇,但他知道儿子不能当兵。他给儿子规划的大学专业是设计类和艺术类,“弹钢琴就挺好,至少睡着了还有肌肉记忆。”
群里一位辽宁农村的家长每天打三份工,为了赚钱给高一的孩子报一对一补课班,“不管多脏多累,给钱多就行。” 她看着群里成年患者不停地换工作,不希望孩子未来和他们一样,没有选择的权利,“就想让他考上大学。”
上课跟不上进度,孩子哭,她也跟着哭。晚上孩子写作业,她看着孩子在演算本上写出答案,往卷子上抄的瞬间笔掉了。孩子又睡着了。她又哭了。
天空把QQ群起名叫“湛蓝的天空”,因为一次给孩子煎中药,看着蓝色火焰,他想撑起一片蓝天,让儿子像小鸟一样自由飞翔。但想起儿子三分之一的时间都被这个病偷走,他在心里问自己,儿子何时能自由?
真正的自由出现在真正被理解时。暴敏冬每次去各地组织公益论坛,都会开线下的病友见面会。他们在一起分享睡觉的痛苦,谈论自己做了什么稀奇的梦,即使有人哈欠连天、脸上的肌肉耷拉下来,也不会有人侧目。有人还提议会后找个地方,集体趴着睡一会儿。她觉得这种陪伴普通人也能做到,“只需要在他睡着的时候,陪着他,保护他,信任他。”
(文中郑坤、王明、周伟为化名)
原标题:被迫“躺平”的人生
【免责声明】上游新闻客户端未标有“来源:上游新闻-重庆晨报”或“上游新闻LOGO、水印的文字、图片、音频视”等稿件均为转载稿。如转载稿涉及版权等问题,请联系上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