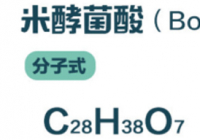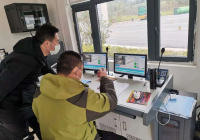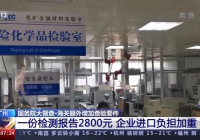南风窗消息,2020年,是张爱玲诞辰100周年。
如果最近到上海,这座张爱玲出生与暂居的城市,来到她曾短暂居住的原爱丁堡公寓、现在的常德公寓,能够看到那座斑驳的建筑物伫立在路口,公寓一楼的咖啡馆在“张爱玲年”正策划着主题活动。
女作家陈丹燕在《上海的风花雪月》中这样描述这幢老楼:“张爱玲的家,是在一个热闹非凡的十字路口,那栋老公寓,被刷成了女人定妆粉的那种肉色,树立在上海闹市中的不蓝的晴天下面。”
沿着这栋“肉色”的公寓向地铁口行走,可以途经凯司令西饼屋——在《色戒》与《半生缘》里,张爱玲总会写到凯司令,念念不忘它的“栗子粉蛋糕”。她写她与好友炎樱总会约着一起到咖啡馆小坐聊天,配套是“一人一份奶油蛋糕,另加一份奶油,一杯热巧克力,另加一份奶油”。到了老年,她亦常常于文章中提及对这口香甜的惦念。
腔调上海的十里洋场、斑驳的意式公寓、柔软的甜品及与其缠绵一生的执念,是众多“张爱玲传奇”中的部分。

张爱玲是一个谜。关于她的一切都镀上了不一样的神秘色彩。在我们最熟知的那幅张爱玲的肖像照片里,34岁的她穿着“一袭华美的袍”,单手叉腰,没有直视镜头,眼神高傲而疏离。她的故事,有贵族身世,天才文笔,也有隐秘爱恋和孤寂余生。
但百年之后,人们依旧执着于反复咀嚼她的传奇,或许并不仅仅只是热衷故事、寻找谜底。今日,我们不妨换个角度,去看看成为“张爱玲”以前,这传奇的来处。
琐碎政治
无可免俗的,“一个作家最好的早期训练,就是不愉快的童年”。
张爱玲的童年,算不上多么“不愉快”,但迥异于普通百姓的、更为精致的“末世贵族”生活,的确也成为了另一种意义上的早期训练,令她有了更敏感、更细致入微的日常嗅觉。
张爱玲出生在旧世家望族残存的尾声。属于祖父的封建士大夫黄金时代已然过去,一家人的生活像是《红楼梦》的后几回,局外人已能嗅到危机,主人公仍在物质生活中难以自拔。
生活在天津家中的童年是暖色调的。张爱玲记得的,都是那些被学界概括为“琐碎政治”的片段。她记得每天早上女佣将她抱到母亲床上去,“是铜床,我爬在方格子青锦被上,跟着她不知所云地背唐诗”,记得姨奶奶“每天带我到起士林去看跳舞。我坐在桌子边,面前的蛋糕上的白奶油高齐眉毛,然而我把那一块全吃了,在那微红的黄昏里渐渐盹着,照例到三四点钟,背在佣人身上背回家”。

童年时的张爱玲与弟弟张子静
她记得很多家中摆设的细枝末节,比如松子糖要装在有金耳、小花修饰着的瓷罐里,痱子粉则要装在黄红色的、蟠桃样式的瓷缸里。如果是晴日的午后,阳光会照进宅子,在“磨白了的旧梳妆台上”留下斑驳的印记。
这些仿若工笔画一样的记忆与再现,展现了张爱玲“琐碎江湖”的开始。陈设的精良、饮食的细致,那种“喜欢吃牛奶的泡沫,喝牛奶的时候设法先把碗边的小白珠子吞下去”的生活,给了她识别生活情趣的可能,让她即使在未来跌宕的人生困境中,也常能自夹缝间找到某种“小确幸”,聊以安慰。
只是聪慧如张爱玲,除了复刻般地记得童年陈设与吃食,到底有着寻常的富贵孩童所不及的敏锐感触。于是,在这样佣人簇拥、吃穿用度随心的生活里,她也常常会有“梦见吃云片糕。吃着吃着,薄薄的糕变成了纸,除了涩,还感到一种难堪的怅惘”这样不知所起、怅然若失的时刻。
有一年除夕,她因为前一夜用功读书,熬夜太久,保姆担心她熬夜太辛苦,没有按照她的要求在第二天早早喊她起来迎新年。
醒来时,新年的庆祝已经过去了,新年的鞭炮也已然放过了。张爱玲躺在床上哭了又哭,不肯起来。最后被拉起来,坐在小藤椅上,佣人替她穿上新年的新鞋子,她还是止不住地伤心。“我觉得一切的繁华都已经成了过去,我没有份了。”
即使好像也在这一天醒过来,也穿上了新鞋子,但新年,连同它代表的幸福温暖、崭新期冀,“即使穿上新鞋也赶不上了”。
赤裸裸地站在天底下
很快,生活的愁苦不再只是错过新年那样简单。
八岁时,张爱玲随家人搬到了上海。上海的房子不比天津的家气派,已是降了一个等级的、“中等人家”的房子。最初,她依旧兴奋,形容新家是“有一种紧紧的朱红的快乐”。
只是这种稳定的快乐,也随着父亲的吸毒成瘾开始逐渐消失,旧式父亲与留洋归来的新式母亲也常常尖声争吵,直到再也过不下去,两人离婚,分道扬镳。
所谓的原生家庭就这样散了。张爱玲随父亲和后母一起搬到了上海的另一所老洋房中。这本是她的出生地,本该拥有某种恬静、舒畅的气氛,但因为沉溺鸦片的父亲与渴望成为主宰的“入侵者”继母在,整个空间笼罩着“昏睡般沉下去”的气息。
这里不再是曾经天津家中的“春日迟迟”的香甜午后了。一切沮丧而怪异:“有太阳的地方使人瞌睡,阴暗的地方有古墓的清凉。房屋的青黑的心子里是清醒的,有它自己的一个怪异的世界。而在阴暗交界的边缘,看得见阳光,听得见电车的铃与大减价的布店里一遍又一遍吹打着‘苏三不要哭’,在那阳光里只有昏睡。”父亲的房间里,“永远是下午,在那里坐久了便觉得沉下去,沉下去”。

张爱玲在常德公寓
感受上的昏沉之外,皮肉上的痛苦也来了。因为与继母之间的嫌隙,张爱玲被父亲毒打,拳脚相加间,“无数次,耳朵也震聋了”;她挣扎着去报案,等待她的当然是被拉回去囚禁在家——这栋她出生的房子,开始展现出狰狞的一面:“突然变成生疏的了,像月光底下的,黑影中现出青白的粉墙,片面的,癫狂的……楼板上的蓝色的月光,那静静的杀机。”此后,她患了严重的痢疾,一病就是半年,差一点死去。
父亲家已经是恶魔一样的存在了。她下决心逃出去,逃到母亲家——留洋归来的、新式的、淑女的母亲,是不是能给自己一个阳光自由的生活?
现实令她失望。这位“先进”的母亲,似乎只能把爱给一个“够得上淑女标准”的女儿。她不关心张爱玲的所思所想,也对她在写作上展现的才华嗤之以鼻。在父亲与继母身边,她频受虐待;在母亲身边,她谨小慎微,客气而疏离。
母亲对她的不在意、对“淑女”的极度坚持,从一件小事里便可见一斑。张爱玲入学时,需在入学证上由家长填写名字。她的小名是“煐”,张煐两字连读又不上口,母亲便暂且将她的英文名胡乱音译成了“爱玲”。此后,母亲常常嫌弃这个名字不够“淑女”,一直说着替她改,但终究也这样以“爱玲”的名字唤了一生。
《小团圆》里,张爱玲写,母亲有100多个名字。小说里母亲名字的丰富与现实中张爱玲名字的潦草互为对照:母亲心中,最爱的或许还是自己,其次,也应该是一个符号的“淑女化”女儿,而不是张爱玲本身。
成年后,张爱玲回首这段在旧式父亲与新式母亲之间辗转、流离失所的岁月时,还是常常黯然。这段时光带来的不仅仅是那个当下的浅表伤害,更是令她产生一种身处荒野的不安全感——这种不安全、无家可归的惘然感,也常常被她附着于笔下的小说主人公身上,讲述着不同的人在不同的社会背景之下,相同的无家可归。

张爱玲的父母、阿姨和堂兄弟姐妹在天津(图片来源:美国南加州大学图书馆东亚图书馆)
有一日她做梦回到香港。“船到的时候是深夜,而且下大雨。我狼狈地拎着箱子上山,管理宿舍的天主教僧尼,我又不敢惊动她们,只得在黑漆漆的门洞子里过夜。(也不知为什么我要把自己刻画得那么可怜,她们何至于这样地苛待我。)风向一变,冷雨大点大点扫进来,我把一双脚直缩直缩,还是没处躲。忽然听见汽车喇叭响,来了阔客,一个施主太太带了女儿,才考进大学,以后要住读的。汽车夫砰砰拍门,宿舍里顿时灯火辉煌。我乱向里一钻,看见舍监,我像见了晚娘似的,赔笑上前……”
醒来,她把这个梦讲给姑姑听,满眼含泪;与友人通话聊到这个梦,又在电话中哭了;在信里提到这个梦,再哭;写在书中的时候,不免又再哭上一次。
梦比她自己更真实地呈现着她无家可归的惶恐与不安。她称之为“身世之感”。“‘身世之感’普通总是自伤、自怜的意思罢,但我想是可以有更大的解释的。”
而她的“身世之感”,是明白自己身处无数的裂隙之间,赤裸裸地站在天底下,身边空无一人。
现代史打上门来
1942年12月,日本进攻香港。
彼时,张爱玲正在港大读书。在彻底走上写作道路、成为一名风格独特的作家之前,此刻,“学生爱玲”最大的愿望,是到英国继续深造。
这场突然的战争打乱了她的计划,也让眼下的书桌无法继续清净下去。
与内地如火如荼、群情激昂的抗战浪潮相比,香港岛上的这场战争对中国人来说有些微妙:这里是英国人的殖民地。发生在香港的“抗战”,是英国人与日本人之间的拉扯,和殖民地之上的“被殖民者”距离感强烈。
张爱玲这样概括当时身处港岛的中国人对英日抗战抱持的态度:“可以打个比喻,是像一个人坐在硬板凳上打瞌睡,虽然不舒服,而且没完没结地抱怨着,到底还是睡着了。能够不理会的,我们一概不理会。”
大家尽量保持着跟战争的距离,尽量“一尘不染”,维持素日的生活方式。张爱玲的同学们依然会为了没有时髦的新衣服伤脑筋;空袭警报来了又走,也没办法威慑到担心手里电车票作废而拼命挤上公车的人群……
只是再不在意,炮弹无情,纷纷扬扬地总还是会落下来,砸在想要躲避的人头上。“不喜欢现代史,现代史打上门来了”是张爱玲的体会。
第一次“打上门”来,是英军空袭时。港大临近英军的一处要塞,日军飞机呼啸而来,频繁轰炸,学校关门大吉,张爱玲不得不跟同学一起到防空总部报名做志愿者参加守城工作,以便换取一些粮食、获得一个住处。战争纷乱,志愿者的身份也常常分不到食物,一连几天,她都是“飘飘然去上工”。
饥饿的侵袭让她开始思考“人生安稳”的定义。年少时离开父母,以为不再能够吃一块甜点、趴在女佣背上醺醺然地归家就是最大的不安了,如今看来,“什么都是模糊,瑟缩,靠不住”,旧时光疾驰不见,房子可以被炮弹夷为平地,乱世中财富一文不值,人的肉身脆弱易逝,是“无牵无挂的空虚与绝望”。

张爱玲与李香兰
如果说,饥饿带来的“打上门来”是物质匮乏带来的思索,那么教授佛朗士的死则是直指人生意义的终极质询。
佛朗士是港大的一名历史教授。和印象中一板一眼的历史教授不同,这位英国人颇为有趣,他热爱细碎且充满烟火味的日常,并时时生活在一些戏剧化的状态里:写中文书法,喝酒吸烟,买一幢房子专门用来养猪,备一辆汽车专门给佣人买菜赶集,与中国教授一同到广州旅游并去一个名声不大好的尼姑庵会小尼姑……他不像寻常的英国绅士,更不像生活在殖民地之上的“大英帝国臣民”。
这样一位风格清奇、又教授历史这样一门很容易叙述枯燥的学科的教授,却获得了张爱玲极为罕见的敬意和怀念。说起他时,张爱玲会说,因为佛朗士不同寻常的个人作风与授课方式,她“得到了一点历史的亲切感和扼要的世界观”,且“可以从他那里学到的还有很多很多”。
但这样一位玩世不恭、流离于殖民地权力体系之外的教授,竟然在这次战争中离奇死亡了。
同其他在港英国人一样,潇洒的佛朗士教授也不得不被征入伍,拿来充数。每逢这群志愿兵操练,佛朗士不能来上课,都会在课堂上调笑着说“下礼拜一不能同你们见面了,孩子们,我要去练武功”。
开战后的某日,佛朗士在回军营的路上,因为没听见哨兵的吆喝,被自家哨兵以为异徒,开枪打死。
这位教授死亡的荒诞震撼了张爱玲。一来,佛朗士对保卫殖民地毫无热情,入伍只是“充数”;二来,他死在“自己人”枪下,甚至称不上是为了战争牺牲。张爱玲几次感慨:“想不到‘练武功’竟送了他的命——一个好先生,一个好人。人类的浪费……”
从第一次理解饥饿,到佛朗士的死,“现代史”轰然袭来,留给张爱玲的,是再一次的“身世之感”,和对人生变化惘然无措的强烈不安全感。个人的世界风雨飘摇,战争、社会运动等大环境浪潮可以轻易将个体裹挟,像无可逃遁的自然灾害一般,摧毁残存的美好。
在《倾城之恋》里,她对白流苏命运的评论,也是她对“现代史打上门来”的感受:“香港的沦落成全了她,但在这不可理喻的世界里,谁知道什么是因?什么是果?谁知道呢?”
无常与惘然,连同工笔画般的琐碎政治和字里行间无家可归的情神疏离,一起交汇成属于张爱玲的点阵,勾勒出这位传奇女作家的某个侧面。在成为“张爱玲”以前,是“春日迟迟”的童年生活、被忽视着的年少尾声、战火纷飞的青年时光,共同推簇着她的写作,左右着未来张爱玲的作品与人生。
这也是百年之后,人们依旧不断想起她、怀念她,不断有新读者阅读她的原因。不只因为字里行间的故事,不都源自对传奇的窥探与打量,更因为她与你我一样,都是鲜活而真实的人,拥有有迹可循的人生,书写热闹的生活,不看低对琐碎的追逐,有真切的迷惘和痛苦。
当传奇不再以传奇的方式绵延,“通常的人生的回响”将获得更广泛、更持久的共鸣,在传奇的浪潮褪去之后,重新成为一种永恒。
原标题:看清楚,这才是真正的上海滩名媛
【免责声明】上游新闻客户端未标有“来源:上游新闻-重庆晨报”或“上游新闻LOGO、水印的文字、图片、音频视频等稿件均为转载稿。如转载稿涉及版权等问题,请与上游新闻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