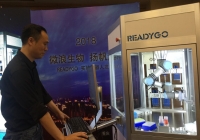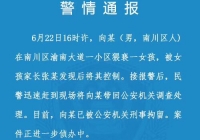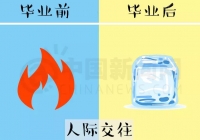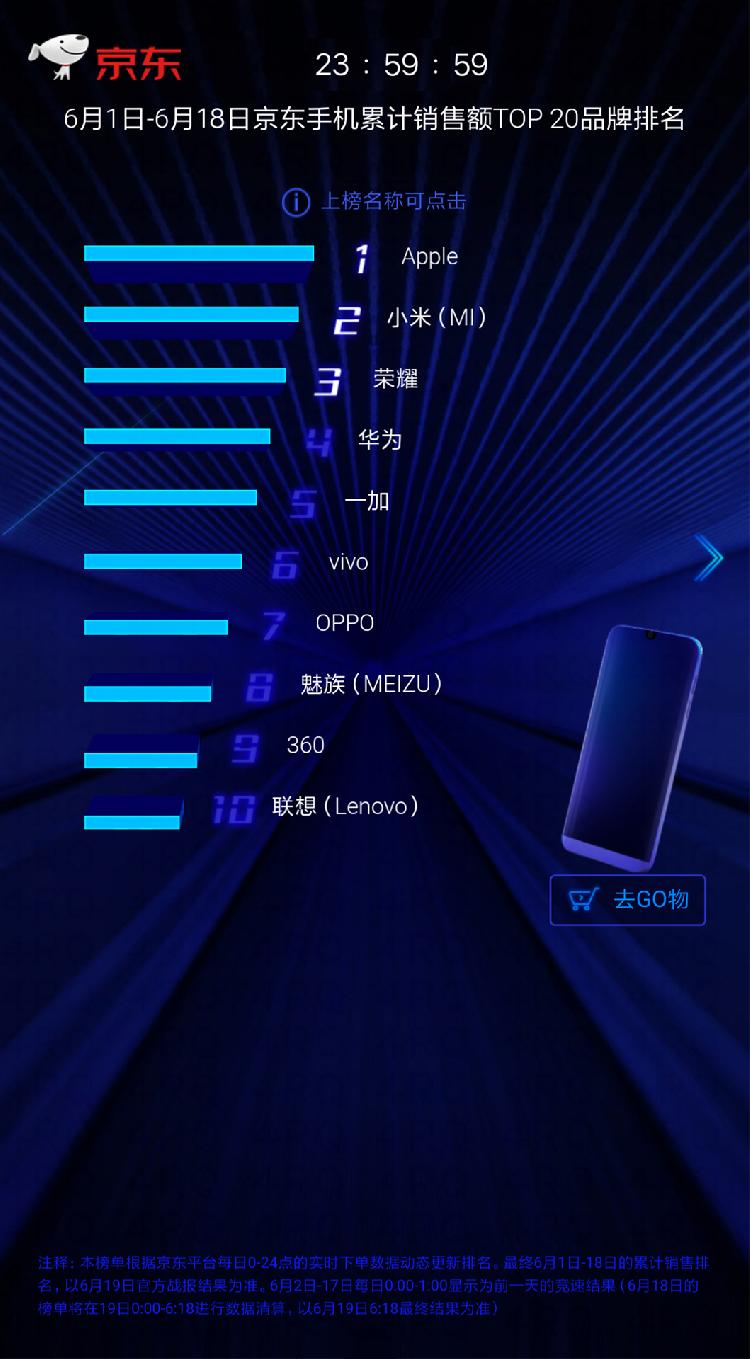时光荏苒,她与你“渐行渐远”
你却走不出她的“碎碎念”
“天黑了就睡,天亮了就起
别在黑夜里耗着,把神儿都耗光了”
小道理中蕴含着朴素的大力量
 节选自 | 倪萍《姥姥语录》
节选自 | 倪萍《姥姥语录》
我生孩子的喜悦,姥姥是第一个知道的;孩子有病的消息,姥姥是最后一个知道的。我不想让90岁的姥姥再替我分担这份苦难了,尽管我自己无论如何是支撑不下去的!
夜里躺在床上,想着姥姥说的话:“天黑了快睡吧,孩子,天亮就快起来。”姥姥把不可避免的灾难说成是“天黑了”。“天黑了就是遇上了挡不住的难事了,你得认命。认命不是撂下,是咬着牙挺着,别在黑夜里耗着,把神儿都耗光了。好事儿来了预先还打个招呼,不好的事儿来了,咣当一下就砸在你头上了。这些灾难从来不会通知你,能人是越砸越结实,不能的人一下子就被砸倒。”

我也是从孩子病的那个月开始抽烟的。初次点上烟的时候,姥姥看见了,相当震惊,她知道孩子的问题大了去了。我旁若无人地拿着烟,烟灭了再点上,点上再灭了,在这样的时刻一般都是后半夜,家里人都睡了,我一定是起来,我不想让他们来安慰我。
我知道这样的时刻,我们家的房子里还有一个人坐在那儿不睡,这就是姥姥。

我们心心相印,可姥姥却苦于帮不上我,主动提出回老家。她叮嘱我:“自己不倒,啥都能过去;自己倒了,谁也扶不起你。”
我努力地想和姥姥笑一笑,只是嘴角往上翘,眼泪往下流,喉咙里热得一个音也发不出来。姥姥拍着我说:“你要是救不了孩子,谁都救不了。姥姥知道你行。”

图 |《朗读者》第一季
我开始不哭了,我坚强地抱着孩子踏上了去美国的求医之路,这一走就是十二年。每年我带孩子去复查就像上刑场一般。直到去年,大夫(对孩子)说:“等你结婚的时候再来检查吧,一切很好,祝你好运。”我的泪水横着飞到大夫的脸上。然后我跟儿子说:“孩子,我们60岁再结婚吧,我真的害怕再上医院。”

这大好的消息姥姥已经无法知道,姥姥在她99岁那年走了。
能够抵挡爸妈责罚的,是她的背后
搂着你舍不得放开的,是她的臂弯
从你出生那刻起,她就把你捧在手心
视作天下最重要的宝贝

节选自 | 迟子建《北极村童话》
大轮船拉笛起锚了,船身慢吞吞地动了。
妈妈走了,把我一人留在这。瞧她站在甲板上向我招手,还不时抬起胳膊蹭眼睛。她哭了。我不愿意看她,更不想跟她招手。

姥姥抹够了眼泪,喊我快走。她的脚小,一走一摇,像是扭秧歌。我不愿意和她一起走,便挣开她的手向前跑。跑累了,再停下来。看着姥姥走路的那副样子,我忍不住喊:“鸭子鸭子快快走,跑悠跑悠上高楼”。
这话可把她气坏了,她边追边喘着,我便又跑,摇晃着柳条棍,东捅捅,西戳戳。一不小心,我把蜂子窝给捅了。一个个小黑绒球向我扑来、压来。立刻,嘴肿了,脖子上,屁股上,都火辣辣的痛。

姥姥赶来了,急得直掉泪。见我哭得凶,她就吓唬我说,“快起来,要不姥可不管你了。”我害怕,抹干眼泪站起来,顺从地趴在姥姥背上。
一颠一颠地,走啊走啊。我累了,渐渐地睡了。等我睁开眼,迷茫中,我就看见了姥姥家的大房子。

房子大,进门是厨房,东西各一间屋。我和姥姥住东屋。屋里一溜大炕。炕上油着蓝漆,光滑滑的。躺上去,忍不住要打几个滚。
晚间,我和姥姥睡一个被窝。她给我讲故事,我爱听,听完了又害怕,便把身子缩在姥姥的胳肢窝下,死死地抓住她的肩膀。

尽管这样,我还是喜欢过晚上。左邻右舍的人挤在厨房里,卷着烟,呷着茶,天南海北地聊,我可以支着下巴听个够。
家,是为你遮风避雨的小屋
她,是沧桑岁月中所有的安顿
三餐茶饭,四季衣裳
她的温暖,细微之处说不尽、道不完

节选自 | 席慕容《外婆和鞋》
我有一双塑胶的拖鞋,它很普通,平底,浅蓝色,前端镂空成六个圆带子,中间用一个结把它们连起来。买的时候是最喜欢它的颜色,穿了五六年后,已经由浅蓝色变成浅灰,鞋底也磨得一边高一边低了……
“你知道我为什么舍不得丢掉它吗?”

这是个让生命在刹那间变得非常温柔的回忆。大学快毕业时,家住在北投山上,没有课的早上,我常常会带着两只小狗满山乱跑。有太阳的日子,山腰上的美丽简直无法形容,最让我快乐的是在行走中猛然回过头,然后再仔细辨认,山坡下面,哪一幢是我的家。
走着走着,我的新拖鞋就不像样了。不过,我没时间管它,直到有一天,傍晚,放学回家,隔着矮矮的石墙,看见我的拖鞋被整整齐齐地摆在花园里的水泥小路上。

“今天下午,我用你们浇花的水管给你把拖鞋洗了,刚放在太阳地里,晒晒就干了!多大的姑娘啦!穿这么脏的鞋给人笑话。”
以后,外婆每次上山时,总会替我把拖鞋洗干净,晒好,有时甚至给我放到床前。傍晚时分,她会安详地坐在客厅里,一面摇扇子,一面等着我们回来。我常常会在穿上拖鞋时,觉得有一股暖和与舒适的感觉,不知是院里下午的太阳,还是外婆手上的余温?

这双拖鞋,也就一直留在身边,舍不得丢。每次接触到它灰旧的表面时,便仿佛也接触到曾洗过它的外婆的温暖而多皱的手,便会想起在夕阳下的园中小径,和外婆在客厅纱门后面的笑容。
那么遥远,那么温柔,而又那么肯定地一去不返。
当稀松白发难掩来路的艰辛
当坚实臂膀变作默默地企盼
你总以为她会陪在身边
一转身却消失不见

节选自 | 胡荣尔《外婆的年》
在我的记忆里,过年,总有一种让我口舌生津的馨香味道。那来自我的童年,与我的外婆有关。
小时候的年,是一段贴着对联、年画和窗花的乡村记忆。红彤彤的,笼罩着一团喜气。我的心像飘浮的纸鸢似的,晃晃悠悠荡在空中,直到吃了元宵节的汤圆,才肯落地。好在,有外婆站在地上,稳稳地接住。

外婆忙年,从腊八开始,响亮地奏起了序曲。营生成倍增长,不止在柴米油盐酱醋茶七件事里转悠了,身边总有干不完的活计:清扫卫生,拆洗缝补,剪窗花剪福,糊顶棚糊窗;逢五遇十,备好大筐小篓,去赶集置办年货……等到小年祭灶后,还有一拉溜的面食,排队等着她去完成:发糕,年糕,豆包,菜包,饽饽,饺子……外公不会做饭,只会拉着个呼哒呼哒响的风箱,往灶膛里添柴火。外婆的双手和双脚各就各位、配合默契,在忙碌的节奏里,保持着忙而不乱的秩序。

现在想来,我外婆堪称是优秀的生活家。再忙再累,她也把日子治理得有条不紊。别人有的,她不缺。别人没有的,她不少。
外婆掌管的春节,如同开启一个宝物匣子,里面涌出百宝光,让我目不暇接。新年零点一过,我迫不及待地张开小嘴,甜甜地向外公外婆拜年。

外婆笑眯眯地将压岁钱塞到我手里,一边看着我笑,一边抚着我的头说,好蓉儿,又长了一岁,更懂事了,外婆可是又老了一岁,白头发更多了。
外婆的笑容里,依稀透着些伤感。但当时年幼的我,并不理解“老了”意味着什么。

长大后,我逐渐明白:一个个的年,好比设置在人生沿途的一个个路标。它们既照亮年少者的前方,又削减年迈者四周的光亮。年少是出发点,年老是目的地。此长彼消,多么温情而冷酷的平衡哲学。
一秒触动绵长泪点的,是她的皱纹
一生走不出的,是她的目光
无论是姥姥、外婆,还是奶奶
都是一生割舍不断的血脉与亲情
原标题:一生走不出的,是她的目光
【免责声明】上游新闻客户端未标有“来源:上游新闻-重庆晨报”或“上游新闻LOGO、水印的文字、图片、音频视频等稿件均为转载稿。如转载稿涉及版权等问题,请与上游新闻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