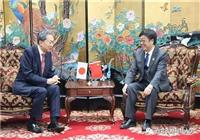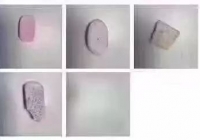2018年10月30日,当代知名武侠小说家金庸(查良镛)去世,享年94岁。
金庸曾给自己设计过墓志铭:“这里躺着一个人。在20世纪、21世纪,他写过十几部武侠小说。他的小说有几亿人喜欢……”这位享有盛名的小说家现已作古,从近日上至文化名流、下至普通读者发起的悼念之语来看,他对自己的盖棺定论不止中肯,甚至有些自谦了。
1954年,太极拳传人吴公仪和白鹤拳传人陈克夫在澳门比武,掀起武侠热潮,梁羽生、金庸遂开始在办报之余创作武侠小说,新派武侠时代就此开启。自1955年《书剑恩仇录》开始至1972年《鹿鼎记》封笔,金庸共创作了15部小说,几乎凭借一己之力构建了一个庞大的江湖世界,令无数读者乐在其中,也定义了我们对武侠的认知。
研究金庸作品的“金学”甚至成为显学,众多小说爱好者深挖金庸作品中的细节,企图找到其与真实历史的勾连。新垣平在《剑桥倚天屠龙史》中戏仿《剑桥中国史》的西方学术文体,将《倚天屠龙记》的小说情节融入中国蒙元史的框架内解读,把金庸笔下的江湖阐释为一个“由于传统的儒家文化和士大夫政府的压抑”而不为人知的“失落的世界”,煞有其事地指出蒙元帝国在中国统治的崩溃很大程度上应当归功于中国武林人士的集体反叛。

《剑桥倚天屠龙史》新垣平著凤凰出版社 2012年9月
这固然是金庸书迷技巧高超的恶搞戏作,不过我们也不免产生好奇:金庸笔下的“武侠”,历史上到底存不存在?历史学家余英时曾用《侠与中国文化》一文系统梳理了侠的历史流变及其在中国文化中扮演的重要角色。他指出,侠源自古代封建秩序的解体。文武兼包的“士”在周代封建制度中原是最底层的贵族,但到了春秋之后原有的固化封建等级制度已无可维系,“士”的阶层不仅出现上下流动,也出现了文武分化,并从中出现了侠。
从春秋战国到秦汉时期,“侠”在大部分时间里指的都是武士群体,接近当代武侠小说意义的“侠客”直到唐代才出现。虽然“侠”作为一种武装力量和社会群体在与封建皇权的激烈冲突中逐渐式微,但我们不难发现,每当到了末世战乱或社会动荡之际,自诩为“侠”的人都会大量出现,力争重建秩序与公义。更重要的是,“侠”逐渐脱离了武士的语境,成为某种备受推崇的精神特质。从这个角度来说,“侠”的确一直存在于中国人的集体意识中,武侠小说的流行亦顺理成章。
侠的起源:“士”的文武分化
近代学者普遍认为,“侠”源自古代封建秩序解体后“士”阶层的分化。在商周时期,文武双全者方可称“士”,他们是最底层的贵族。到了春秋时期,固定的封建等级制度难以为继,“士”出现了文武的分化。到了战国时代,文士与武士已经形成两个截然不同的社会集团。顾颉刚在《武士与文士之蜕化》中写道:“文者谓之儒,武者谓之侠。儒重名誉,侠重义气。……古代文武兼包之士至是分歧为二,惮用力者归儒,好用力者为侠,所业既专,则文者益文,武者益武,各作极端之表现耳。”
《史记·游侠列传》云:“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在这段描述中,司马迁塑造了“侠”之典范,也将这一类人正式命名,自此成为中国文化中不可忽视的一部分。余英时指出,不是所有的武士都能被称为侠的,唯有将武士道德发展至最高水平的人方可称侠。
《史记》告诉我们,战国时期有一类侠可称为“有土卿相”之侠——他们名列卿相、参与朝政,召集天下侠士作为食客豢养,利用他们的能力执行外交、军事上的政策。有“战国四公子”之称的齐国孟尝君、楚国春申君、赵国平原君和魏国信陵君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
然而“侠”自出现在历史舞台上起就包括平民在内,而非局限于贵族。在战国时期,士、庶之间的界限趋于模糊,关于“士”的礼仪已经松弛,平民亦可上升为“士”。事实上,司马迁在《史记》中屡屡使用“布衣之侠”“闾巷之侠”“匹夫之侠”之类的词语用来指代平民侠客,且对他们颇为推崇,因此他曾写道:“自秦以前,匹夫之侠,湮灭不见,余甚恨之。”
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的侠除了“言必行、行必果、诺必成”的个别“游侠”之外,还指法外武装集团,因此也有“任侠”的说法。“任侠”一词出自《史记·季布传》,据三国曹魏人如淳的注解:“相与信为任;同是非为侠。所谓权行州里,力折公侯者也。”也就是说,任侠是一种有一致的价值取向,共同进退的团体,他们或许有很大的地方势力(“权行州里”),且和政治权威形成了某种对抗性(“力折公侯”)。

《文化评论与中国情怀(下)》余英时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4年6月
从“游侠”到“豪侠”:皇权扩张下的侠客群体
“我们必须明确,‘江和湖’是缺乏海洋文明的中国文化中和坚实的陆地以及故土相对立的概念,它们构成中国的内河航运体系以及广义的交通运输体系。像鱼一样在江湖中生存者,必然首先是摆脱了对土地依附关系的自由人。”
新垣平的这段话可以很贴切地用来形容战国时代的“游侠”——他们周游各国,无拘无束,有时亦会接受有权有势者的招徕,成为死士。这种情况到了汉代之后发生了改变。继短命的秦王朝后,汉朝继承了秦的政治遗产,再度形成大一统的政治秩序。社会流动性急速下降后,人们亦开始重建对土地、宗族、乡党的依附关系,正如“游士”转变为具有恒产和社会地位的“士大夫”一样,“游侠”亦有相同的士族化和恒产化过程,演变成一股令统治者侧目、心悸的社会力量。
虽然《史记》《汉书》沿用了“游侠”的旧称,但其实汉代的“侠”更多是指“豪侠”,即具有深厚地方势力和武装力量的地方豪强。西汉中晚期以来,“豪侠”已取代了“游侠”的名称,根据清代史学家全祖望的考证,游侠至王莽时期已式微。《汉书》之后,中国正史中再也没有“游侠”这个概念了。
地方豪杰盘踞一方,有的时候甚至具有干预地方官吏工作的实力,势必引起官方的警惕。侠客们固然讲究义气,行侠仗义,但从皇权的角度来看,他们就是游离于法度之外、视律令若无物的社会不稳定分子,是需要严厉打击的对象。整个西汉时期,汉廷都在打击侠客群体,早在文、景两朝,诛杀“游侠”的行动已经开始,大规模打压“游侠”则从武帝时期开始,其中一个策略就是要求地方豪杰迁徙关中,切断其与地方宗族乡党势力的联系。
《史记·游侠列传》中记录的郭解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郭解,字翁伯,河内轵人,是武帝时期的著名侠客。他年少时蛮狠斗勇、作恶多端,长大后一改作风,行侠仗义,吸引了许多仰慕者。元硕二年(前127年),武帝下令迁豪富往茂陵邑居住,特别指定了郭解必须迁徙。郭解以家境贫寒、不符合资材三百万迁徙标准为由拜托大将军卫青向武帝求情,武帝却说:“解布衣,权至使将军。此其家不贫。(郭解一介布衣平民,竟能使将军替他说话,可见他不穷。)”郭解于是被迁徙到了茂陵。
左丘萌在《到长安去》一书中指出,侠客与皇权的冲突根源在于两者都是在人治社会中建立一套自己的行事规则,自立法度,随意决定他人的生死。以“正义”之名施行的暴力行为有些时候也是对作恶的纵容,侠客的行为,很多情况下会和皇权的意志(或者说全社会的主导性共识)相违背。例如郭解迁徙之后,郭解的侄子割去了一个主张迁徙郭解的杨姓县吏的头颅,郭解的门客还刺杀了杨县吏的父亲,他的家人试图上书申冤也被一并杀害。“如此不允许有对立意见、任意夺人性命的事,在治民者眼中,不仅是滥杀无辜,更是大逆不道。”

《到长安去》左丘萌著/负笈道人绘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8年7月
整体而言,“豪侠”自西汉中叶以后便逐渐向士族转化,在从武帝时期开始的一系列抑武崇文政策推波助澜下,各地豪族中的第一流人才开始放弃“侠”,转而谋求“儒士”之路,其中最为成功者就有以“累世经学”“累世公卿”名动海内的袁绍一族。不过这并不是说豪族完全放弃了武力,在汉魏两晋南北朝的史书中,我们可以看到豪族一直保有武力以求自保,并在战乱或朝代更替之时凭借武力保护族人和当地社区,产生了大量的“豪侠”“游侠”“任侠”。
个人主义的“剑侠”:武侠的历史原型
从汉末直到隋唐之际,正史中不乏“豪侠”“任侠”的记载,然而进入唐代后,这种具有集体组织和行动的侠就基本绝迹了,“侠”开始变成了个人行动。中唐以后,独来独往的剑侠开始成为侠客群体的主流,这一形象一直延续至今,可以说是武侠的历史原型。
《太平广记》193至196卷收录了“豪侠”类的唐传奇,其中最有名的有《虬髯客》《昆仑奴》《聂隐娘》《红线》等,这些传奇大多是关于男女剑侠、刺客、大道的侠义故事,他们的行为符合言必行、行必果、诺必成、轻生死的古代游侠核心道德观,但他们不再具有“权行州里、力折公侯”的社会势力,彼此之间也无联系。
以《聂隐娘》的故事为例:聂隐娘是魏博大将军聂锋之女,10岁时被一女尼用法术偷去教以剑术,五年后送其返家。聂父死后,魏博主帅与陈许节度使刘昌裔不和,欲令身怀绝技的聂隐娘前往刺杀刘,聂隐娘却被他的气度折服,转而投刘。主帅另派精精儿与空空儿前往暗杀,被聂隐娘以法术破解。后刘昌裔入朝觐见天子,聂隐娘辞别。刘死后,聂隐娘又来到京师在他的灵柩前恸哭。

电影《刺客聂隐娘》中,舒淇扮演聂隐娘。
余英时指出,这些豪侠故事并非完全是虚构的,例如侠士许后从番将沙叱利府中为翰翊夺还美人柳氏一事(《太平广记》卷485《柳氏传》),也见于孟棨记录唐朝诗人逸事诗歌的《本事诗》;进士赵中行和荆娘救人报仇一事(《太平广记》卷196《荆十三娘》)也见于晚唐词人孙光宪的《北梦琐言》。因此,“豪侠”传奇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唐代的社会现实。
千古文人侠客梦:“侠”与“儒”的合流
有意思的是,虽然作为社会群体的“侠”逐渐消失于历史长河中,但作为一种精神气概和行动法则的“侠”,突破了武士的局限性,进入了儒生文士的道德意识中。余英时指出,由于许多儒生出身于尚武的豪族家庭,他们从小就浸润在“侠”的道德风气中,因此东汉的士大夫往往具有“侠”的精神。清代史学家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指出:
“自战国豫让、聂政、荆轲、侯赢之徒,以意气相尚,一意孤行,能为人所不敢为。世竞羡之。其后贯高、田叔、朱家、郭解辈,徇人刻己,然诺不欺,以立名节。驯至东汉,其风益盛。盖当时荐举征辟,必采名誉。故凡可以得名者必全力赴之,好为苟难,遂成风俗。”
除了重义守诺之外,东汉士大夫还具有侠客的社群意识,在危难之际往往互相援引,这一点集中反映在汉末党锢之祸中。东汉桓帝、灵帝时,士大夫集团对宦官专政的乱象不满,爆发了激烈的党争。宦官集团两次以“党人”罪名禁锢士人,士大夫群体被残酷镇压。根据《后汉书》的记载,党锢之祸时期士大夫借送葬之名进行大规模集会,与“侠”的传统颇有关联。“党锢之士在道理上固以儒家为依归,然而激昂慷慨的侠节却给他们提供了情感上的动力。所以后世富于批判精神的儒者也往往带有‘侠气’。这一发展其实也是很自然的,因为儒家传统中本有一股狂的精神,能与‘侠风’一拍即合。”余英时说。
宋元明清时期,“侠”与“儒”合流的趋势愈发明显,“侠”的概念被儒家思想内化为一种精神状态和道德标准,“千古文人侠客梦”成为儒家士人的重要人生理想。王阳明“心学”泰州学派弟子何心隐认为,“儒”与“侠”本来就是合流的,因为二者同是“意气”落实的结果:“战国诸公之意之气,相与以成侠者也,其所落也小,孔门师弟之意之气,相与以成道者也,其所落也大。”事实上,他在当时也的确因泰州学派的讲学运动,特别是其“无父无君非弑父弑君”的“异端”思想而被正统士大夫斥为“借讲学而为豪侠之具”。
晚明清初同样是社会动荡不安的混乱时期,于是我们再一次看到“任侠”的大规模出现,不过这一次,出任“任侠”的主角是不满现状、有志于社会活动的儒生文士,譬如王阳明、何心隐。“侠”之精神驱动着儒士们,为了心中的道义去振臂一呼,应者云集。
很大程度上来说,金庸的一生就是在实践他自己的文人侠客梦。
1950年,钦慕新中国政府的金庸北上北京,希望实现“外交官”的梦想,报效国家,却因为家庭出身的原因报国无门,失望地返回香港,继续其在《大公报》旗下副刊《新晚报》的编辑工作。1959年,由于看不惯《大公报》所报道的“虚假事实”,35岁的金庸创办《明报》,其宗旨是“把事实真相告诉给读者”,开始了每天一篇一千多字社评、八九百字小说的办报生涯。《明报》一直针砭时弊,不惮于批评当局,在1962年大胆报道了香港难民潮后,获得了香港市民的广泛赞誉。在复杂的政治环境和人身安全的威胁下,金庸从未屈服,他说过:“我虽然成为暗杀目标,生命受到威胁,内心不免害怕,但我绝不屈服于无理的压力之下,以至被我书中的英雄瞧不起。”
“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这位“以文乱法”、有着浓重家国情怀的小说家用他的小说和人生告诉我们,侠,的确存在。
(本文写作主要参考了余英时《侠与中国文化》一文,收录于《文化评论与中国情怀(下)》。)
原标题:金庸笔下的“武侠” 历史上到底存不存在?
【免责声明】上游新闻客户端未标有“来源:上游新闻-重庆晨报”或“上游新闻LOGO、水印的文字、图片、音频视频等稿件均为转载稿。如转载稿涉及版权等问题,请与上游新闻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