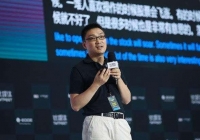澎湃新闻消息,礼拜天早上七点,43岁的念斌骑电动车到花巷教堂,头发花白的他,坐在教堂的凳子上,闭上眼睛,双手合十,低头祷告,之后默默地听牧师讲解《圣经》……一直到八点半结束离开。
自从无罪释放以来,念斌每个周末都会去教堂。

每个星期天早上,念斌都在教堂祈祷。除特殊标注外,本文图片均为澎湃新闻记者 明鹊 图
2006年7月,福建平潭县一起投毒致死案致6人中毒2幼童死亡,杂货店老板念斌被认定为犯罪嫌疑人。接下来8年时间,在历经宣判、上诉、驳回、复核等10次开庭,念斌有4次判被处死刑,手脚戴着“工”字形镣铐。他说,那时候,白天害怕黑夜,黑夜害怕白天。
直到2014年8月22日,法官敲响法槌,当场宣判念斌无罪释放。
这起没有真凶再现,没有亡者归来,嫌疑人最终无罪释放的投毒案,因其贯彻的”疑罪从无”理念,在中国司法界和舆论界激起强烈反响。
2019年8月22日,念斌重获自由五年了,“嫌疑人”的身份挥之不去,老家再无安身之处,他仍期待找到真凶。
无家可归
“哗”的一声,生锈的铁门被打开。
平潭县澳前村,这栋2000年修建的两层楼房,外表是水泥墙,里面有八间房,曾是全村最好的楼房之一。

平潭县澳前村念斌的老家。自事发后至今,已有13年没有人居住。
如今,空置的老屋玻璃窗户被打碎,屋内一片狼籍,沙发、凳子、冰箱……歪倒在地上,布满厚厚的一层灰,已看不出什么颜色。堂屋的墙壁上,挂着念斌父母的遗像,照片有些开裂。过去,念斌和父母、哥哥、姐姐都住在这里。
姐姐念建兰为念斌的案件奔走十几年,至今未婚。她穿一双小白鞋,踩着老屋地上积满灰尘的窗帘布说,弟弟念斌无罪释放后,依旧无家可归,每天过得像逃犯一样。
念斌的五哥念孝叔说,念斌宣判无罪释放后,澳前村干部反复叮嘱他:你们不要回家,不要放鞭炮庆祝,以免受害者亲属受到刺激。按照平潭的习惯,死里逃生的人回家,应该放鞭炮、戴红布庆祝,但为了能顺利迎接念斌,念家亲戚只准备了新衣和“平安面”。
与此同时,受害者家属在村里设了灵堂、拉上横幅,挂上念斌和其辩护律师张燕生的照片。旁边摆了一台电视,将念斌供述投毒过程的录像反复播放。
8月17日,受害者的奶奶向记者说起此事,依旧坚称念斌就是投毒的凶手。“三次(其实是四次)判了死刑,他不是凶手谁是凶手?他都不敢来这条马路上走。”
仇恨早在13年前就被点燃。2006年8月10日,警方查封了念斌的杂货店,并向外公布,念斌就是投毒案凶手。瞬间,愤怒的受害者家属跑进念斌家,打砸家里的一切,并烧毁了里面的衣物和窗帘布,姐姐念建兰带着父母逃去了福州。

念斌站在被打砸一空的老屋玻璃窗前。
自从念斌被刑拘后,妻子戴佳佳一个人带着儿子去了福州市。“他们(受害者家属)说,要打死我儿子。”她说。
直至今日,念家兄妹也都回不了老家——两个哥哥在平潭县租房子,念建兰则一人四处漂泊。念斌无罪释放后,跟妻子租住在福州市,直到2015年冬天,他去老家坟地给父母烧判决书,看到破败的房子——早已不再是从前那个家。
8月15日,阳光明媚,念斌和念建兰又一次回到家中。半个月前,一位亲戚想租他们的老屋做民宿,但他到实地一看,估算全屋装修要花三十万元,就犹豫了。
有那么一瞬间,念斌也想回家开民宿,但这个念头很快被打消,他没有钱搞装修,也很难面对死者家属的责难和村民的闲言碎语。
屋内是13年前的模样,念斌杵在门口,前前后后看了一圈:大门外,半空中拉了一条渔网,丝瓜藤爬在上面,大大小小的丝瓜垂了下来。他走到大门边上水井旁,熟练地掀开水井盖,把吊着长绳的水桶丢进吊井,打上来一桶井水,依旧像从前一样清凉彻骨。
很多时候,念斌回想起事发前的日子:傍晚时分,海风呼呼地吹,像唱歌一样,一家人聚在一起吹风聊天,小孩在空地上你追我打……
这一切都一去不复返了。

平潭县澳前村,念斌家离海边不到500米,出事前,他经常来海边玩。
投毒案
2006年7月27日,平潭县澳前村两户人家一起食用鱿鱼、稀饭,包括杂货店老板丁云虾及其3个孩子,房东陈炎娇母女,6人全部中毒。其中,丁云虾10岁的儿子和8岁的女儿因抢救无效身亡。
据警方检验,两人系鼠药(注:氟乙酸盐)中毒致死,警方怀疑是邻居念斌所为。
念斌记得,当年8月7日,他在岳母家吃完饭后,开车带着儿子回店铺,公安让他配合协助调查。当着4岁儿子的面,念斌被警方带走了。
念斌在录口供时交代,2006年7月26日晚上,一个顾客从对面走来,被隔壁杂货店的丁云虾招揽了过去。他怀恨在心,凌晨一点多,来到和丁云虾共同租用的厨房,将半包老鼠药倒进矿泉水瓶,盛好水后,沿水壶嘴口倒进丁云虾煤炉上正在烧水的水壶中。当天,铝壶里的水被丁家做了鱿鱼和稀饭,最终导致丁家两名小孩的死亡。
13年后,念斌再次回忆此事称,他当时遭到公安刑讯逼供,对方用会连累妻子来威胁他,“我是一个男人,是一家之主,不想把老婆牵连进来。”
2007年2月,福州检察院向福州中院提起公诉。3月,福州中院首次公开审理该案,念斌当庭翻供,称遭受了刑讯逼供。2008年2月1日,福州中院一审以投放危险物质罪,判处念斌死刑。念斌不服判决,提起上诉。
此后,念建兰辞掉了财会的工作,为弟弟开始了东奔西跑的生活。
8月12日,45岁的念建兰坐在宾馆的凳子上,剪一头短发,圆脸,身材微胖,自称接受过上百家媒体的采访。
她回忆说,自己原本是个内向的人,看见人都会脸红,一切都是被逼出来的。父亲过世前,曾对她说:“是念斌做的,千刀万剐不为过;不是他做的,砸锅卖铁都要救。”
2008年12月31日,福建高院裁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撤销原判,发回重审。2009年6月8日,福州中院再此判决念斌死刑。念斌上诉。2010年4月,福建高院二审判处念斌死刑,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念斌命悬一线。
律师李肖霖觉得,念斌非常幸运,碰上了中国的司法改革。2006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修改,明确规定,从2007年1月1日起,最高人民法院统一行使死刑案件核准权。
2010年10月,最高法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为由,不核准念斌死刑,发回福建高院重审,福建高院发回福州中院重审。2011年11月24日,福州中院再次判处念斌死刑。
念斌案演变成“拉锯战”。一方面,念斌的辩护律师通过网络和媒体列举案件疑点,另一方,控方和侦办此案的公安干警坚称没有“刑讯逼供”。
念斌的辩护律师张燕生回忆,一开始,她也怀疑就是念斌投毒,但后来所有证据、细节都证明,念斌就是无罪的。
2013年后,最高法6次批准该案延期审理,办案人员出庭作证、控辩双方邀请专家证人出庭交锋,使该案成为新刑诉法实施以来最受关注的悬案之一。
2014年8月22日,福建省高院终审宣判念斌无罪。
死亡阴影
在牢狱中随时感觉大限将至,是念斌至今无法挣脱的心理阴影。
他至今记得那种疲惫不堪,却又无法入睡的感觉,对死亡的恐惧,让他“每晚最多只能睡三个小时”。白天的时候,戴着“工”字形镣铐的他,失去了大部分自理能力,不能正常穿衣、洗澡、吃饭,甚至刷牙这样简单的动作,也必须有人协助才能完成。
“没有一点自尊,像狗一样活着。”他一边说,一边蹲在地上示范戴着镣铐吃饭、睡觉、穿衣的模样。
念斌记得,2012年左右,看守所有一个死刑犯,和他一样戴“工”字形镣铐,他们走得比较近。
对方告诉他,被判处死刑后,他很后悔,但一切无可挽回。而他则告诉对方,自己是被冤枉的,不想就这样死去。
一天早上,他们和往常一样,起床洗脸刷牙,之后吃了稀饭、包子。大约七点多,铁门打开了,两名武警走了进来,大家都怔住了,“我们都知道要执行死刑了”。
念斌说,一般情况下,武警不能进看守所,一旦进来,就是要带犯人去执行死刑。
他杵在铁门外,看到那名和他一样判死刑的犯人被武警押着,一边走,一边朝着他微笑,念斌说不出话,他眼睁睁地看着对方离开,流下了眼泪来。
他说:“我不知道,自己会不会也这样离开,离开的时候,能不能像他一样微笑着走。”
2010年4月,福建高院二审判处念斌死刑,之后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
那段日子,念斌每天都胆战心惊,害怕第二天醒来看到武警。他至今记得,得知高院判死刑,送去最高法核准时,他发高烧了三天三夜,迷迷糊糊中,感觉有东西压在他身上。
念斌默默地祷告,“主啊,救救我,给我力量……忽然之间就有了力量,压在我身上的东西没有了……”
直到最高法发回重审,他又看到了生的希望。
念斌觉得,虽然他只是小学毕业,但历经了这一切,让自己更理解生命,宇宙,以及自然的力量。后来,他在看守所看到一份报告,讲有人种无公害蔬菜,突然被这种生命吸引。“一颗种子,破土而出,生根发芽,这种力量,任何东西都无可阻挡……”
他甚至想过,如果以后能从看守所出来,就去承包一块地,种大棚蔬菜。
“犯罪嫌疑人”
然而,真正无罪释放后的生活和念斌想象的不太一样。
首先是身体的状态,刚摘掉铁链子时,念斌身体往前倾,就像跌倒一样,走几百米都觉得辛苦。
2014年9月2日,念斌在北京长安中西医结合医院的体检显示:他有胃溃疡,浅表性胃炎;前列腺增大,膀胱壁增厚;腰椎间盘病变;肌肉萎缩、抑郁症等症状。
念建兰发现,弟弟回来后,精神状况很差,“他只跟从监狱出来的人聊天,喜欢说‘监规’、‘坐靶’等监狱用语,对外面的世界不感兴趣,经常失眠、紧张。”
那时候,律师帮忙联系了一位香港心理专家,对方愿意免费给念斌提供心理治疗,念建兰打算带弟弟去香港进行治疗。
2014年11月14日,他和姐姐前往福州市出入境服务大厅办理护照时发现,其身份信息在出入境管理系统中显示为“犯罪嫌疑人”。
姐弟俩都懵了。
事实上,念斌被无罪释放的第9天,平潭县公安局已报备将他列为“法定不准予出境人员”。

2015年1月,平潭县公安局提供的情况说明。受访者供图
平潭县公安局负责人此前接受澎湃新闻采访称,念斌被宣告无罪以后,从公安的角度来讲,已破的案子变成未破,因此重新启动侦查程序。而警方将念斌列为嫌疑人不准予出境,“是有新的证据,但是什么证据,我们不方便透露。”
妻子戴佳佳发现,在那之后,念斌不喜欢出门,整天躲在家里,不知道怎么跟人相处,经常说自己还是“嫌疑人”。
“很多人用异样的眼光看你,在背后对你指指点点的。”念斌说。
他坐在出租屋的客厅里,听着风扇呼呼地吹。客厅没有窗户,不到10平方米,显得有些压抑。
念斌没有工作,家里所有开支,包括一个月2500块钱的房租,全靠妻子一个人在托管所的工作支撑。念斌一直想出去工作,他觉得自己还年轻,可以奋斗二十年,靠自己的双手,肯定能把日子过好。
2016年,他跟人一起去修地铁,一个月工资四千多块钱,但只做了两个月,他就无法坚持了,“腰腿痛得受不了”。

念斌在地铁工地上干活。受访者供图
此后,他也出去打过零工,断断续续。大部分时间,念斌不上班,除了出去散步外,每天待在家里给儿子做饭、洗碗。
念斌跟儿子不亲,两个人待在一起经常没话说,这也让他很困惑。
他记不清搬了多少次家。案件重启侦查后,公安经常上门找他,公安一来,房东就催促他们搬家。
念斌觉得,他虽然已经无罪释放,被列为嫌疑人的他依旧戴着无形的镣铐,无法回归正常的生活。
律师张燕生认为,念斌被列为犯罪嫌疑人已经五年,平潭县公安应该设置一个期限。
法学家彭新林解释道,《刑事诉讼法》仅就侦查羁押期限做出了规定,但是司法实践中,如果犯罪嫌疑人未被采取强制措施,侦查机关的侦查是不受诉讼期间的限制的。
困顿前行
念建兰的朋友廖芬在医院工作,她觉得念斌精神过度紧张,只要有人生病,不管是家人还是自己,念斌每次都不停地打电话过来问,“他可能还是有后遗症吧”。
为了恢复健康,念斌坚持每天锻炼,不下雨的时候,他傍晚到外面走一圈,下雨的话,他就躲在家里踩跑步机。
他在福州市没有朋友,生活不太习惯,偶尔会带儿子回岳父岳母家。
念斌回家前,戴佳佳一个人在福州带着儿子读书,因为没有亲戚朋友,每次去上班,她都必须把儿子一块儿带过去。那时候,最让她头痛的是,儿子看到别人一家三口开开心心,很是羡慕,拉着她问“爸爸去哪儿了?”她每次都告诉儿子,爸爸去国外打工了,不方便回来。
念斌无罪释放后,戴佳佳本以为一家人团聚,自己能轻松一些。却没想到,一个个问题接踵而至——
她发现,念斌仍然无法适应现在的生活——曾经活泼开朗的他,如今变得胆小谨慎;夫妻俩经常说不到一起,很容易就发生冲突;念斌还是“嫌疑人”,村里人依旧对他们有看法……

傍晚时分,平潭县澳前村集市上有人卖鱼。
被改变的不只念斌,还有念建兰。这个在朋友眼中,曾经“是一个很简单,大大咧咧的女生,如今变得‘愤世嫉俗’,只看到社会的黑暗面。”
“她经常晚上不睡觉,想东想西,四十几岁头发都白了。”朋友廖芬说念建兰。
念家七兄妹(老二和老三已过世),只有念建兰上过大学,“他们整个家庭都靠她。”廖芬觉得,念斌出来后,很依赖姐姐,有什么事都会问念建兰。而念建兰也觉得,弟弟的事就是她的责任。
廖芬曾劝念建兰回归正常生活,找个人结婚,再不行就找个男朋友,但念建兰似乎对此并不感兴趣,“她身体不太好,而且过了结婚年龄”。

念建兰指着地面说,他们的衣物和窗帘在这里被烧成灰烬。
2014年12月26日,念斌提出1500万的国家赔偿。2017年1月19日,最高法赔偿委员会决定驳回念斌的申诉,赔偿数额止步119万元,但可另向公安机关索赔。
念建兰说,这些钱还不够他们还账,更不要说念斌的治疗费和回归正常生活后的支出。此后,念斌又起诉平潭县公安局和福州市公安局,要求双方赔偿医疗费、后续治疗费、伤残赔偿金等四百多万。
今年3月27日,最高法驳回了念斌的国家赔偿申请。
一晃五年过去了,念建兰不知下一步该如何是好。去年开始,她进了北京一家律所做财务,生活慢慢回归正常。“我们都要生活。”
念斌则不想回忆过去,他称,回来后最开心的事就是去教堂,一边听牧师布道,一边祷告早日找到真凶。

念斌和丁云虾的杂货店门面,如今已被打通,改成了移动营业厅门面。
(部分人物为化名)
原标题:念斌无罪获释这五年:被“嫌疑人”身份笼罩的人生
【免责声明】上游新闻客户端未标有“来源:上游新闻-重庆晨报”或“上游新闻LOGO、水印的文字、图片、音频视频等稿件均为转载稿。如转载稿涉及版权等问题,请与上游新闻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