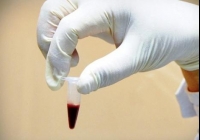漫画:程璨

在家也是战“疫” 北京市育翔小学学生 王安博(9岁)

普石,本名李强,中国铁路文联副主席、秘书长。
中国青年报消息,2003年的“非典”,对于00后来说,记忆几乎是空白:要么没有出生,要么最多只有3岁。而在这次新冠肺炎疫情中,这些移动互联网的原住民,通过网络时刻追踪着方方面面的信息,通过他们的眼睛观察着身边形形色色的人和事,由此形成了他们人生中一块新的记忆碎片。
我们家有两个人上前线
何叶琪 湖北省黄冈市罗田县实验中学(14岁)
我们家有好几位医务人员,有在武汉的,也有在我们县城的。以前,家人视频时总是围绕着我和弟弟妹妹们说说笑笑,但最近,笑容变成了担忧——无论是姨妈所处的武汉还是妈妈所在的黄冈,疫情都很严重。
妈妈是护士,在人民医院呼吸内科上班,由于县城的医疗物资短缺,她们的防护措施没有保障,每天都会有无数个被病毒盯上的可能性。家里人都十分担心她,可她却说:“没事,我们有办法保护自己。”原来她和同事们一起自制防护用品,用废旧的胸透胶片制作了防护面罩。
由于病人越来越多,她们的工作越来越忙,加班成了家常便饭。她不怕自己被感染,却害怕会把病毒传染给我和爸爸。于是,她独自一人搬了出去,除了工作,过上了“与世隔绝”的日子。我和从来没有分开过的妈妈只能视频见面,一个星期、两个星期……我从来没觉得时间是如此漫长。
视频中的妈妈有时会吃着前夜的剩饭剩菜,脸上一点妆容都没有,反而有清晰的、因长时间戴口罩被压出的深深的红痕,眼睛里布满了红血丝,尽显疲态。往日里妈妈是最爱美的,我不知道她有没有看到镜子里那青一块红一块的脸。突然间心疼,妈妈这次搬出去,一个人在外面过着孤单清冷的年,一个人吃着简单的饭菜,一个人承受所有的心理压力,不知道还要多久,她才能回来。
眼前空荡荡的家,有时让我十分害怕。爸爸每天去社区值班,妈妈也时刻处在危险之中,我却什么都不能做。想着想着,我的眼泪就止不住往外流。妈妈安慰我说:“妈妈也想回家陪你,可现在,有比家更需要妈妈的地方。你一定要坚强,你看生病的姨妈都那么坚强,我们应该更坚强。”是啊,姨妈是武汉同济医院的医生,过年的头一天被确诊感染。全家人得知消息后都很着急,外婆更是心急如焚,尽管已封城,还是吵着要去武汉照顾姨妈。尽管年幼的弟弟妹妹每天趴在阳台上眼巴巴盼着姨妈回家,尽管姨妈偷偷抹着泪跟姨父说生死有命富贵在天,但视频里,我从来没在她的脸上看到一丝愁容,反而经常说着哪个好友痊愈了,哪位同事又回到了工作岗位,等等。她说,她要快点好起来,早日归队与前线的同事并肩作战,只有战胜了疫情,才能回家团聚。
在海外 我过了一个最不像春节的春节
李芊逸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生(18岁)
自从我记事起,每年春晚直播都没落下过。往年过节,一家人早早地打扫完卫生,福字春联一贴,再做一大桌子年夜饭,红红火火地聚在一起,然后在沙发上堆满枕头、被子等着看春晚直播。
今年过年我在捷克,除夕当天恰巧期末考试。由于时差,春晚开播的那一刻我们正在考场上奋笔疾书,等到考试结束,晚会也只剩下半场可看。原本在家不看春晚的同学,今年也兴致勃勃,甚至要求大家一起看。
晚上7点,5个人把房间挤得暖烘烘。我们炖了肉也包了饺子,又学着炸肉和藕盒,勉强有了点过年的样子。小方桌上摆着努力拼凑的年味,电脑上放着春晚录播,再咬一口热腾腾的饺子,肉馅里的油就滚了满嘴,恍惚间有了些许家的味道。
几个人围着小方桌胡侃,但所有人都刻意避开了家的话题,想把这个最平淡的春节当做一个热闹的派对来过,勾肩搭背地说着不能想家。除夕夜里闹久了,第二天自然都赖了床,我一直睡到中午才醒。醒来后才知道,一批在捷克的华人联系了快递公司,发起了募捐口罩支援武汉。
我一直在网上关注着疫情。这真是一场大灾难,那么多人坚守一线,又那么多人从四面八方前往增援,可我们什么也帮不上,只能在远离祖国8000公里外,眼睁睁看着确诊人数逐步攀升,至多只能给家里打几通电话,让家人多注意身体、少出门。
没想到,一个同学大年初一开始手脚颤抖、呼吸困难,没几分钟就直接倒在房间里,把我吓坏了。她低烧已经有两天了,我也出现了低烧咳嗽的症状,却因为临近考试而拖到现在。我的脑子里第一时间就指向新冠肺炎。把她安置在我床上后,我迅速给中国驻捷克大使馆和当地医院打了电话,然后拿上了她的所有证件和曾用的退烧药,戴上口罩等待救护车到来。
救护车来的时候,她已经憋得满脸通红、几近昏迷。她本人后来讲,当时就像有什么东西卡在肺里一样,一点空气也吸不进来。我和另一位同学扛着她送进救护车,然后我一个人陪她去了医院。幸运的是,她是流感,发烧以后吃不下东西,导致了重度低血糖。
早晨6点,天仍然黑着,由于医院的规定不能陪床,我离开住院部独自乘车返回。在行驶的电车上,我看到了留学至今的第一个日出。这是我有生以来经历的最繁忙、最不像春节的春节,但没有人会停下,我们仍要走下去。
责任
李雨霏 广州市华阳小学学生(9岁)
今年的春节与众不同,因为疫情,我们全家人都待在家里不敢出门。突然有一天,爸爸接到了任务,要去北京工作20天。我在做作业的时候,听见妈妈轻声对爸爸说:“请个假行吗?”爸爸摇摇头说:“不能,放心吧,我会照顾好自己的!”接着爸爸开始收拾行李了……
大年初五早晨,爸爸戴着口罩出发了,我们把爸爸送到电梯口。往外看时我发现,往日人山人海、车水马龙的街道此时却空无一人、冷冷清清。我开始有点担心爸爸了,他要去那么远的地方,去那么多天和那么多人接触,会不会被传染啊?
晚上临睡前,我问妈妈:“平时不是教育我们说生命和安全是最重要的吗?为什么这么危险的时候爸爸还要外出工作呢?”妈妈搂着我说:“这个时候,比生命和安全更重要的还有责任啊!”我想到了这个时候还在工作的那些人,有保障我们通水通电的,有保障我们有食物的,还有最勇敢的白衣天使,他们也都不顾自己安危、心怀责任坚持在工作!这时妹妹突然说:“长大了,我想做一名白衣天使。”我在心里默默地说:妹妹加油,我支持你!
希望这个病毒早点被消灭,希望和爸爸一样坚持工作的叔叔阿姨们平平安安!
爸爸在疫情面前挺身而出,以无所畏惧的逆行让孩子体会到什么是责任!言传身教是最好的教育,危难时刻有担当,我们的社会和国家才越来越有希望!
(点评人:十九大代表、广州市华阳小学校长 周洁)
春节日志
徐延 天津财经大学学生(19岁)
父母要开车载我回延庆老家的村子过年。想起来应该是个完美的假期,约了同学过年期间来延庆一起滑雪,过完年就回北京城区,约了几个朋友聚餐吃饭。
2020年1月20日
同往年一样,回老家之前要去稻香村装点心匣子。新型冠状病毒今天在微博上很火。起初并没有在意,看到了一条说这个病毒和“SARS”同源,便再也不能安静下来。“非典”那年我上幼儿园,对于“非典”,没有太多的印象。只记得放假在家疯玩磕破了头,需要缝针,母亲捂着我流血的头,匆匆赶到医院。因为没有麻醉药,也记下了撕心裂肺的疼。
“医生说千万不能发烧,一旦发烧,就是隔离……”这是之后我妈给我或朋友讲“非典”的时候我的“光荣事迹”。
在去装点心匣子的路上,阳光正好,电线上的麻雀如往常叽叽喳喳,平时人流匆匆的鼓楼后街却没什么人。戴着厚厚口罩的我步伐稳健,心中有点慌,有点空,但是我什么都没说。
2020年1月21日
今天我们回了延庆,乡下的空气总是很清新,温度也比城里要低。吃完饭和父母在村子里遛弯,道路两旁的积雪还没化,隐约可以看见天上的星星,和小时候一样。日子过得有些莫名,但总归是朝期望的方向走着。此时的村子是个世外桃源,它与外界纷乱无关。
2020年1月22日
前一天晚上玩到1点多,第二天将近10点才起床,正好看到没戴口罩的三姑和三姑父从大门进来。“出门要戴口罩了呀!现在这个肺炎闹得很严重。”可能我的音量有些高,三姑和三姑父都转头看我。
到了下午,新型冠状病毒好像有燎原之势。我和朋友联系,说这期间就不聚了,有点怕。好在朋友都回我,他们也觉得小命更重要,也支持暂时不聚,看他们警觉,我稍稍有些安心。
2020年1月23日
武汉封城的消息出来以后,我有些松口气,感觉只要把武汉控制住了,全国就控制住了。但是母亲却嘀咕一句:“‘非典’闹得最凶的时候也没封过城啊!”于是,我意识到事情好像不是我想的那样。
2020年1月24日
我捐了钱,捐了200元。感觉天空变阴了,我的心很痛,但我还是不相信阳光会败给阴霾。
2020年2月7日
有点困惑了。我要去相信什么呢?我要去提升些什么呢?语文功力?来判断自己到底要不要买双黄连?推理能力?来判断各种说法是真是假?我心疼那些医务人员,也心疼那些在武汉的人们。不知他们是否知道这里有一个我,在为他们虔诚祈祷。
我也看到钟南山,看到那些老专家的拼命。我在担心呀,我在心疼呀,他们的岁数已经那么大,他们也是易感人群,那么高强度的工作,他们身体受得了吗?如果他们倒下了呢?有人在以生命的代价去奋斗,我还能做什么呢?看到有诸如此类的报道,在下面评论一个“加油”,把手机屏保换成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宅在家里不出门不聚餐,总觉得自己这样还是在袖手旁观。
另外,庆祝雷神山医院顺利启用。
2020年2月8日
希望物资能尽快到需要的人手里,现在有部门如果还用物资发财,那就是吃人血馒头是谋财害命,是难以被原谅的。
2020年2月9日
已经死了1000多人了。1000多人是个什么概念,就是25个我们班,我的整个小学的人。对我来说1000是个数字,对某些人来说那个“1”就是灭顶之灾。
刚才看了热搜,钟南山说疫情的峰值在2月下旬。学校已经安排好了上网课,我也注册好了账号。估计再见到朋友,大概要3月了,我有点想小伙伴们,也好想和豆豆一起逛学校的小卖部呀。
希望再见到你们的春天,看到你们笑面如花。
2020年2月11日
我们的记忆里增加的不仅是无聊
闫海伊 河南省焦作市第一中学学生(16岁)
这个春节,新型冠状病毒将我的生活围得平静乏味。
原打算趁假期能好好美一番的,结果从大年初一开始,我差不多天天都穿着睡衣、拖着棉拖、顶着鸡窝似的乱发在家待着,所有的计划都被病毒打乱。网络上,不少热搜话题都在讲述着自己打发无聊的无聊方法。现实生活中,本该热热闹闹、喜气洋洋的城市变得空空荡荡,本该车水马龙的街道变得像一台老旧的电视机,时不时只有一道残影一闪而过。那些出现在街道上的身影,或者是起早贪黑的清洁工,或者是救死扶伤的医生,或者是志愿者,等等,他们甚至在除夕都没有好好和家人吃一顿团圆饭。为了攻克新冠肺炎疫情,为了让像我一样宅在家里的人可以早日出门呼吸新鲜空气,他们在无声战斗着。
控制病毒传播的重要途径是少出门。但人是向往自由的,没有人愿意被封闭在家里或小区里。刚开始的几天,我们小区还能自由出入。现在,出入小区需要出入证,两天内一家只能有一个人出入一次,外出还不能超过3个小时。对学生来说,当前最热门的讨论话题就是网上授课。在第一天新鲜劲过后,有人开始抱怨网课占了自己大量时间,有人开始组团去给钉钉打低分,也有人上网课时偷偷玩游戏,这些都是在学校上课时不可能会发生的事情。
危机是契机,生活也是功课。在这场疫情中,我们的记忆里增加的不仅是无聊的感受,更会有每个人的经历和成长。
我心中的最美逆行者
陈奕帆 广州市农林下路小学学生(11岁)
我的妈妈是一位记者。年前疫情蔓延时,妈妈就开始没日没夜地工作起来。她半夜写稿,早上广播,下午采访,晚上回来经常连饭都来不及吃,就又开始工作了。
一天中午,妈妈和外公正在厨房忙碌着。突然,妈妈匆匆准备出门。我问妈妈:“你要去哪里?”妈妈回答说,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有100多名医护人员,要去驰援武汉。
看着妈妈那匆匆离去的背影,我的脑海里,浮现出电视画面中那些奋战在武汉第一线的白衣天使们。他们正在为千千万万人的生命奉献自己的一切,而妈妈就是要去报道他们的出征仪式。我真想好好帮帮她,真希望自己快快长大。
今天是元宵节,我很期待能和妈妈一起吃一顿团圆饭。下午2点妈妈又开始收拾装备准备出发。妈妈摸了摸我的头说,这次是去医院采访今天痊愈出院的一个母亲,今天她可以和两岁宝宝共度元宵节了。妈妈说,她采访后要去办公室写稿,不一定能赶回来吃晚饭。我跑到厨房,把冰箱里的汤圆拿了出来。十几分钟后,一碗热腾腾的汤圆就煮好了。我把汤圆端到妈妈面前,说:“今天是元宵节,你吃了汤圆再去工作吧。”
我在电视里常常听人们把医护工作者称为“最美逆行者”,因为当大家都希望离病毒越远越好的时候,他们却义无反顾地向疫情重灾区进发。但是我认为,妈妈和她的记者同行们也都是“最美逆行者”。
该文以一个小学生的视角,从一个普通家庭生活场景触及抗疫,正面表现了包括新闻工作者在内的“逆行者”的精神风貌,叙述自然、亲切、生动。
(点评人:中国作协主席团委员、辽宁省作协名誉主席 刘兆林)
疫情时期我在信阳
张豫湘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生(18岁)
“未发现人传人”,这是我回信阳时看到的最后一条新闻片段。除了一句叹息,我没有放在心上。
于我而言,今年冬天本来就很特殊,爷爷肠癌晚期,医生也不知道还能坚持多少时日。爷爷一直和我们住在东莞,如今病重,他执意落叶归根。大半年来的住院,让他感到疲惫。
他想躺在信阳的家里度过最后的时光,而这个家已10年不曾住人。到家时是深夜,一开灯,我看到白漆剥落,露出块块红砖,窗纸烂得如若无物。墙上还有几个洞,窗户和墙洞一同邀请冷风进来做客,于是冷风呼喊着进入我家,尽情狂欢。
家里只有两张床,父亲和爷爷一起睡,而我、弟弟和母亲挤在一张床上。躺在床上,我渐渐温暖起来,但我的脸却被冷风肆虐,早上起来时已经冻僵了,好在后来住到了酒店。
父亲和来看爷爷的亲戚攀谈,母亲在院子里摘青菜,弟弟在外面跑来跑去。这样过了还没3天,新闻就在不停地拉警报了。但这儿的集市人来人往,热闹得紧,没有人戴口罩。我生于2001年,对非典没有记忆,看着大家又都如常,便放松了警惕。
除夕夜,我们要和亲戚一起吃饭,我反对过,但是拗不过父亲,他总要固守传统。父亲还说,这两天不住酒店,过年住外面,像什么话。为了不再受风吹、不挤在一起,我们借宿在隔壁,只是没想到,借宿两天还不够,酒店之后全部歇业。
大年初一,本该是拜年的时候。我家总有人来,但一个陌生人来后就没什么人了。我对他印象深刻,因为只有他一个人戴口罩。听父亲说,那是村长,说是村路将封,不许串门。
我顿时紧张起来,怕回不了东莞。母亲也说要走,工厂有一批货年后要交。父亲看着爷爷吃力地啜下半碗面,皱皱眉,还是同意了。所幸爷爷说话仍中气十足,宛如常日,他颤颤巍巍地从枕头下拿红包给我们,说:“没事,你们先走吧。”
父亲又犹豫了。“算命的说,老爷子活不过今年……”炉火烧得很旺,父亲的脸被映照着,却显得气色很差。
家里的门虚掩着,禁令虽下,总还有人来看望爷爷,不看,也不知道还有没有机会再看了。
这一天没走,大年初二了。我推开门,漫天飞雪。雪落在屋檐上,黑白两色,是我见过最好的景了。弟弟第一次看到雪,欢脱得像只猴子,地上的雪留下了他一串串的脚印。这是2020年信阳第一场雪,美得像一场梦,却让我担心大雪封路,家不能回。我的思绪就像这雪,白茫茫一片。父亲也急了,要我们早点走。
每一刻都有新的禁令,封城、封路……这些通知在我的脑子里嗡嗡作响。还不能开车回去,若爷爷病情加重,父亲要送他去医院,幸好我们买到了当晚仅剩的两张卧铺。
父亲送我们到火车站,车站有几个人还暴露着口鼻。在车站给弟弟补买了票,一切准备妥当,我一看时间,还有3个小时才发车。“我刚开车开到一半,路被封了。”父亲打来了电话。
“那怎么办?”
“我调头停到镇上二姑家里了,还得走一小时才能到家呢。”
母亲感叹我们运气真好。可只要没到家,都得悬着一颗心了。在火车上睡觉时我不敢取下口罩,早上醒来,一呼吸就是自己的浊气,很憋闷,但我只是换了个口罩,也不敢再取下。
到了东莞,出站也没有量体温,有个工作人员还在下巴处挂着口罩对别人说话。我拉着弟弟走,躲开取下口罩拉客的司机。
一回到家,我像是一根紧绷的琴弦突然断开,瘫在了床上。
过了3天,父亲打来电话。
“爸在交代后事了。”
“我们现在回去?”
“路都封了,你们不来也没事,他没叫你们。可爸非要见我妹,一直在喊。”
父亲的妹妹,我的姑姑,她在丈夫家。
她的丈夫是武汉人。
本文好在真实,好在真切。文章所表现、所描述的,你都可以真切地感觉到。客观地说,这比较难。除了对疫情的记述,此文还涉及了其他内容,诸如老家的环境、家人的生活情状、亲人之间的相互表达等,相信读者能够感觉到那种强劲的冲击!文贵真,而非伪。
(点评人:鲍十,作家,小说《纪念》被改编为电影《我的父亲母亲》。)
爱与祝福蔓延得比病毒更快
黄玳柔 广州市南武实验学校学生(14岁)
春节前一周,我和弟弟前往斯里兰卡做野生海龟救助志愿者。与此同时,国内的疫情暴发。当我们启程回国时,我们专门去买了口罩,飞机上全程佩戴。我从报道中了解到,本次疫情是因为人类食用了野生动物而引起的。这给刚结束海龟救助工作的我带来巨大的冲击。我疑惑、愤懑、惋惜,目前全球物种正在以惊人的速度灭绝着,却仍有人会因为“猎奇”去食用野生动物!
回到家后我们终日待在家里,下楼散步买菜都成了一种危险的奢侈品,没有挨家挨户的串门拜年、没有逛花市的热闹喧哗,就算外出也不敢靠近生人。路上冷冷清清,为数不多的路人也都是口罩人,到处弥漫着紧张的气氛。这个年还真的是很没有年味。作为一个中考倒计时以分钟计算的“初三狗”,连我们在中考前的重要备考阶段都必须在家上网课,丝毫没有了学校时的集体学习氛围与效率。最焦虑的是我的“母上”(日语中母亲的敬称——编者注)大人,每天几次问学习进度。而在春节中最令人失望的是爸爸全天的忙碌,早上不见人影,晚上归家后是一个又一个电话,还经常大半夜匆匆忙忙出门。
几天过后我才知道爸爸一直在忙着找工厂买口罩、防护服等捐赠给疫区,他一直亲自盯着这个活动的进程,甚至想尽办法用救护车运送物资。
新冠肺炎疫情突如其来,无数英雄勇赴险境,他们品格可昭日月,精神感人至深,创造着一个又一个奇迹。奇迹背后,有无数逆行而上、负重前行的普通中国人,每人都有一分热发一分光,星星点点汇聚成了炬火,照亮了黑暗,让我们看见平凡人的灵魂在闪闪发光。
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我们众志成城,终能驱散浓云密雾和看不见光芒的黑暗,不信你看,爱与祝福不是蔓延得比病毒更快吗?
我们不是有很多好吃的吗
张欣瑶 北京市垂杨柳中心小学馨园分校学生(9岁)
以往的大年初二,我们都会去姥姥家,一大家子将近40口团聚在一起,哥哥姐姐弟弟妹妹一群人在一起玩,是我每年过年最期待的日子。可是今年妈妈接到姥姥的电话:“不要过来了,小区不让进门了。你们在家千万别出门,如果你们必须出门就戴上口罩。不要去人多的地方,不要和别人交谈。”
爸爸天天看电视上的新闻频道,全是新冠肺炎。这个词我虽然不明白,但是听着好可怕。爸爸说,这种病毒是从野生动物身上传播给人的,而且病毒还可以人传人,很危险。没法出门,我就趴在窗台上往楼下看,以前热闹的小区广场,现在只有几个人匆匆忙忙走过,但楼下的两只小花猫还窝着草地上,懒洋洋晒着太阳。
我问爸爸:“小花猫在外面是不是很危险,我们能不能把它们抱回家呀?”爸爸急忙说:“那可不行,很危险的,万一有病毒怎么办?电视上不是说,病毒在野生动物身上吗?”
我说:“小花猫不是野生动物。课本上讲过野生动物都生活在深山老林里,它们是我们小区的老住户了。可是爸爸,为什么我很少能见到野生动物呢?”爸爸无奈地说:“因为人们吃了很多野生动物。爱吃的人,就算野生动物住在月球上估计也会被抓回来吃。”
可是我想不通,为什么呀,我们不是有很多好吃的吗?
原标题:疫情,让00后有了人生新的记忆碎片
【免责声明】上游新闻客户端未标有“来源:上游新闻-重庆晨报”或“上游新闻LOGO、水印的文字、图片、音频视频等稿件均为转载稿。如转载稿涉及版权等问题,请与上游新闻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