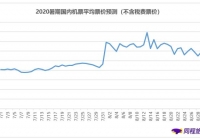△当年送我上学的地下党员、小学校长徐国钧和师母的照片。
今年7月1日,是中国共产党99岁生日。《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是我一生中都在唱的歌。共产党给了我一切。其中最难忘的第一件事,是共产党送我上学堂。
我出生在涪陵李渡一个极贫的李氏农家,不满两岁,父亲就因肺痨去世。7岁时,正逢曙光即将到来的1949年夏,母亲带着我改嫁到长寿山区一熊姓家。熊家继父孤独一人,身患黄肿病(钩虫病),住在一间上不能避雨、墙不能挡风的茅草棚里,就这个茅草棚也是一小土地出租人家的,因租种这一小土地出租人家的土地,这间草屋就连带送住。
正在这时,院子里一位胡姓地主为了教自家孙子读书,请了村里一位名叫刘锡凡的先生到他家开私塾馆。这位地主还算开明,允许刘先生在教自家孙子的同时,招收院子和附近的农家孩子为学生。我母亲找到刘先生,哭求他收我为学生。刘先生也是一位穷苦人,经常是在一件长衫遮挡下没有穿裤子就来教书。无奈之下,也出于穷人之间的同情,他仅以交一升胡豆为学费,收下了我这个学生。在刘先生教授下,我读了一期私塾。一期后,私塾闭馆,我也辍学在家。
我的继父,本就不想我读书,只想让我给他放牛割草打猪草学种地。就这样,我天天就干着继父要我干的事。
解放了,天亮了!土改工作队来到了村里。他们访贫问苦,访问到了我家,我母亲也成了在村里苦大仇深的人,也了解到了我这个快10岁还在家放牛割草打猪草的苦孩子。
一天,一位土改工作队穿军装的解放军女战士和在乡中心校任校长还未公开身份的地下党员徐国钧来到我家。徐国钧与我家是同一个村民组,我由李家带到熊家,还是他给我们立的契约,对我家知根知底。徐校长把我继父和母亲叫在一起,那位解放军女战士对他们说:“现在解放了,我们穷人当家做主人了,为了今后不再受苦,我们穷人的娃儿必须读书。可你们的娃儿都快10岁了,还没有上学,这可不行。你们必须让他上学。”徐校长也说:“我已和玉华小学黄世信校长联系好了,熊庆元明天就去上学。村农会李德明主席明天也要去学校,给熊庆元办理手续,书费学费全免。”两位共产党人不是在说服,而是在命令。我的母亲当然是喜极而泪,不愿我读书的继父,也无话可说。
第二天,我和已经在玉华小学上学的同院子同学刘光才一起去了学校,他把我带到黄校长面前,村农会李主席已经等在那里,并已给我盖章办理好了免书学费的手续。黄校长说:“你就是熊庆元?好,欢迎你上学!你是穷人家的娃儿,你要记住,是共产党送你来读书的,可要努力哟!”他把我编在一年级一册班。当我拿到书后,看了看,找到黄校长说:“校长,这些字我认识,我不读一册班。”他想了想,对我说:“好!那只有跳级读二年级三册班了。”他把坐在旁边的高老师叫来,对他说:“这位学生叫熊庆元,是土改工作队和徐国钧校长送来的,他不愿意读一册班,现在把他安排在你的三册班。他只读过一期私塾,没有读一年级,基础差。你把他安排和成绩最好的学生坐一张桌子,好帮助他。”
高老师把我安排在第一排,和我坐一张桌子的同学叫郑保全,他比我大四岁,也是刘锡凡先生的学生,和我同读了一期私塾。他是全班学习成绩的第一名。他对我帮助很大。最难忘记的是算数。我读私塾一期,刘先生只叫我们认字,不教算数,连阿拉伯数字“1、2、3……”也没有教过。学阿拉伯数字很容易,在郑保全的辅导下,我两天就学会了,但算数题就难倒我了。开初做算数题,我都瞟眼照抄郑保全的,他发现后,不让我照抄,凡是照抄他的,老师全打“√”,凡是他没让我照抄的,全是“×”,因为我不懂什么是“加法”“减法”。还算我不笨,我对着做对了的算术题,看了又看,想了又想,问郑保全:“加法是不是比如3加2等于5,5加3等于8;减法是不是5减3等于2,8减5等于3?”他高兴地回答:“对对对!就是这样。”我便一下开了窍。第一学期考试结束,在学校大门口的墙上公布的成绩榜上,郑保全是班上第一名,我是第二名,黄校长笑眯眯地对我点了点头;在第二学期考试公布的成绩榜上,我和郑保全颠倒了个个儿,我成为了班上第一名,郑保全成为了第二名。黄校长摸着我的头说:“熊庆元,好样的,你这个穷人家的孩子,没有辜负共产党送你上学!”
不久,玉华小学从初级小学改为完全小学,已公开地下党员身份的徐国钧校长调来玉华小学当校长,黄校长我就不知道调到哪里去了。我在黄校长名下当学生,虽然只有两三年时间,但他是我的启蒙校长,他对我的关怀至今难忘。更没有想到的是,在我后来走上工作岗位时,他又成为我的引路人,这是后话。
徐国钧校长在我面前,是严师,更似严父。夸我时,爱之过甚。有一次,他的儿子和我同班的徐良玉考试成绩不好,他把我和徐良玉叫在一起,骂徐良玉:“你这个不成才的东西,你的学习条件比熊庆元好多了,为什么考这个成绩?你看熊庆元学习条件那么差,为什么考得那么好!”但他训我时,那真是让我无地自容。他教我们数学课,有一次考试,我做掉了一道题,很骄傲地第一个交卷。当我回到座位后,想起还有一道题做掉了,去向他想要回考卷补答上,他不但不给,还当着全班同学训斥我:“这是考试,不是办家家。熊庆元呀熊庆元!你这样的学习,对得起共产党送你来上学吗?要是将来工作了,给你一项任务,你能这样粗心吗?!”最后他恶狠狠地甩给我一句我至今没有理解的话:“你就是瞎子狗吃屎,只投堆头多!”他恶狠狠的话,成为我工作后严谨认真的警语。
1956年我小学毕业,以全区第一名的成绩考入长寿县第一初级中学。徐校长到我家报喜,他那个顽童般跳起来的高兴劲,让我至今难忘。但他深知,我这个家庭,根本没有办法让我到百里之外去读初中。他如法炮制,要村里开了一张家庭困难介绍信,让村里在长寿一中读书的学校团委副书记张品儒带我到学校报到,争取助学金。
我去长寿一中报到时,正逢全县教师在县里集训,徐校长把全校9名老师叫在一起,也带上我,在电影院门前一家豆花馆吃豆花饭。席间,他对老师们说:“熊庆元是我们大家的优秀学生,现在他考入一中了,是他的努力,也是我们的光荣。大家知道,他是读不起这个书的。现在我们大家都凑点钱,让他先入学再说。”9位老师,一人1元,学校大队辅导员袁老师出2元,一共凑齐10元。我拿着母校恩师们的这10元钱,向老师们深深鞠了一躬,到一中报名入了册。这10元钱,奠定了我一生的命运。
在长寿一中,我拼命地学习,成绩始终保持班上第一名,还成为班干部。一个学期后的1957年“五·四”青年节前,我在全年级9个班学生中,第一个加入共青团。
1958年,长寿县在长寿湖畔的龙溪区组建新的第四初级中学,除招新生外,在全县其它中学调剂学生。长寿四中离我家只两个小时的路程,我报名去了四中。我的班主任吴素芝也是一位共产党员,她了解我的情况,对我特别的关心,母亲般的爱护。她还让我担任学生会宣传部副部长,让我锻炼。一年后,又面临升学。她对我说:“我了解你家庭情况,你的读书路走得很艰难。继续报考高中、大学,很难读下去。这样吧,你就去读师范学校,那里至少吃饭是不要钱的,毕业后,还可以当老师。”就这样,我被保送进入长寿师范学校。
在长寿师范学校,我的班主任栾文成,也是一位共产党员。他是本校毕业留校任教的,比我只长四岁。他是我的老师,又如我的兄长,百般的呵护,更严格的要求,也让我担任学生会宣传部副部长。
回忆我一生的读书路,是共产党送我上学,又是一个一个的共产党员像接力棒一样,呵护我的读书路。
1962年,我师范学校毕业,带着县人事科的派遣函,到了龙溪区中心校报到。接待我的,竟然是我日思梦想的小学启蒙校长、龙溪区文教党支部专职书记黄世信。一见面,我们都愣住了。我深深地向他鞠了一躬,递上派遣函说:“黄校长,我来向你报到了!”他回答我的,还是当年夸奖我的那句话:“熊庆元,好样的,你这个穷人家的孩子,没有辜负共产党送你上学!”停顿了一会儿,他又对我说:“熊庆元,你过去没有辜负共产党送你上学,是好样的;现在,我要派你到一个艰苦的地方继续锻炼,看你能不能经受住这个考验!”从此,当年我的启蒙校长,又成了我工作的引路人。
黄校长派我去的是在山沟里的焦家乡中心村村小,那里就一个班,我一个教师。为了给我引路,黄校长还不时爬山涉水来学校看望考察我。我也不辜负他的期望,我和村里共同努力,改变了学校的破烂面貌,我的教学经验被送到县里交流。一年后,我被调回区中心校,除继续教书外,还担任区文教团委副书记;再一年后,又被调到县委机关,196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以后又成为重庆日报记者。
我一生不忘,是共产党送我上学堂,是一个一个共产党员一路接力呵护我的读书路。如今,我也是共产党员,我也接过了接力棒。1997年7月,我带领一个采访组去黔江地区采访扶贫攻坚工作。一天,在酉阳县毛坝乡苦草村采访,一个村民告诉我们:“我们村有一个女孩,叫刘建,小学毕业考初中,考试成绩全区第二名,可是家里贫穷,连体检都没有去参加,现在录取已过,好可惜哟!”“走,我们看看去!”我对采访组的同志说。在刘建家,我看着墙上贴着的刘建读书的两排奖状沉思,脑海里浮现出我小时候共产党送我上学堂的情景,在同行记者刘长发、罗华宇的鼓动下,我收下了刘建当我的孙女,并立即驱车赶到县中学,为我这位土家族孙女补办了录取通知书,由我供给她上学,一直到大学。如今,她已是硕士研究生,一位优秀的共产党员、国家干部。
熊庆元/重庆日报报业集团退休干部
【免责声明】上游新闻客户端未标有“来源:上游新闻-重庆晨报”或“上游新闻LOGO、水印的文字、图片、音频视频等稿件均为转载稿。如转载稿涉及版权等问题,请与上游新闻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