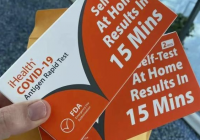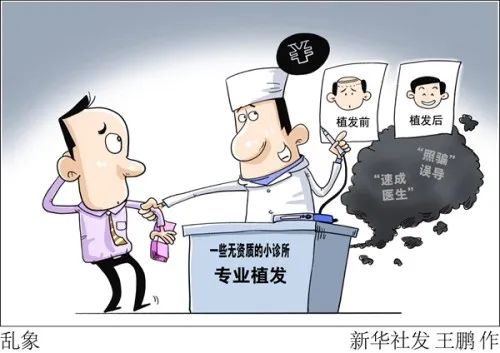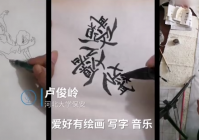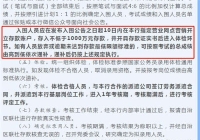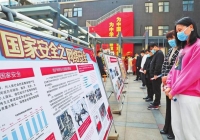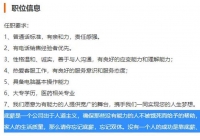女儿在上海工作这两三年,我们常劝她回厦门。奶奶每次听到就说:“傻瓜才回来,上海多好呀。”爷爷总会补一句:“那个郑计,还能找到吗?”
郑计是上海人。对我爸妈来说,他代表着一个值得感激的上海。
1973年夏天,爸妈带我去上海求医。那个年代,别说互联网,连电话都还没有普及呢。在上海,我们不认识任何人,要住在哪儿,找哪个医院,该怎么办?近50年之后,我以一般的处世原则,推演了几遍,还是觉得爸爸的办法,以及后来的际遇,太神奇了。
那年,爸爸在县级人民银行的基层网点上班。当时可没有六大国有银行,全国主要就是人民银行,职能跟现在商业银行差不多。银行后台有一块业务,叫“联行往来”,即各地银行在划拨资金时交换往来账务。具体操作,就是互相发送账单及所附凭证。账单装在印有宽红边的信封里,通过邮政局挂号寄送。
爸爸向做联行业务的同事打听,我们跟上海往来多不,认识什么人吗?也就是顺口一问,结果有个同事笑着说:“我知道上海那边,有个叫郑计的会计,不过没见过真人。”
我爸当然知道,他不可能见过对方。郑计这个人,就是账单上一个扁扁的红色小印章而已。对县支行来说,往来账目不少,但上海的账务不多。我猜,是郑计这个简洁务实的名字,容易让人记住吧。
总之,爸爸想办法联系上了郑计。上世纪50年代有“笔友”,如今社交平台上有网友。郑计在当时,什么“友”都不算,在未见面之前,只是一个抽象的承诺者。
郑计温文尔雅,总是微笑着说话。爸爸只是想麻烦他指指路子,推荐个招待所,介绍个医院什么的。有个熟人好办事啊。没想到, 郑计一见面就说:“走,住我家去。”爸爸吃了一惊,立即推辞:“那怎么行,随便住哪里都行,就是不能住你家,我们是一家四口啊。"弟弟不到3岁,也要看医生,爸妈是带着两个孩子一块来的。
郑计很坚决:“为什么不行,明明家里可以住,没道理要住在外面。”他提起地上的一个行李包就走,爸妈几番推辞不成,一家人只好跟着走了。
辗转来到一条旧街道,路面铺着石块,街两边是木板门面房。郑计的家在二楼,沿木梯转上去是屋子,咯吱咯吱的木地板,家具不多。一楼有个烧水的灶,不断有人拎着暖水瓶来打水。后来我才知道,那叫老虎灶。
郑计说,这里生活很方便。我老婆带着女儿在郊区上班,周末才回来。你们就安心住着。这段时间我在办公室先凑合。忘了在他家住了多久,中途我还到儿童医院住了几天。
记得有个周末,郑计太太带着两三岁的女儿回来了。爸爸讲:“这也太不好意思了,我们马上搬去招待所。”郑计说:“搬什么搬,简单得很啊。中间拉一道布帘,大家都睡地板,男的统统睡一边,女的睡另一边。这个办法不要太好啦。”他那个表情,像小孩子过家家一样,特别开心。
说实话,我至今也不甚理解,郑计何以如此热情待人。那么多人挤在一间,晚上起夜还没有卫生间,用的还是木马桶。回想起来,人的善意、隐私和界限,确实是不能脱离年代感的。
之所以讲起马桶,是我记得,每天一早就在窗口看到,有人拖着箱型人力板车,一路喊着收粪。家家户户都有人拎着马桶出门。接着,整条大街上,人人埋头刷马桶,洗刷刷之声,响彻天宇,蔚为壮观。
那段日子,郑计把我们当成了远来的亲戚。他还带着我们一家,去外头吃饭,去他单位参观。郑计的上班地点在外滩,那个银行的营业厅,布局像民房的天井,柜台环绕在四周,二楼也是一圈走廊,栏杆后是办公室。疫情之前我去上海,特意在外滩找了找,可惜没能找到。
这些事情,讲起来平淡如水,但爸妈每次提起,就仿佛有一片光笼罩着他们。我那次在外滩,边回忆边找那个旧址,也有同样感受,就像再次路过了温暖与明亮。

右一为郑计(图片由作者提供)
要离开上海了。那天一大早,郑计就领着我们出门,去照相馆合影留念。那是我和爸妈的黑白照片中,笑得最厉害最忘情的一张。那个照相师傅无比敬业,非要逗到所有人开心,才肯按快门。没料到,我弟弟不识逗,坚决不肯笑。师傅拿着一只橡皮黄小鸭,手舞足蹈,像个滑稽演员,把我们的上海之行,推到了欢乐最高潮。
分别之后,我爸与郑计还保持着书信往来。后来,我们连着搬了几次家,把地址给弄丢了。就这样,郑计遗憾地消失在时间与人海之中。
爸爸今年93岁了,眼底黄斑变性,听力丧失大半,还换了人工关节。这个状况,让他更易陷于往事之中。一提到上海,爸爸总是满脸感激:“还是应该找到郑计啊,再说一声谢谢。”
法国伦理学家安德烈说,感激是归属于喜悦的一种感受。感激是对过去的爱,是对存在过的一切的愉快回忆。感激是爱之上的爱,快乐之上的快乐。
这段时间,我一直关注上海的疫情,愿郑计一家,一切都安好。如果我们能隔着遥远的岁月,亲口对郑计说一声谢谢,那该有多高兴啊。
原标题:夜读|寻找上海人郑计
【免责声明】上游新闻客户端未标有“来源:上游新闻”或“上游新闻LOGO、水印的文字、图片、音频视”等稿件均为转载稿。如转载稿涉及版权等问题,请联系上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