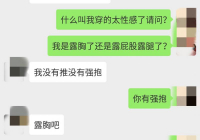夏孃孃
廖伟
9岁以前我担心廖叔叔会死,结果廖叔叔真的死了。9岁以后我开始担心夏孃孃也会死,经常半夜醒了发呆,看着窗外黑洞洞的天空,感觉那么无助。
大人们都以为我调皮不懂事,其实他们不晓得,在他们慌乱的一年多时间里,一直有双惊恐不安的眼睛在追逐着他们的背影。先是廖叔叔早晨在家门缝捡到一封匿名信,说“我认得到你,刀子认不到你”,念信的声音在发抖,“哪个写的呢?”他问夏孃孃,问话的声音也在发抖;紧接着梅叔叔、易叔叔也上门来了,说有人给区上(当时的区公所,非现在县区的“区”)告廖叔叔家吃不完的鸡整只整只丢,廖叔叔睡的是“刘文彩式的宁波床”。廖叔叔脸唰地白了。
“怕啥子怕!”夏孃孃是粮站的工作人员,遇事倒还镇定,断定是廖叔叔刚当了供销社负责人,有人“不安逸”在诬告。她宽慰廖叔叔:“嫁给你十年,娃儿生了三个,房子都是租的公房。除了新做了张床,另外两张床都是借的。是不是宁波床,到家一看就清楚了。”我觉得夏孃孃说得有道理,告状的人肯定在打胡乱说,因为我都很久没闻过鸡腿的香味了,哪里舍得整只整只鸡往外头甩?
可惜没有人向我求证这些,廖叔叔背起换洗衣物和铺盖卷,去区里上“学习班”了。几年前,我在“重庆晚报-夜雨”副刊上一篇短文中记叙了这一过程——
1975年某天,一个名叫河包的小乡场上,一个8岁的孩童闹着让妈妈买下一对小鹅。那是真正的雏鹅,羽毛也是细细的,黄黄的。
从此以后,每天早上,小孩就晃着细竹条,司令般指挥着两只小鹅出门觅食。孩子给两个朋友取了自己认为很美的名字:大母子、二母子……就这样,孩子和鹅一天天长大。终于有一天大母子下蛋了,不久二母子也下蛋了。什么是成就感,那就是成就感。
秋天的时候,孩子的父亲要出远门了,是进区里的“学习班”。孩子虽小,但是他从父母的恐惧中感受到了恐惧,“学习班”肯定不是一个好地方。
“杀只鹅吧。”父亲对母亲说,母亲看着孩子没有回答。孩子已经泪流满面。
鹅没有杀,依然不停生蛋,生蛋。
……
春节过后父亲回来了,他是用车送回来的。父亲得了癌症,瘦得没了人形。发病的时候,“学习班”开始不允许去医院,实在拖不下去了,医院检查已经是肝癌晚期。
两个月后,父亲去世了。孩子已懂得生离死别的含义,他整天整天地哭,肚子竟然胀得像皮球。
鹅最终还是杀了,这次,孩子没有流泪。
三十多年过去了,每次看见鹅,当初那个孩子就会想起父亲,心里就会流泪……
大家喊孩子“伟子”,就是现在秃顶的我。这么多年,我多想给我的父亲杀很多很多的鹅啊。
没错,廖叔叔是我的父亲,夏孃孃是我的母亲。河包场老老少少都这样喊,我和弟弟妹妹在家这样脆生生叫他们,他们总是很开心。父亲进“学习班”之后,母亲也整天愁眉苦脸起来,家里再也没有“廖叔叔”“夏孃孃”脆生生的叫声了。后来父亲在泸州医院检查得了癌症,母亲急忙把我们兄妹三个托付给邻居郭娘娘,去泸州照顾父亲。郭娘娘一字不识,善良本分,待我们胜过亲儿女,看着我们几个总是悄悄抹泪:“娃儿恁个小,啷个开交哟。”
从此以后我提心吊胆,担心父亲真的会离开我,死亡的恐怖居然成天折磨着一个未满9岁的孩子。但是我没有向任何人吐露过,郭娘娘和其他人摆龙门阵说有人吃活蟑螂医好了癌症,我就期望我的父亲也会吃活蟑螂。
1976年4月一天下午,我还在学校上课,被人拉出教室急匆匆往家里跑。两根木条凳架着家里的门板,门板上躺着父亲,剃头匠正在给他剃头,寿衣寿鞋都穿好了。母亲正哭着对父亲说:“是癌,是癌啊……”之前一直瞒着父亲的。父亲睁着眼,落不下最后一口气。有人说,他是放不下几个娃儿。我和弟弟妹妹跪在门板旁,母亲泪水大滴大滴地掉,她抚着父亲的脸说:“老廖,我不得去死,孩子我会盘大的。”就这样,我生命里第一个让我痛彻心扉的男人离开了我的世界。此后大约有十年时间,我常常做一个梦,梦中总是说父亲死是假的。
那时弟弟6岁多,妹妹4岁多,父亲去世一个月后我满了9岁,我的母亲34岁。看到这么一家,很多好心人都在叹息,心软的还会流泪。
但是,从那以后,我再没看见母亲流过泪。安葬了父亲,母亲一剪刀剪断了油黑的长发,剪掉的长发在墙上的铁钉上挂了很多年。她开始不停向有关单位写信,一有空就徒步几十里去区公所、区供销社、县政府、县供销社找领导,要为父亲讨公道。她敢闯官员办公室,敢掀官员的桌子,甚至还扇过官员的耳光。
母亲不再是和蔼可亲的夏孃孃。过年的时候,可能是看我们可怜,长辈们给了我许多压岁钱,大概有三四块钱。正月初几,我和一个街坊姐姐去县城,用压岁钱买了双白网鞋。结果遭母亲臭骂一顿,还把鞋子寄放在场上的商店卖。卖了四个月竟然卖不脱。于是,儿童节我穿上了白网鞋。可是,鞋子短了……
那些日子母亲每次出远门,依然把我们托付给郭娘娘一家。老实巴交的郭娘娘很为母亲担心,每天都在扳着手指数日子:“焦人哟,夏孃孃又出去好多天喽。”有一次母亲四天都没回到河包场,我开始担心失去母亲,开始梦见母亲死去。没有人知道,我天天在盼望那个熟悉的身影突然出现,再也不要离开我们。
这种担忧困扰了我至少一年半,到1977年底母亲不再出去了。那时刚刚恢复高考,母亲意识到孩子的前程更重要,“讨公道”的事必须放一放。在这小乡镇,母亲对知识的崇敬让人惊讶——她请我的班主任刘光雄老师教我学初中数学,还把我送去后来任荣昌中学校长的胡世春叔叔家里学习,甚至找河包小学懂点英语的成力老师给我讲ABC……这些老师都是我父亲生前的朋友,辅导都是免费的。
我的母亲在河包场创了两项“第一”:首个订阅儿童报刊的家庭。我们家订了《中国少年报》《儿童时代》《我们爱科学》,代价就是兄妹三人新年没有新衣穿。我就是读了叶永烈的一篇文章后,投出了人生的第一篇稿子;首个把孩子送到县城上初中的家庭。母亲求了许多人,托了很多关系,1979年我以借读的方式进入荣昌中学,弟弟小学毕业之后,也考进了荣昌中学。
最终我在1985年考上中专,弟弟在1989年考上大学本科,妹妹也在1990年招工考试中以全县第一名的成绩走上工作岗位。现在母亲已经76岁了,她对目前的状态还是很知足的,老人家说:“北京城有孙儿和外孙的家,重庆城有儿子和外孙的家,荣昌城有儿子和女儿的家,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满意!”

(作者单位:重庆晚报)
版 面 欣 赏

【免责声明】上游新闻客户端未标有“来源:上游新闻-重庆晨报”或“上游新闻LOGO、水印的文字、图片、音频视频等稿件均为转载稿。如转载稿涉及版权等问题,请与上游新闻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