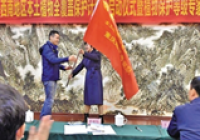后头有根梧桐树
梧桐树上站阳雀
阳雀长的五色毛
姐姐穿的五色衣
往回穿起吃大酒
这回穿起坐歌堂
歌堂已经五更了
姐姐歌堂放得了
……
公路下面的老式瓦房里传出苍老、轻细的歌声。这初冬的阴天,乌云在房屋背后的山上越积越厚,随时准备倾斜而下。歌声低沉,有说有唱,如歌如泣。一曲北碚东阳哭歌。刘支友在唱,如今也只有她会唱。

刘支友,东阳哭歌最后的传人
1
刘支友,79岁,东阳哭歌民间艺术唯一传承人。她估摸唱了足足70年,比她住的老房子还老,而这歌声,听起来比她本人还苍老。
从北碚东阳街道一直往合川方向走,十多分钟车程到了黄泥嘴村。顺一条很陡的岔路,走到底,是刘支友的家。

刘支友的家
屋侧几块菜地,葱绿的冬寒菜、白菜、莴笋,让人清新。两条黄狗早早跑上来,其中一条戴了一个小小的铁笼子,刚好把嘴罩住,叫得还是不依不饶的,显然,它不那么听话,“要咬人”,刘支友的儿子、58岁的明道洪在院坝的铁门前招呼我们。
走进铁门,一个水泥坝子,不怎么干净,几个大缸子占去不少地方,一家人在做红苕粉。坝子靠墙边铺晒了不少,白白的,像小孩的拳头那么大,一小块一小块的。端头是厕所,门开着,污迹斑斑,时不时散发臭气。
刘支友在正屋。上方一张木方桌,桌上横七竖八几根兔儿瓜,准备晚上吃;地上两个长条形老南瓜,刘支友中午吃了小半个。屋子凌乱。泥土的地面,不大平,几张凳子不容易放稳。桌边立着一个破旧水泥台子,有些奇怪,上面盖了一张更破旧的化肥口袋。
刘支友说,那是我炒菜的灶。上面布满灰尘,好像多年都没用过。 刘支友坐在靠门的塑料圆凳上。她穿一件大红裤子,白色的高领毛衣。 她站了起来,矮小、苍老、瘦弱,颤悠悠的,我生怕她摔倒。灰白的头发用三个铁夹子固着,因为她上午参加了一个商品展销会,有商家在乡村做推销,发了点米。她想准备点过年的东西。其实,过年还早呢。

刘支友在晾晒红苕粉
老人听力正常,说话吐字清晰。她说,没读过书,认不到字。但她能完整唱好几十首歌,有的词句复杂,要唱十多分钟;大部分三四分钟;还有的只能唱几句,曾经张口就来的唱词,在岁月的冲洗下,渐渐只言片句。
她说,没牙齿了,唱不好。我这时才注意到,她的嘴松松塌塌的。
她又说,“老四”走了,心情不好,没心思唱。今年重阳节,老人的四女儿生病去世。一会儿,老人又提到了“老四”,突然流露出悲伤,她一下好像把周围的一切都带进这悲伤中。
她突然提高声音说,现在病也多,高血压、冠心病,不久前还检查出肺气肿,唱歌也没过去好听了。
刘支友的儿子在一旁说:唱吧,慢慢唱。
老人又坐回那张圆形的粉红色凳子。她说起小时候的事情,语速飞快:“我妈是广安人,叫沈文玉”,“很小就没了妈,婆婆把我带大”,“我17岁结婚,10块钱安了个家,买一对猪,一口锅”……

刘支友用电饭煲煮饭
2
四周安静了,那狗之前还叫个不停,现在无声无息,躺在老人的脚边,温顺得大气也不出;头顶公路上的车子好多分钟跑过一辆,嗖一声就过了;一声鸡叫也没有,远处树枝上像有低声啾啾的小鸟。这初冬时节,乡村安静得如稻田里纹丝不动的水。
老人细声细语,像时间不紧不慢说着:“我小时候跟我妈和外婆学唱哭嫁歌,哪家人要嫁闺女,不管关系亲不亲,近不近,我们还没出嫁的女儿都会跑到对方家里,听新娘唱哭歌,听得多了,慢慢会了。”越讲越慢,声音越来越沉郁,几十年前的生活好像又回来了——嫁必哭,哭爹娘、哭哥嫂、哭姐妹、哭叔伯、哭陪客......以歌代哭,以哭伴歌,哭父母长辈的养育之恩,哭哥嫂弟妹的挂念之情;哭未来不安的新生活。“不哭,要被人嘲笑,被父母打。”
说着,说着,不知怎么,老人哼了一句,很轻,很模糊,接着唱起来:
天上明灯照宫明
爹妈催我出房门
亏得爹娘硬得心
奈何把儿留余生
今早我妈下牙床
脚踩我妈红榻被
手拉我妈心肠边
不留女儿把情诉
一曲二呼海棠开
海棠开花花又红
今年我妈将不同
……
这是一首哭嫁歌。

刘支友唱起东阳哭歌
低低沉沉的曲调回荡在室内,飘到寂静的院坝,好像又向屋子后面的山顶飘去,翻到山那边,到很远的地方去。山顶是兔儿寨,远远望上去,参参差差,墨绿一片,是竹林。
东阳哭嫁,长的可哭一个多月,少则三至五天。过礼至结亲前,出嫁的姑娘便坐床,放下蚊帐,手帕捂脸哭嫁,先哭父母、亲戚,之后,哭过礼,哭上梳,哭添箱,哭谢客,哭辞祖,哭离娘,哭上轿。哭上轿最悲,哭嫁的高潮,呼天抢地嚎哭。
这时传来火车的汽笛声,襄渝铁路在村子不远的地方,估计又是一列火车要分道了。火车来来去去,从这里到远方,又从远方回到这里。
3
刘支友一生也没离开过这里。
她不知道什么时候有了东阳哭歌,也不知道源于何处,她在哭歌中出生、长大,她说:很多年没有正儿八经唱了,歌本全没了,花轿、唢呐、花鼓也难幸免。

刘支友平时吃的菜,就从这片自种菜地里来
2008年,东阳哭歌被记入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老人和当时84岁的罗代碧一起被北碚区认定为“东阳哭歌民间艺术传承人”。
东阳哭歌,以“哭”命名,但并非都是“哭”,嬉笑怒骂皆有,红白喜事时演唱,在婚嫁、孝敬公婆、长辈去世,亦在生儿育女、拜新年等,哭嫁、哭丧尤常见。哭嫁复杂多样,哭丧亦如此,发孝帕要唱,挖井要唱,出殡要唱……
欢乐的哭歌也不少,生小孩、拜新年、收礼物、祝生日等。
那个时候,哪一天呢?忘了!村里有嫁女的,热热闹闹。出嫁前一天晚上,吃过“花筵酒”后,摆上茶点,搭起歌台,新娘与姑嫂、姊妹、耍得好的,轮流开始唱歌,在笑声荡漾、红烛闪烁中,迎接第二天出嫁。这是摆歌台,东阳哭歌最喜庆的时刻。
两张桌子合拢来
桌上织的绣花鞋
粮食礼品拿出来
新打剪刀玉铜钱
歌堂好坐头轮排
你把歌堂头排起
从大由小唱起来
一把金块十二双
丢了六双留六双
爹妈接到寿延高
哥哥接到买田庄
姐姐接到刷衣裳
弟弟接到读文章
关了轿门换了锁
一朵乌云遮了我
这首歌台上唱的歌,老人已记不起唱了多少回。她差不多一段换一次气,熟悉得可以用任何调子唱。有几句,她的嘴唇根本没有动,但声音依然清亮。
东阳哭歌还有骂,比如骂媒人,据考证,这源于土家族,不知什么时候被东阳哭歌吸收,比如这两首:
“人家丈夫像条龙,我家丈夫像条虫;哪年哪月毛虫死,斑鸠跳出画眉笼。不怨爹不怨娘,光怨媒人坏心肠。媒人肉放锅煮,媒人骨头当柴烧,媒人的皮当鼓敲。”
“哭声媒公与媒婆,一来一往操心多。千言万语是为我,其实你是想喝酒。千操心来万操心,你帮人家来说亲。过河翻山又越岭,为的使我成贱人。”
语义夸张,情感强烈,曲调戏谑,唱起来,轻松有趣。
4
老人的卧室在楼上,二楼端头,挨楼梯。门上了锁。
要不是那张雕花大床,我以为进入了一间拥挤的仓库。床特别的大,雕花繁复,保存完好,刘支友父亲送她的嫁妆。床前又是一张木桌,相距很近,上面摆了台老式电视机,然后就是各种瓶瓶罐罐,还有一个电饭煲,里面剩有中午没吃完的米饭。老人常常在上面煮饭,吃饭。

刘支友坐在她的雕花大床上,对面的桌上有一台老式电视机
卧室两边堆了很多箱子,上面都遮了塑料口袋。老人又慢慢锁好门,慢慢走下楼。
楼下还有一间卧室,比上面的乱。床上堆满了衣服,房间杂乱地摆了各种不知道的东西。夏天就住这里。现在天气变冷,就到楼上去了,屋子还没来得及收拾。
老人清净淡泊,自己煮饭,自己打理生活,无丝毫埋怨,唯有没了牙齿,很多东西不能吃。
斜坡边,用竹栅栏隔离开的地方是老人的菜地。蒜苗、莲白、莴笋,绿油油的。她说:自己种的,吃起来硬些。她挖地,播种,她担粪,扯草。坡太陡了,老人摔下来两次:“我以为自己摔死了,结果还活起,只断了两只手,现在好了。”
从地里出来,老人把栅栏门关得严严得,她很细心,动作特别慢:“过去没安门,背时些狗就在地里乱踩乱刨,几下就把菜整烂了。”

菜地的坡太陡,刘支友曾经在这里摔倒了两次
老人说,现在的生活好,大家更不喜欢哭歌了。“我啷个劝说娃儿们学唱哭歌,她们都不愿学。”
谁愿意哭呢?又有谁希望听到哭声呢?今天的人都爱笑。老人的儿子也说,哭的歌还是少唱。
过去,刘支友差不多天天和罗代碧对歌,那是多快乐的日子,每天去找她,两人摆龙门阵,摆到摆到就唱,从早到晚。“她唱一句我唱一句,她唱上段我唱下段。又说又唱。”哭歌让她俩幸福地笑了。
再过去,20年前,刘支友的老伴还在。他也唱哭歌。“我爸爸唱得好,还会几种乐器。”老人的儿子和大女儿都这么说。
老伴走了,罗代碧也走了有好几年,刘支友只有自己一个人唱。她过去不喜欢一个人唱,现在习惯了。自己唱,自己听:“一天念起耍,自个儿念起耍。”在地里拔草,一个人,哼几句;躺在床上,夜黑得没个底,唱一段;坐在院坝,独自晒太阳,望着远方发呆,不由得自说自唱。
“想到哪个,就唱哪个。”唱几句,说一段,过去的日子就在眼前,过去的人仿佛也回来了。
明年,老人80,大寿。她的儿子女儿希望我们到时来给老人祝寿:“多找些人来,闹热,她也可以多唱几首。”
唱啊唱,说啊说,这日子,唱着说着就走了;那岁月,又依依稀稀唱回来。刘支友就这个样子唱唱说说,过去也这样活着。

上游新闻-慢新闻记者 刘涛
【免责声明】上游新闻客户端未标有“来源:上游新闻-重庆晨报”或“上游新闻LOGO、水印的文字、图片、音频视频等稿件均为转载稿。如转载稿涉及版权等问题,请与上游新闻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