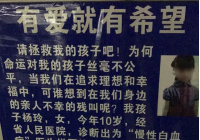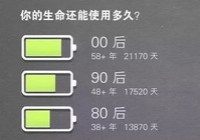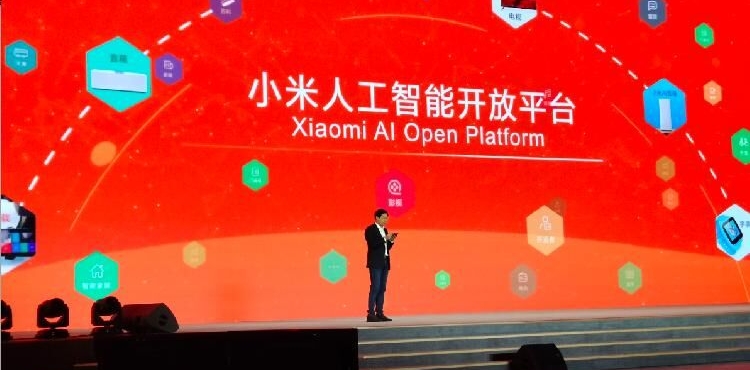10月18日中午,飞机降落在重庆江北机场时,萧慧蓉在父亲耳边说:“爸爸,我们到了。”萧家福一脸恍惚,看着机窗外陌生的一切。
这是萧家福第二次离开家乡,从台湾到重庆。第一次是72年前,从重庆到南京。
他拄着拐杖,慢慢走出机舱,工作人员扶了他一把,对他说:“欢迎来到重庆。”萧家福像个兴高采烈的孩子,频频跟工作人员击掌,“我是重庆人哦!这里是我的家。”
坐在大巴上,看着窗外的高楼大厦,他突然问身边的女儿:“这是台北?”
92岁的萧家福已经很老了,老到记不起刚刚发生的事,他的记忆就像斑驳的墙面,一块块掉落,只有“回家”这件事,几十年来在心里生根发芽倔强生长,成为一棵弯弯曲曲的藤。

在江北机场下飞机时,萧家福高兴得像个孩子。
回家:他一生都在努力
1943年的某一天,山河愈发破碎。
听说乡里来抓壮丁,16岁的萧家福躲到家后面的山上。这是重庆南温泉背后的一个山谷,南山山脉在这里形成一条狭长的谷地,一直延续到鱼洞。萧家福是家里的长子,下面有一个妹妹三个弟弟。萧家福说,他最终没能躲过去,被抓到中央军某部,先是当运输工,后来就被强制征了兵。但当时当兵的地方是在李家沱,离家并不远。
那时,家对于他就像那盏桐油灯,微光照拂,长夜不冷。
一年多以后,他经历了短暂的离乡。1944年11月底,日本兵打进贵州直逼重庆。萧家福回忆说,“政府机关停工,学校停课,年轻人们聚集在西南公路(川黔公路)上,只要看到有向贵州方向开的车就跳上去,要跟日本人拼了,赤手空拳。”
萧家福所在部队紧急开往贵州,他已经记不起战斗的过程,“伤员们一队队抬下来,没有医院,就在路边,女学生们用溪沟里的水烧开了擦洗伤口。”战斗很惨烈,萧家福以为自己再也回不去家了,谁知道他们在独山挡住了日本人的最后一击。家还在。
1946年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还都南京。萧家福这位帅气的19岁青年,唱着“风云起 山河动”的陆军军歌,随部队在朝天门登船。萧家福的颠沛流离,就从1946年的朝天门开始——上了船,就是一生。他以为这是一次普通的离家,那时的中国看上去一片光明。他回家跟父母告别,握着只有3岁的幼弟的手——70多年后,他衰老的记忆中,只记得有这一个弟弟。
1949年,萧家福记得,在那一年中,他随部队去了浙江、贵州、云南、海南,在贵州是离家最近的一次,他本以为可以有机会回家。然而历史一个细微的转身,就能改写几代人的命运。他的部队撤到了台湾,与很多不谙世事的年轻人一样,萧家福身后的门轻轻关上,那声音轻不可闻,要很久之后,他们才后知后觉。

年轻时的萧家福
撤到台湾,是另一段故事的开始。
萧家福改了名字叫萧运骞,“骞”字意即腾飞,他大概是希望自己的运气好一点。大儿子萧邦纳说,父亲为了回家,报考了装甲部队,因为这支部队会被派到金门,金门离大陆很近很近,就隔着一湾窄窄的海峡,鸡犬之声相闻。除了能眺望大陆,他的青年时代就在铜墙铁壁的装甲车里苦熬。他小学只念过两年,吟不出于右任《望故乡》这样涕泪滂沱的诗句,但他一定深深体会“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乡;故乡不可见兮,永不能忘”这样的悲戚。
40多岁的时候,萧家福跟一个台湾本地女子结婚。他终于接受了无法回家的现实。他努力生存、繁衍,生了三个女儿两个儿子,在台湾开枝散叶。不过他没有忘记老家的传统,他几十年里在家说着一口重庆话,儿子都按照萧家的字辈排行为“邦”字辈。小女儿萧慧蓉说,“父亲经常给我们讲,你们出生在台湾,但你们的根在大陆,重庆是你们的故乡。”
萧家福是典型的重庆男子,吃苦耐劳、韧劲十足。小女儿9岁时,因为受不了家里的贫穷,妻子开了他,萧家福一个人撑起这个家。从部队退役后,他到处打工,直到76岁在钢铁厂上班出事故断了腿,才彻底退休。萧慧蓉回忆:“爸爸是个固执的人,脾气不好,但这一路上都是爸爸在撑这个家。在退休之前,他没买过一双出门穿的鞋,都是穿部队和工厂发的鞋。”
寻亲:寻人启事贴满整条街
这是个被大时代拆得七零八落的家族。
1952年,萧家福离开大陆3年后,他的父亲萧汉卿过度劳累,吐血而死。也在这一年,因为土地不够分,萧家从南泉幺铺子搬到山后面的界石镇。四年后,母亲刘仁碧也过世。
1988年,两岸刚刚恢复交流,萧家福在重庆的弟弟妹妹托从台湾回来的远亲,在台湾联系上了萧家福。在离开大陆39年后,萧家福终于重新得到家里的消息。弟弟妹妹们来信,告诉他父母已经去世,三弟身患癌症……小女儿萧慧蓉回忆说:“爸爸接到那封信,那几天看一次哭一次。”萧家福想回家,但现实是他拖着五个孩子,最大的还未成年,最小的才4岁。那时从台湾回大陆,老兵们都要带很多电器和钱回来,但萧家福只有一身债。对于回家这件事,他沉默了。他唯一能做的,就是带着全家照了一张全家福寄回重庆,以解亲人们的思念之苦。那也是最后一张全家福,之后不久,妻子因为受不了穷困的生活,离开了这个家。二女儿萧彤芳当时已经上初中,记得很清楚,“那之前,他经常说重庆老家的事,那之后就再也不说。他不敢提。当时都认为荣民(退伍老兵)有钱,但他实际上没有,他不敢回去。”
子女们不知道父亲心中压着怎样的痛,但他们感受得到。“父亲把父母的牌位摆放在家里二楼,每天爬上去祭拜。虽然他嘴上没说要回去,但我们知道这是他心中的痛,因为身为长子却从小离家,也没法照顾家里,可能他才不愿提起。”大儿子萧邦纳说。
在那次短暂通信后,因为搬家和城市变迁,萧家福和重庆的亲人再次失去联系。
整整三十年后的2018年,萧家福已经92岁。这些年萧家福日渐衰老,记忆如琥珀,一个个被封锁,越来越模糊。五个儿女决定要帮父亲找到老家。萧慧蓉说,父亲一生漂泊,只有找到老家,父亲才有来处,只有找到老家,我们才知道方向。

电线杆上贴的寻亲启事
这是一次撞大运般的寻亲,确切地说,是两次,但冥冥中自有天意。
被寻者姓名:未知。萧家福已经记不起重庆任何一个亲属的名字,连自己有几个弟弟妹妹都记不清。寻找地方:模糊。他只记得自己住在巴县鱼洞仁厚乡,这是个1949年之前的地名。他们通过《今日头条》的头条寻人栏目发布了寻亲消息,上游新闻·重庆晚报慢新闻记者看到这则寻亲消息后,经过在原仁厚乡范围内一个村一个村的找寻,终于在南泉幺铺子找到了萧家福的表弟刘荣勇(见重庆晚报慢新闻5月11日报道《台湾老兵寻亲七十年》),通过他联系上萧家福的大侄子萧邦华。
在台湾方面与重庆亲属联系上之后,紧接着又是一次撞大运般的寻亲。萧家福的四弟萧家伦从1956年当兵离开重庆,后来定居成都,当年留的都是传呼号码,早已联系不上。他们在四叔曾经工作的新都机械厂附近,用在电线杆上贴寻人启事的原始方法寻亲。萧家伦的儿子萧光荣说,“我们一家已经不在厂区住了,但正好我一个从小长大的同学回厂区怀旧,看到寻人启事贴满了一整条街,那时刚刚贴出来一个小时。他要是晚两个小时也看不到了,会被环卫工清除掉。而我这个同学也是一个月前开同学会才拿到我的电话。”至此,萧家福五兄妹才全部联系上。
但寻亲的结果充满遗憾。二弟萧家禄于1988年去世,肺气肿,53岁;三弟萧家伦于2001年去世,糖尿病,63岁;四弟萧家贵于1989年去世,肺癌,46岁;妹妹萧家玉于2008年去世,80岁。兄妹5人,只有92岁的萧家福一个人还活着。
当得知这个结果,萧慧蓉悲从中来:“找得太晚了,太晚了,我怎么跟父亲开口啊!”
祭祖:他在母亲坟前求得原谅
5个月后,10月19日,小雨。
萧家福带着5个子女及孙辈一家14口,回重庆祭祖。所有的侄儿侄女都从各地赶过来相见,一行浩浩荡荡四十多人。
界石镇屋基湾,路窄、弯急,萧家福母亲的坟埋在离乡村公路一公里多远的一个坡上。
萧家福拄着拐杖,迷茫地看着周围的一切。萧家于上世纪五十年代搬到这里,这里是萧家的老屋,却与萧家福无关。乡间的石板路很窄,小儿子萧邦言站到路旁的庄稼地里,扶着父亲往前走,拐杖在石板路上戳得“笃笃”作响,缓慢而沉稳。
石板路的尽头,是萧家的老屋,黄土筑成的断壁残垣立于荒草之中,当年建的土墙房子早已经垮塌,旁边新修了一栋水泥砖房,属于大侄子萧邦华一家。萧家福母亲的坟在几百米外一个树林中,一路全是湿滑的泥泞。侄子们劝大伯别去了,路实在不好走。萧家福没说话,拄着拐杖往前走去,一位侄子赶紧抄起一把锄头在前面开路,把坑洞填平,小坡上挖几步台阶,清楚挡路的杂草树枝。大儿子萧邦纳扛着一根板凳跟在后面,走一段就让父亲坐下来歇歇。

为母亲上坟的路上
萧家福母亲的坟在一片坡地上,唯一一点平地被坟墓占据,人只能站在斜坡上,一不小心就要滑下去。萧家福坐在坟前,背靠在一棵树上,静静看着坟头的杂草。儿子和女儿们将买来的香烛纸钱取出来,萧家福点燃了香烛,两个儿子帮他一一插在坟前。
萧家福双手合十拜了几拜,膝盖一弯就要跪下去,大儿子萧邦纳一把搀着他,大声说:“爸爸你不用跪了!”大女儿萧琇蔓在一边哭了起来:“爸爸你别跪了,跪了起不来。”萧家福没说话,身子往下沉,缓缓跪下,两个儿子赶紧一个在旁边扶着,一个在背后撑着,生怕他从这个斜坡上滑下去。
萧家福双手合在胸前,口里小声说着话,渐渐有了哭腔,外人很难听清他在说什么。离家72年,他大概无数次在梦中和母亲见过,梦中的身影再清晰,也远没有眼前的一抔黄土和一片杂草来得真实。在十几公里外的山谷里,一个少年跟着母亲一起卖针头线脑,一起种红薯玉米,一起熬过堪堪能吃饱的丰年和饥肠辘辘的灾年,眼看着将成为家里的顶梁柱,却在某一个下午不知所踪,及至三年后离开重庆,从此音讯杳无。如今,萧家福跪在母亲的坟前,跟母亲说着话,是问候,是祈福,是诉苦,还是求得原谅?

萧家福执意要给母亲下跪
回来的路上,又到萧家老屋歇息了一阵,侄女拿来一张布,小心地擦掉大伯鞋上的稀泥。萧家福突然一下哭了出来,眼泪大颗滑落,双手颤抖,反复说着一句话:“太麻烦你们了,你们都是我的恩人……”吓得几个后辈连连摆手。
小儿子萧邦言对记者说:“这次回来,爸爸其实很抗拒,这三个月我们反反复复劝说他才得以成行。他不敢在我们面前表露自己的感情,但我们感觉得到,他想回来,但又觉得没脸回来,他觉得自己不孝。他从小离家,没能照顾家里,父母离世也没能尽孝,这些愧疚和委屈在心里憋了几十年。刚才他在奶奶坟前,就跟奶奶说着这些话。”
祭祖的第二站是南温泉背后山谷里的幺铺子,这也是萧家福出生和长大的地方。这里封闭、狭窄,山多地少,几十年前的贫穷显而易见。

萧家福和刘仁贵这对儿时伙伴
91岁的刘仁贵专门从十几里外赶过来,他是萧家福隔房的舅舅,如今也是风烛残年,走起路颤颤巍巍。“金元,你还记得我不?”金元是萧家福的小名,在刘仁贵的记忆中,他和萧家是邻居,经常和这个大一岁的外甥一起去挑煤换粮食,“那时候人小,挑一趟来回一天,只能挣3角米(约1.5斤)。”
萧家福握着刘仁贵的手,看了一会,涩然地说:“记不得了。”两个老人坐在院坝里聊天,刘仁贵说的好多事,萧家福有些能想起一点影子,偏偏就记不得眼前这个讲故事的人。记者问他,能否记起这是小时候生活的地方,他犹疑了一下,摇摇头。
他太老了,曾经心里的故乡,对他已是一个符号化的图腾,真实的面貌早已模糊不堪。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这样的悲哀,只能化为喟然一叹。小儿子萧邦言说:“要是早几年回来就好了……”
萧家福的父亲就埋在幺铺子对面的山上,山高、路远、湿滑,草木乱石挡路,五个子女都极力反对萧家福上去祭拜,怕出现危险。他们像哄小孩子一样哄着爸爸,萧家福委屈地说,“别人都可以去,为什么我不能去!”他反复以这句话来回应子女们的劝说。小女儿萧慧蓉说:“这样吧爸爸,我们先去老屋看一下。”
萧家的老屋并不是他们的祖产,萧家福的父亲是从大渡口茄子溪做小生意来到这里结婚生子,租住的汪姓人家的房子。如今老房子早已拆去,原来的地基成了一片玉米地,玉米地中只剩下一堵残墙。
萧家福拄着拐杖走进玉米地里,大家都在外面看着他。三个女儿悄悄跟两个儿子商量,让他们上山去,给爷爷上坟,“让爸爸留在这里,他一会就忘了。”

萧氏家族合影
萧家福站在那堵石块垒成的半截墙壁前,仔细地看着,似乎想从那里找到旧时的痕迹。半晌,他放弃了这种努力。儿女们和孙辈们拥着萧家福,在残墙前照了个合影。这是他们对老家最后的留影,从此相隔迢递山河,再要回来已经不大可能。
儿子们和堂哥堂姐们悄悄上山去了,萧家福像个孩子一样乐呵呵地坐着,已经忘了上山祭拜这件事。
他坐在老屋的残墙前,就像很多年前他还是个小男孩,在家门前静静坐着,盯着前面过人的小路,手里拿着一根喷香的烤玉米。

萧家福走向老屋的残墙
上游新闻·重庆晚报慢新闻记者 廖平 文 钱波 图
【免责声明】上游新闻客户端未标有“来源:上游新闻-重庆晨报”或“上游新闻LOGO、水印的文字、图片、音频视频等稿件均为转载稿。如转载稿涉及版权等问题,请与上游新闻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