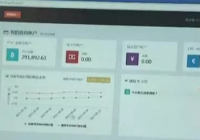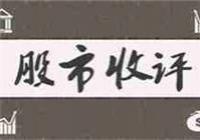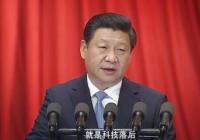新京报微信公号消息,学文科,就是自作孽吗?
你看,在现今人们的一种印象中,学文科的学生,教文科的教师,都似乎“低人一等”,全不及理工医等学科。
于学生而言,就业更难,工资更低;于教师而言,哪个学院的年终奖更高,哪个学院的大楼更派,哪个学院楼前停的私家车更豪,简直不言而喻,且悄无声息地见证着一种学科分层。
文科,即学科分类中的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于是被等同于“无用之学”,是不是?我们选择为其辩护。

《雅典学院》(拉斐尔)
学习有学科,研究有专业,但人类知识没有——它是完整的。而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在分工中所承担的是,以专业的能力到个体与社会中寻找事实、逻辑的使命,不管是价值中立的研究,还是价值干预的行动派。
然而,当今有一种担忧越来越突出:在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领域,学科的壁垒正在阻碍完整的知识交流,研究更精致了,更好看了,但处理重大且真正的问题的能力却在变弱。

《国学研究院》(陈丹青)
现在,回到我们自己身上,从一个“我是谁”的哲学问题出发,由我及他者,按序推进,前往更广阔的天地。
我们选择一些点面来认识一门学科,一个侧面:语言学考古那些理所当然的说法由来、伦理学寻求一个良善社会的秩序、社会学直抵最大的变量“阶层”、经济学在曲折中通往自由市场之路,还有法学对正义实践的不息探索,政治学在政治理念中对“乌托邦”迷思的解构。
只是一旦回到残酷的阶层流动这一现实语境下,改变生活境遇,向上爬升,“读文科无用”便显得正当。而作辩护像是回避我们时代的阶层流动状况,苍白无力。一个社会的阶层状况和向上爬升的需求,可见也决定着一种学科的地位。可不要忘记,它们参与的文明进程,对个体、人性、文化、伦理和正义的探索,是一种影响我们普通人判断和选择的力量。愿你更懂自己,不卑不亢,辨清世间迷雾,不被欺骗,还要头顶一片光。
哲学
“我是人,凡是人所具有的东西我都有”
我是什么?或者我是谁?让我们试着这样回答:我是一个人,是人类这一种群中的一员。或者就像古罗马剧作家特伦希奥所说的那样:“我是人,凡是人所具有的东西我都有。”
大约公元前500年,古希腊悲剧作家索福克勒斯在他的作品《安提戈涅》中以合唱的形式作过关于人的反思,值得我们在此摘录:
“奇异的事物虽然多,却没有一件比人更奇异;他要在狂暴的南风下渡过灰色的海,在汹涌的波浪间冒险航行;那不朽不倦的大地,最高的女神,他要去搅扰,用变种的马耕地,犁头年年来回地犁土。他用多网眼的网兜捕那快乐的飞鸟、凶猛的走兽和海里的游鱼——人真是聪明无比;他用技巧制服了居住在旷野的猛兽,驯服了鬃毛蓬松的马,使它们引颈受轭,他还把不知疲倦的山牛也养驯了。他学会了怎样运用语言和像风一般快的思想,怎样养成社会生活的习性,怎样在不利于露宿的时候躲避霜箭和雨箭;什么事他都有办法,对未来的事也样样有办法,甚至难以医治的疾病他都能设法避免,只是无法免于死亡。他拥有的能力超出一般人的想象,他善于运用各种资源,只是有时把它用于正途,有时难免用于邪道上。”
在这段著名的描述中,人所具备的所有突出特征都被集中起来了:控制自然力量以为我们服务的技术上的能力;猎取并饲养许多其他生命体的能力;语言和理性思维的能力;躲避恶劣气候条件的聪明才智;对未来和对威胁的预见力,以便事先想办法应付;能从疾病中康复的能力;尤其是正确地或错误地使用所有这些聪明才智的能力。
但或许真正最具人性的一点,正是索福克勒斯笔下的合唱队在人性面前所感到的惊奇。这种惊奇是钦佩、骄傲、责任和人类的业绩和罪行(索福克勒斯并未过多地涉及人类的罪行,但我们不应忘记,这个片段正对应于震撼人心的悲剧中的描述)在人类自身(内心)激起的恐惧的混合物。人类的首要命运似乎是:一些人对另一些人(不论是为他们的善还是他们的恶)感到惊奇。
然而,这种惊奇要产生的第一件事,恐怕是要为其他人命名,比如怎样称呼他们?为了便利,会不会用一种便签掩盖一个人的丰富性?
语言学
“取名字”与头脑顽固
我们替东西取名字的时候,就是在给它们分类。我们正在定名的事物,本身当然没有名字,而且在我们给它们分类之前,并不属于任何种类。
譬如有人要我们解释“韩国人”的外向意义。我们唯一的方法,就是指着现在活着的全体韩国人说:“‘韩国人’这个字,目前是指这些人,甲一、甲二、甲三……甲未知数。”倘若这些韩国人里生了一个小孩(可以用申代表)。“韩国人”那字的外向意义,本来是在申产生之前决定的,并不包括申。
申是一个新人,什么种类都不属,因为所有的种类,在归类时,都没有把申计算在内。可是申为什么也是一个“韩国人”呢?因为我们说他是韩国人。我们既然这样讲了,定了种类后,将来对申的态度,就有了相当的规定。譬如说,在韩国,申将永远会有某种权利;在别的国家,他将永远被看成一个“韩国人”,受有关“韩国人”的法律限制。
不幸的是,许多人对于自己怎样分门别类,并不是永远注意到的。他们没有注意到把张三称为犯人,不但没有顾及他本人许多真的特性,而且还派给他这个名词的情感含义所暗示的一切性质,却贸然对张三作了最后的判断:“唉,犯人总归是犯人,没有办法。”
硬把别人叫做“广东人”“上海人”“老小姐”“交际花”“穷鬼”“守财奴”“滑头”“书呆子”等,进而对他(她)们下一个草率的判断,或者不如说是起一种固定的反应,是一件何等不公平的事,我们在这里也毋需细述了。
而不论被贴上何种标签,我们都在渴望成为一个更好的人,并用自己认定的“好”“坏”标准衡量其他人。这可已经是一个伦理学问题了。
伦理学
“做个‘好人’真难”
“好”和“坏”这两个词,不只用于道德行为,也不单是用于指人。比如,大家都说足球明星里瓦尔多和劳尔是“好”的足球运动员,但却并不用这个形容词去表示他们在球场外捐赠任何陷入困境的人的善心,或是他们坚持说真话的品性。他们的“好”,仅仅表现在踢足球上,这一性质与他们的私生活没有任何关系。
我们也可以说一辆摩托车“好”,但不是指它来自德兰修女特蕾莎嬷嬷的赏赐,而是说它开起来非常顺手,有一辆摩托车应当具备的一切优点。
那么我要问了:为什么我们不用同样的方式来定义成为一个好人所必要的条件呢?这不是能解决我们之前好多页中提出的问题吗?
事情可没这么简单。说到好的足球运动员、好摩托车、好马等等,大部分人都能取得一致意见,可是要想大体断定一个人是好是坏,仅仅是作为“人”来看,也很难众口一词。比如动画片中的小纯,在家里,她妈妈以为她从来不做坏事,又听话又有礼貌,但在班上,所有同学都讨厌她,因为她老是乱开玩笑、挑拨离间。或如在奥斯维辛放毒气杀害犹太人的纳粹军官,在上级眼中是好的、正确的,但犹太人对他们必定会有不同的看法。
有时说一个人“好”,并不代表任何的好,甚至我们常常还会听到人们说:“某人太好了,真可怜!”我们的西班牙诗人安东尼奥·马查多,就意识到了“好”这种模棱两可的用意,并在其自传诗中写道:“当好意味着好,我便是好的。”他的意思是说:在很多情况下,说一个人“好”,仅仅表示其温顺、习惯于不反抗、不制造麻烦、别人跳舞时主动换碟,以及其他类似这样的事情。对有些人来说,做个好人意味着屈从和耐心;另有一些人则只对积极、新颖、即使惹人不高兴也敢于说出自己想法的人,才使用这一标签。
你是否想过,相较于好坏等伦理层面,一个人在全社会的位置更可能影响TA在别人眼中的样子?社会学中的结构决定论者就持这样的观点。跟着我们往下看。
社会学
“我们受制于在社会上的位置”
我们的教育体制产生了很多积极的效用,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学校为每个个体和整个社会提供其所需要的东西,包括社会化、文化传递、职业培训、文化创新和儿童保育。我们也很容易将教育的拓展,理想化地认为是会扩大所有人的自由和机会。
一个人的社会地位应当以其才智、技术、能力和学习为基础,而非取决于父母的地位。我们在很大程度上信赖学校能够公平地选拔出拥有适合不同职业能力的人并对其进行平等的培育。为了提供流动机会,我们选择发展支持公共教育。我们愿意相信:富家子弟若愚笨会一事无成,而家境贫寒的孩子因其聪明才智则会有所作为。
但与这一理想相反的是,教育体制也有助于限制机会,使学生们保持在同其家庭出身一样的社会等级上。例如,就像社会学家安尼特·拉里奥所指出的,父母的受教育水平会影响到子女:母亲受过高等教育的孩子,在整个学习阶段,比那些母亲受教育水平较低的孩子表现更出色。
这个例子体现出一个基本的社会学观点——我们所处的社会地位十分重要,它既能为我们提供有利的资源,也能带来我们想要的结果。然而问题在于,这个事例的结果,与我们的教育理想却是背道而驰的。
撇开教育所提供的机会,教育可能有利于永久性地维护不平等体系,其可能只对已经拥有经济、社会、文化资源的人有利。当然,有些人会视教育为达成个人自由、解放和公正的工具,但与此同时,教育的扩展和正规化,也符合工业化经济发展的需要。企业需要具备基本知识技能的员工,同时也需要能接受权威服从上级的职员。教育体制内的三类机制——社会控制、分轨和不平等的资源分配——有助于维护社会不平等,并在这一过程中展示了其差异造成的结果。
问题是,如果真的全是像结构决定论者说的那样,社会是不是就不可改变了?怎么解释千百年来的人类历史进步?换言之,即便教育的安排延续了既定的社会分层和结构,那些试图冲破安排,要生产出一种力量改变自身的努力,是否可能成功?经济学说可能,因为我们都有一种“效用最大”的选择欲望。
经济学
“如果不是效用最大化者,就不正常了”
假如一个杰出的电脑专家发明了一个终极快乐机器。你躺在床上,电极附在头上,身体被各种人工设备包围着,比如静脉注射和其他高科技东西。此时电脑取代了你的大脑。但你无须恐慌。电脑是完全友好的,它是你的朋友而不是某种占有你灵魂侵占你生命的机械怪物。
它知道你的偏好,明白你的价值取向,了解什么让你不快乐,它可以运用这些信息创造一个符合你愿望的理想生活。
由于你和电脑连为一体,你不会意识到自己躺在床上、头上插满了电极且看起来很痛苦,因为你确信电脑产生的画面是真实的。你在夏威夷冲浪,赢得摩纳哥大奖赛冠军,证明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是错误的——任何遐想你都能实现。现在的问题是:假如你对以上情况都很满意,并且和电脑连起的身体也被照顾得很好,你愿意下半生都和电脑一起生活吗?
回答前请想清楚,这个机器是一个纯粹的效用最大化者:不管你偏好清单(即序数排列)的最顶端是什么,它都会实现。由于实际生活恰恰就是各种体验的汇总,这个机器也就创造了符合自己愿望的一生体验。现在,我们提出一个更大胆的结论:如果你拒绝和电脑一起生活,你的这个决定就和“个人是效用最大化者”的经济学观点彻底相反了。
那么,你是否会和这个效用机器连在一起呢?如果答案是愿意,那么在新古典经济理论中,你就是有效率的效用最大化者(因为把自己和电脑连起来是实现效用最大化的最好方法)。如果这么做是值得的,你就已经发现了一个关于人类天性的简单理论。该理论具有一致性,并可在任何经济学教科书里找到。但按照这些教科书的说法,如果答案是否定的,你就有问题了。
如果答案是肯定的,人人都追求最大效用,欲望被释放的自由会不会打破秩序?有人说,自由和秩序是矛盾的,但因为正义的存在,以及我们对正义的不断修正和调试,两者恰恰构成了文明的两面。看下面的法学是怎么说的。
法学
“正义就像真理和美一样”
正义就像真理和美一样,所有人都爱,但却都又很难说清它到底是什么。一种可以将其复杂含义梳理清楚的方法,就是区分我们通常在使用这一概念时所要表达的不同意思。
我们用到正义(justice)的第一种情况,似乎是将其等同于法律(law)。原因在于:正义所关注的焦点,是确保人们得到他们有权得到或理应得到的东西,而这些似乎也是所有法律体系中最具代表性的法庭关注的焦点。不然法庭还能起别的什么作用呢?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把“正义”与“法”作为同义词来使用;这一做法反映出,正义与法之间的联系存在于其本质中,因为法律自身就涵盖了其目的。
第二种情况往往出现在“公正执法”的标题下。据此,如果一个人得到了他有权得到的所有东西,或者为他的罪行受到了法律的惩罚,就可以说他得到了正义。因此,公正执法是一个评判性的概念,可以通过比较现实的结果和理想状态下应该出现的结果,来评价某一项法律裁决。
我们使用“正义”的第三种情况,需要我们对法律抱持一种批判态度,置身法律之外,更加理智地看待它,因为这种态度源于假定法律本身也可能是公正或者不公正的。所以一个人可能依法获得了正义,但如果法律本身是不公正的,或者它使法官作出了不公正的判定,法律的裁决就可能也是不公正的。这种关于正义的更为激进的批判性观点,有时被叫做实质正义(substantialjustice),在大多数情况下也被称为公平(fairness)。它依赖于三个基本观点。首先是平等(equality),其次是应得(desert),再次是道德或自然的授权(moralor natural entitlement)。这三点都有疑问,但却是我们在进行有关法律和社会安排的讨论和争执中经常用到的——极有可能每天都会用到。
与平等和自由一样,正义是迷人的。那么问题来了,这些在文明史上耀眼的词汇,究竟可不可以完美实现?社会实验试图用“乌托邦”解决这样的问题。然而,平等、自由、正义,更可能只是一种过程,而不是结果。临末,我们是时候来听听政治学是怎样评说“乌托邦”的了。
政治学
“乌托邦会封闭头脑,理念则能开启思路”
有人向波兰当代哲学家科拉柯夫斯基提问:他最愿意住在什么地方。哲学家凭他一贯的幽默感,提供了一个标准答案:“我愿住在高山之巅原始丛林深处的小湖岸边,那房子坐落于曼哈顿麦迪逊大街与巴黎香榭丽舍大街交汇的街角上,而这片田宅归属于一座宁静的外省小城。”看见了没有?这就是个乌托邦:一个不存在的地方,但那不是因为我们不够慷慨,或是没有足够的胆气来创造这样一个地方,而是因为乌托邦原本就是一幅拼图游戏,构成拼图的片断互不相容。
因此,我不希望你对乌托邦太过着迷,就像我不愿意你沉迷于电视连续剧一样。相反,我非常期待你能够具备政治理念,因为乌托邦会封闭头脑,理念则能开启思路;乌托邦会通向无所作为和毁灭性的绝望(因为没有什么事物可以如设想一般完美),理念则能激发参与的欲望,使我们永远保持积极主动的心态。当然,现在我跟你谈的是政治理念,而不是道德理念、美学理念、宗教理念,或其他类别—实际上,每一类都有其独到之处。那么怎样辨识政治理念呢?首先,政治理念永远不是绝对的,因为不同类型的政治理念总要并列一处,而且每种理念都有它的禁忌症候。
如果我们生活在更好的社会中就能成为更好的人,那实在是太好了;倘若我们依然如故,还是那样的贪婪、吝啬,那么政府的法律和惯例也还能够发挥作用,帮助弥补我们的缺点,或者提出替代方案,让我们的缺陷不至于造成重大破坏。乌托邦近乎谵妄,提出培养“新人”;政治理念则更乐意扶助“旧人”,因为他们更有耐性,更多一些责任,更少一些冲动。
你是不是觉得这种态度过于随波逐流?我认为随波逐流者永远听从可行性的安排,眼光不够长远;具备政治理念的人与其不同,他们努力谋求可能性,尽管他们知道这并不容易,况且我们永远也不会感到满足。所有的政治理念都是循序渐进的:当我们达到新的水准,也许过去看起来近乎神奇的事情现今就会成为现实,但是我们提高的不是满足感,而是需求。
作者 | 萨瓦特尔等北大出版社“大学的邀请”系列图书作者
本文由北京大学出版社授权,整合自《哲学的邀请》第三章、《语言学的邀请》第十三章、《伦理学的邀请》第二章、《社会学的邀请》是十章、《经济学的邀请》第四章、《法学的邀请》第二章和《政治学的邀请》第九章及尾声等。标题为编者所加,整合有增删。
原标题:学文科自作孽?无文科不可活
【免责声明】上游新闻客户端未标有“来源:上游新闻-重庆晨报”或“上游新闻LOGO、水印的文字、图片、音频视频等稿件均为转载稿。如转载稿涉及版权等问题,请与上游新闻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