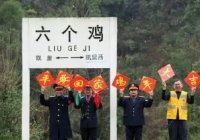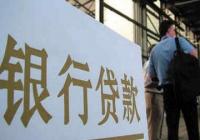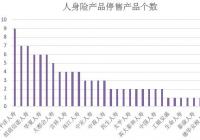1924年夏,(左起)梁漱溟、王平叔、黄艮庸、朱谦之从左至右在北京某公园合影。
近日,西南师大出版社推出李炼、王治森、王家伟编注的《王平叔致梁漱溟的二十八封信》,这些写于1922-1940年间已经泛黄的旧式书信,让一位重庆先贤王平叔的形象浮出水面,中国近代史上一些大人物如张澜、陈铭枢、白崇禧,都和他有过交集。
出生于原巴县姜家场的王平叔,是一代大儒梁漱溟先生最早的贴身大弟子,参加过北伐,也是川渝五四运动和乡村教育的先驱人物,曾创办北碚勉仁中学,1940年42岁病逝并葬于校园中。
本期专栏我们将还原这位“知行合一”的重庆大儒和一代乡贤的文化形象,揭秘他和师父梁漱溟在山东办学的一些往事。
办学
话说那重庆巴县姜家场青年书生王平叔投师心切,从川北南充中学教师任上向北出发,一意孤行。而北京崇文门缨子胡同的梁漱溟先生又广撒英雄帖,招徒心切,两人一拍即合。
王平叔不但自己去了,其风尘仆仆的节奏,还“裹挟”了几个成都高师的大学同学。1976年,83岁的梁漱溟先生在《略记当年师友会合之缘》一文中,忆及当年门下弟子时,对平叔尤为推重:“平叔毕业于四川高师……决心从游于我……张俶知、钟伯良、刘砚僧等姓名,盖皆平叔在高师同学友好,有动于平叔之风,亦先后北来从我,……惜伯良、砚僧故去均早。—似均不足四十岁。而平叔之故(1940年)亦只四十二三岁而已。平叔在吾侪朋友中最具有主动力,恒能主动帮助人,无论同辈后辈莫不身受其益。回忆我所得朋友的帮助,屈指而计,必首推平叔也。”
1923年春,王平叔身在北京梁漱溟、熊十力两位大师主持的梁门师友团体,第二年夏天,师友们接到一个大活,随梁漱溟赴山东曹州筹备曲阜大学并创办省立六中(现菏泽一中)高中部。王平叔外孙李炼说:“他们之所以接到这单大业务,是因为当地有两个梁漱溟的铁粉:一个是梁的学生陈亚三,一个是当时山东省议会议长兼省立第一中学校长王鸿一,是亚三的中学老师。1920年,亚三在北大听梁先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讲演,暑假回山东为王鸿一转述,王大喜,觉得很能解决他的思想问题,马上赴京请梁先生第二年赴济南讲演,两人相见恨晚,就合作了办学一事。”
这是梁漱溟第一次走出书斋“首度奔赴理想”“再创宋明讲学之风”。他认为“教育应当是着眼一个人的全生活而领着他去走人生大路,于身体的活泼、心理的活泼两点,实为根本重要;至于知识的讲习,原自重要,然固后于此”。他在招收王平叔等门生时就说过“大家对我自由纳费,不规定数目,即不纳亦无不可”。这次曹州办学的“收费标准”,他又“故伎重演”,其实就成了一个“不收费标准”:“我们想打破从来学校一例征收同等金额之学费膳宿费的成例,而改为或纳费或不纳费,纳费或多或少,一视学生家境如何而自己乐输。这也就是不愿靠法律对待人而彻底地信任天下人!不过在预算上我们也有个标准总数,在不足数时则向各家长征补之……却要声明一句:虽然学生纳费多寡不等,而我们待遇上则没有分别,都是一律的”。
失败
这种收费的结果,梁先生可能也有所预感,所以最后强调:“这样办去,究竟办好办不好不敢知,不过我们决意要试着作,想从这里替教育界打出一条路来”。现存王平叔1925年致恩师的两封信,先后勾勒出曹州办学最后的结局。
第一封“一月五号”的信,“漱师:谅已至京,途中必大受苦,望善自养息也。郭先生必欲辞庶务,实困难。另觅不易得相当人,由同人分任亦不对。嗟乎!为曹州人办学校,曹州人反要辞去,使吾侪作客者为难”。可见恩师已打道回京,留下一个烂摊子,他们只好留守“揩屁股”,连“庶务”(后勤总务)都没人干了,可见学校一片混乱。
约半年以后的第二封信,写“山东省立第六中学校”信笺上:“师座:与亚三信,读之泣下(读信感师一向之忍辱负重,诚切弘远也)。亚三但着眼在事情之妥贴,而忘却吾人平日之志行,义利之辨遂尔滑突,依违游移,此为大错。前日之痛责者以此,我辈惟因负荷此事,而后世间之一切艰难困苦忧患屈辱,乃始麇集我身,无可幸免。不负荷此事或可有饭吃,一有负荷之志,则已便决心去捱受饥饿,死而不辞也。诚心事天,前途如何,待之而已。惟我辈自勉之。再过五天此间事一切结束,一年之局,至此而终”。
“一年之局,至此而终”,系指1924年暑期梁漱溟师友团队赴曹州办学,到1925年暑期全部撤出,大约一年时间。平叔用此八字,总结了恩师生平第一次大动作。李炼说:“梁先生这次办学之所以失败,据梁漱溟次子梁培恕考证,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梁漱溟)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二是办学理念与人际关系的矛盾。比如收费问题,据当年曹州中学学生王先进回忆:开学第一个月没有问题,第二个月主持伙食的人就为难了,第三个月办不下去。那些不出钱的学生‘还嫌只有面食,没有大米’,并声称他们正是看了招生简章上说可以不交费才来投考这个学校的。”
当然,除了钱,还有政治原因。开学未半年,国内政局风云突起,梁漱溟在当地最大的政治靠山王鸿一,卷入冯玉祥和曹(锟)吴(佩孚)之间的军阀混战,战祸将起,曹州人心惶惶,梁先生还曾责问王鸿一,悔悟和他的合作,所以自己先回京,把干满一个学年的工作留给朋友们。
后来,他在给门生的书信中陈述了这些原因:“此即漱溟所以先诸兄而去,秘密不以相告,至今日乃向大家说明之故也”。作为一个古风犹存的儒者,他检讨自己前往曹州办学有失身份:“往在民国初年北京大学聘请马一浮先生任讲席,马先生谢曰:礼闻来学不闻往教。当时闻之颇以为是笑话,今乃深悟古语之所谓。而我之于曹正所谓往教也。”
这次打击之大,作为一个“一日三省吾身”的谦谦君子,他也把自己骂得体无完肤:“然回视以前心理已大不同。以前一派豪强自以为是的态度已无有。什么‘一身系中国前途’、‘言动出处天下观听所系’、‘牺牲一切赤心赤胆以天下为己任’,真是大言不惭,一派梦话。自欺自蔽犹懵然不知。虚矫气、豪侠气,与暗中作祟之大欲望,真伪混杂。每每自言自语‘我是牺牲一切的’,自命慷慨负荷,此实最谬、最自蔽处。来曹诚为有所牺牲,然念念不忘,正是牵挂甚重,不肯牺牲。且说个牺牲,正是有所图,暗中有鬼而不自知。以是明明晓得自己生活没路子,无把握,而有此一股假正气在,竟不知回头”。
师友
梁师父已经下了矮桩,但王平叔诸生本着梁门儒者耿介直谏之风,还是没放过老大。充分体现了梁培恕总结的梁门师徒“亦师亦友”的关系:“还不是老师以朋友待学生,是学生当老师之师”。他说:“1924年父亲去办曹州中学高中部,这是他第一次自己出来‘挂帅’做事。仅半年就无法进行下去,自己先回京,把干满一个学年的工作留给朋友们(共十余人)。信中愧悔自责,恐怕生平无过于此了:‘漱溟今负疚怀惭伏地再拜,不敢仰视,嗫嚅陈词于诸兄之前,求加罪责……’既自责‘昏妄不自揣量’又复自承‘半生盖未有无一毫自信力如今日者’。这件事对父亲诚然是一大挫折,对朋友团体也影响至剧。王平叔、黄艮庸都有信批评老师。王信引王船山语间接批评父亲做事轻忽。‘人静而审则可动,故天常有递消递长之机,以平天下之险阻;而恒苦人之不相待耳’。”
熊十力有信致王平叔,说办学失败一事,朋友团体亦应自警,有帮梁先生圆场的意思。王平叔读后,直截修书一封给梁公,怼将回去:“漱师:……真师适示彻者,哀痛吾侪之情至矣。吾侪此时尚有何话说?借来曹之种种扑倒观之,不实心踏地重新死炼苦修一番,将何以哉?吾师病实不轻,有转机否在真能一下回头不耳。”
平叔的批评,还算温和,梁门另一高徒黄艮庸长信一封,更是火力全开,针对梁先生的“错误”和试图改过自新的措施,逐一批评。梁先生对两个徒儿的批评,是何态度呢?梁培恕说:“1976年8月父亲在黄艮庸信的信首页写道:‘此信重要应保存之。’末页又写道:‘平叔、艮庸从游于我,皆胜于我。如此信所教我者,皆不易之道也’。”
师生之间有批评之意,更有诗文之情。1925年5月13日,对师父火力全开的黄艮庸对师兄王平叔诗兴大发,平叔把此诗抄给师父分享:“艮弟昨夜赠彻一诗,词意清纯,高古情深。《咏竹一首赠平叔兄》冉冉孤生竹,结根于磐石。风雨晦乾坤,我心良匪席。长叹望修竹,枝柯幸弗折。守身如执玉,乃有固穷节。岁寒思至友,独立凌霜雪。但愿上阳生,毋使春景绝。”
来而不往非君子也。第二天,1925年5月14日,王平叔又把自己给师弟的和诗,再寄给恩师分享:“漱师:昨日寄一信到邪?中有艮弟赠彻诗。昨晚答诗成,并附一简云:‘答诗呈上,我终腾突,不能如弟之安详和缓。奈何天寒岁暮,孤舟漾漾,与弟共载浮海寻漱师去也。《答艮弟且自惧励》朝发昆仑颠,俯拾一卷石。暮投沧海中,澜漪如卷席。突闻长风发,潇潇枯枝折。山川遂改异,栗栗深秋节。天寒岁云暮,孤舟迎霜雪。仰首横空望,渺渺云间绝。’”
文/图片翻拍 上游新闻-重庆晨报记者 马拉
【免责声明】上游新闻客户端未标有“来源:上游新闻-重庆晨报”或“上游新闻LOGO、水印的文字、图片、音频视频等稿件均为转载稿。如转载稿涉及版权等问题,请与上游新闻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