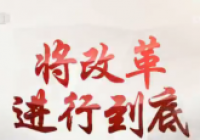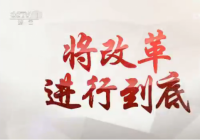北大和保安的化学反应
“只要能去北大,有机会在重点大学旁听,哪怕是打扫卫生我也愿意。”
在2017年高考季,“北大保安”成为热词。一份得到北大保安大队长王桂明认可的数据显示,到2016年,北大保安考上大学的数量增加到500人,其中大部分是大专,少量本科,还有12名研究生。
近日挂在网上的一则北大保安招聘信息,专门提到了这一点:“(北大保安)还可以参加北京市的成人高考和自考,做到工作学习两不耽误。”“近几年来,北大保安大队有百余名保安员靠自学和成考,拿到大专或本科学历。”
到北大当保安
江斌是在2011年成为北大保安的。
在到北大报到一周前,江斌在网上看到一条“保安北大讲《论语》”的新闻。
一位名叫谭景伟的高中毕业生,在北京当了十年保安,2002年开始读《论语》,2006年写成20余万字的《论语布衣解》,后改名为《一位保安的〈论语〉心得》出版。2007年5月,谭景伟在北大讲论语,有人说他“糟蹋经典”,他说自己“仰不愧天,俯不愧地”。
江斌读着他的故事,反复咀嚼这句话,心神震荡。1988年出生的江斌来自西北某省一个偏僻的村庄,这里地处青藏高原东麓。高中毕业后,他在西安某民办学校读大专。有时候,他对着校园里的湖发呆,满心不甘。这个民办大学发的学位证国家不承认,他好不容易走出大山,依然只能挣扎在社会底层。
他看到了一个励志故事——湖北广水山区的高考落榜生甘相伟,在北大当保安期间成功考取北京大学应用文理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并在四年后因出版《站着上北大》一书而声名鹊起。
甘相伟在逆境中艰苦奋斗的故事,成为了中国高考作文十大素材之一。他本人被评为“中国教育2011年度十大影响人物”。
2010年,江斌决定要改变自己的命运。
“只要能去北大,有机会在重点大学旁听,哪怕是打扫卫生我也愿意。”江斌向《中国新闻周刊》回忆自己当时的心情。
在未名湖巡逻了一天,江斌被分配到东门站岗。八小时工作制,三班倒,早班是7点半至下午两点半,中班是下午两点半至晚上10点;夜班是10点至次日7点半。由于缺人,需要经常加班,一小时加班费3.7元,最忙的时候连续24小时都无法休息。
刚工作那段时间,江斌好几次想要放弃。他发现,在北大当保安不像想象中那么美好,要想统筹好学习和工作,需要付出比常人多几倍的努力。站岗时无法开小差,即便下了班,时间也无法自由支配,需要在宿舍备勤,即不经请假不能擅离宿舍。
几周后,他渐渐摸索出了自己的学习方法。由于四人一班岗,两人一组,在门口站两小时后,轮换为传达室内的坐岗,负责登记来访游客的身份证,坐岗和站岗交替进行。于是他利用两小时的坐岗时间读书学习。 那时候,他还没有明确的学习目标和计划,只觉得知识重要,于是拼命读书读报。
他书读得很杂,文学、哲学、法律、历史均有涉猎。还常有教授把自己出版的著作或闲余的书籍送给他们,他都会认真去读。
由于工作努力,他被提升为班长,随后调至东北门站岗,手下管着十个人。
成为班长后,他更忙了,几乎没有时间休息和读书。两个小时的坐岗期间,他要分配工作,协调突发状况;如果保安和人产生矛盾,他还要调解;晚上要查岗和巡夜;周末更忙,遇到游客众多的日子,经常焦头烂额。
2011年4月,因为表现优异,队里要提江斌做分队长,推荐他申报北京市保安系统先进个人。他交了申请,也通过了。但对于是否做分队长,江斌很纠结——如果做,工作会更忙,投入会更多,离他的大学梦可能越来越远;如果辞职专心学习,又没有收入支撑。
恰在此时,东北门打扫卫生的一位老人给了他一个建议。
这位大爷是陕西省某小学退休校长,儿子在北大读博士后,现已留校做讲师。他推荐江斌去各院系办公楼里当保安,工作较保卫队更清闲,室内坐岗,学习时间多。
北大在安保工作上采取外聘制,具体业务外包给北京市保安服务总公司文安分公司和各个物业公司。其中,保卫部隶属于文安公司,归管部门是北京市公安局,队长王桂明同时也是文安公司的副总经理和工会副主席,下辖保卫大队和各分队,主要负责校门的驻守和校园内的巡逻工作。
而大部分教学楼和院系办公楼里的安保,则由物业公司负责。 每个院系办公楼一般配备3~4名物业,分属不同的物业公司。与保卫队的保安一样,这些物业人员同样是合同工,没有三方协议,没有五险一金。
但对于江斌而言,这的确是更好的选择。5月,江斌没有等到20号领工资,就和一帮在东北门站岗的兄弟一起去了法学院,成了一名物业管理人员。
江斌终于有了更多的时间学习。此前他就对法律感兴趣,又在法学院工作,就利用得天独厚的资源,在不上班的时间旁听。让他印象较深的有朱苏力教授的法理学、张千帆教授的宪法,以及薛军教授的民法等课程。
每天,在上午跑完步后,江斌回到宿舍或去二教自习看书。中饭后回宿舍练会儿书法,然后继续看书。晚饭后开始上班。他值晚班,从下午5点到晚上12点,在法学院凯原楼的前台值守,负责整理老师的快递,收发报刊杂志,做一些杂活。
他喜欢写书法,尤其是行草,大气自由。以前在东门和东北门站岗的时候,他都不忘带去自己的文房四宝。
有一天,一位法学院的在职研究生跑来跟他说:“我观察你好久了,如果真的喜欢法律,不如系统学习一下。”法学院的老师也建议他,与其这样旁听,不如考法学院的成人自考本科,踏踏实实地学。
他于是咨询了北大继续教育学院,领回了一套成人考试的教材。他开始给自己制定严密的学习计划,早上起来朗读,因为清晨的记忆力最好,适合背唐诗和文言文。下午复习英语语法,晚上上班间隙看《民法》,不懂的可以随时问路过的老师和同学。2013年9月,他顺利专升本,成为一名北大法学院的在职本科生。
“看你挺上进的,想帮帮你”
和江斌不一样,张俊成一开始并没有考学的想法,人生的转折源于一次遭遇外国人的经历。有一天,正在站岗的张俊成拦下了7个进北大观赏的外国游客。由于语言不通,他只能试图用中文解释他们不符合进校条件。不知道外国人是否听懂了,但见他们转身走到马路对面,对他竖起了大拇指。
他正要扬起笑脸,不过一瞬,外国人的拇指朝下,做了一个鄙视动作。张俊成顿时感到血冲向了头顶。
张俊成下定决心要学好英语,不仅是为了维护自尊,更是出于北大保安与外宾沟通的需要。北大保安大队大队长王桂明在接受采访时曾经提及,1994年文保保安公司入驻北大时,保安经常遇到外国人问路的尴尬,虽然都是一些简单的词汇,但大多只有初中学历的保安也听着像天书。
后来,王桂明发现有的保安开始在业余时间自学“英语100句”。他向公司建议为保安创造一个好的学习环境,得到了支持。
2016年,《鲁豫有约》委托哈佛毕业生彭朗去北大测验保安的英语水平。被采访的四位保安,有两位不会英文;一位口语发音地道、流利,用英语聊天没有障碍;还有一位口语发音一般,但能顺利解决老外遇到的问题。
在被老外挫伤自尊的第二天,张俊成就去对面的早市,买了两本初中用的英语教材。他底子薄,基础差,100分的初中英语试卷,他只能考7分。刚开始自学时瞎念瞎背,没有章法。
一天傍晚,他正在传达室里读英语,英语系的教授曹燕路过,停下来听了一会儿,说:“小伙子很上进,但你这种学习方法不仅学不好,还会学坏。”
过了一段时间,曹燕突然把张俊成叫到了自己的办公室。桌上摆着两张听课证,一张是北大英语强化班,一张是成人高考考前辅导班。
对于英语强化班,曹燕推荐了四门适合他的基础类课程。22年后,张俊成还清清楚楚地记得这四门分别是许国璋英语、新概念英语、英语精读和听力。
曹燕看着他,说了一句话:“你要想改变现状,光靠自己学是不行的。”
张俊成于是开始在老化学楼、老地学楼和西门之间奔跑。上午7点开始上课,中午12点临下课前,他提前离开,心里默数着时间,从教学楼跑到西门要八九分钟,快一点的话七八分钟。12点一到,他已经换好了衣服,站在西门的岗亭上,由学生变成了保安。值班到下午3点,他又匆匆忙忙跑去上下午的课,直到5点,再次跑回西门。
张俊成住在6个人的宿舍,每晚10点熄灯,一开始,他在熄灯后偷偷蒙在被子里拿手电筒看书。后来,他跟保卫队申请,希望可以到会议室自习,时间延续到11点。队里体谅他,同意了他的请求。
北大保安大队大队长王桂明曾在一次接受采访时自豪地说,北大的保安队为保安的学习创造了良好的环境,为求学的保安大开绿灯,帮他们调整适合学习的岗位和班次;另外,北大工会组织开办的平民学校,每年都会为保安留出20个听课名额。
张俊成于1995年10月考上了北大法学院专科。回忆起当年,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当初曹燕老师把两个听课证放到他眼前时,最初他是婉拒的。英语培训班一学期的学费是3600元,成人高考是1800多元。那时候,他每月的工资只有214元,根本上不起。
曹燕当时就说,已经跟老师说好了,了解了他的情况,让他免费听。“看你挺上进的,阿姨想帮帮你。”
张俊成哭了。不仅是感动和感激,更因为对于一个背井离乡的少年而言,这份温暖太难得。
考上北大后,张俊成的睡眠时间更少。在三年法学院求学期间,他周一到周五白天上课,晚上值夜班,从十点到次日七点。周末没有课,全天值班。平均每天睡三个小时。
问到他如何坚持下来,他淡淡地说:“习惯成自然。”
没有围墙的校园
王谦手捧《国家人物历史》,看得入迷,桌上摊开的还有《世界社会主义研究》《史学月刊》等文史类学术期刊。曾在山西当过初三化学老师的他,已经在北大历史系待了近四年。
王谦是山西大学中文系2004级的本科生,毕业后当过老师,兼职过酒店大堂助理,还和朋友一起做过转运煤的生意,最多时候月入7000元。直到2014年,他来到北京。
在参观了几次北大后,王谦觉得这里“恬静又温暖”。他自称不喜欢忙忙碌碌的快节奏生活,正好历史系的一位保安刚离职,于是王谦就留在北大,当起了保安。
进入校园后,王谦发现北大并不像他想象中那么高不可攀,“以前觉得北大很神圣,就像琼楼玉宇,现在觉得很朴素。”
从北大教授身上,他最能感受这种朴素的美。这些在他眼里学富五车的教授们,大多为人谦虚、真诚,穿着也低调含蓄,对保安讲话也不会盛气凌人。
王谦喜欢和这些教授们交流。以前,他只能在百度上看到他们的照片,现在,教授们进进出出,图片变成了真人。他对上一个,就打一声招呼:“××老师您好,我拜读过您的×××。”
一来二去,历史系的教授们也对这个懂历史的小伙子上了心。
他经常收到历史系老师的赠书,有宋成有教授送的《中外文化交流史》,李新峰教授的《明代卫所政区研究》,以及王元周教授的《小中华意识的嬗变》等。王谦希望通过大量阅读文史类书籍和期刊,加深文史修养,为以后的工作做好铺垫。
白天上班有空的时候,他就看文史杂志和国学著作,下班后一个人在宿舍,研究一些复杂的问题。他承认,很多史学领域细而深,专业论文很难看懂,“自学起来很吃力”。
由于怕老师觉得问题幼稚,他很少提问。有时,他看一篇学报上的文章需要两天时间,在不懂的地方做个标记,然后自己反复研究。他戏称自己是在“练功”,只不过目前功力尚浅,仍需努力。
江斌也收到过老师的赠书,有张千帆教授的《宪法导论》、汪建成教授的《刑事诉讼法》,以及陈瑞华教授赠送的司法考试教材。遇到看不懂的,他会主动问老师和同学。
有一次,法学泰斗江平来北大作讲座,主题是“中国法治的困境与突破”。江斌回忆,当时的报告厅里人山人海,走廊和过道处全是人,连窗台上也坐满了人。他从未见过这样的场面。他站在最后,听完了整场。
直到现在,江斌还能活灵活现地模仿江平老师的语气,说出那句让他印象深刻的话:如果国家对法治不采取什么措施,最后只有一部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没办法。
江斌说着便笑了。
张俊成还记得和北大西语系教授张玉书一起遛弯儿的日子。那时候,张玉书爱拉着他绕未名湖散步,边走路边讲马哲、讲黑格尔。张俊成一开始还不懂,后来才意识到,他在以这种方式给自己上课。
他努力集中精神听,什么唯物唯心,萨特尼采,哲学实在艰深,他不懂,也不敢问。后来熟了,他慢慢鼓起勇气打断张教授的话,提出自己的困惑,他发现张教授不仅不会不耐烦,还会深入浅出地讲解。
后来,他也做了别人的老师。升任分队长后,张俊成每周都会组织一两次学习,利用保安们在传达室坐岗的时间开展教学。他有时教英语,有时就某个他能讲清的文史哲或社会类话题组织大家讨论。有路过的教授看到,经常会给予他们指导或参与讨论。
他还要求参与学习的保安记笔记,每月参加月考,巩固知识。但他也坦承,由于保安均为20岁左右的年轻小伙,多数来自农村,教育程度低,没有定性,很多人一开始不太积极。 张俊成对他们说:“知识改变命运,道理你们都懂。但你们要想改变命运,得拿出实际行动。”
他感慨,北大的文化学术氛围浓厚,无形中影响了很多人。“那个时候,混日子的比较少,大多数保安都很珍惜在北大工作考学的机会。”
1998年,张俊成从北大法学院专科毕业。在他读书的三年期间,约有16名保安顺利通过成人高考考入北大。
有一首歌叫《未名湖是个海洋》。歌词写道:“未名湖是个海洋,诗人都藏在水底。灵魂们都是一条鱼,也会从水面跃起。”
这首歌的专辑的名字是《没有围墙的校园》。
变和不变
有时候,江斌会觉得自己和周围的环境格格不入。
保安队多数人来自农村,河北、河南、山东人较多,文化程度不高,怀抱考学目的的人占比很小,江斌和他们之间仿佛有一面无形的墙横亘其间,几乎没有共同语言。
王谦也很少和不爱学习的保安来往。他见过保安和领导争吵,见过有些保安难改痞子习气,有些人满嘴脏话。
相较而言,他更喜欢和学生交朋友。问他在当保安期间最感动的是什么事?他说是一顿饺子。
刚当保安没多久,王谦听说康博思的水饺很好吃,但保安的饭卡不能用。一次,他无意间跟新交的朋友阿城提起,阿城说:“这有什么,我带你去吃。”滚烫的饺子落肚,如同他的心,热乎乎的。
阿城是历史系博士生,后来王谦和他熟了,每隔一周就会去他那吃饭,他带去啤酒和小菜,两个人热热闹闹地吃火锅或烧烤。他说,这样的生活“干净又热烈”。
但有些现实也让他沮丧。在北大,保安只能在农园、艺园和畅春园一层吃饭,无法登录校园网,不能进图书馆。王谦每月的工资是2400元,没有奖金和加班费,也没有五险一金和社保。
2015年,由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会组织,来自社会学系、中文系、法学院、新闻与传播学院等19个院系61名本科和硕博研究生参与撰写的《北大后勤工人调研报告》指出,承担北大校本部安全保卫任务的文安公司,没有为在北大工作年限在两年以下的任何一名保安缴纳过社会保险。保安的流动性非常高。
江斌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有的保安来一段就走了,有的甚至早上八九点来了,中午饭吃完就走了。王谦回忆自己在北大历史系工作四年间,人文学苑的保安来来去去至少有50个人。
考入北大后,有半年时间,江斌发现自己“怎么都读不进去书”。那年他已经25岁,以前的同学多数已经成家立业。同学聚会的时候,有人说,你怎么还一个人孤零零漂着,多可怜。
而王谦则萌生了考研的想法,但父亲不赞成,认为到了他这个年龄应该成家立业,不适合再读书。
在老家的同学也劝他回去。一位同学在老家开了公司和酒店,年收入五六百万。王谦觉得,家乡人不懂他的追求。
“我就喜欢看书,越读书越感到自己无知。他们过他们的生活,我过我的生活。”
来北京后,王谦只告诉父母自己做物业工作,不敢提到工资。这几年,他一直用着以前攒下来的9万元存款。
毕业后的张俊成渐渐明白,北大毕业证书只是代表了一段学习经历,能否实现自己的抱负,还需要实际行动。
2015年,张俊成创办了长治市科技中等职业学校,自己担任校长。现在,他可以将自己的观点传递给更多的孩子了。
江斌先后三次考研,都失败了。2017年1月,他拿到北大的专科毕业证,回老家参加公务员考试,也落榜了。现在,他打算继续考研。
王谦仍在历史系读书。不工作的时候,他喜欢在北京城闲逛。他去过五道口的酒吧,到工体看过球,参观过国家大剧院和外交部。
他想起自己第一次来北京,发现公交坐反了。他一声不吭地下了车,默默走回来时的路。现在,他觉得自己“完成了从乡村到城市的转变”。
江斌有时会想起自己在北大当保安的同事——来自西安翻译学院的小方,从北大离职后自己开了公司,后来在全国各地作巡回演讲;从景德镇陶瓷大学毕业的佳佳,喜欢在水杯上画画;焦哥自己写了本书,叫《拯救中华》;从解放军侦察连退役的王哥在国际安全防卫学院学习过保镖技术,身手一等一的好;丁诗人笔名未名苦丁,发表过诸多诗作。
2015年,丁诗人写道:“莫道英姿晚,大器乃晚成。”
(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江斌、王谦、李仁木为化名)
【免责声明】上游新闻客户端未标有“来源:上游新闻-重庆晨报”或“上游新闻LOGO、水印的文字、图片、音频视频等稿件均为转载稿。如转载稿涉及版权等问题,请与上游新闻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