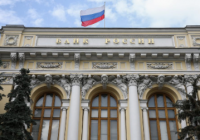诗与散文的界标
(诗话12则)
吕进
中国新诗理论的话语体系
诞生已经超过百年的中国新诗,现在几乎还是游离于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和社会文化生活之外。初期新诗致力于爆破,现在回头看去,这种爆破是必须的,又是粗放的。连同我们民族的传统诗学的精华也成了爆破对象,这就必然给新诗留下了“先天不足”、“漂移不定”的祸根。许多诞生之初就出现的争议,至今仍然困扰着新诗。新诗必须面对这些周而复始的话题进行辩证反思,拒绝剑走偏锋,努力构建中国新诗的话语体系。新诗的第二个百年的美学任务应该是“立”,推出中国新诗理论的话语体系。新诗的第二个百年的重头戏应该是“立”。
作为中国诗学的现代形态,中国新诗理论的话语体系建设离不开对中国传统诗学的批判继承。初初看去,中国传统诗学似乎只是零散的诗话,其实它拥有一个潜在的全面的丰富的理论框架,是从诗的内部产生、贴近艺术本质的理论。中国新诗理论的话语体系应该对它进行现代化处理,然后从这里出发,守“常”求变。西方现代诗学也是中国新诗理论话语体系的一个来源,但是必须经过本土化处理。必须明白,中国传统诗学和西方诗学有许多区别。中国传统诗学是运用前逻辑的艺术,喜欢运用类概念,注重领悟性、整体性、经验性;而西方诗学则是运用逻辑的科学,喜欢运用纯概念,注重分析性、抽象性、系统性。中国传统诗学注重对几千年诗学遗传的“通”,而西方诗学则往往主张“从零开始”。所以,对西方现代诗学的本土化处理是必要前提,这样才可言借鉴。
诗与散文的界标:体验性
从审美视点来说,散文的视点偏于绘画,是外视点。外视点文学具有人物化、情节化的倾向,作家把他对外部世界的感知,在作品里还原为外部世界。因此,小说、戏剧、散文所讲的故事不是实有之人,却是应有之人;不是实有之事,却是应有之事。《红楼梦》里的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虽然只是作家的虚构人物,却使读者相信他和她的真实存在,如见其人,如闻其声,从“满纸荒唐言”中去体会“一把辛酸泪”。散文作家往往采用不在场的叙事策略,回避直说,他对外部世界的审美判断淹没、融化在他所创造的审美世界中,淹没得越深、融化得越彻底越好。相反,诗的视点偏于音乐,是内视点。文善醒,诗善醉。诗遵从的是心灵化的体验方式,心灵化的艺术思维与审美选择。诗人的创作状态是“肉眼闭而心眼开”,得于心而忘于形。诗总是尽量去掉客观性,尽量增加主观性;诗总是尽量去掉可述性,尽量增加可感性。诗人的体验不是淹没、融化在叙述里,而是把外部的客观世界吸收到、融化到主观的内心世界来,让它分解起来,提升起来,净化起来,然后直接说出来。诗不是观,而是观感;诗不是情,而是情感;“感”就是诗人的审美体验,这就是诗的直接内容。
化事为情,升情为感
诗不是叙述的艺术,诗是体验的艺术。诗化客观为主观,化事为情,每一首诗都是诗人心灵的公开展览。散文使用形象和图画表现自然中的形象和图画,诗则使用形象和图画来表现不具象的、构成人性内质的情感。不但抒情诗,就是叙事诗在叙事时也从不纠缠于“事”,而是绕着“事”走,跳着“事”走,从不留恋“事”本身。古诗名篇《木兰诗》只用了三十个字表现木兰十年的代父从军的戎马生活:“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朔气传金柝,寒光照铁衣。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然而,在“愿为市鞍马,从此替爷征”;“脱我战时袍,着我旧时装”这些情重的地方,《木兰诗》就走弯路、绕圈子、“说废话”(黑格尔语),因为这是诗。
只是情,还不是诗,原生态的情只属于个人所有。诗人的美学使命是诗化处理和艺术加工,让“情”上升到“感”,“感”就是诗美体验,歌唱着的诗人和歌唱者本人既有紧密联系,又有美学区别。既是诗人,就应当不只是充当自己灵魂的保姆,更不能只是一个自恋者。诗人传达的诗美体验要获得高度的普视性,为读者提供从诗中找到自己、了解自己、丰富自己、提高自己的广泛可能。艾略特在他的著名论文《传统与个人才能》里说:“艺术家越是完美,那么在他身上,感受的个人和创造的心灵越是完全的分开”。从“事”到“情”,从“情”到“感”,就像德国作家让·保尔·里希特所说:“创造者最后成为自己的创造品”,这就是一首诗诞生的完整过程。
避 俗
对于诗,重要的,不是客观世界本来怎么样,而是在诗人看起来怎么样。由于这个“直接性”,诗人自己就是自己的书写的对象。诗总是和诗人个人的身世、遭际、个性非常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但是诗的价值又并不全在诗人的身世中。有贵气的诗才拥有艺术的力量,去升华人们的现实世界,净化读者的心灵世界。所谓诗的贵气,就是诗的纯净与升华。诗抒发的是艺术情感:经过淘洗、提高的公众情感,而不是原生态的私人情感。个人身世的琐碎情感不具备入诗的资格。以自己的独特嗓音唱出与众人相通的人生体验,言人之难言,言人之未言,言人之不敢言,读者才可能有认同感,归属感,在读诗中进入响应状态。如同诗人要有入世的热情一样,诗人也要有出世的智慧,所谓“有第一等襟抱,才有第一等真诗”。对于滚滚红尘,诗人要给予诗的观照,诗的提升,从共同经历中找到自己的“个别”,从历史进展里抽出个人的角度。敬畏人性的纯净,倾听内心的声音,寻找诗的品位,在世俗世界、功利世界里和读者一起寻找诗的境界。
文明与原始
诗人是文明的“原始人”。与同时代人相比,诗人更文明,又更“原始”。诗人比同时代人更文明,这自不待言,因为诗人应该是民族的智慧和时代的良知。诗人比同时代人更“原始”,是指他进入创作过程后的前逻辑心态。这种前逻辑心态,使得诗人此时似乎是来到世界的第一个人,他用惊喜的目光打量自己的四周,给世界万物命名。他似乎不懂得人们习以为常的基本常识与逻辑,而是对生活作出不同凡响的新奇领会与感应。诗人见到的世界是心灵的太阳重新照亮的世界。
地气:生命力
诗要接地气。诗人要有入世的热情,就像无锡东林书院的那副对联说的那样:“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要有深入现实世界和内心世界、把握时代精神和人性精微的接通地气的热情与能力。地气,即诗的生命力。中国诗歌从来崇尚家国情怀。气不可御的李白,沉郁顿挫的杜甫,纯净内向的李商隐,哀婉悲痛的李煜,笔墨凝重的苏东坡,愁思满怀的纳兰性德,虽然他们的艺术个性相距甚远,但是他们的诗词总是以家国为本位的。他们对个人命运的咏叹和同情,总是通过某种渠道和对家国兴衰的关注联系在一起的。“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是古诗发展的一个规律。在创作过程中,诗人必然寻求审美静观,他走出世界以观照世界,走出人生以观照人生。没有“走出”,没有审美距离,就没有诗美体验,也就没有诗。但这是创作状态。“走出”之前,却有“走入”;“出世”之前却有“入世”,不然就没有优秀的诗。玩世玩诗、个人哀愁之作在中国不被看重,中国诗歌的评价标准从来以匡时济世、同情草根的诗人为大手笔。这是中国诗歌的一种“常”。在现代社会,尽管现实多变,艺术多姿,但这个“常”是难以违反的。个人琐事、杯水风波总有局限,如果在这方面“反常”,诗歌就会在现代中国丧魂落魄。接地气的诗才可能拥有广泛的人气和民族诗歌的底气。
诗与散文的界标:音乐性
许多搞理论的人总是讲,诗与散文在语言上的根本区别在形象性和精炼性。其实,形象性和精炼性,这些是任何一种文学样式都在追求的目标,并非诗歌独有。唯有神圣的音乐性把诗和散文分别开来。内外节奏就是音乐性的基础,散文是无节奏的语言,音乐是无语言的节奏,诗是有节奏的语言。翻开中国古代诗歌史,古诗和音乐的关系从来密切。从古朴典雅的《诗经》和汪洋恣肆的《楚骚》开始,乐府诗、绝句、律诗、词曲都离不开和音乐的联姻。从“以诗入乐”到“采诗入乐”再到“倚声填词”是中国古诗的音乐性的流变过程。用耳从诗质上去捕捉诗情的音乐性,用眼从诗形上去捕捉诗的音乐性,这是中国诗歌几千年为读者造就的审美习惯和审美标准。读读倡导“散文美”的诗人艾青的后期作品就可以发现,艾青后期的短诗大都已经变成有韵诗了。他在1980年新版的《诗论》里还加上了一句话,自由诗要“加上明显的节奏和大体相近的脚韵”,你承认也好,不承认也好,我认为,这是艾青诗学思想的发展与完善。
新诗的内容必须形式化
新诗之新绝不可能在于它是“裸体美人”。对于诗歌,它的美还在衣裳。新诗的内容必须形式化,“裸体”就不是“美人”了。自由体新诗一定要有自己的文体规范。应当说,没有文体规范就没有诗。诗的审美表现力和审美感染力,都与文体规范有关。作为艺术品的诗歌是否出现,主要取决于诗人运用诗的文体可能的成功程度。许多自由体诗人早就习惯了跑野马,对于倡导诗体重建、倡导形式感和分寸感一概反感和反对,认为这是在妨碍他的创作自由,在给他制造麻烦。野马拒绝笼头。但不知他们想没有想过,艺术总是有限制的。艺术的美、艺术家的才华正是在巧妙地运用这限制中得到发挥。像现在这样“撒野”下去,会不会妨碍读者的读诗兴趣,会不会取消新诗在艺术领域的生存。读者都没有了,新诗都没有了,你要那自由有何用。对于诗来说,形式就是内容。没有形式,就没有了内容。没有形式感的人,可以去干别的,但绝对不能做诗人。
诗是情感体验的演出
诗不是情感的“露出”,它是情感的“演出”;读诗,其实主要就是欣赏诗的语言。诗人注意传达什么情感,他同样注意怎样传达情感,注意让一种情感如何在诗的方式中呈现于读者面前。用不加提炼的日常语写诗,是摧残诗美的最好手段,读者读到的不是诗,而是美好诗意的非诗表达。绝对地说,诗就是体验性、音乐性的诗家语而已,不能体悟、把握诗家语精妙的人不可能是诗人。 当有人请美国诗人罗伯特·弗罗斯特解释一下他的一首作品时,诗人回答说:“你们要我做什么——用蹩脚些的语言重述一遍吗?”弗罗斯特的意思是:诗的语言并不是一般的(蹩脚些的)语言。
外节奏是诗的专属
节奏是诗与生俱来的特质。从诗歌起源学着眼,诗脱胎于原始时代舞、乐、诗的混合艺术。三者的分离,形成三种独立的艺术:舞以形体为媒介向具象的时间性节奏发展,乐以声音为媒介向抽象的空间性节奏发展,诗以特殊语言结构为媒介向具象化的抽象和抽象化的具象发展,但三者都保留了一个共同的要素——节奏。节奏之于诗,如同脉搏之于人,诗的节奏就是人的生活节奏的诗化。
所谓诗的内节奏,就是情绪的起伏形成新诗的内在旋律。内节奏显然并非诗的专属,一切文学作品,一切艺术作品,都会有自己的内节奏。戏剧文学的起始-发展-高潮-结局就是内节奏。而外节奏则从来是诗歌身份的专属,是诗的辨识标志,只有外节奏才是诗与散文的分水岭。日本学者松浦友久说:“诗最本质的东西在于韵律与抒情。”韵式是外节奏的听觉化,段式是外节奏的视觉化,它们使读者产生节律化的审美期待。
外节奏是中国古诗最富成就的一环,又是百年新诗最薄弱的环节,是新诗目前最有待加强的领域。现在有一种贬低外节奏的倾向,说实话,推动这个倾向的诗人中不少人对于自己民族诗歌传统是比较陌生的。这实际上就强化了诗的散文化倾向,使得新诗丢掉了自己特殊的美,从而丢掉了自己的读者。
诗的篇幅受限于音乐性
音乐性带来诗歌在篇幅上的简约。在他的《美学》第3卷中,德国学者黑格尔有一段我以为是很精辟的话:“事件构成史诗的内容,像风飘过琴弦一样震动诗人心灵的瞬息感觉构成抒情作品的内容。因此,无论抒情作品有怎样的思想,它不应该太长,往往应该是很短的。”黑格尔这里讲的“史诗”是指叙事文学,而诗则是抒情文学。“瞬间感觉”要求简约篇幅,诗家语的每一个字都要诗人付出很辛苦的劳动,才可能片言之中有深意,方寸之间见乾坤。在中国古诗中,刘邦的《大风歌》只有三行,荆轲的《易水歌》则只有两行,但它们都是传世名作。诗是“空白”艺术,诗甚至不在诗之内,而是在意象之外,笔墨之外,诗之外。“恰似未曾落墨处,烟波浩渺满目前”。明代李东阳这样题柯敬仲的墨竹画:“莫将画竹论难易,刚道繁难简更难。君看萧萧只数叶,满堂风雨不胜寒。”可以说,由于诗歌篇幅的文体规范,诗家语追求的也是这种功力。优秀诗人无不具有把“满堂风雨”变为“萧萧数叶”的艺术手腕。
诗的数学:一与万
一与万,简与丰,有限与无限,是诗家语的美学。诗人总是两种相反品格的统一:内心倾吐的慷慨和语言表达的吝啬。从中国诗歌史看,中国诗歌的四言、五言、七言而长短句、散曲、近体和新诗,一个比一个获得倾吐复杂情感的更大的自由,这样的发展趋势和社会生活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的发展遥相呼应。可是从表达着眼,与诗歌内容的由简到繁正相反,诗家语却始终坚守着、提高着它的纯度,按照与内容相对而言的由繁到简的方向发展。五言是两句四言的省约,七言是两句五言的省约。新诗应该注意这一点,这可是诗歌艺术发展的铁的法则。违背艺术法则的诗是短命的。

(作者系西南大学教授、重庆市文联荣誉主席)
版面欣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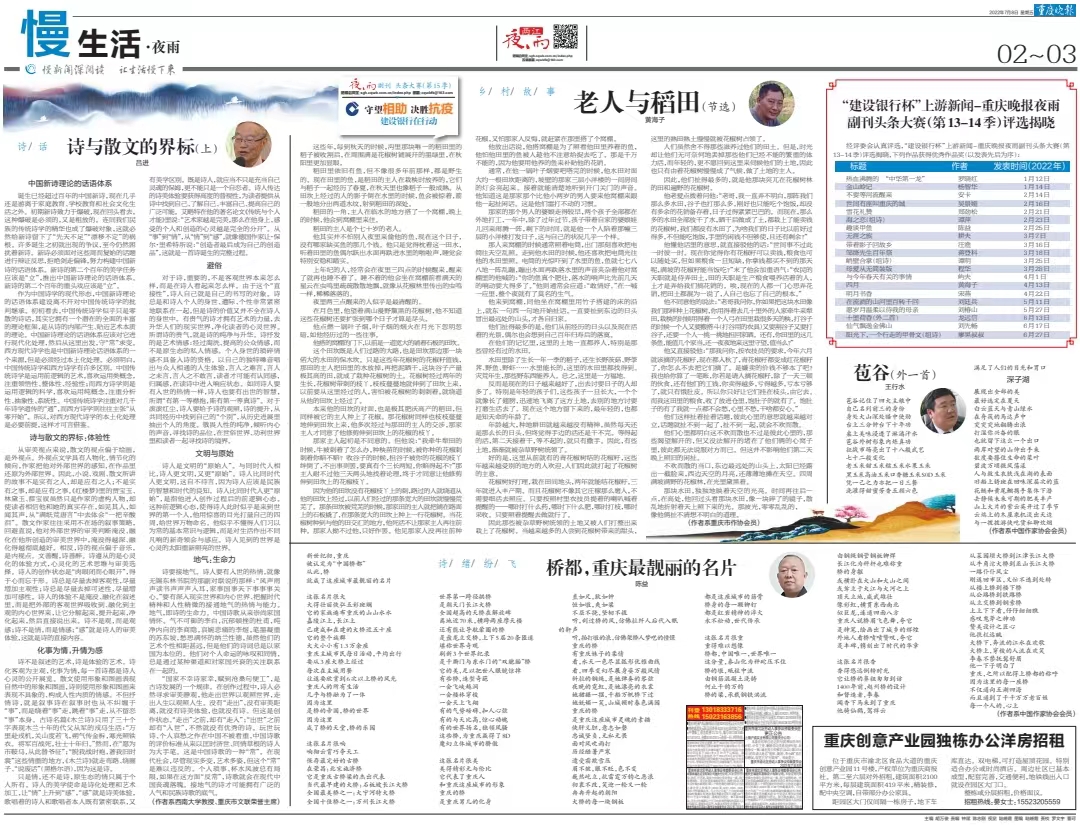
【免责声明】上游新闻客户端未标有“来源:上游新闻”或“上游新闻LOGO、水印的文字、图片、音频、视频”等稿件均为转载稿。如转载稿涉及版权等问题,请联系上游。